- +1
胡恩海︱科学史绝非科学的注脚:科学革命的人文理解
过去数百年间,当基督教世界的大师都在从事哲学研究,一个近乎全新的自然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毫无疑问,如果科学被正确且普遍地培育,没有什么会比它传播得更快了。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68
现代早期的科学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当诗人德莱顿在十七世纪中叶目睹了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剧变,出于惊叹写下这段话,他并未料想到这是一把即将开启现代闸门的钥匙。可以说,科学革命的影响渗透到了西方文明的各个层次:围绕新科学本性的思想论争,带动了现代哲学的发展;科学观念对伦理价值的冲击,开启了与基督教传统充满张力的世俗化进程;技术手段的变革,引发了后续数次工业革命;最终,科学发展伴随殖民扩张,亦成为全球化的核心推手。
关于科学革命的讨论滥觞于十七世纪。不过其时革命尚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相关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科学的本性,而未有所谓“科学革命史”的理解。到十九世纪,现代科学的基本模式逐渐定型,一些学者便回到现代科学的源头做起了编史和整理工作。科学编史学之父、英国学者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的三卷本巨著《归纳科学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是历史地理解科学进程的开端。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哲学社会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把人类知识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前两个阶段的意义仅在于开创第三个阶段,后者开始的标志正是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十九世纪末,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力学史评》(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成型。

批判辉格史学:今天的数学是古代的数学的进步?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前的科学史学者为后人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但他们的研究却受困于当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巴特菲尔德(Herb Butterfield)在《现代科学的起源》中批判了受“历史的辉格解释”(Whig history)影响的科学史书写。所谓辉格史观,乃进步史观的一个分支,认为人类文明不可逆转地从落后迈向先进,从愚昧转为开明。辉格史观在科学史书写中尤为泛滥,它使科学史沦为现代自然科学帝国的附庸,为后者的正当性辩护,从而丧失自身本应有的批判、反思能力。我们中学和大学的数学教材就是典型的辉格数学史:用最新的数学进展统摄理解之前的数学史,以刻画我们如何取得现阶段的成就。欧几里得几何是人类数学的初级形式,从欧式几何到近代早期的解析几何是一种“进步”,从解析几何到黎曼几何又是一种“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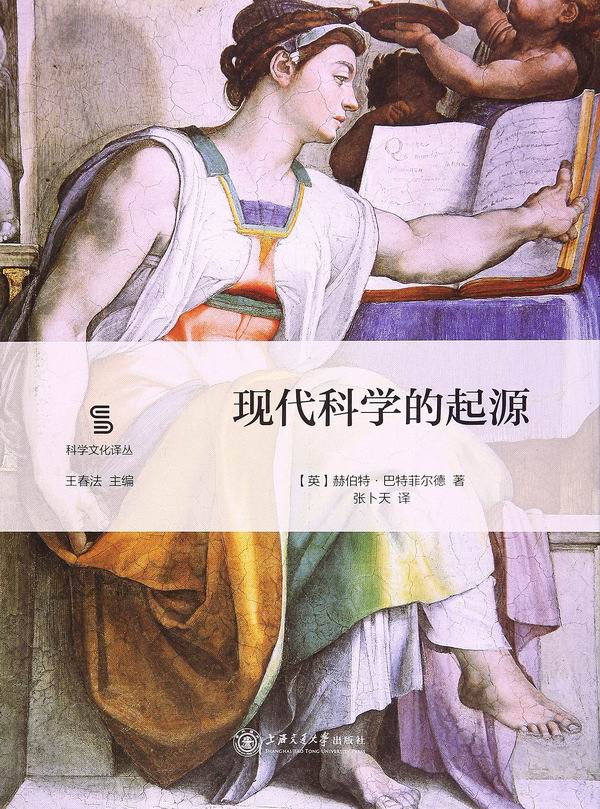
但敏锐的数学思想史家如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激烈地反对这种数学进步观。克莱因曾师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与列奥·施特劳斯关系密切,施特劳斯多次表示,克莱因是自己最佩服的哲学家之一。在《希腊数学和哲学中的数的概念》一文(收于《雅各布·克莱因思想史文集》)中,克莱因讨论了古希腊的数(arithmos)的概念的意向性,继而在代表作《希腊数学思想与代数的起源》(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Algebra),他又从数的意向变化,分析了数的概念的演变:古希腊的数总是“被计数之物”,系由确定数目的确定之物构成,因此不包括无理数和分数;现代的数,经过阿拉伯-近代早期的数学变革,完全丧失了原初直接指向确定之物的“第一意向”,成为抽空了意义的符号,是故,能把一些最初仅由运算规则规定的对象(如负数、无理数、虚数)纳入其中——而只有在这种符号性的思维方式下,一种普遍适用于数和量的代数学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数从古到今是一种“进步”,不如说是一种“嬗变”(mutation);可见,辉格史观是简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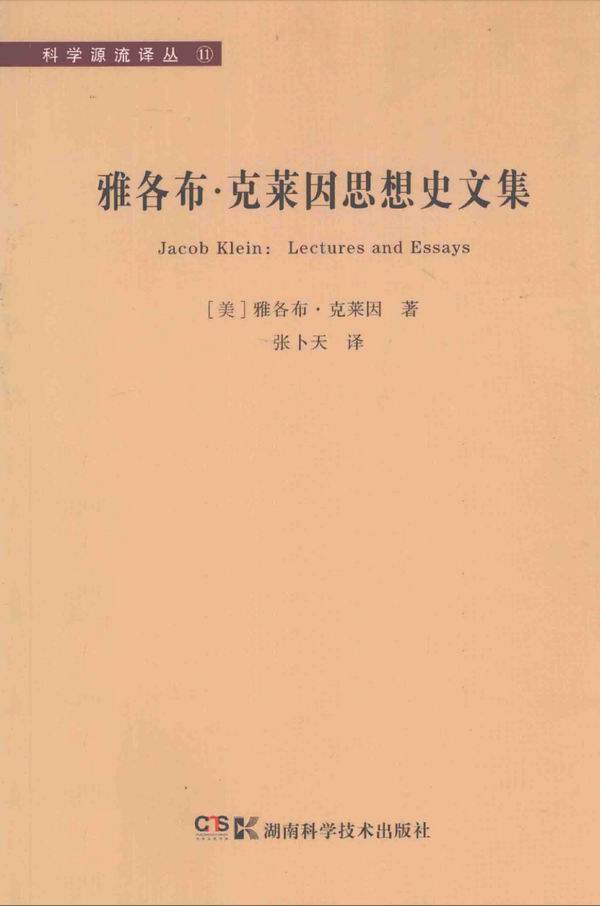
除了对辉格史观的批判,巴特菲尔德在《现代科学的起源》中另一项令人瞩目的贡献是,他第一次把“科学革命”作为核心概念使用,由此,这个命名便初步流行了开来。依照巴特菲尔德的定义,科学革命指西方科学在1300年到1800年间发生的变革——不同于后来的科学史家聚焦于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做法,他把科学革命的上限提到了中世纪晚期。显然,这是受到了法国科学史的开创性人物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影响。正是迪昂关于中世纪力学的研究把现代科学革命的起源确定在了中世纪晚期。
亚历山大·柯瓦雷:伽利略和笛卡尔犯下同一个错误是巧合?
皮埃尔·迪昂
迪昂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国科学思想史流派的开山鼻祖。他几乎以一己之力查阅文献,单枪匹马地撬开了整个中世纪物理学的思想宝库。在研究达芬奇手稿时,迪昂发现了一些十四世纪巴黎经院学者的工作,所幸法国国家图书馆完好地保存了这些哲学家的手稿,使他得以一窥究竟。此后,迪昂的三卷本《莱昂纳多·达·芬奇研究》(Étude sur Léonard de Vinci)问世,让布里丹等巴黎学者的工作重见天日。在迪昂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优秀学者投身到了科学史的事业之中,其中就包括后来对科学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柯瓦雷是俄国贵族后裔,年少时负笈前往哥廷根大学,跟过胡塞尔和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后在巴黎大学求学。他的《伽利略研究》是科学思想史流派的奠基性作品,不过该书在1934年出版后并没有立刻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当时二战的乌云已经蔓延到欧罗巴的上空。柯瓦雷虽为俄国人,却深爱法兰西,国难当头,他辗转开罗,决定加入“自由法国”组织,为戴高乐效力。戴高乐欣赏柯瓦雷的才干和勇气,但也认为“如果能有这么一位学识卓越之士留在美国,那么‘自由法国’事业或许会受益”。于是,柯瓦雷和法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流亡纽约,开始了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在某种意义上,柯瓦雷在北美崭露头角是天时地利的结果。战后,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辛苦耕耘的北美科学史研究开始生根发芽。新一代科学史家在编制日益扩大的北美大学体系中寻找契机,他们想以完全职业化的方式来构建这门学科。正当他们苦苦寻求理想范式的时候,《伽利略研究》如同缪斯女神一般给了他们灵感:这本极富洞见的著作揭示了他们初创的学科可能会具有怎样激动人心的思想意义。于是,在柯瓦雷的指引下,法国科学思想史传统开始积极深入地影响美国新一代科学史家。后来执掌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I. B. 科恩曾是柯瓦雷的学生;日后凭借《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而获得跨学科、世界性影响的托马斯·库恩更直言不讳道:“我有三位法国导师:迪昂、梅耶松和柯瓦雷。”此外,吉利斯皮(Gillispie)也说:“科学史作为一种职业,产生于萨顿和柯瓦雷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初的联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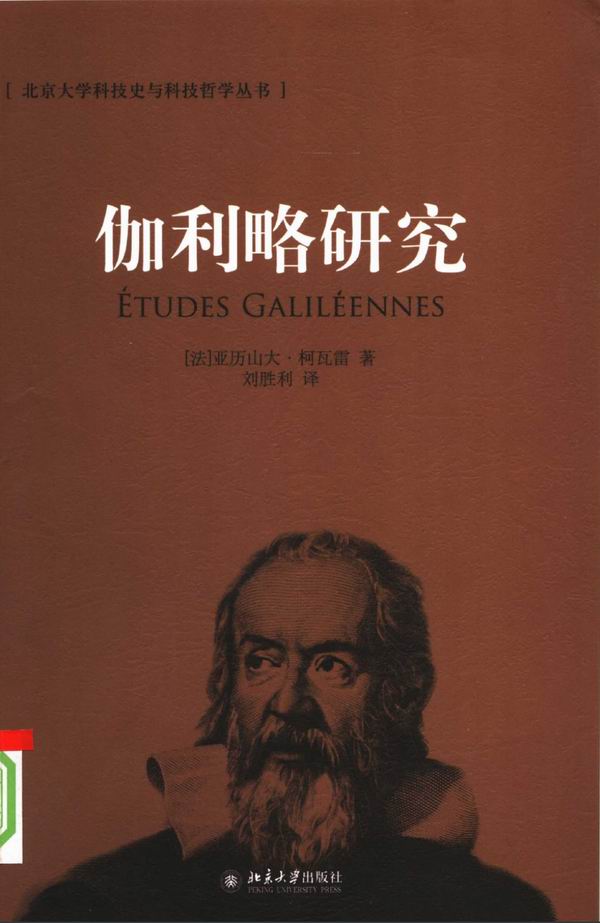
《伽利略研究》通常被看作是柯瓦雷最典型、最具个人特色的科学史作品。该书由三个独立,但彼此相关的篇章构成,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典物理学如何起源于表述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努力?其中第二篇《落体定律——笛卡尔与伽利略》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1604年,伽利略率先提出了经典物理学的第一个定律——落体定律。十五年后,荷兰物理学家毕克曼(Beeckman)在笛卡尔回信的帮助下,表述了另一个版本的落体定律,而这个版本正是该定律的完成时态,即我们时代的版本(运动物体的速度与时间成正比,v=gt)。有趣的是,毕克曼的“正确”表述是通过曲解笛卡尔的回信得出的,笛卡尔在信中犯了一个和十五年前的伽利略一样的错误,认为运动物体的速度与通过的距离成正比。在柯瓦雷看来,错误的巧合也是真理的巧合,体现了伽利略、笛卡尔二人“思想的隐秘的发展历程”:他们表述的是一个内核相似,但形态“错误”的落体定律,在这个“错误”的定律所涉及的特定概念(空间、作用、运动)中,已然隐含着从传统亚里士多德和冲力物理学的转变。柯瓦雷深情地说:
人类心灵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形成了这种关于运动的新观念……并越来越准确地将它表达出来。……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心灵顽强地对付着同样的问题,不知疲倦地遭遇到同样的困难与障碍,然后缓慢和艰难地为自身锻造出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与障碍的工具。(《伽利略研究》,165页)
[法] 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68元。
如果说《伽利略研究》关注的是“世界观”(world views)的革命,那么柯瓦雷另一部声誉斐然的著作、《伽利略研究》的姊妹篇《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讨论的则是“世界感”(world-feelings)的革命:用柯瓦雷自己的说法,前者是后者的前史。《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始于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的宇宙观,终于牛顿关于无限空间的绝对性,以及一位与自然相区别的人格上帝的全能性的断言,揭示了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对宇宙论的改造:“和谐整体宇宙(cosmos)的打碎和空间的几何化。”在柯瓦雷看来,古希腊的cosmos是一个有限、有序的整体,其空间结构体现了世界本然的完美与价值;后来的universe则是一个无限的、不确定的、没有等级结构的现代宇宙概念。这种宇宙论的嬗变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空间概念(世界内面被分化了的一系列处所)被欧几里得的空间概念(本质无限且均匀的广延)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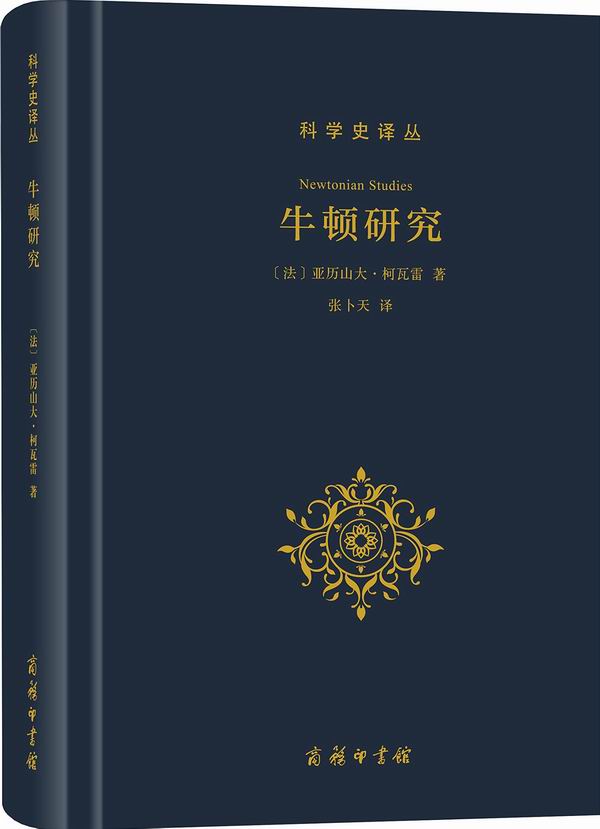
张卜天:翻译者的任务
在柯瓦雷之后,二十世纪后半叶,新一代科学史家纷纷以不同的方式、维度来刻画科学革命的进程,其中荷兰科学史家H. 弗洛里斯·科恩编纂的《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是对科学革命研究工作的百科全书式总结。他网罗了几乎所有关于科学革命的看法,很好地协调了“内史”(关注科学自身脉络的演化迭代)与“外史”(强调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决定性作用)的关系。对科恩而言,内史、外史的不同路径并不冲突,应该把科学史研究“从非此即彼的无果立场中解救出来”。通过对科学革命各个层次和研究方式的编史学综述,科恩首次为我们描绘了西方科学史这一年轻的学科在科学革命方向所积累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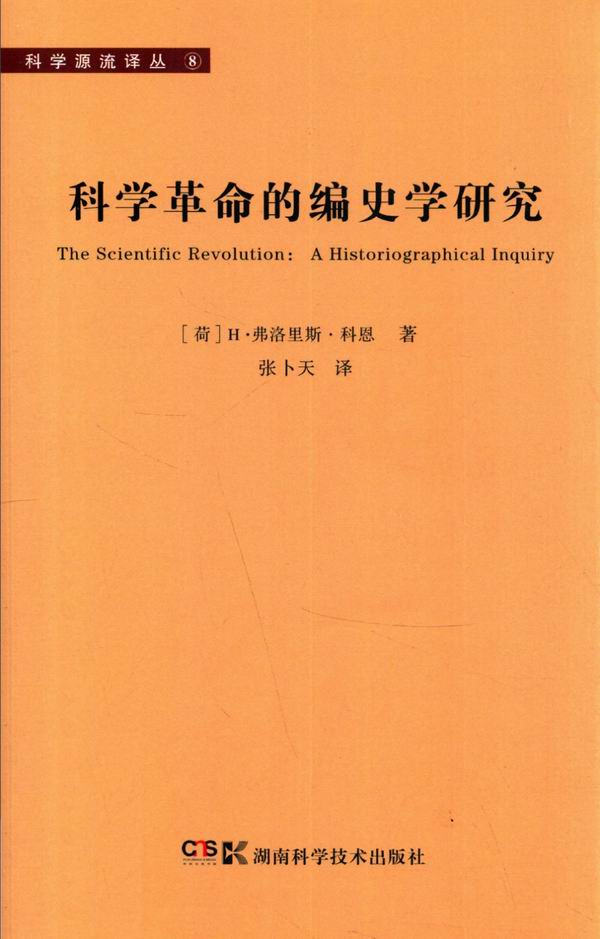
不过对中国读者和学界而言,除了需要思考西方科学史研究自身的意义,一个更引人深思的问题是:研究西方科学史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是什么?
不少人发现,西方科学史的经典著作也就是最近十多年才像变戏法似的有了汉译,而大多数译本总离不开一个叫张卜天的名字。和迪昂的单枪匹马一样,张卜天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承担起翻译西方科学史名著的事业。他以“科学源流译丛”和“科学史译丛”为主阵地,笔耕不辍地把一本又一本的科学史名著翻译为现代汉语:“我早就定位清楚了,翻译是我第一重要的事。”对西方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张卜天有自己的思考:
中国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从西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的反思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来自西方科学视角的反思严重滞后。…… 研究西方科学史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我们当前的处境,照亮前进的道路。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只有互相参照,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科学史绝非科学的注脚……(《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总序 ,第3页)
张卜天
哲学家莱布尼兹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文明之间的借鉴是“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应该成为这个比喻的写照,生发真正的人文意义和科学价值,照亮前进的道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