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 +1285
家族志 | 赤脚大夫:乡村最后的守候者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访并文 | 宋方凝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编辑 | 林子尧
编者按:
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象征着一场新的轮回。在漫长的人生里,是这样顺应着节气、天文变化的历时里的节日昭示着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在中国传统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依托把人与人联结起来,因而在纷乱流离的生活里,人在时空中始终有一个确定的坐标,通过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镜相联合北大传播学课程的作者们,共同书写家族历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视角的转换,折射出几代人沟通、理解和凝视。是在代际轮回里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与情感,故土与新人,赋予了中国人“家”的精神归属。

卡夫卡《乡村医生》改编动画
记忆里,六岁前的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呆在山村的老家。午后我闹着不愿午睡,外婆就会打发我:“去杨树湾寻你外爷,他带你去药铺。”
这里多山,杨树湾是山间一片相对平缓的坡地,家里的玉米地就在那里。沿着大路找过去,外爷的身影一定掩在高人一头的玉米丛里。我喊他,他便应一声,缓缓从里面钻出来,拍拍手上和衣服上沾的泥土,戴上放在田坎的草帽。
“走,值班去。”
再走一小段路,爬上一段草木掩映的陡坡,就能看到坐落在平地上的三间土胚房——麻洞村卫生所,也就是外婆说的药铺。因为太小,只有储药间和诊断室,村里人久之就这么称呼。门没锁,里面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都是木质。桌上摆着一块算盘,一沓处方用纸,一个磨损的听诊器。进去隔间,靠墙一排沉木柜子切成小方格,散发苦涩清凉的味道;旁边是玻璃橱柜,各式西药稍显局促地陈列其中。
外爷是村卫生所的医生,和另外一名医生轮流值班,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赤脚大夫”。我常随他来这里,他值班,我就在隔间里把小木柜挨个拉开又关上,逐字读外面贴的字条:陈皮、木香、甘草,是我认识的;白芷,这个字怎么念?我会发问。他若是给病人看病,就会随便打发我让我自己玩;若是空闲,就不厌其烦地来我旁边,用乡音教给我病理。
据说这三间房子几十年前就是卫生所,中途翻修过,外爷也在这里工作了大半生。幼时听了,我只会觉得这满屋药香原来飘了几十年。而后来检索起这段过去,记忆与讲述拼接,几代师徒,百余户人家,一条从崎岖凹凸到被水泥覆盖的县道,一个人的命运如何融入一个村庄的消亡。当生老病死的叙事被时间冲淡,故事反而无从讲起,能抓住的竟也只是一缕药香。
一
麻洞村是一个行政村,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县城以北70公里。又包括六个自然村,彼此间距离不一。汉中盆地人称“小江南”,这里却是名副其实的山区,海拔高达两千米,往南向下到县城,往北向下到华阳古镇(长青自然保护区),因此又被当地人叫“麻洞梁”。县城到村庄多年来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仅容一辆架子车通行。直到1980年华阳景区设立,这条路才被硬化,农用车和小型客车才逐渐通车。虽然对外交通不便,当地村民却走动频繁,互相熟悉。
全村掌握医术的人不多,平日里都是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当有人患病,便找大夫开些中草药的方子,简单医治。没有白大褂,没有固定诊所,洗去种完庄稼的泥就成了深山里的回春妙手。村里人若是得了普通伤寒感冒,就亲自前往大夫家里买药;若是病的重了,家里人来唤一声,大夫便背着药箱翻山越岭,急急赶去病人身边。报酬不多,几块毛票或是贫瘠土地随处可见的洋芋都可抵出诊费。外爷的师父、师父的师父,代代相传,皆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心转移到城镇,资源向工业建设倾斜,农业合作化运动普遍推广,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的问题同样亟需解决。因此,农村原有的“赤脚医生”队伍得到扶持和充分利用,一批不脱产的农民医生承担起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同时,建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承担医疗成本。麻洞村卫生所就是在这个时候建起的,村里两三位大夫被召集起来,简单修缮村委会搬走后剩下的三间土胚房,当做固定行医点。
外爷生于1950年,小学毕业后便当了劳动力,下田挣工分。当时村里的大夫都不用参与劳动,年末可按看病人数核算工分,算是个让人羡慕的行当。外爷从小对医术感兴趣,在19岁那年拜了村里的名医为师。白日里学习把脉,望闻问切,晚上就睡在卫生所,当做是值夜班。为了帮外爷牢记不同草药的药性,师父将汤头(中药配方)编成歌诀,让外爷每日诵读:
苻苓味淡,粉饰利窍
白化痰淹,赤通水道
黄芪性温,收汗固表
托疮生肌,体虚莫少
……
外爷的确有学医的天分,最初只是负责按师父开好的药方包药,半年后就能独立上手开药方了。1971年,终于出师,也成了卫生所的一名大夫。学医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小两岁的姑娘,也就是我的外婆。尽管外爷家条件困顿,外婆还是看中外爷的老实、勤劳,与他操持起一个家。

外爷使用过的医学专业书籍
当时村里的大夫都没有接触过西医,虽然按照县卫生部门的要求,卫生所购入了常用的西药,却只能按照说明书给病人谨慎服用,并不清楚用药原理。1972年,国家卫生系统重视乡村医生培养,出资扶持一批年轻的乡村医生进修学习。外爷作为麻洞村最年轻的大夫,与同县的另外三名乡村医生一起前往市卫生学校,系统学习中西医知识。当时外爷外婆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姨刚刚出生。
从麻洞梁要先经山路步行五小时到县城,再坐大巴统一到市区。外爷简单收拾了衣物,就一路向下,那是他平生第一次走出洋县。一同进修的有几百人,均是20岁左右,除了各个农村的村医,还有来自略阳钢铁厂、405厂等的工人。这是70年代才能呈现的独特景象。一年以后,经过考核,这批年轻人获得中专水平的“中医师”证书,被纳入国家认证的医疗体系;同时将西医知识带到广阔的农村,像火种传播开。
二
从市卫生学校进修结束回到麻洞村后,外爷继续在村卫生所工作下去。仍是以中医为主,同时西医诊断方法和药物被更多运用,常见的慢性病以外,一些急性病得到更好的医治。
1975年,外婆生下我的母亲和小姨。由于母亲和小姨是双胞胎,生产难度大,外婆被提前送到县医院。之后由外爷和曾祖父、曾外祖父一起用架子车将外婆和两个女儿带回家。因为外爷行医为人皆诚恳谨慎,外婆勤劳吃苦,这个五口之家很快便被撑起来。1980年,他们最小的孩子——我的舅舅出生。
那是七十年代的西部农村,历史中的宏大叙事并未将羽翼覆到这里,改革开放的春风似乎都吹的慢一些。劳动,工分,家庭,这些内容构成这个村庄里人们生活的一切。直到1982年,大生产和集体劳动终于被废除,不再有公社,不再有公田,就连卫生所也因为赖以生存的制度倒塌而解散。实际上,根据国家政策,合作医疗制度应当继续维持,由基层群众共同承担成本。但迟滞和闭塞既意味着坚固,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意味脆弱,麻洞村的合作医疗尝试就这样仓促终结。外爷和另一名医生清空卫生所,将原本不多的药物等物资均分,各自以私人形式继续行医。村里人将一间废弃的存放粮食的仓库简单清理,腾给外爷做新的行医点。同样是土胚房,虽然更小,陈设上倒是仍与卫生所相似。
往后的日子艰难了许多。没有生产队拨款作为成本支持,也没有稳定的工分核算,一切自负盈亏,行医之余外爷又回到农田,担负起一家人吃饭的责任。原本卫生所定期前往县药材公司采购药物,私人化之后,药材公司高昂的价格和并不算新鲜的草药品质让采购难以维持。
后来,偶然经人介绍,得知西安和成都的药材市场且药材更新鲜且价格更低廉,最远只去过市区的外爷作出大胆的决定:更换货源地。于是,和同县的其他几个乡村医生约好,一起前往西安和成都购买药材。当时西汉高速还未通车,前往西安只能走险峭狭窄的山路,经过秦岭,紧贴着山势而行,探头一望,车窗外就是万丈深渊,九小时抵达,而到达成都要花费一天一夜。并没有丰裕的旅费,除去购药成本,往往付完车费之后就只能住最便宜的旅社,吃一碗车站的热汤面。一次行程一周之久,如此五年。
除了更换采购地,外爷还尝试自己采挖药材。山上的药材并不容易寻找,多生长在灌木丛里,初秋时节背着半人高的竹编背篓,带着镢头镰刀,一去便是大半天,归来时能收获半背篓药材。像麦冬、野菊花、柴胡、金银花,有些只需要晒干切段即可直接入药,有些则要先切成饮片,再加麸皮去炒,然后用蜂蜜去炙。诊所门口的一亩空地上,外爷也种植了一些容易养殖的药材,比如桔梗、白芷。

卡夫卡《乡村医生》改编动画
就这样各种方法并用,总算是将私人诊所维持了下来。几个孩子都坚持念书,成绩相当不错。病人得急性病,家人半夜来敲外爷家的门,外爷二话不说披件外套,带着药箱出门。最远的一次翻山越岭走了十公里,救治完病人回家,天已大亮。这群医者坚持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传统仍然持续地流动。外爷的口碑在当地有了名气,一位对医术感兴趣的年轻人来拜他为师,学成之后回自己的村庄开了诊所,救治更多病人。仿佛庄稼年复一年生长,这个村庄里的一切以某种缓慢的、不同于大时代的步调构建着自己的循环。指针被拨动,又在坚韧生命力的驱使下,转了一圈又回到相似的位置。然而时间的齿轮总是在转的——以察觉得到或察觉不到的方式。
三
1987年,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提出的第九年,为了适应农村医疗卫生建设新要求,在县卫生局的调整下,农村私人诊所终于被取消。正如三十年前“赤脚大夫”被召集成为联结体,分散行医的医生们再次回到卫生所,重新建立起轮班制度,运行至今。经过近十年的包产到户实践适应,村财政可以承担起每年较稳定的医疗投入,作为卫生所的运营基础。没有了工分制度,卫生所延续私人诊所采用的收费模式,除个人的出诊费外,药物溢价由几人平分。麻洞村曾以仓皇的面貌迎接公共基础的崩塌和市场的闯入,尽管艰难且缓慢,最终还是适应了市场规则。
卫生所仍然建在三间平房处。外爷不再去西安成都购买药材了,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县药材公司有了更灵活的价格调整方针。但种植草药、自制草药的习惯没有变,一亩药田转移到卫生所门前,由几位大夫共同照料。秋风造访贫瘠的山梁,桔梗星星点点,摇曳出一方安宁祥和。
孩子们慢慢长大。在不看重读书的村子里,外爷和外婆却格外重视教育,无论家里经济条件多紧张,都坚持供几个孩子上学。长女以前几名的成绩,成为同级唯一升入县一中的女孩;两个小女儿到镇上读初中,小儿子也上了小学。一切步入稳定轨道时,外爷却因病住进县医院。平日硬朗的身体突然病倒,全家人都猝不及防,那年长女读高二,正要升入高三。恰巧碰上108国道洋县段开工,按政府规定,全县每户人均集资近百元,并至少出一个劳动力去工地干活。万般无奈之下,外婆去同村里人一道修路,长女退了学,去医院照顾父亲。木兰“归来见天子”的故事大概只是千年前的歌谣,当现实的命运与之暗合,女孩的一生只能就此被改写,蒙上荒诞又无奈的色彩。不甘就此走上祖辈的老路,她恳求父亲教她学医,像父亲一样为乡邻服务。然而,这个请求很快被外爷否决,因为村里从未有女孩学医,他更不愿女儿像他一样在山间扛着药箱奔波一辈子。就这样,长女外出打工,剩下的几个孩子相继读完大学,留在城市工作。
或许从那时起,外爷已经察觉到乡村医生隐隐指向消亡的命运,尽管这个预感显得太早,也并不具备普适性——它更像是麻洞村的命运。凹凸的羊肠小道早已铺成水泥路,并在之后两次拓宽,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班车日日驶过;年轻人见过了外面的世界,瘠薄的土地早已留不住他们的双脚。由于地形缺陷,这里的耕地并不适合机械化操作,仍是一把锄头的影子拉的斜长。游客们奔向更北方的古镇景区,麻洞村作为一个中点站,从来往车辆往出去望,被遗忘在道路两旁,遮盖在层林里。它似乎不适宜现代化,在大量文学作品惋惜城市文明入侵乡村文明的时代,它反而成为一个停滞、却并不完整的标本。
外爷就是这个标本的守护者,以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姿态,或者说更像是一种淡然。做乡村医生行医五十年,他救过太多人,也见过太多的生老病死,和整个村庄融为一体。外爷的医者生涯早年间,村庄常有因为贫穷,或因为固执不听劝告而不愿去正规医院看病而发生的悲剧。有因胎位不顺难产而死的产妇,有患脑膜炎因耽误治疗而智力停滞的孩子,还有心脏病突发,等大夫赶到就已断气的中年人。文学作品中说“生命是一种大而脆弱的东西”,很难说清是什么为每个生命设下终点,封闭、愚昧、贫穷……作为乡村医生的外爷只是置身于其中的一环,很难改变什么。而当村庄终于与外界联通,尽管它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逝,外爷却能以一个平和的姿态停驻。

卡夫卡《乡村医生》改编动画
外爷一直留在村卫生所,与另外两位同样年纪的大夫一起,为越来越少的病人提供治疗。村里的住户越来越少,从百余户缩减到到几十户、最后只剩几户零星分散在山坡间。我十岁那年,卫生所搬出三间土胚房,转移到离马路更近的砖瓦房里。依据现代农村卫生室标准建立的新场地更大了,消毒室、治疗室、注射室、观察室、诊断室和药房的完整结构终于齐全,只是大多数时候仅仅由医生守着,终日无人光顾。他们不会离开,出于眷恋,或是仅仅出于职责。而无论当我多少次踏入这间房子,熟悉的中药柜陈设和满屋药香都为我复现了五十年前的历史。
到了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影响下,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均被禁止营业,卫生所的大门终于锁上。
这年外爷70岁,按照国家规定,正式退休,结束乡村医生职业生涯。由于外爷身体不太好,杨树湾的玉米地已经荒了,上次回家,我看到上一年的秸秆覆了满地,无人处理。风吹过,像大地的呼吸节律,提醒我这里曾有一个村庄跳动的脉搏。
后记: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我回到老家。卫生所重新开张了,外爷退休后,另外两名医生还在坚守,尽管几乎没有病人。根据县政府计划,2022年麻洞村将完成移民搬迁,并入县城附近灌溪镇移民安置点,届时原卫生所也将裁撤。我借外公的故事,叙述整个麻洞村从新中国建设以来医疗状况的变化。在更多的农村地区,医疗合作制度确实与新农村建设结合,正在焕发蓬勃生命力。
我仅仅想记录包括外爷在内的乡村医生几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与生命经验,因为在“大多数”与宏大叙事之外,个人微小的情感因素同样值得作为时代的一部分被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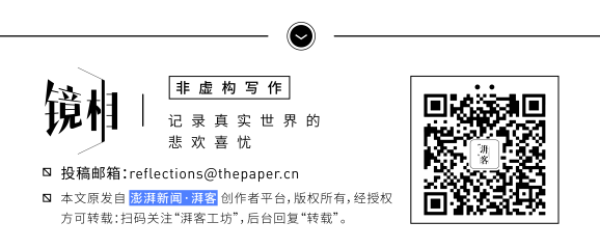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周继红退休
- 中方回应对日水产品限制是否会解除
- 周继红,跳水梦之队“家长”

- 美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道指涨0.18%
- 魔法原子正式推出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要打造1000个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场景

-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
- 敦煌莫高窟的主要艺术形式是雕塑和

- 12西川|怀念海子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