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每月读书二三十本,梁小民说:我是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
【编者按】
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每月的读书书单受到了许多读者和业内人士的关注,他长期每月读书二三十本且口味驳杂,着实令普通读者叹服。
近日,梁小民出版了新著《无用才读书》,他在“代序”中说“我最喜欢还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状态”,这或许恰恰道出了他如此“高产”的缘由。
本文节选自该书“代序”部分,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最喜欢还是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状态: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的,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正如喝一杯茶或品一杯酒那样。这正是这本书题目的来由。
要读无用之书,必须成为无用之人。人无用了,完全没有约束了,才有完全自主决策的自由,才可以为所欲为。一般来说,人是在退休后才能处于这种状态。不过由于我成长于革命时代,就有了两段作为无用之人的时间。一段是大学毕业后1968—1978年被发配到东北林区。当然也有工作,还算有用之人,但所学知识无用,也看不到什么前途,没有目标。这时在读书上就属于无用了。尽管这一段生活颇为艰难,政治环境又不好,且心情郁闷,但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生中最愉快的读书时期之一。
另一个则是六十岁退休之后,我是在六十岁生日那一天彻底裸退的。单位的约束完全摆脱,尽管还出去讲点课,发挥发挥余热,但“热度”几乎近于零,不能温暖别人,更不会引起温室效应,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这时读书又回到无用状态。有人问我,一生什么时候最幸福,我认为就是退休之后。这是完全任意读书的时代。
先讲“文革”时那一段。上大学时总感到自由读书的时间太少,毕业后赶上这么一个混乱但也约束不多的时光。毕业时就想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好好读书,这样就来到无人愿去的黑龙江林区。尽管当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流行,且可读的书也有限,但毕竟自己有点藏书,且读书条件也可以自己争取,因此也还是读了点书的。
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书还有一些。我就从认真读这些书开始。当年毛主席曾给高干们开了一个30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书目,“文革”中又倡导高干们读6本书。我就从读这些书开始。有一次我读《反杜林论》被工宣队看到了,指责我还读资产阶级的书。我把书扔给他,告诉他这是恩格斯的书,是毛主席推荐的,又上纲上线了一下,反问:“你反对我读马列的书,该当何罪?”他是文盲,不敢再说,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读书。即使读其他书,包一个书皮写上马克思什么书,就无人敢问了。我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且写了两大本笔记,还写了一些读书体会之类的文字。以后读了一些单位编写的辅导资料,感觉我理解得比他们好。大约1970年代初,有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含义,并寄给《黑龙江日报》。不久该报发了一篇介绍这个问题的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但比我写的差多了。虽然我知道写文章想发表是不可能了,但我仍然认真读书。以后又读了《资本论》三卷。这是我一生中读马列最认真,且读的最多的一个时期。从读书中也认识到“四人帮”宣传的那一套并非马克思主义,自己反抗,当然不可能,但不同流合污还是可以的。
此外读得多的就是古文。我有一套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认真学了一遍后,又借讲“儒法斗争”读了《论衡》《韩非子集》《史记》《资治通鉴》等允许读的书。同时向别人借了一本《辞源》,解决读这些书中不解的问题。“文革”前我买过五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在校时选读过,这次就全读了。还读了一些古诗词,甚至还为我的孩子选编了一本儿童读的古诗词(刚编了一点就赶上考研了,未完成)。当时年轻,尽管是无用的读,自己还想做点事。读《巴黎公社史》,还想写一本小说;读商鞅变法的书还想写一本“商鞅之死”的剧,赞扬商鞅的改革精神,不过都是想想而已。《商鞅之死》写了一幕也写不下去了,想来还是自己天分不够。
我爱文学书,但除了一套《鲁迅全集》(1963年版)外,其他藏书不多,于是就认真读鲁迅。我特别推崇鲁迅先生,读这套书时还摘录了其中一些格言式语录。当时有哈尔滨下放的干部到林区,我也向他们借书读。《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就是借来读的。他们有什么书,我就借什么,读过的,没读过的,都读。当然,我也无法穿越,只能出什么书读什么书,而无论好坏。当时我订阅了《自然辩证法》《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每期都读。当时出书少,书也便宜,只要见到的书就买,什么《李白与杜甫》《牛洋田》《虹南作战史》,等等,都是那时购买并读过的。那时真是饥不择食。
除读书之外就是自学英语。我中学、大学一直学的是俄语,自己还译过俄文版的《西欧六国共同市场》(当然没出版)。后来中苏交恶,感到俄语没用了,于是“文革”中开始自学英语。当时用的课本是英国出版的《基础英语》(旧书店所买)和北大的第二外语教材三本。在此基础上又读了张道真先生的《实用英语语法》,并阅读了其他书刊。除《北京周刊》外,还订阅澳大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先锋报》,读旧书店买来的英语故事书、小说等。没有人教,也没法学习口语,因此我的英语听说始终很差,至今成为憾事。
这些读书学习完全从兴趣出发,没有任何目标,也没想过“读书改变命运”之类,但以后对我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因为一直坚持读书,1978年招考研究生时,我才能以五门课439分的总成绩,再次进入北大,这才有以后的一切。看来无用的读书,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有用的了。“文革”中认真读书,读得比我多、比我好的人还有一大批。就当年我们研究生同学而言,中文系的钱理群、西语系的张隆溪、哲学系的陈来,还有不少如今已成为院士的理科同学,都是“于黑暗处静读书”的佼佼者。比起他们我常反省自己,不过这也有天分的原因,我不如他们很正常,但我努力了,就是没有虚度光阴。
第二个作为无用之人读无用之书的时期,就是60岁退休至今天。退休,没有了一切工作任务和约束,也再没有什么追求,这就是随意读书最好的时光。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就读什么,甚至《鬼吹灯》这类书也读过,而那些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不爱读就不读。人退休之后最怕寂寞无聊,我住郊区乡下,来往朋友不多,对老年人的街舞、麻将、养生之类毫无兴趣,唯一填补退休空虚的就是读书了。读到一本好书,有一点感悟,就是一种幸福。如同打麻将的老人赢了钱,或跳舞的老人浑身大汗一样。我退休生活的模式就是“活着,读着”。
当然,退休了,读点书作为燃料就可以发挥余热。退休后,主要为一些学校的EMBA或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讲课。读书可以给讲课更新增加点内容,“中国商帮文化”就是在自由读书的基础上新开的一门课。也可以任意写点东西,我许多普及经济学的书,如《经济学是什么》《寓言中的经济学》都是退休后写的。退休了,没有任何考核指标,也不想评奖之类,写起来更自由。尽管一些普及性的书在许多专家看来“没有学术水平”,但自己觉得好就写,退休老人还讲什么“学术水平”?人最大的欢乐来自自由,对一个读书人而言,自由地读,自由地写,就是最大的自由。如此自由的生活给个皇帝也不换。
我在无用的读书中有所感悟也写了一些文章,所写的文章陆续编为《想读》《随书而飞》出版。如今这本《无用才读书》就是近年来写的文章的汇集,与爱读书的朋友交流,也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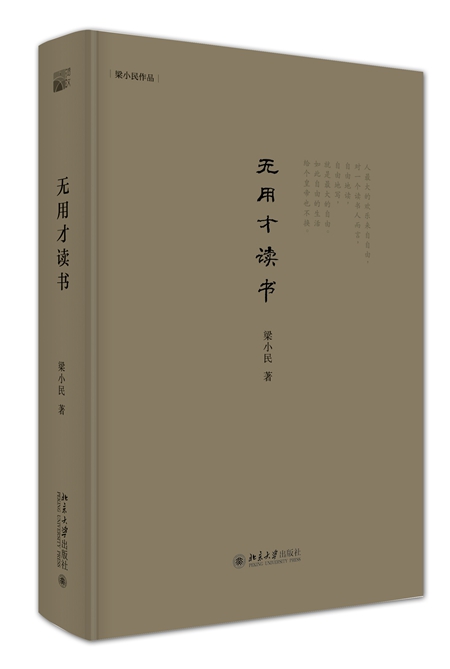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