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季剑青评《北京的人力车夫》︱作为“中介”的人力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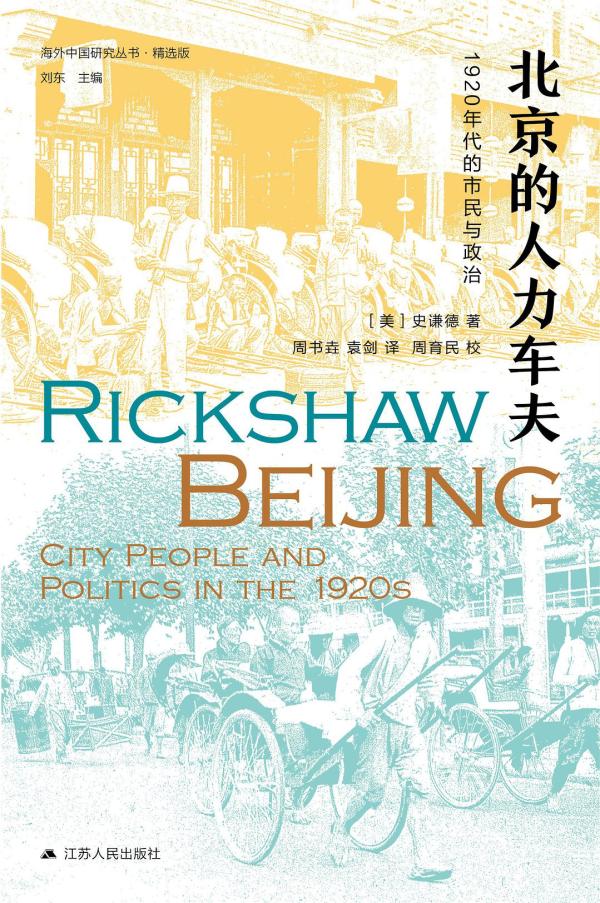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美]史谦德著,袁剑、周书垚、周育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92页,88.00元
1927年7月,胡适离京取道苏联前往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途经哈尔滨时有了一个“绝大的发现”,即哈尔滨乃是“东西文明的交界点”,因为哈尔滨原为租界的“道里”地区不准用人力车,只见电车与汽车,而“道外”的街道上则随处都是人力车。胡适感叹:“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5页)对于拥抱西方文明的胡适来说,拿人做牛马的人力车显然是传统与落后文明的象征。而在胡适常年生活的北京城,并无类似哈尔滨“道里”的区域,汽车与电车屈指可数(北京的电车系统1924年12月才建成投入运营),人力车是绝对主导的交通工具,人力车夫及其家眷竟占到北京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这与北京前工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倒也相称。
然而饶有意味的是,人力车本身就是一项现代发明。它于1860年代末诞生于日本,很快就因较低的资金投入和技术门槛而风行于亚洲各地。1886年第一批人力车出现在北京街头,庚子事变后伴随车辆技术和道路建设的改进而获得迅猛发展。胡适将人力车抬升到“东方文明”之象征的地位未免有些浮夸,但若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北京城,那么这种既“现代”又显得传统与落后的交通工具,堪称北京现代性的绝佳隐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史谦德(David Strand)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作为第一部以北京人力车夫群体为对象的专著,为我们探索民国北京现代进程的复杂性提供了出色的个案研究。作者抓住了人力车夫身上所体现的现代性的内在张力,从城市政治的视角展开了一段生动的1920年代北京社会史。
史谦德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时说,他的这本著作受到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中介阶段(liminality)”学说的影响:“‘中介阶段’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和心理状态,可能产生的结果不止一种。人力车夫吸引我的,正是这种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状态,因为1920年代,一般中国城市的处境大抵如此。”(《上海书评》2021年12月12日)北京是否可作为1920年代“一般中国城市”的代表,容有商榷的余地,但人力车夫处于“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中介阶段”,确实是个敏锐的观察。“中介”一词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理解,即人力车夫在北京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某种“媒介”的角色。作为北京最主要的交通从业者,人力车夫与普通乘客、警察、地方精英、政党工作者等社会各色人等都有直接的接触,透过人力车夫的活动,可以“窥探整个城市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运作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一部以“北京的人力车夫”为题的著作,却涵盖了1920年代北京市民生活和城市政治的诸多方面。
一般读者对老北京人力车夫的印象,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文学作品塑造的。“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都写过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诗文,人力车夫主要以亟待救济的贫苦劳动人民的形象出现(参见孟邻《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老舍的《骆驼祥子》当然是写人力车夫的经典之作,主人公祥子虽然奉行“个人主义”的生活哲学,但小说实际上始终是扣住祥子作为人力车夫的职业身份来展开叙事的,描绘的是整个人力车夫群体的“劳苦社会”(见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注重老北京特有的职业行为以及人物的职业性格,是包括老舍在内的京味作家的普遍特点(参见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7-38页),诸如齐如山这样的学者,也将“洋车行”列入他笔下的“北京三百六十行”中(齐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72页)。不管是早期新文学作家对人力车夫的描写,还是老舍和齐如山有意将人力车夫作为北京特有的职业文化的样本来再现,都出之以某种外部的视角,人力车夫作为一个群体因而就呈现出某种相对静态的稳定的特征。《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书恰恰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引入城市政治的视角,史谦德打破了关于人力车夫的定型化的想象,在他的论述中,人力车夫构成了1920年代北京的一股活跃的社会力量。

悉尼·甘博拍摄的北京的人力车夫
与亚洲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人力车夫行动和组织的速度并不算快,低廉的租金多少化解了车厂主和车夫之间的紧张关系,小规模的店铺式车厂经营模式使得矛盾局限在个人层面,大规模的冲突不太可能发生,加之车夫数量大且分布范围广泛,全市规模的组织或行动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车夫只能靠传统的商业行会(merchant-guild)出面来保护自己的利益”(72页,中译本将merchant-guild译为“商会”,不太准确,容易与北京正式的商会[the Beijing Chamber or the Beijing Chamber of Commerce]相混淆)。在这种传统行会的体制下,车厂主和车夫会形成某种家庭式的庇佑关系,现代阶级政治难以插足其间。社会学家黄公度在1929年夏天的一次调查中失望地发现,人力车夫并没有他所期待的“无产阶级”意识,车夫心目中的敌人不是车厂主而是与他们竞争的汽车和电车,“他们不独不恨车主,并且还认为车主与他们是同一阶级的”(292页)。这是传统的行业意识在现代城市政治中的反映,也为1929年10月那场震惊国内的人力车夫捣毁电车的暴乱埋下了伏笔。
行会传统不仅保留在人力车行业中,诸如泥瓦匠、木匠、水夫、粪夫等手工业或服务业都拥有自己的行会,这当然与北京作为前工业化城市缺少现代产业工人及相关的制度和组织有关。行会的持久不衰不是文化惰性的反映,而在于“它们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十分有效”(170页)。除了工人群体,商人、律师、学生等阶层也都在1920年代的北京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它们多少也都仰仗了前现代社会的自治传统。不同的地方在于,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士绅等地方精英的公益活动保留了较大的自主性,而晚清以降,伴随着近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地方精英的团体出现了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趋向,并且被置于国家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正如史谦德在书中指出的,“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里,官方支持建立一些诸如商会、律师公会和银行公会这样的自治行业协会(法团),把相当权力交给绅商领域的趋势正规化了”(20页)。即便是在中央政府权力衰微的1920年代的北京,“商人、学生、工人、记者以及其他各界依旧会迎合北京官僚,以期获得特权、放权和照顾”(227页)。
史谦德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将1920年代北京各种职业群体共同参与和彼此互动的场域界定为“新公共领域”:“这一新政治舞台,或者说公共领域,是一种新旧惯例和态度的结合体”,并指出由于城市精英对于官僚的依赖和内部的分化,这个“新公共领域”从未达到完全的“自主性”(194页)。“公共领域”这一源于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经验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民国初年的北京社会,学界不乏质疑之声,魏斐德就对此明确持批评态度(参见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63-165页)。不过在我看来,史谦德在他的研究中已经成功地改造了“公共领域”概念,使之不局限于资产阶级或地方精英,而将如人力车夫这样的底层平民也容纳进来。因而史谦德特别看重“新公共领域”中政治参与日益扩大的面向,这也是1920年代北京城市政治自身演进的逻辑。1919年五四运动的主角是学生和商人,而到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则出现了“人力车夫爱国团”的身影,自来水厂的工人、印刷工乃至郊区的农民也都参与其中(214页)。
政治参与的扩大离不开政党的动员。史谦德在书中勾勒出不同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参与北京城市政治的历史线索,从中可见现代阶级政治与传统派系和行业纷争的纠缠。在早期共产党人看来,北京作为一座以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为经济支柱的城市,缺少激进政治的阶级基础。“五四”时期邓中夏等人组织人力车夫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他们转向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也就顺利成章了(166-167页)。1925年前后,北京政局的变化使得劳工再次成为激进分子动员和组织的对象,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这方面形成了彼此竞争的关系。“国民党发现,共产党的基础主要是在城市现代工厂这部分,于是他们就向城里广大尚未工业化的经济体寻求支持。”(190页)国民党比共产党更能容受行会政治的运作模式,他们很快深入到水夫、粪夫和人力车夫之中。1928年北伐胜利后,北平市内已经没有共产党的活动空间,该年6月由国民党地方党部组织成立的北平市总工会,将现代工厂和传统行业一网打尽,电车工人、印刷工、粪夫、人力车夫都在党部和总工会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工会(260页)。然而,如果说传统行会可以像工会那样代表工人利益,那么工会“也就可以像行会那样运作,再生出一套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派系倾向的内部政治”(191页)。国民党的工人政治没有将北平工人组织为集体抗争的力量,而是充斥着行业和派系之间围绕各自利益的纷争与倾轧,最终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事实上,北平市总工会的成立本身,就是国民党北平党部谋求自身权力的手段之一。北平市党部由原北平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党员选举成立,思想上偏向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只有很松散的组织关系,他们同时也被摈弃在掌握实权的北平军政体系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建立工会,发展工人政治,就成为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途径(参见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与国民党的蜕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与此同时,北平市党部乃至总工会内部也存在着派系斗争。总工会的负责人、北平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组织科主任张寅卿,面临着得到国民党中央支持的右翼干部的挑战,由于他在工人运动中树敌过多,总工会中的电车工人和电灯工人也与反对派结成盟友,意在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旧势力”赶下台。张寅卿及其支持者于是转而寻求人力车夫的帮助,试图借助人力车夫的力量来维护他们在党内和总工会内的地位(273-275页)。人力车夫则利用这一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1929年秋,事态朝着越来越激烈的方向发展,最终酿成了10月22日捣毁电车的大规模暴乱。
史谦德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场暴乱的经过,他肯定人力车夫的“政治积极性”:“他们动用了城市居民能用上的全部集体战术和公共策略,这些都源自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传承、法团和行会的惯例、国民党干部提供的群众政治框架,以及他们自己在街头斗殴的习气。”(278页)然而,其他学者却对此有不同看法,杜丽红就认为史谦德“对1929年人力车夫暴动的解释太过理想化,未能注意到人力车夫自身的复杂性,也高估了其政治能动性”。她指出,这场暴乱的根本原因是人力车夫生活困难,饥寒交迫,他们认为是电车公司抢夺了他们的饭碗,只有破坏电车才有出路。大部分人力车夫对北平市党部和总工会内部的派系斗争懵然无知,他们并非为了支持张寅卿一派才走上街头,而是在对方的煽动下通过捣毁电车来宣泄长年郁积的不满情绪,因而暴乱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形势失控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国民党党部建立的总工会并没有真正改善人力车夫的生存境遇,反而成为政客把持操控的工具(参见杜丽红《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暴乱遭到北平军政当局的残酷镇压,四人被判处死刑,大量人力车夫遭到拘押,后被驱逐出北平,北平市总工会则于1930年2月被明令取消。这场暴乱最终成为人力车夫和北平工人政治的双重悲剧。
如何看待人力车夫在1920年代北平城市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在史谦德的笔下,人力车夫不再是沉默的客体,他们通过行会、工会等组织形式,为了自身的利益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力车夫的活动和抗争中保留了大量前现代的要素,他们并未获得现代阶级意识,而是把依托传统“民生”观念的“道德经济”作为自己的诉求。就此而言,很难说1920年代北平的人力车夫已经成长为自觉的政治主体。与此相关的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共产党如何看待这场暴乱?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在北平处于地下状态,基本没有在人力车夫中发展起组织,1929年到1930年间,北平的人力车夫中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见杜丽红《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152页注释),其中一名就是被害的四人之一贾春山,他是人力车夫工会太平湖分会的负责人。当人力车夫与电车工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北平团市委书记王青士的意见是:“由于革命处于低潮,党的任务主要是积蓄力量,人力车夫和电车工人都是劳动者,要说服人力车夫不要去砸电车。”他告诫贾春山不要卷入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然而“一心只考虑为穷哥儿们撑腰、谋利益”的贾春山还是加入了打砸电车的队伍,最终遇害(参见张秋生、陶小康《贾春山与北平“人力车夫暴动”事件》,《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6期)。这一细节也许可以用来说明贾春山政治觉悟的“落后”,但同时也表明共产党拥有从阶级政治出发的、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视野。
由此我们不妨对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阮明这一人物的命运做一番新的解读。在《骆驼祥子》的初版本中,阮明是一个打着进步思想的幌子来敛财的没有原则的工会组织者,最终因为祥子的出卖而丧命。这一形象长期被认为是对革命政治的扭曲,老舍为此遭受了左翼批评家的攻击,并在1955年的修改本中删去了阮明及其相关情节。正如孙洁在《〈骆驼祥子〉为何没写1929年的洋车夫暴乱》(《上海书评》2021年12月13日)一文中正确地指出的,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错位”,因为阮明的原型张寅卿恰恰是一个自利的政客,并非左翼批评家所想象的革命者,尽管彼时的国民党也以“革命党”自居。老舍未必熟悉1929年北平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内幕,他对现代政治总体上的厌恶体现了他自身的道德感,然而他却在无意中揭示了人力车夫所参与的北平城市政治的内在逻辑,为他的左翼对手所不及。

电影《骆驼祥子》
或许正是因为1929年的人力车夫暴乱并非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符合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定义,它几乎没有被写进主流的工人运动史中,左翼批评家对之不甚了然也就情有可原。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看,人力车夫阶层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属性,也使得他们很难成为共产党真正倚重的革命力量。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车夫们虽然是被压迫者的缩影,但同时也是落后社会令人不舒服的遗留物,所以,年轻的进步人士往往不屑一顾”(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275-276页)。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民国时期人力车夫始终难以摆脱的悲惨命运呢?然而,正是这种极其困难的社会境遇,才使得他们的奋力抗争显得如此地悲壮而令人动容。史谦德以他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他们在历史夹缝中活跃的身影,这是他的著作在出版三十多年后仍旧魅力不减的重要原因。
史谦德没有讳言人力车夫的“落后”,但落后同时又深深嵌入到1920年代北京城市政治之中的人力车夫,恰好体现了北京现代性乃至转型中的中国现代社会的“自相矛盾的本质”:“越是抵制进步,就越会被卷入现代资本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发展中去”(323页)。这一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精彩论断,提示了人力车夫作为理解现代性之悖论性质的“中介”的深刻意义。
最后简单谈一下本书的翻译问题。该书由多位译者合力完成,但读起来并无不连贯之感,可见译校者在润饰统一文笔方面颇为用心。译笔总体而言平正通达,堪称准确,个别地方或可商榷,但瑕不掩瑜。第7页“未擦干净的画布”对应的原文是palimpsest,这是城市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通常译为“重写本”或“重写羊皮纸”,原指古希腊一种可反复刮去原有痕迹重新书写的羊皮纸,故用来形容城市变迁中历史痕迹的抹去与残留。第二章标题“人力车:老少咸宜的谋生方式”,原文为“The Rickshaw: Machine for a Mixed-up Age”。Mixed-up Age此处意指新旧混杂的年代,译为“老少咸宜”显然不太合适。第30页“令骡车夫无可奈何的是,人力车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骡车”一句,原文为“But by the teens the rickshaw had overtaken the mule cart in popularity”,应译为“但到了1910年代,人力车在受欢迎程度上已经超过了骡车”。第42页“但与此同时,人力车不仅是简单地用机械装置替换畜力或者人力”,“不仅是”原文为“instead of”,应译为“不是”,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意思却大相径庭。第74页“尽管车夫往往显得没什么规矩,给人的印象也不好”,原文为“Even though pullers tended to be poorly organized and represented”,意为车夫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和代表。第177页“这一争执不休的过程简直就是建邦立国的缩微版”,其中“建邦立国”原文为“state building”,显然应译为“国家建设”,这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常用术语。以上诸条属于白璧微玷,希望再版时有机会得到订正。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