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年味读年画|历史之年画与今日之年画
何谓年画?
伴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必要回顾年画的原始定义,并进一步确定其学术概念。然而,历史之年画与今日之年画所指是否存在错位?海内外学者阐释的年画差异在哪里?学界研究的年画与艺人制作的年画以及政府保护的年画又是同一概念吗?本文尝试追溯年画之名的起源与古今释义,希冀有益于年画研究方法的拓展以及分类方式的呈现,从而更大程度地释放其学术阐释的张力。

泰山神虎 河北
一、清代文献中的“年画”及其沿袭
年画一词并非新创,作为专有语汇其使用已近三百年。查阅《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可知,“年画”在乾隆时期始载,“乾隆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事录”于七月十八日载:“于本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画得各样节活纸样十张、挑杆吊挂纸样四张、画彩胜纸样十张、堆彩胜纸样六张、年画纸样十张持进交太监张玉、胡世杰呈览。奉旨节活样不必做挑杆吊挂,照样准用绫绢堆做,年画用纸画,其余俱照样准做,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将以上之物俱交进讫。”这段记载虽不涉及年画所绘之内容,但明确了宫廷在年节需要使用年画的习俗。而“年画用纸画”也表明其工艺是手绘而非版印,其材质是纸而非绢。相似记述还可见于“乾隆五十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事录”,十月载:“初九日照年例画得年画纸样十张,画彩胜纸样十张……上曰俱照样准做,钦此。”
上述记载表明,过年使用年画在乾隆时期已成固定年例。但在雍正时期,这种年俗是否形成?目前看,《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雍正年间的记述,仅月光、门神、三星等语汇频现,如“雍正九年表作”七月载:“二十四日员外郎满毗传做年例备用月光像二分,着照例糊表,记此。于八月初三日糊得月光像二分交太监夏安讫。”留意雍、乾时期这些记述的时间点可以发现,农历七月后开始准备年节用品的惯例从清早期的宫廷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期的民间。笔者曾访谈多位经历农耕时期传承有序、门里出身的“自然传人”如杨立仁(1923年生)、韩清亮(1924年生)、杨洛书(1927年生)等,在回忆早期年画作坊时均谈道:为了在腊月里集中销售,画店通常在秋收以后开始大量印制年画。这种遵循时节的生产规律跨越时代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宝坻文士李光庭著《乡言解颐》,“卷四·物部(上)‘年画’”载:“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依旧胡卢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这段记载此前多被误认为是年画定名的肇始。作者前半段虽含有对此类画作的不屑,但同时也点明年画兼具教化功能。后半段赋诗,李氏首先道出年画图像的来源系依样画葫芦,即“年画”这种画样被作者认定旧时已存在。同时,李氏在这篇题为“年画”的专文中所赞扬的画作内容皆与农事紧密相关。历史上,杨柳青、杨家埠、桃花坞、武强、凤翔等年画产地确曾出现诸多“耕桑”题材年画。
同是道光年间,苏州文士顾禄著《清嘉录》“卷一·正月·新年”载:“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表明当时的农事题材画作(芒神、春牛图)被统称为“画张”,这说明位于南方的苏州在表述相同的“耕桑”画作时并未使用“年画”称谓。由此可知,即便同处一个时代,不同地区(北方和南方)的民间对年画的称呼有所不同。顾氏的另一著作《桐桥倚棹录》“卷十·市廛”详细描述了苏州山塘画铺所售年画之风格,文载:“异于城内之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坞、寺前之多用印板也,惟工笔、粗笔各有师承。山塘画铺以沙氏为最著,谓之‘沙相’。所绘则有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而画美人为尤工耳。”
这段记述不仅说明苏州年画在套版印刷工艺之外,曾存在过以手绘(大幅小帧俱以笔描)为主要特色的年画形式,同时还记录了这类年画的各类题材以及代表性画师。据学者徐文琴的调研,此类创制于18世纪早期的苏州手绘年画在德国利克森华尔德城堡被完好地收藏与展示。

德国利克森华尔德城堡的苏州手绘年画
清乾隆年间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十二月·市卖”载:“初十外则卖卫画、门神、挂钱、金银箔……请十八佛天地百分。”因天津自明代筑城设卫,文中的“卫画”应指天津年画,“百分”则是对北京纸马的称呼。在“皇都品汇”一节又载:“置年货之何先,香镫云马;祀神堂之必用,元宝千张。门神来无锡,爆竹贩徽州。”潘氏对清中期北京岁时风物的记录,一方面表明其未将年画与门神、纸马视作同种,一方面又道出这三类民间过年使用之物产自不同地区。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十二月·画儿棚子”一节载:“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这段记述同样是关于北京在农历腊月的节令风俗。与前文清中期使用“卫画”一语不同,清晚期的北京将年画呼作“画片”。购买的群体为女性及孩子,购画的目的则是装饰新年。
以上诸引文表明,年画语汇在清代并非固定且流行的特定表达。即使同处清末的中国北方,“年画”一语的使用也未全覆盖,更不必说南方的语汇惯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狗·猫·鼠》一文曾道:“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两幅装饰墙壁的画作,在文中虽称为“花纸”,但显然是年画,且有学者考证出自湖南滩头。通过梳理清代文献可知,门神、纸马、月光等我们现今归为年画类的画作,在过去曾是与年画并列的称谓,而不是具有包含关系的概念,这些语汇的出现不仅早于年画,并且沿用至今。
二、作为宣介的“年画”之生成与接受
年画被国内文人志士广泛关注始自清末。“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观念在当时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基于这种思潮,民间创办了大量的白话报刊,推广普及初级教育。在众多创刊于清末的白话刊物中,与年画密切相关的是由彭翼仲创办的《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体现“开民智”观念的改良年画不断刊印其上。从学术角度看,“改良年画”是具有特指含义的专有名词;从受众角度看,“改良年画”不过依然是年画,“改良”二字也许远不及“年画”一语深入民间。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年画在不同地域都能得到民众的一致认同(遍布全国的众多年画产地是明证),因此,即便附加了新观念、新思想,年画作为共同的认知符号在当时的流行仍旧通畅。
历史地看,年画语汇在全国广泛普及,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紧密相关。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延安和解放区,不断涌现利用传统年画形式创作的“新年画”,其目的是为抗战和政治宣传服务。在“新年画”发轫之前,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曾影响整个中国,它与此后“新年画”的产生、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王树村评价这段历史曾言:“年画能有今天的发展,与五十多年前鲁迅对年画的重视和提倡,与他向青年画家提出的要向传统木版年画学习的主张是有密切联系的。”新年画创作者的身份与从前大不相同,几乎没有来自于民间的画师、艺人,绝大多数创作者既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又是革命战士,所以,这一时期的年画自然而然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1949年11月26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由毛泽东批示同意并且公开发表执行的第一号文件为《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按照延安文艺思想的模式指导艺术家,各地政府文教部门和文艺团体纷纷响应并立即投入。这一时期,随着年画全国性的创作、出版、展览的大规模展开,“年画”一语自然而然成为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称谓。
在过去(主要指清代),年画的重大价值也许并未被它的创作者和购买者所注意,那时大众的休闲娱乐方式很少,观赏戏曲题材的年画都可算作一道精神盛宴。正是由于“过去的年画都是属于民间的……传统性很强”,才使得《用新年画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等观念在基层迅速流行起来,冠以“新”字的“年画”用语随之广泛深入民间。为政治服务的“新年画”大批量出现,充分证明了在上层建筑中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即“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一种民间美术比得上民间年画接触群众多,影响广”。而群众的支持与信赖是一个新政权得到巩固的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发扬传统艺术,提倡为广大工农服务,它才被广泛重视起来,并以‘年画’之名确定为一大画种”。
三、国内学者对年画概念的阐释
最早关注年画并将其视为学术对象的国内学者是民国时期的作家、画家、史学家。比如,前文提到鲁迅对年画的重视和提倡;又如,郑振铎对木刻版画的收集、研究与编印;再如,阿英对年画的搜集研究,其出版的《中国年画发展史略》开创了年画著述之先河;另外,郭味蕖对年画的收集考察,所著《中国版画史略》也对年画的形成发展有所论及。
郑振铎在开展中国版画研究之际,曾着手探讨年画相关问题。关于定义,郑氏曾言:“‘年画’是在新年的时候粘贴于门上、室内墙壁上作为装饰品之用的。”从年画的木刻工艺出发追根溯源,郑氏认为:“年画的创始是很早的,也许和木刻的创始是同时的。最早的单帧印行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在五代晋开运四年(947)就印施流行。这些佛像是作为人民供养之资的,虽然不能说就是正式的年画,但性质是很相同的,也许就是年画的开始。”早期国内学者常将年画视为木刻画、版画的一种进行研究。王伯敏在溯源版画的雏形画像石与画像砖时也写道:“从其以刀或凿子等工具在版面上镂刻出画像这一特点来说,诚为一种具有版画性质的制作。若从后人拓印的效果来看,更具有与版画制作相类似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一溯源较为合理,从木版年画以刀刻版的特点,以及绵竹活态传承至今的拓印年画均可作为印证。

绵竹年画艺人正在拓印年画
王树村在专著《中国年画发展史》中设“‘年画’之称的考据”一节,并对年画的定义进行阐述:“狭义上,专指新年时城乡民众张贴于居室内外门、窗、墙、灶等处的,由各地作坊刻绘的绘画作品;广义上,凡民间艺人创作并经由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的、以描写和反映民间世俗生活为特征的绘画作品,均可归为年画类。”同一时期,薄松年在专著《中国民间美术》中的“品类篇”将“年画”与“门神及神祃”分而设成两章,这种有意区分在行文时却又合并归为年画,载:“宋代年画在内容及表现形式手法上都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不止有驱邪降福的神像(如门神、钟馗、灶神、财神之类),而且扩展到风俗、戏曲、美女、婴戏等吉祥题材。”
自2002年至2011年,冯骥才发起、组织与实施了“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抢救工程”。关于什么是年画,他说:“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汉代驱邪的神荼和郁垒;而狭义的用木版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的确立起来。”
以上各家在年画的搜集整理研究等方面贡献卓越。在明确年画之功能时各家虽侧重不同,但都延续清代文献记述中所形成的观点——强调农历新年与年画的密切关系。《辞海》中的“年画”词条也作:“中国画的一种。夏历新年时张贴,故名。”
四、国外学者对年画的称谓
自20世纪初至今,俄罗斯学者完成了大量以年画为主题的研究。从李福清院士撰写的《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年画研究成果目录》可知,俄籍学者较少只用“年画”二字作为研究成果的标题,而是将题材、类型等属性与之结合命名,常用的题目关键字有民间年画、戏出年画、木版年画、吉祥年画、宗教题材年画等。其中,又以“民间年画”的使用为最多,如《中国民间年画:旧中国的精神生活》(阿理克),《从中国民间年画看中国艺术中的象征》(鲁多娃),《中国民间年画中的戏出年画题材》(维诺格拉多娃),《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李福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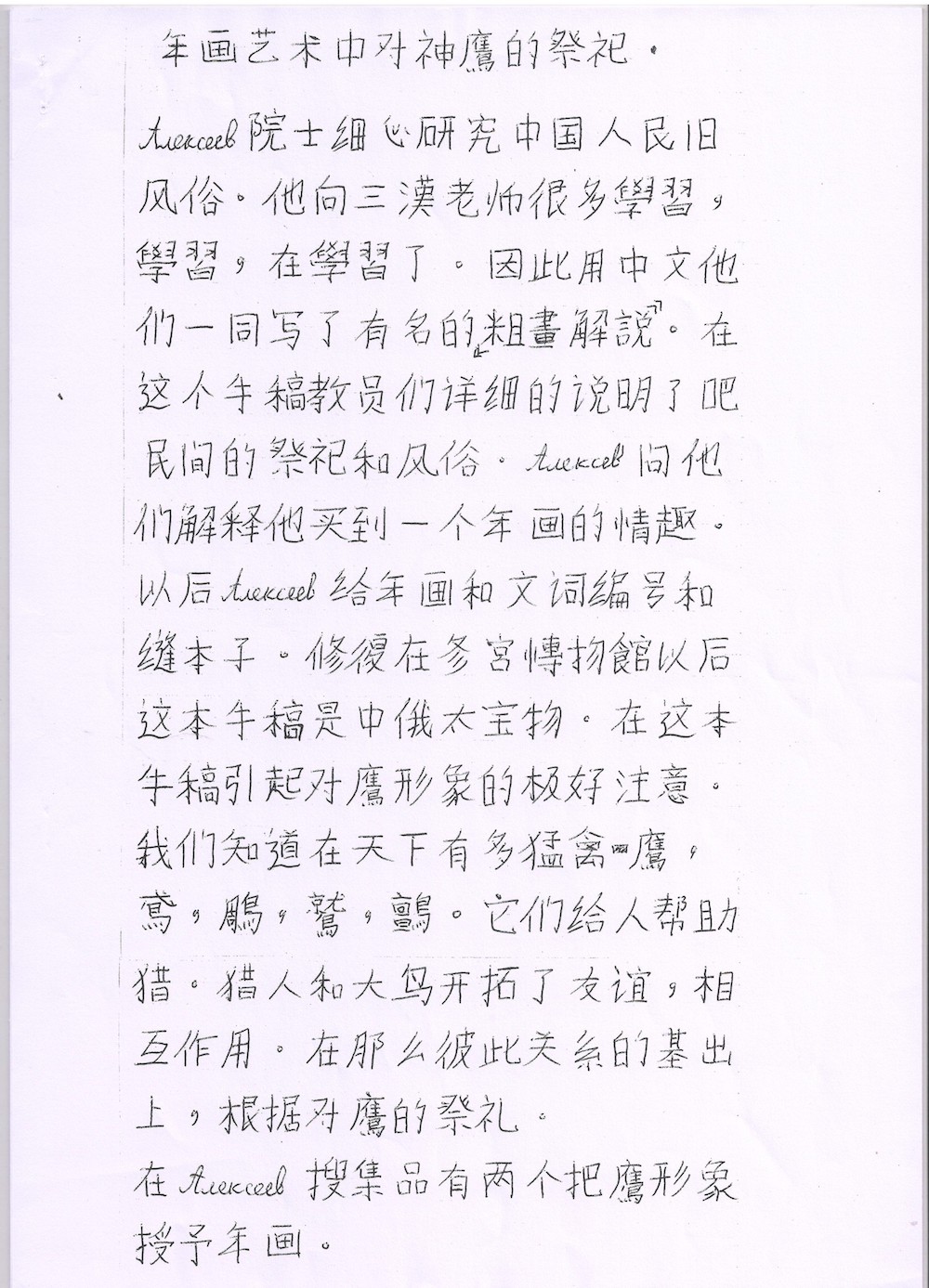
俄罗斯学者普切林使用中文写就年画论文的手稿照片
在日本,除了藏有大量中国珍品年画外,还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年画的研究。泷本弘之在《近现代日本的中国民间版画研究史及诸问题》一文中系统论述了日本的中国民间版画研究史。虽然这些研究的内容涉及年画,但直到21世纪初,日本学界一直沿用“版画”或“民间版画”作为论著题目。近十余年,以三山陵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开始使用“年画”一语定名研究成果及展览内容,如《中国年画的小宇宙》(三山陵),《“马赛克型”〈三国志演义〉年画前后本研究》(泷本弘之),《利用了祈福版画的“伪满洲国策年画”》(中城正尧),《从年画看〈九更天〉戏曲的演变》(中冢亮),以及“早稻田大学藏中国木版年画展”等。
1943年1月,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出版的摄影杂志《北支》刊载了几幅年画作品及其张贴、售卖的照片。其中一张画贩于街边摆摊卖画的照片旁注写道:“年画(正月用来装饰墙壁)几乎销售一空。”照片中的画作虽不清晰,但从画上印着的整齐边框以及细腻的背景处理方式,大致可判断出这是一摞尺寸一致兼有戏曲与美人等题材的胶印年画。另一张贴着东丰台年画风格的门户照片旁注写道:“贴好作为装饰的门神挂钱。”其余几幅作品分别写着“灶神(陕西省)纸马”“灶神(四川省)”“百份(北京)人物炉火之神”这组图像及说明文字不仅显示出刊物编者及摄影师对年画的称谓,或许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当时采集视觉影像时民间自有的俗呼用语。
1967年,日本记者樋口弘编辑出版了《中国版画集成》。从图集的“解说目录”可以明显看出,编者有意将“年画”从“版画”中剥离。即前四章按年代顺序介绍中国版画自唐至清的发展,如“唐、五代的版画”等,后面则将年画视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大类单独设列章节,如“年画的确立与发展”“各地各样的年画”等。其中,第七章虽定名“苏州版画”,但在内容上既有“苏州桃花坞的年画制作”“扬州、南通、上海的年画制作”等明确带有“年画”语的题目,也有“苏州版画的题材”“苏州洋风版画的衰亡”等强调“版画”的标题。就图集本身而言,尽管未将苏州版画与桃花坞年画之间的关系道明,但是,编者有意将版画与年画分而呈现的尝试是明确的。
2007年,法国学者柯孟德策划的“中法民间版画:王树村及亨利佐治藏品展”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出。虽然展览的关键词为“民间版画”,但是,王树村专为展览撰写的文章却题为“中国年画展览前言”,并在开篇写道:“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刊物上读到中国民间版画(年画)在法国里昂展出介绍了。”显然,王氏认为年画而非民间版画更符合对展出的中国作品的称呼。这也体现出海内外学者对年画定名的不同侧重。

加拿大学者傅凌智在其专著中全文使用 拼音“Nianhua”
欧洲及北美多国近年开始重视对年画的研究和展示。2011年,《年画研究》专题杂志创刊,诸多欧美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首发。这些学者或用NewYearprints表示年画,如美国学者梁庄爱伦(ELLENJOHNSTONLAING)的论文《域外来财、迎财神和发财还家:年画中的三个相关主题》;或用Chinese popularprints表示年画,如瑞士学者Alina的论文《“配色歌”和中国传统木版年画中的民间审美原则》;也有直接用中文书写包括“年画”语汇的全文,如捷克学者包捷(LUCIEOLIVOVA)的论文《年画的海外收藏及藏品研究》以及俄罗斯学者普切林(NikdayPchelin)的论文《年画艺术中神鹰的祭祀》。加拿大学者傅凌智(JamesFlath)在其专著《幸福的文化——年画、艺术和中国北方乡村的历史》中全文使用拼音“Nianhua”。种种成果表明,“年画”一语正逐渐成为海外学者开展研究所共用的学术名词。
五、乡土空间中的“原境”与“非遗”观念下的认同
由于过去年画作坊中的艺人经过学徒,大都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因此,有必要呈现年画在乡土空间中的原始境况,特别是其创制者(有时兼为经营者)的用语、观点与态度。
历史上,杨柳青镇南的众多作坊更多将年画俗呼为“活”与“货”。比如“粗活”“细活”用语,是对杨柳青年画精细程度的区分;“线活”指仅印墨线不套色的“画坯子”;“订货”指画贩给画店下订单;“上货”“堆货”指画贩、民众前来买年画。民国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杨柳青镇南三十六村存在数量众多的小作坊,他们仅从大画店“领活加工”,并不从事销售,年画在这些仅负责彩绘工序的村民眼中不过就是“活儿”,画年画也就被他们称为“画活”。而今,为了展现年画的品种齐全、题材丰富,许多杨柳青的画店一直保持着同时经营多种类别年画的传统,既提供美人、戏出、娃娃等世俗画,也出售门神、灶王、全神等神像画。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时期“义成永”画店制作的年画,左下角印其字号
一般而言,大型画店的经营者通常既是年画的印制者也是销售者。笔者曾于2011年参与“南乡年画抢救性记录”,期间数次访谈知名画店“义成永”的传人杨立仁(1923—2020),梳理6万余字的采访口述实录,“年画”作为专有名词仅被杨老提及两次。一次是“画年画和种地是两条道。种地的专门种地去,画画的专门画画,都是雇的人,大伙帮忙”;一次是“武强的人都上咱这干这个,武强也是出年画的地方,还有丰台、唐山那边儿的,他们都是原来干过才来咱这儿干这个的”。访谈过程中,杨老不仅很少使用“年画”表达自己过去从事的行业,在谈到画店制作的门神时,也多用“小云”“喜字”“执瓜”等语汇代替。显然,如果笼统唤作门神,很难说明具体所指,而用画面背景的不同符号,以及门神手中所执器具则很容易区分。此外,杨立仁还将尺寸约为“三裁”的《天地全神》呼作“小天”;以整张雪连纸套印的《全神像》叫做“大纸”,又因农民和渔民所供之不同而分为“平大纸”与“海大纸”;而“对楼”则是对包括《麒麟送子》《天仙配》等十余种“娶媳妇用的”图像的代称。与今天各年画产地的多数代表性传承人以及新生代传人不同,过去的年画艺人更习惯于使用乡土语汇表达年画的各种题材。
在谈到旧时哪些地方给“义成永”下的订单最多时,杨立仁说:“一个是纸马铺,一个是杂货铺,一个是纸行。”由此可知,专卖纸马的店铺同时也出售年画。而在杂货铺销售年画的情况则不止天津独有,山东杨家埠同顺德画店至今珍藏着祖上到莫斯科销售年画的护照,上载:“驻哈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发给护照事。兹据本国商人杨俊三,现赴俄国毛四各瓦六顺堂杂货铺……”由此可知,今人所称的年画店在过去很可能是杂货铺,而“义成永”“六顺堂”等名词不过是字号,可用于画店亦可以用于铺面。或许,过去的从业艺人并不看重称谓,经营年画仅是他们的谋生方式之一。与绵竹艺人将“黑货、红货”作为不同工艺年画的称谓相似,滑县艺人用“轴”,画轴、轴贩、发轴、神轴、祖宗轴分别表示画年画、卖年画的商贩、批发年画、神像年画、家堂年画。考察各年画产地的方言称谓可知,年画一语在过去的艺人间并不十分普及。

山东杨家埠同顺德画店于1917年到莫斯科销售年画的护照
实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被视为是实现文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互相了解方面的重要力量。自2006年至2011年,国务院分三批将18个年画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2018年,先后命名了26位年画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二十年间,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兴起、传播与普及,学界对于传承、发展、创新等问题的探讨也一直未曾中断。事实上,文化一旦作为政府项目,很难遵循原先一任自然的发展轨迹,必将受到上层力量的主导,从而使原本自发的民间文化出现新的前所未遇的发展动向。
目前看,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文化举措,无论是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项目的地方,还是被命名为国家级年画项目传承人的个体,“年画”一语已然成为自官方到民间普遍认同的专有名词。
结语
年画的“年”代表其有较强的节俗性,“画”则凸显其作为美术品的观赏特征。通过前文梳理,此处可以为木版年画定义为运用木刻雕版、套色印刷、手工彩绘等技艺呈现艺术形象的民俗绘画。狭义的年画,依俗于农历新年之际张贴在大门、居室内外、灶台等处,既表达出民众辞旧迎新、纳福迎祥的共同心愿,又体现出个性化的家庭理想;广义的年画,凡是由民间作坊制作并销售,内容描写百姓的信仰观念、内心愿景与世俗生活的绘画,均可被视为年画。
从售卖、张贴、使用者的角度看,历史上,年画曾一度专指戏曲、美人等少数几类世俗题材的画作,门神、纸马、神像等信仰题材的画面极少被民间称为年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遍及全国的“新年画运动”,以及近二十年间各级政府保护、管理、利用年画项目的种种举措,都使得“年画”一语深入人心。至于研究者的视角,随着学界近年对本土语汇的重视,年画这一曾经的专有名词正在成为学术概念。无论是“年画”一词的来源和本义,还是其作为学术概念的生成,或是不同语境下的释义,使用本土话语都不妨碍理解其背后的文化表达和艺术特征,也并不违背相关的学术传统,或许更能释放其学术阐释的张力。
(本文作者单位为天津大学,原文标题为《年画之名溯源及其释义》,全文原刊于《民艺》2021年第6期,澎湃新闻经作者转刊时,注释未收录。)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