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书评︱一周书记:由“文体问题”重返……历史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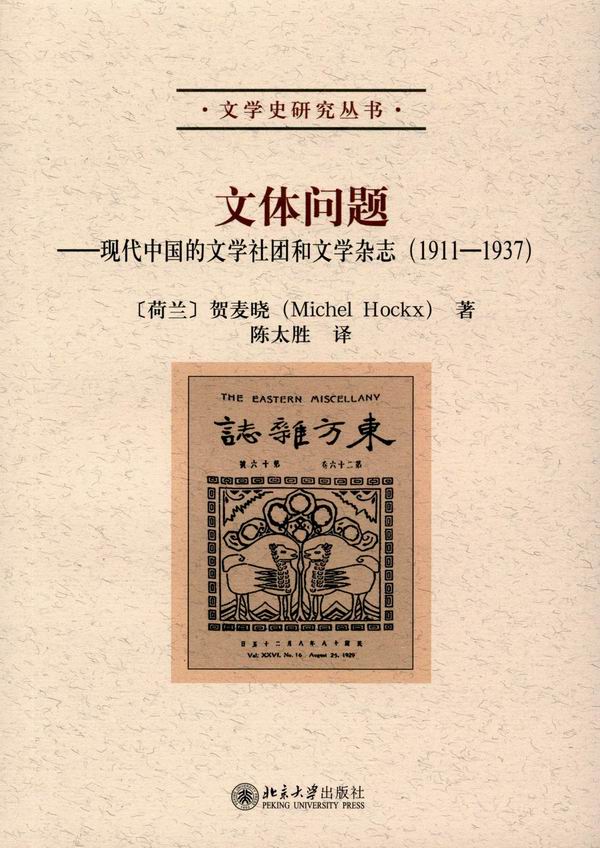
首先,何谓“文体问题”?“文体”(style)作为该书的核心概念远远超出了常见的文体学范畴,它“指的不仅仅是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像在社团中)和发表方式(像在杂志中)的聚合物。我相信,这些聚合物,常常可以从民国时期文学共同体的成员中辨认出来,而且也是差异形成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中,我认为,文体这个概念比其他任何尝试区分文体的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概念都更具实用性”。作者解释说,支持如此使用“文体”这个概念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文学社会学),还有在中国传统中“文体”和“体”的术语使用以及在民国语言中这两个概念所带有的清晰的社会意义(14页)。

作者承认是布迪厄的“习性”(habitus)概念启发了他,只是没有使用“习性”而是选择了更能适应研究材料的“文体”这个术语(13页)。我们知道在布迪厄那里,“习性”这个从“文学场”中衍生出来的概念含有感觉、认知、判断和行动之意,是对个体如何进入“社会化”的文学实践的浓缩。在“文体”这个概念背后,作者最终提出和试图解决的真正“问题”是:“中国现代的文学共同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如何保持自身同别的共同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成员内部存在的差异?”(第1页)与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论相比,以“文体”作为核心问题和论述视角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使文本分析、个人生活方式、文学体制和社会场域多重研究融为一体,在文学与社会学之间建立起坚实的联系。
其次,作者对研究范式转换的理解使“文体问题”的重要性更显突出。与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研究的批判性反思不同,该书的主旨并非重新质疑“五四”传统在所谓的经典化进程中被赋予的主导性地位,因为在作者看来这种研究只是具有重要的知识贡献但没有导致研究范式的转换。“简而言之,到了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抛弃‘五四’范式的时候了”(第5页),目的是从严谨的历史视角出发,描述和分析文学创作与接受进程,让真实的文学实践及其社会生产图景呈现出来。这里涉及对“五四”传统叙事的认识问题,作者显然无意于作简单化的反对或辩护,而是以其对“文体问题”的研究作为走出“五四思维”的范式转换实践。
在我看来,上述关于“文体问题”的两个层面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文史研究中具有更为普遍性的范式意义。在“文体问题”之下,发挥着体制功能的文学社团和传播其成果的文学杂志互为表里,共同构筑着一个多元、竞争、变化和持续性的文学共同体。同时,上述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中,传统的文学惯例和价值仍然广泛存在。

对关注现代文学场域中的政治性因素的读者来说,该书第六和第七章分别从文学批评与出版审查制度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角度。从流行于民国文坛的“骂”中,作者既注意到像西式表达符号作为工具这样的细节(207页),更从整体上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尽管1930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是紧张和两极分化的,但在所有这些论争中,政治只起到了微弱的作用,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个非凡的文学场地理论和威望,它可以容纳这么多不同的文体和立场。”(233页)而在第七章“写作的力量:审查制度和文学价值的建立”中,作者关注的是关于文学的基本价值和信仰如何使文学共同体直接对抗国民党政府在1930年代推行的政治压迫,结论是那场有时被称为“文化围剿”的运动一再被文学法则所挫败,整个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仍然是高度独立的(261页)。
导致这些研究结论的,正是得益于在“文体问题”之中对文学共同体内部及其外部关系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作者尚未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这种范式转换中上升到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视野,如何以重返历史现场的现代文学的整体书写回应起承转合式的“大叙事”告退后的框架空白。当然这并非本书所能承担的任务,而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必须突破的瓶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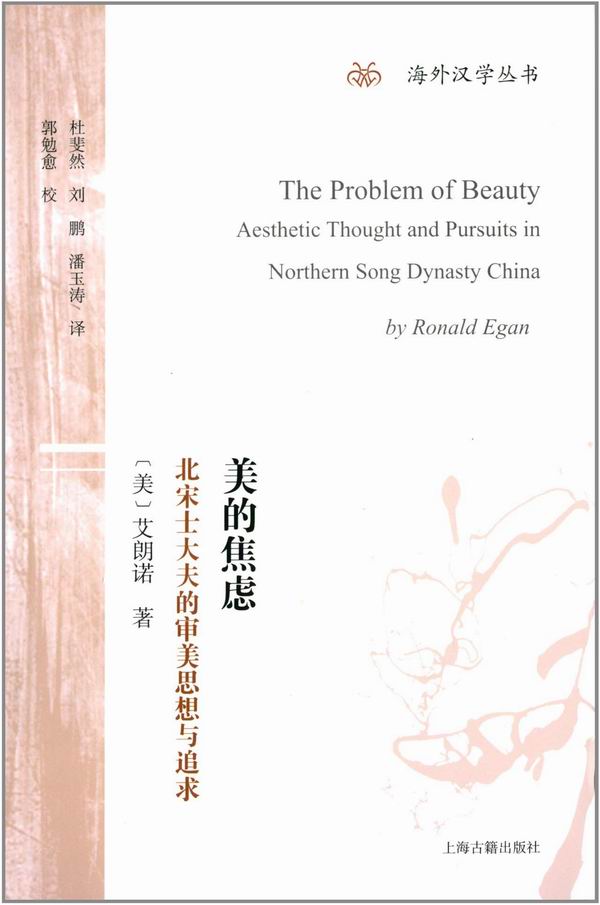
虽然作者没有表现出对社会学方法的明确运用和对“文体问题”的自觉关注,但是对宋代社会形态的变化、各阶层审美兴趣的转移、文人个人的才情与性格等因素所导致的审美需求共性与差异性等等议题的论述,尤其是对如诗话、鉴赏文、文评家对词的激烈争议等议题的深入分析,以及最后“结论”一章题为“社会阶层、市场和性别中的审美”,都时隐时现地呈现出进入“文学场”的研究旨趣。
读完全书,读者不难感受到所谓“美的焦虑”根源于审美转型中遭遇的种种外在压抑与内在矛盾,而北宋士大夫对审美价值和个人趣味的坚信促使他们“敢于挣脱教条的束缚,勉力给出一个说法以自辩”(第3页),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史上有点激动人心的一章。
点击下方链接,阅读李公明的“一周书记”系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