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黄灯:文化复苏会激发年轻人对家乡的认同
2016年年初,黄灯突然火了。
她在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中,将丈夫出生成长的丰三村置于文字的手术刀下,冷静克制地进行剖析。这篇文章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也成为了谈论“返乡书写”时一个不可绕开的标志性事件。黄灯说那篇文章之后,很多出版社找到她,想帮她出书。而十年之前,她想出版书无人问津。
新媒体的热闹喧腾只呈现了部分事实:一个文学博士,因为一篇爆红的文章,得到了出版社的一纸合约,于一年之后交出了一份书稿《大地上的亲人》,分别描绘黄灯嫁入、成长以及出生的丰三村、凤形村和隘口村三个村庄里,老中青三代人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城乡转型大背景之下复杂的个体命运图景。
这样一个线性逻辑链条中暗含着一种简单粗暴且看似容易复制的成功学:一夜爆红,然后机会纷至沓来。如今在媒体上出现,很多时候黄灯的头衔都是《乡村图景》一文的作者,她的身份被大众媒体变得扁平化、标签化。在大众媒体的呈现中,她是一个生在农村,后来通过接受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女博士,但这却忽略了黄灯1990年代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忽略了她是一个持续而且长久的写作者,也忽略了她根植于自身经验的乡村思考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

黄灯很清楚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作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黄灯表示,对像自己这样的写作者而言,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要辩证地看待媒体,肯定是有利有弊。以前没人关注我,我的很多想法别人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关注我,但是很多人也会质疑我,但这些我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一个东西一旦传播开来,就属于公共产品。你有辩解的权利,但是别人也有质疑的权利,这个是正常的,是一个公共化了的产品的交流过程。”
而在《黄灯的自我追问:“返乡书写”不是在消费农村》一文中,黄灯对于新媒体以及当下的乡村书写的形式给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毕竟以流量、点击率为衡量标准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同商业运作有更深的渗透关系,在便捷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陷阱。对写作者和读者而言,如何呵护彼此之间的诚信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黄灯的这本《大地上的亲人》,对于中国的乡村图景给出更为全面、更为复杂的思考。黄灯说面对这些问题,自己不是医生,充其量也只是个写病历的人。“我尽管没有办法提出结论性的东西,但是我尽量用社会学的方法,用人类学的眼光,用文学的笔法,把我所看到的、理解到的人的那种转型期的状况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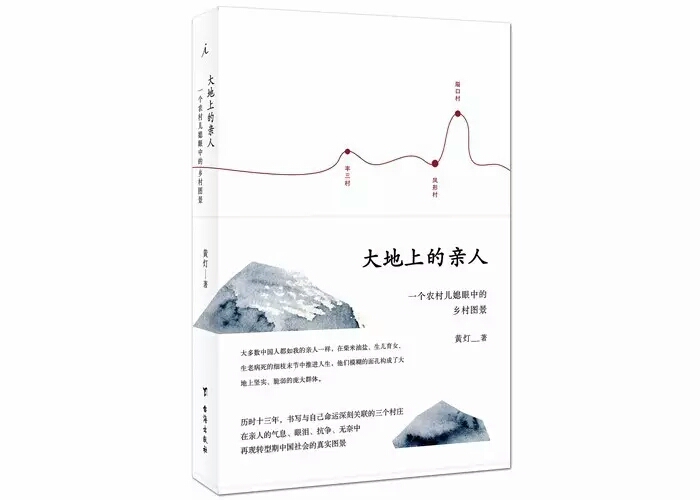
亲人们的生活值得被记录
澎湃新闻:《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中多次提到,书写亲人的想法差不多从2003年就开始酝酿,并且有一些章节也已经公开发表过了,能否谈谈写作初衷?
黄灯:那个时候还没有写一本书的愿望,但当时我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细节》,不是专门写农村的,那个书没有出版也没有发表。博士期间我跟我在广州工作的很多亲人联系很多,那时候就打算写一本书专门写他们,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我的亲人在广州》。当时我只打算写一个村子,就是我出生的凤形村,但这本书的架构是三个村子,所以就没办法把凤形村写得很详细,当时的很多访谈资料也没用上。至于为什么要写他们,就是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被更多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有被记录的意义的,就是这种初衷。
澎湃新闻:写和亲人相关的题材其实很需要勇气,在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黄灯:我并不是突然要写一本书,就强化地、密集地去采访他们,平时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会和他们聊天,问他们生活的一些情况。我一般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材料,我不会让他们觉得我是在采访,那样他们会觉得特别别扭,会觉得不自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澎湃新闻:之后要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吗?
黄灯:我会跟他们说,特别是涉及到一些负面的,我都问他们要不要紧。尤其是我那个吸毒的表弟。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他老婆也很喜欢他,不存在对他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而且他的小孩都知道,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我跟他们说我打算写一本书,他们说,“那我也可以被你写进去啊”。这些比我小十来岁的小表弟和小堂弟在过年的时候就坐在桌子旁边讲他们的故事。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会被书写,所以就讲得很仔细,从童年开始讲起。
文学的眼神是温柔的,脆弱的
澎湃新闻:媒体传播带来的影响中,可能作为表达者、书写者、在主流知识分子话语中的你,从中获得的要比在家乡的亲人多,如何对待和处理这样的问题?
黄灯:我在写的时候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我大部分的写作、耗费我更多精力的写作是默默无闻的,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被关注之后,确实带来很多东西。至少知名度高了,我的书不愁出版了。以前我写再多的东西没人主动跟我约稿,现在是抢着出版。那我确实比他们获益更多。但我觉得写作行径本来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后果和结果,这应该是属于一次书写行为的后续。如果这么说,作家就不该成名,成名了就是有道德罪恶感的,因为一旦成名,你的书好卖了,你就有更多的钱,这个逻辑我不太能接受。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经常提到写作中的痛苦,要怎么排解?
黄灯:这个也没什么排解的,因为文字有疗愈作用,写作过程本身就会排解很多东西。就像流眼泪一样,很伤心的时候,哭一场就好了。内心的很多困惑,通过文字的梳理,说不定就清晰了,内心说不定就舒服了。写作其实是很有快感的,尤其是愿意写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那就是一种很隐秘的快乐。别人也许会觉得你很苦,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以前写的东西也不发表,也不进入公共流通领域,那我为什么还要写呢?那肯定是为了快乐,我有大量这样的文字。就是不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不当做公共产品的,就是我私人的写作。所以写作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闻:文学在这种类型的写作中会提供什么样的养分?
黄灯:文学肯定是很有用的,至少文学不强势,像经济学这种工具性比较强的学科其实是很强势的。文学的眼神是很温柔的,很脆弱的,它关注的是人内心很隐秘、很幽暗的东西。一个人本身选择文学就跟他的性格有关系,这一点在呈现这类题材的时候是天然的,因为它打动的是人的情感,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命运的那种很细微的转变过程,它并不提供结论性的东西。

农村有足够的空间和能量可以释放
澎湃新闻:书中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从一个点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延伸开,涉及到了几乎当下中国乡村中各个年龄层的人面临的问题:社交媒体在农村的盛行、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以及留守儿童、彩礼问题、赌博等等,你写的三个村庄可以说构成了很全面的人类学样本,而它们的对比又充分展示了乡村图景的复杂性。书中最后的落脚点在乡村建设上。因此该如何看待当下乡村中经济和文化二者的关系?
黄灯: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在问自己,隘口村之所以文化很容易复苏,是和它的经济基础有关的。更重要的是,前面两个村庄是没有那种文化根基的。隘口村在十年以前是很麻烦的,但是现在慢慢地,这些人的元气在恢复,恰好是这些文化产品和文化习俗在修复它。所以从纵向的角度来说,在那样的空间范围内它是有效的文化复苏还是有用的,因为文化的东西会有巨大的力量,它那种原始的生命力和对家族的认同感,会激发年轻人最原始的东西——对家乡的认同、和亲人共命运的感觉。
澎湃新闻:说到乡村建设,这也是中国的农村研究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
黄灯:乡村建设在中国始终在进行,但是面目不是说特别清晰。它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东西,但是它的实践性特别强,它也是慢慢渗透的,我觉得与其说做乡村建设,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观念的传达,它让更多的人明白有一群人在实践。我觉得这本身就很有意义。说实话乡村建设的力量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很多问题确实需要通过更大层面的资源分配才能实现,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的修复行为,它会带领一帮读书人重新走向田地,走到基层去做事情。只要有这种行动,就会有新的可能,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因为它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资源。他们哪怕没有成功,我觉得这种实践也是很伟大的。
澎湃新闻:忽略现实的限制,能否谈谈你理想中的乡村图景是什么样的?
黄灯:理想的状态就是每个人付出了他的劳动,就能够在社会上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比如知识界付出了知识就应该有相应的回报,而不是说那些爱赌的人、胆子大的人、敢利用社会资源的人、敢掠夺别人的人就过得好。我希望每一个人有自己内心安定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付出,社会反馈给他相应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应该提供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澎湃新闻:到时候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黄灯:农村和城市应该是互补,一个社会有活力是因为它有弹性。农村就是一个弹簧最柔软的、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它有足够的空间和足够的能量可以释放。做一点算一点,把困境呈现出来就是美好开端的第一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