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书城》专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英国男人的爱情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是可谓争议小王子的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因其中露骨的性描写与直接粗暴的诅咒与脏话,一九二八年一经发表便引来争议,在各国都遭到禁令。最初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独立印刷,一九六〇年才在英国发行。但出版商企鹅图书遭到新出台的猥亵法案的控告,是年十一月才获得无罪判决。

尽管劳伦斯在世之时屡遭官司和封禁,此书日后却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小说以一座英国乡村庄园为坐标,讲述贵族青年克里夫·查泰莱爵士(Clifford Chatterly)在一战中负伤瘫痪后,与新婚太太康斯坦丝(Constance)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及康斯坦丝与园丁奥立佛·梅勒斯(Oliver Mellors)之间的情感与觉醒。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劳伦斯不仅着重描绘个人情感,也反思他们所处的体制:小说刻意写到两人如何申请离婚,离开庄园后在更广阔的现实生活中共同面对的社会生活。
在之后的各式影视改编中,个人最中意的是并不被影评人叫好的一九八一年电影版:热爱文学创作也具有文艺气质的英国演员谢恩·布莱恩特(Shane Briant)将在一战中负伤而残疾的年轻爵爷克里夫的英俊和病态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小说中的庄园也在改拍过多部情色文学作品的法国导演贾斯特·杰克金(Just Jaeckin)的镜头中显得古朴而苍凉。其他版本,尤其法国导演帕斯卡·费兰(Pascale Ferrand)二〇〇六年的凯撒奖获奖版本,则重在描绘查泰莱夫人康斯坦丝的个人解放;而在一九八一年的版本中,查泰莱爵士的内心世界似乎得到更丰富的诠释。
从赋闲乡野到都市精进:绅士标准的变迁
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对维多利亚至乔治五世时期的男性气质有精确的捕捉。维多利亚时期伊始,社会结构开始改变,固有世袭贵族制度变得松散,城市新贵有晋升可能。绅士成为一种道德品质和社会规则,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出身头衔。

“绅士”在社会中的泛化使其标准更为可及:曾经在公共话语中不出现的有了明细的规则。譬如经典小说《简爱》中的男性角色——牧师、商人、医生、教师——都并非绅士阶层出身,但他们都以绅士为教养,也以此自居。到了乔治五世时期,也就是劳伦斯写作的时候,中产阶级更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绅士”也被赋予新的意涵:努力、上进、有社会和家庭责任感。这与绅士阶层本身的属性相悖:传统贵族并不工作,甚至鄙视职业,认为那太中产阶级。如果大家看过《唐顿庄园》,可能还记得第一季中老夫人对身为律师的爵位继承人马修的质疑:
马修:“我平时会继续工作,周末来打理庄园。”
老夫人:“呃……周末是什么?”
剧中马修向大小姐玛丽推荐管理庄园的新招时,也有多次提到“I hope it’s not too middle-class…”(希望我的做法没有太中产阶级)。马修作为唐顿的穷亲戚,已经脱离乡村贵族成为伦敦新兴中产的一员(律师),因此在最初来到唐顿时常提出有悖传统习俗的观点。对唐顿的主人传统士绅阶层而言,赋闲是美德,不能具有劳薪之味。但中产阶级改变士绅的定义时,也通过他们的勤劳努力改变了这一点。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成书之时,阶层鸿沟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思和挑战。
劳工阶层的生命力
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的英国工党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大选中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并在一九二四年首次执政。因此贵族夫人康斯坦丝与附属庄园的劳工奥立佛(Oliver Mellors)之间的情感,也可看作是对社会变动的一种回应,既提醒人们既有阶层问题的禁忌,也对劳工阶层的生命力和能动性赋予想象。
劳伦斯本人便是劳工、中产阶层能动性的代表。他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曾是教师,但后来因为家庭拮据而在工厂做工。劳伦斯天资聪颖,在学校时曾是首位郡议会奖学金(County Council scholarship)的获得者。在农场打工时与农场少爷结下友情,得以进入他们的私人图书馆,大量阅读书籍,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基础。一九〇八年,劳伦斯从诺丁汉大学毕业,获取教师资格,已经依靠自身努力和种种机缘跳出了阶级的局限。相比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诸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伊夫林·沃等等,都出身上流社会,劳伦斯的经历也代表了英国教育和生产等社会机制的改变。因此可以看出,劳伦斯本人就经历了阶层流动的过程,既能通过机遇和努力改变背景,又对其中的不公正有切身体会。

在《唐顿庄园》中也提到工党的形成,但没有给予太多正面描写。相反,在同样描写贵族及“楼下”家仆的英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1970)中,则对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期的工党和保守党中的左翼有了更立体的描绘。尽管上流社会认为秘书等的社会出身及地位低下,该剧的主角贝爵士(Lord Bellamy)依然敬重女秘书的专业精神与品格,并告诫游手好闲、眼高手低的儿子:“你根本配不上她。”
瘫痪的精英:逐渐变迁的阶层
爵爷从战场回归庄园之后,似乎就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和生机(哪怕没有残废),所有生活都在庄园内。这种男性的内向性显得过时,因为外界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
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另一层社会语境:一战对英国精英阶层的摧毁。战争时贵族须最先投身,这也与中世纪制度中骑士必须效忠领主的传统一脉相承。一战的直接作战方法葬送了大批将士,其中有参战义务的贵族男丁的死亡率,几乎是其他士兵的两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自从血洗南北英格兰的玫瑰战争以来,贵族死亡数量最大的事件,在民间也被称为英国贵族的大屠杀。因此瘫痪和阳痿(一蹶不振)的不只是那位年轻爵爷,还有一整个精英阶层。
战争凸显了英国男性贵族的传统责任,这在二〇一一年的英剧《楼上楼下》(1970年代英剧的续拍)中也有提及:全副戎装的肯特公爵颤抖但坚决地说“我的兄长、英国国王决定加入战争……我们都对国家有义务,我的义务是为它而战”,而那已是二战。前几年大红的英国影片《国王的演讲》(King’s Speech,2010)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小口吃的乔治六世在兄长退位后被迫担起重担,反复练习演讲,以在战时鼓舞士气,因自觉国家责任深重。但可惜的是二战之后这种责任感被消耗殆尽,今天的许多上流社会空余傲气和势力,而少了责任与天下。饱受诟病的布灵顿俱乐部(Burlington Club)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牛津大学精英俱乐部以奢华与排外著名,前任首相卡梅伦与现任外长约翰逊都曾是其中一员。舞台剧《喧嚣贵族》(Riot Club,2014)及同名电影写到该俱乐部成员如何花天酒地并肆意破坏小酒馆、侮辱伤害酒馆老板及侍应,且因为家庭地位及社会关系,无需承担责任。在英国电影院观看此片时,一半观众中途起立、退场,以示愤慨。
男性气质与克己复礼的情感
一九八一年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对克里夫的情感也有细腻的描绘。对情感的自我控制是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品格之一。流露情感被认为俗不可耐,“自然”——包括人类情感和欲望——都需加以节制和修正。有学者认为这与以达尔文为首的科学家有关:科学的发展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对自身与自然“同流合污”的地位感到不安。人之精贵高雅有礼有节,怎会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丁尼生男爵(Alfred Tennyson)有诗道:
我们总希望有生之物
在死后生命也不止熄,
这莫非是来自我们心底——
灵魂中最像上帝之处?
上帝和自然是否有冲突?
因为自然给予的全是噩梦,
她似乎仅仅关心物种,
而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在乎。
(悼念集之五五)
因此,必须冶炼和升华人性,以对抗自然之粗鄙。一九八一年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剧中多次描绘克里夫留意到康斯坦丝的失落,但并未走近安慰,而是故作轻快和不经意地掩饰。
追寻抗拒既有秩序的生命之流与男性现代主义
克里夫的清俊冷淡与猎场看守人奥立佛的野性恰好相反,这种灵与肉的对比,在更早期的英国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也有体现:苍白的小绅士埃德加对比野兽般的希斯克利夫,二〇一一年的电影改编中对此更有直接的表现。劳伦斯终生致力描绘劳工阶层英雄的生命力,也抗拒了传统英国社会对情感和本能的节制。
劳伦斯笔下随时代逐渐茁壮丰满的劳工阶层英雄(working-class hero)形象不但体现在肢体上,更体现在精神上。许多人认为劳伦斯本质化了劳工阶层,但实际上劳伦斯在其他小说中也致力于体现劳工阶层的柔韧性:比如在小说《亚伦杖》(Aaron’ Rod,1922)中,才华横溢的矿工在佛罗伦萨得到教育和社交机会,能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平等地谈论艺术、政治与哲学。因此他并不认为阶层与出身能决定智力和能力,关键在于公平的机遇。更为可贵的是劳伦斯周游世界,试图寻找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外的人性光辉,以及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何能够带给人类社会不同的未来。在小说《羽蛇》(The Plumed Serpent,1926)中,描绘了墨西哥革命者。非基督教的文明在劳伦斯的时代仍然常被认为是异端,劳伦斯的追寻也象征了对西方主流文化的挑战。
但另一方面,批评家也质疑劳伦斯小说中的性别角度。一战也是英国女性运动兴盛的阶段。战争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社会习俗,女性得以穿裤装。女性参政运动也在一战后兴起,被认为是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电影《女性参政论者》(The Suffragettes)对当时运动的情况有生动表现。劳伦斯肯定了女权运动的成功,但认为这些运动将女人变成了“暴君”;认为“本该属于男人的活动由女人承担,会造成女性对自己青春的可怕摧毁”,从而“从根本上摧毁男人”。劳伦斯的性别观念一直颇受争议。一方面他认可女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他笔下的女性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力和把握命运的权力;另一方面女性又契合男性气质和生命力,似乎在英国现代性的建构中仅仅起到辅助作用。
改变与矜傲的坚持
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的审判,也标志着第一个英语文学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力量和乔治·奥威尔笔下那些“冠冕堂皇的统治者”的卫道士之间的道德战争。同时期有关人权与自由的司法斗争还包括同性恋与堕胎的合法化、死刑的废除、离婚法的改革、戏剧审查。御用大法官/皇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iner QC,1964-1970年的英国工党大法官)的判决向世人宣告,对自由的合法诉求是可以通过机制性抗议达到的。更重要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案件胜利的关键也在企鹅出版社愿意以低价出售,使得普通妇女和劳工阶层也能购得此书。这一做法也使得文学变得更亲近大众,因此劳伦斯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所描绘的文学世界对自由禁锢的抗争,也在于在现实世界中推动司法、阶层和其他社会机制的进步。
但改变有时来得抽丝剥茧,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自矜和克制依然是相对习惯,也使得英国人常有情感疏离、无法接近的口碑——有时加上固执。而劳伦斯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不断逐渐消亡的生活方式和旧秩序。如同一九八一年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剧中的结局:查泰莱爵士眼看爱人随人远去,悲愤却依然矜持高傲,只有在苍凉空旷的领土上回响沉默的心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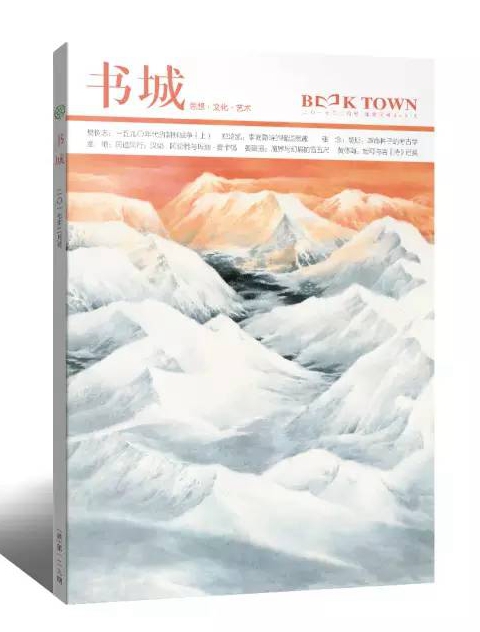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