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实现共同富裕:西方不同时代的财富观
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就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主张。西方社会的财富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演变。一些典型的财富观及政策主张,对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选择或有启发,现作简单梳理。
西方财富观:从古代到市场经济不同时期的总体看法
关于“财富”,古希腊的柏拉图早有相关的阐述。“拥有财富能大大帮助一个人不欺骗任何人(即使是无意地欺骗)或对他不忠实,不亏欠神任何祭祀或亏欠人任何钱财——这些都会使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害怕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是柏拉图《理想国》中谈及的财富最大功能。
关于“财富”,经济思想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什么是财富,有的简单地将“财富”理解为能够买卖的东西,所代表的财富的多少是用它们在市场上能换的钱数来计量的。“财富”另有一种比较广义且大不相同的用法,就是把财富看成和人类的幸福是一回事。财富来自何处,有重农主义的主张,有重商主义的观点,不同的认识,决定了不同的财富观,决定了不同的公共政策主张。
1559-1715年,欧洲依据远谈不上富裕的小康社会的社会特征,制定了很多政策。在当时,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财富分配同样非常不均。实际上,财富几乎没有得到分配。欧洲各地的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不断拉大。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经济上实行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它们的重商主义政策,充分表现了16和17世纪欧洲财富匮乏的时代特色。16和17世纪的作家构想的理想社会也都能看到奴隶和仆人的影子。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描绘了一个经济上实行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仍然有一个奴隶阶层,来干脏活累活。可见,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无所谓共同富裕观。
西方国家通常不直接提“共同富裕”,一般都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这样,只要是发达国家,公平问题处理地较好,我们就把这样的国家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效果比较好的国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的主流,国家干预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国家甚至被当成“必要的邪恶”。这样,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就是由市场决定的。即使是不合理的分配状况,一般认为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改变。有这样的理论认识,就有相应的政策实践。总之,在这样的认识下,国家基本上不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爆发和工人阶级的觉醒,统治者开始采取一些社会政策对工人阶级进行安抚。在19世纪晚期,德国开始探索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29-1933年大萧条的发生,更是催生社会福利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逐渐成为潮流,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成为西方国家公平的典范。累进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成为西方国家的标配。累进所得税税率达到畸高的水平,遗产税和赠予税也采取累进的征税办法。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方面福利国家病逐渐被意识到,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特别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经济自由主义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开始流行。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贫富差距问题得到更多人的重视,但是提高税率遭遇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一些本来应该用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的出台极为艰难。
亨利·乔治的观点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是美国人,主张征收单一地价税。写于1877年8月至1879年3月代表作《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阐述他的财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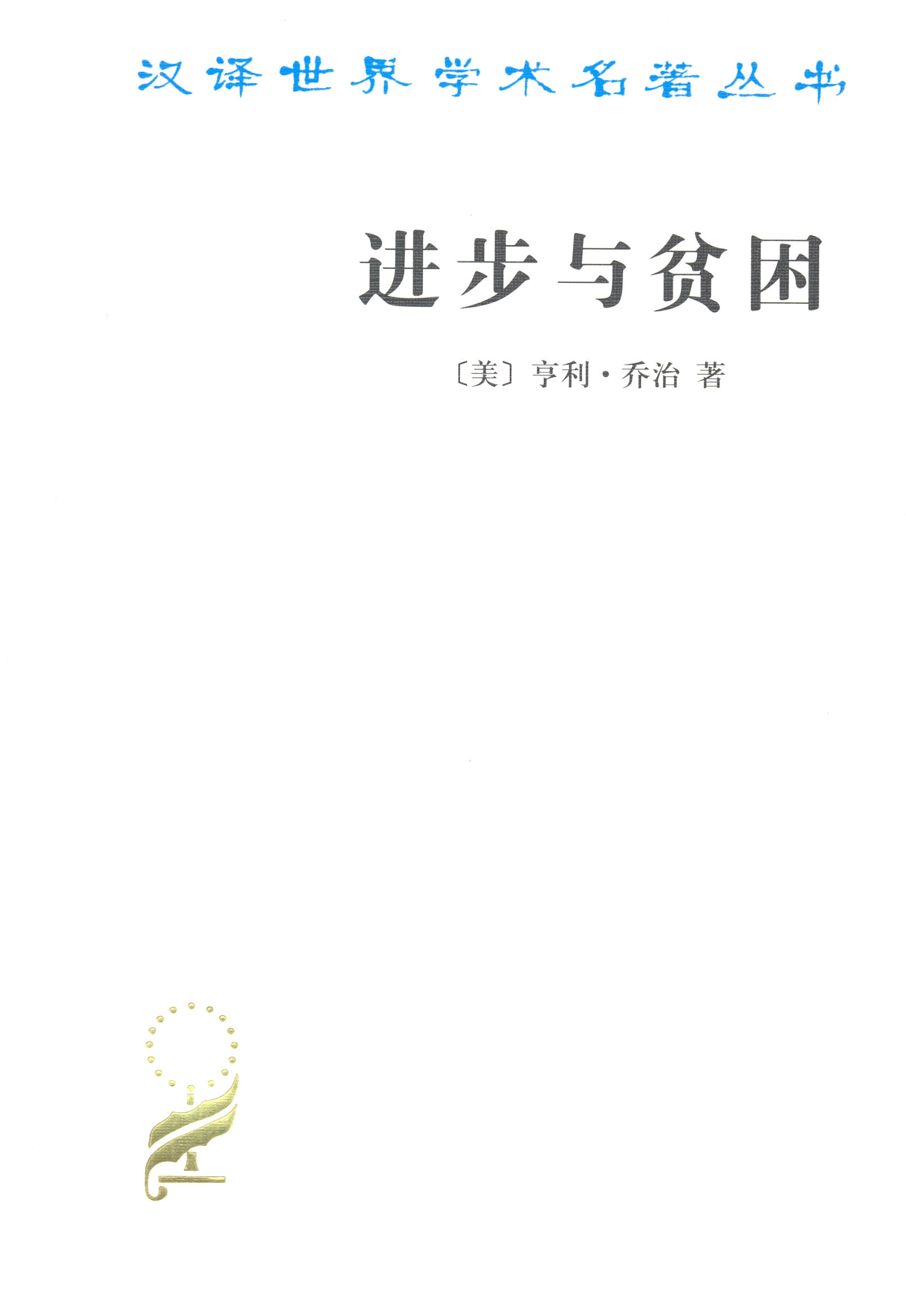
《进步与贫困》,亨利·乔治 著,吴良健、王翼龙 译,商务印书馆2012版
亨利·乔治指出,19世纪以生产财富能力的巨大增加为特征,期待生产财富能力的大幅提升势必让贫困消失,但是物质条件的丰富,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贫困与进步的这种形影相随是时代难解之谜。只要进步所带来的财富增加,增加的是个人巨额财产,让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也难以持久。贫困与物质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不能得到满意解释。答案必须到支配财富分配的规律中去寻找。
他认为,土地形式的私有财产是罪魁祸首。《进步与贫困》提出六种纠正方法:大幅度节约政府开支;让工人阶级得到较好教育,改进他们的勤俭习惯;工人联合起来,争取提高工资;劳动与资本的合作;政府的指导和干预;土地更普遍的分配。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让土地成为公有财产。
亨利·乔治的这种观点影响了中国人,包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与亨利·乔治密切相关。
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摆脱贫困,摆脱贫困、实现发展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费景汉(John C.H. Fei)、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1997年出版的《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从演进的视角探讨增长和发展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集中体现在就业和产出增长上。成功发展的“底线”,最终要看对减贫、收入分配调整、对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贡献。这一点也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概念区别之所在。随着经济的增长,长期收入分配会有什么变化的问题即相对贫困如何形成?贫困家庭比例会有什么变化,即绝对贫困会有什么变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试图作出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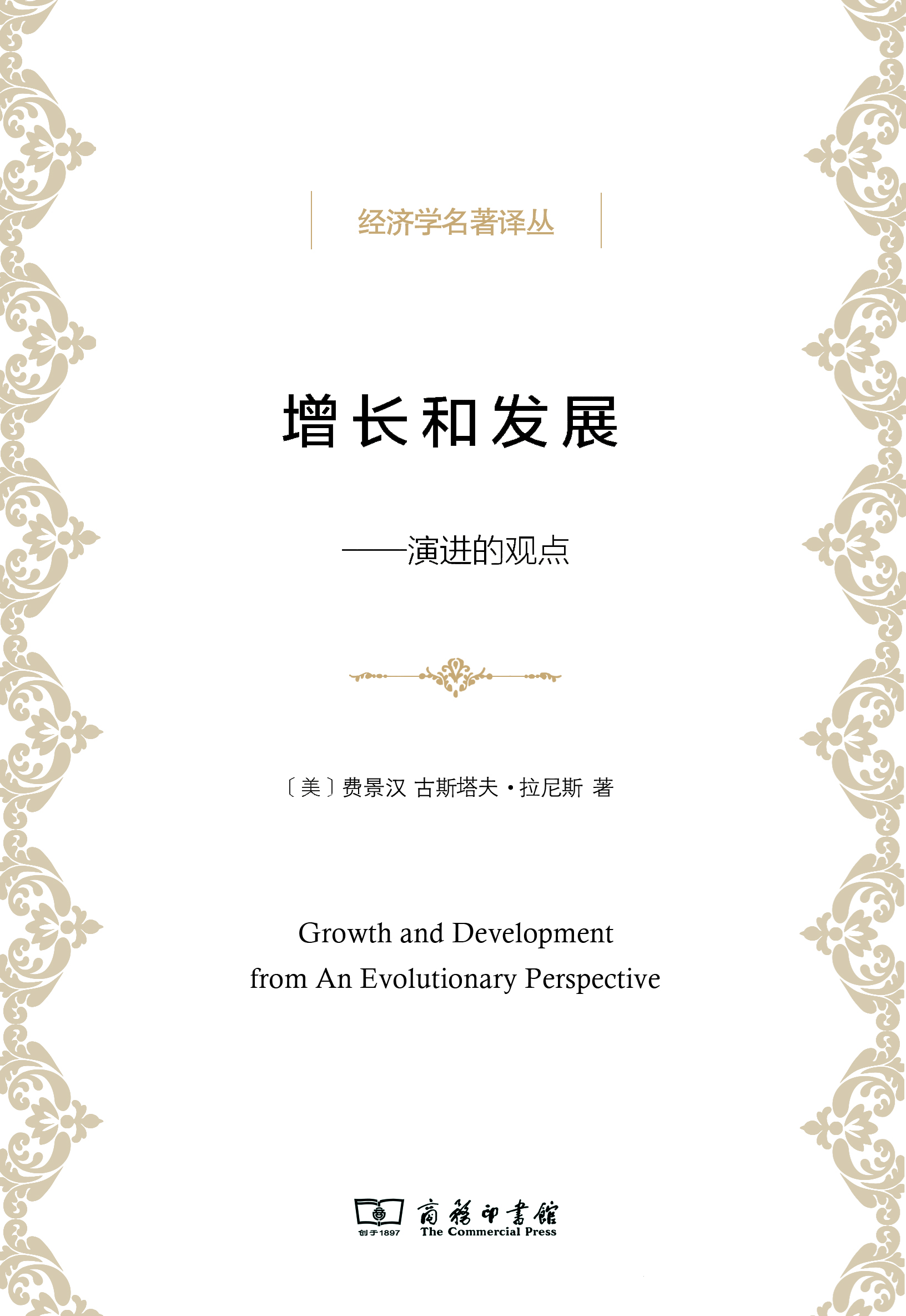
《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 著,洪银兴、郑江淮 译,商务印书馆2014版
他们认为,贫困可以用收入来衡量,可以用某些由私人及公共产品共同提供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缺乏来衡量,或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说,可以用某些“能力”实现来衡量。归根到底,真正重要的是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而不是他们的收入或消费状况如何。他们认为,仅仅以收入为基础来定义贫困的方法有一严重缺陷,即没有考虑到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饮用水的获得以及卫生的最低程度的支配权。仅仅依靠收入再分配也许不能确保穷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总之,实现发展,摆脱贫困,需要靠发展,尔后分配还必须超越收入,这反映了他们超越收入看待发展的观点。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的视角探究贫困的成因。他分析国际援助机构造成的扭曲,指出日本、德国靠贸易机会获得奇迹般的复苏和增长,但低收入国家农民获得国际援助的效果并不理想。他比较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指出前者的成功在于弥补了西欧经济复苏所需要的资本(战争摧毁大量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损害小得多),后者却对该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未起作用。各对外援助机构分配给受援国(欠发达国家)用于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和增强其市场作用的物资和资金太少,促进农业发展的资本缺乏。
总之,高收入国家为帮助低收入国家提高经济生产力所做的许多事情,主要有三大缺陷:
第一,没有优先考虑对人力资本,即对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人民的健康水平进行投资所导致的结果。
第二,各种对外援助附加社会改革条件。
第三,对市场作用的普遍存在偏见。
舒尔茨所讨论的是国际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但对一国内部的横向转移支付以及对口援助效率的改善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阿特金森的观点
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 1944-2017)是英国经济学家,生前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或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与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合著的研究生教材《公共经济学讲义》受到学界的普遍欢迎,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领军人物。
阿特金森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Inequality – What Can Be Done?)针对不平等,主张恢复更加累进的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征收全球企业最低税;主张人人享有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的设计,儿童津贴,基本收入,社会保险的复兴等方面的内容。他提出旨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15项建议。他认为,这些建议不可能都得到实施,但也不能只依赖一种建议。这些建议会不会导致蛋糕缩小?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但分配更公平的小蛋糕可能要好于以当前的不平等份额分配的大蛋糕;有些建议可能导致蛋糕缩小,有些建议可能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指向同一方向,公平和效率之间可能具有互补性。
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他不认为全球化会阻碍行动,福利国家制度正是起源于19世纪全球化早期的欧洲,指出全球化会有相反的反应令人费解,而且面对世界新情况,各国并非完全消极被动。他认为,把当今的高度不平等状况归咎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是不对的,将之归咎于全球化同样毫无依据。他对国际合作的潜力持温和的乐观态度。他认为,应当把欧洲推出社会福利方案视为实现经济目标的补充,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
21世纪负担不起福利国家制度?对此,他认为,全球化降低了福利国家制度增加税收收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缩小或者不扩大福利国家制度,私人供给将增加。如果政府不提供帮助,那么个人将求助于私人部门。他指出,对社会支出的需求会得到市场的满足,如果放弃公共支出,私人支出会取而代之。这种论证很有意思,相关成本将转由雇主或家庭承担。雇主成本提高,降低竞争力,与提高税收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雇员自己承担,那么由于实得工资减少,这很可能带来涨工资的诉求。
所以,国家提供转向私人提供对经济的影响,要看用哪个渠道更有效率。私人社会支出的增加,往往会带来税式支出。社会支出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是无法解决各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财政问题。
21世纪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全球失衡带来挑战,仍然有应对办法,只要愿意用当今的更多财富来应对,并相信应当更加公平地分享资源。他认为,不平等程度在历史上的降低,就是以政府的成功干预为基础的(虽然不是唯一因素)。政府计划的失败,是因为缺乏事前的周密计划和磋商。
皮凯蒂的观点
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在其风靡全球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法文版2013年版,英文版2014年版)中,分析累进所得税的由来以及影响最高税率选择的因素,认为美国所发明的对过高收入的没收性税收(最高边际税率曾达到94%),因所带来的收入不多,目标不是要增加额外收入,而是要终结该类收入;巨额遗产的高税率也是要终结巨额遗产,政府未作出绝对禁止和征用的声明,走得是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通过企业公有制和设定高管薪酬的路。
他分析美国社会抱怨经济和金融精英为了自己致富而把国家推向破产,是累进税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他分析法国的类似情形,指出法国累进税制选择中也存在政治操纵因素。他比较法国、德国与美国的不同最高边际税率,指出美国税率总体上高于法国、德国。他认为,美国最高所得税税率后来的下降和最高收入的增长似乎都没有刺激生产率,或对生产率刺激不够。
皮凯蒂认为,最高收入80%以上的税率是可行的,但受政治程序操纵,不要说80%,就是40%以上都有点悬。他指出,关于对收入阶层中最高的0.5%或1%的群体课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实施起来比欧洲的小国容易。他和合作者对发达世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数据库的研究表明,飙升的高管薪酬可以很好地用讨价还价模型解释,较低的边际税率鼓励高管为了高薪拼命周旋,与假设的管理层生产率提升没有多少关系。这也进一步证明高税率只会降低高管薪酬,而不会影响生产率,同时这还对减少不平等有利。
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还对全球资本税的课征作了研究。他认为,社会国家和累进所得税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创新,在未来会继续扮演核心角色;21世纪需要创造新工具来应对挑战,即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辅以非常高的国际金融透明度,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和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
在皮凯蒂看来,全球资本税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是一种新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所设计的,需要全球财富的税收安排,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税收收入;从技术上看,欧洲财富税的征收不是问题;对于私人资本及其回报的永恒问题,资本税是一种较少暴力且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依赖私人产权和竞争力量的同时,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将以大众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资本税仅仅在一国课征有难度,但是资本税的替代者——其他监管方式不如资本税,有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比如保护主义和金融管制。
关于财富观和共同富裕(以解决不平等问题为代表)的文献汗牛充栋,显然不是几种观点所能概括的。这里只是聚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的描绘给人们以信心,即收入差距先随经济增长而扩大,到达顶点后又会随之缩小,但近年来针对倒U型曲线能否成立,又有相关研究。库兹涅茨波浪是对经济增长中的多个倒U型曲线的形象描述,这也说明库兹涅茨的研究还需要结合新情况作进一步优化。财富观的变化背后既有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变化,也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影响社会观念的因素很多,这也是分析财富观需要关注 。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本文是“实现共同富裕”系列文章之三,系在作者发表于2021年第6期《财经智库》的《财富观、共同财富与公共政策》一文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