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为一朵“木兰花”:我的木兰游戏剧场体验与个人史的社会性
在一家社工机构的志愿者微信群里,我看到了“木兰的故事”——基层流动女性叙事展演的推荐,这样的主题在充满后工业时尚感的798展览推介中显得独树一格,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通知时间较晚,参与游戏剧场的名额已满无法再报名。我原本打算只去看看展览。由于当天的报名者中有人未能到场,我十分幸运地获得了替补参与演出的资格,有机会通过这个大胆而真诚的项目,短暂地体验流动女工的生命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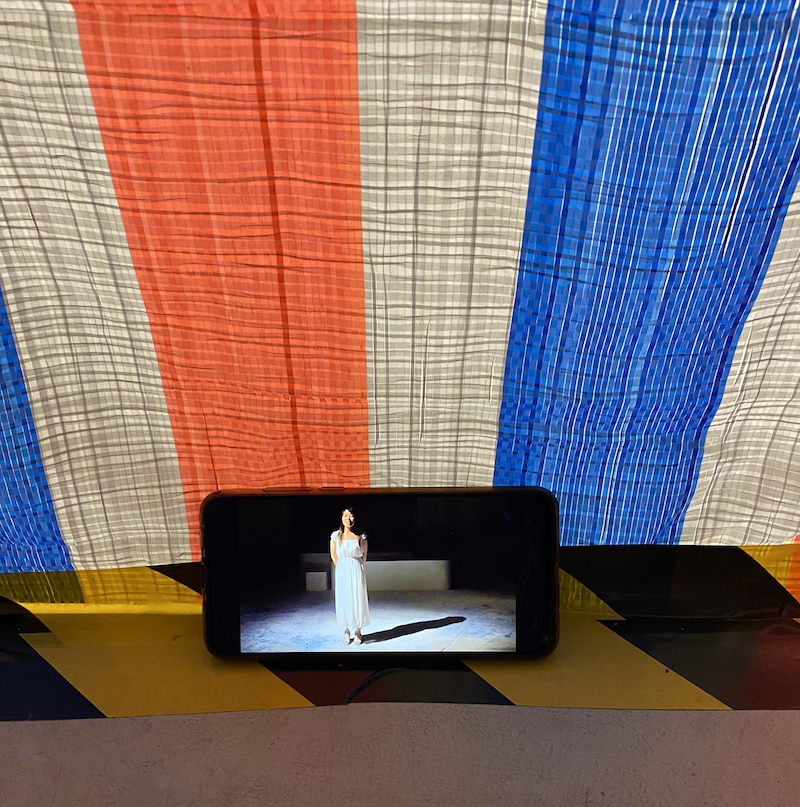
“木兰的故事”展览现场
从社区戏剧到游戏剧场
很多人知晓这次“木兰的故事”的项目策划赵志勇老师和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是从一部叫做《生育纪事》的戏剧作品。这部作品是由赵老师和“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共同完成的。赵老师将这部作品定位为“社区戏剧”。他认为,社区戏剧与一般参与式戏剧的区别在于,在社区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职业艺术家和非职业艺术家处于平等地位,演出具有“赋权”的功能,使得在社会结构中被压抑的人群能够在表演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形式上来看,这次“木兰的故事”游戏剧场回到了一般参与式戏剧的模式:“游戏规则”由编剧事先设定好,参与者并不期待为自己发声,而是来探索通过角色扮演,共情另一种人生境遇的可能性。不过,相较于一般参与式戏剧对美学体验方面的强调,“木兰的故事”依然保留了社区戏剧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意图。如果说《生育纪事》的参与性在于让身处城市边缘的流动女工成为表达的主体,与主流声音形成对话;“木兰的故事”的参与性则体现在让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反向地来到城市边缘,走近这些在为城市提供服务之外就几乎隐形于公众视野的女性,尝试理解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抗争。正如编剧佳静所说,她希望游戏剧场成为“帮助我们彼此链接,缩小理解的鸿沟”的媒介。
发声者不再是流动女工自己,仍然要让参与者尽可能身临其境地感受流动女工的生活处境,这有赖于主创团队多年来从事打工者聚居社区服务,以及亲身参与工人文艺创作所积累的真实素材。对我来说,“这是另一个人的人生”的旁观者心态只持续到播放第一道人生选择题的录音时。在这段录音中,“我”的一位学校老师要“我”每天下午抽出两个小时帮她照看孩子,她向“我”保证会帮“我”补上功课,并且告诉“我”,“我”是她最信任的学生,把孩子交给“我”,她最放心。这道选择题就是“我”是否愿意帮老师照看孩子,在做出不同的选择后,“我”的人生资源也将被相应增减。游戏模拟人生体验,我们只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却无法知道另一个选择将导向怎样的未来。这段录音让我在一瞬间理解,游戏中的“我”和真实的我自己,尽管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却曾经面临多么相似的纠结。
成为一朵“木兰花”
在游戏开始前,我们会抽取一张“初始装备”卡片,卡片上标示出此时“我”的学历、健康值、人际关系值和拥有财富的状态。这些“初始装备”值并非凭空编写,每张卡片的背后都是一位真实的流动女工的故事。“我”和她的人生开始于同样的起点,随着游戏的进行逐渐走上不同的轨道。
尽管在每次可以做出选择时都放弃掉一些其他的资源以继续学习,“我”依然没能读完高中,就以初中学历外出打工了,这将影响“我”未来可从事的工种。这个时候的“我”健康值尚可,而人际关系值已经所剩无几,我暗自决定,在接下来的选择中要偏向能够增加人际关系的选项了。
也许是出于对参与者普遍认知中的女工形象的预期,或者方便将所有人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游戏的实际考量,“我”和其他姐妹们的工作场所被选在一家位于南方的电子工厂。在这里,我们通过各种相当有难度的身体扭曲和团队配合实现“老板”的刁钻要求,并被鼓励以夸张有创意的肢体动作表现工作积极性从而获得额外加分。作为一个并不擅长外放式表达的人,我原本自认与加分无缘地随便喊着口号,直到在我身旁的姑娘眼中看到了同样“爱咋咋地”的光。我俩福至心灵,以抱团取暖的姿势得到了一个创意表达的意外加分。在所有的环节中,友伴关系都是暂时的,只有竞争关系贯穿始终。在经历了这一番折腾之后,从大家口中说出“异化”这样在书本上读来概念颇为复杂晦涩的词语,简直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

游戏现场
完成岗前培训后,“我”成为了一名质检员。初次上手“找不同”这项工作,身体里那个拥有硕士学历的我也并没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我”依然找到眼花也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我”要面临另一件人生大事的抉择了:远嫁或回家相亲。对于“我”来说,保持单身状态并不在选择的范围内。“我”选择了远嫁。和丈夫生了一个女娃后,“我”不想再要二胎,被夫家百般为难。“我”生完孩子之后的生活重心就转向了家庭,一面在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中分身乏术,一面消化丈夫“这点事都做不好”的困惑。还好我们都还愿意坦诚沟通,尝试彼此理解。
“我”出钱帮家里盖了房子,也实现了人际关系的提升。在游戏结束时,“我”是一个网店的老板,和父母、丈夫、孩子一起生活,没有多少钱,但所幸没有负债,命运的盲盒没有拆出太大的灾难,健康和人际关系值都比较高。系统判定,以一名流动女工的身份,“我”获得了幸福的生活。
“非典型”流动女工
在游戏的结尾,我得以阅读“借”我身份以度过这一个半小时的女工Y自述的真实经历。和“我”一样,她高中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了,不过并不在南方的大型电子产品工厂,而是在家乡所在城市的小型服装工厂。在结婚之后,她随丈夫一起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全职主妇。
比起“我”,Y的经历在“木兰花开”的姐妹们中间更加具有代表性。沈琴琴,张燕华(2010)发现,在2006年北京市农业人口普查中,70.9%的流动人口集中在第三产业,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流动人口分别仅占12.1%和14.8%。作为对比,2006年上海市流动人口中有54.1%从事第二产业,43.6%从事第三产业。这意味着,比起制造业工厂流水线,在北京的流动女工有更大可能从事家政、餐饮等服务行业。因此她们的生活往往并不围绕着工厂园区,在市里完成工作后,她们会回到自己的在五环外打工人聚居区租下的房间。赵志勇老师在与“木兰花开”的成员们交流时也发现,“她们大多是跟着老公来北京打工,生了孩子之后就只能回家做家务、带孩子。”这样看来,“木兰花开”的北京流动女工们,其实多少颠覆了我们对“女工”的刻板印象。她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正式工作,为照顾家庭,只能从事更加灵活,同时也更少福利保障的零工经济。她们的大量劳动付出是在家庭内部,劳动的价值不会体现为工资报酬。
在我对“木兰的故事”游戏剧场的记忆中,“工作”的内容占了一大半。在我看来,虽然工厂的制度中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这份工作依然是最能体现“我”的价值的所在,它使得“我”能够独自在异乡生活,也是“我”独立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底气。但在Y的叙述中,工作所占的篇幅是相当短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于是从第二次怀上孩子开始,她就不再出门工作。自述余下的大半内容,Y都在讲述她的婚姻。与“我”不同,Y没有远嫁,她和丈夫通过家人的介绍认识,很快便步入婚姻。Y讲述了自己与丈夫从起初的隔阂,到丈夫出轨,双方冷战,再到和好的整个过程。出于对对方的依赖、为孩子考虑或其他因素,期间Y始终不同意和丈夫离婚。
“我”远嫁他乡可以被视为对父母试图安排自己的人生的一种反抗,“我”自主选择了自己的配偶,但远嫁之后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与Y遵父母之命的婚姻并没有太大不同。那些“我”渴望逃离的桎梏,在接下来的生活中重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在游戏剧场中“我”的叙事框架下,父权制家庭的结构性压迫是相对外露的,我在游戏中可以感受到较为明显的不合理之处,“重男轻女”、“忽视再生产的价值”……我可以轻易为这些情节命名。但在Y的叙述中,家庭与社会的结构是相对模糊的,我更多看到的,是Y讲述她自己与丈夫的情感关系中的冲突、博弈与和解。或许在了解她们的故事之前,“流动女工”这一位于边缘之边缘的身份标签会让我们期待她们的故事中出现“压迫”、“抗争”这些关键词。Y经历了很多次艰难的时刻,但在她的叙述中,自己从来不是以一个被动的受害者的身份存在的,她反思自己,积极行动。Y的确以她的方式抗争了,抗争的目的是维系这段婚姻,保住自己的生活。这是Y以有限的人生资源能够为自己和孩子做出的最好的选择。“我们现在很好。”Y在接近结尾时写道。从这句看起来和系统给予“我”的评语“生活幸福”十分相像的总结中我读出的是,Y不是一个童话里等待幸福的公主,她是自己真实生活中的英雄。

展览现场
个人史的社会性
“木兰的故事”游戏剧场脱胎于“木兰花开”社区女工们的真实故事,同时又表现出建立关于“流动女工”的普遍化叙事的企图。剧场里的每一位“木兰花”,受到初始设置的原型人物与每位参与者的行为惯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可能性,但大体上,她是一位来自农村地区,到南方一家流水线大工厂打工,而后结婚、生育的女性。在这个框架之内,编剧最大可能地呈现了一位流动女工在成长、工作、家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境。流动女工面临选择的有限性(例如无法选择是否结婚、生育,只能选择与谁结婚)是我在游戏中获得的最深切的体会。从“我”与Y的人生经历对比中可以看出,这样淡化区域特征的叙事模式已经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木兰花开”姐妹们的真实经历。此外,夫妻共同在外地打工的设定,也无法体现出独自外出打工的已婚女性的生活境遇。由此便可以看出,“木兰的故事”项目的两个组成部分组成部分——游戏剧场和流动女工个人史展览——之间的互补性。个人史展览将“木兰花”的形象还原为一个一个真实的人物,在这里,地理的凹凸绵延、家庭组成形式的多样、不同人生阶段的感悟与愿望都得以显现。
“木兰花开”的公益艺术项目以丰富流动女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主要目标。犹记得在为我们进行导览时,“木兰花开”的创办人齐丽霞表示,希望通过参与文艺创作活动,流动女工们能够找到对自我的认同,不要在“母亲”、“女儿”等身份之中丢掉自己。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了解到,专注于文娱公益的“木兰花开”,并不试图打造分离于现实社会的乌托邦小团体,而是一直意在帮助流动女工认识社会、了解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积极融入社会,训练在主流话语体系中患上“失语症”的边缘人找到自己的语言。这种直指矛盾的锋利性,似乎是在非以工人为主要参与者的、商业化的文娱活动中难得见到的。由此来讲,参与这次“木兰的故事”活动,于我绝不是单向的了解,更不是居高临下式的猎奇,它反而成为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提出问题,质疑习以为常的阶序结构与观念的合理性。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授权转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