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妞妞》出版20年:那些紧紧抓住生命的孩子

上个月,学者周国平的畅销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发行了二十周年珍藏纪念版。
我还读书的时候,在北大曾有一场周国平的活动,我和同学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北大。到时天已全黑,我们踩着雪走到会场门口,却被告知校外人士没有资格进入会场。天寒地冻,我们一百多号慕名而来的“校外人士”仍执着而有序地维持着队形。等了四十多分钟,直到会场的门紧关。
五年的时间,从隔着一百人的队伍末端,到被熙攘的人群挤压到临近新书首发主持台;五年的时间,细细读过他的书,感觉不到那一刻的接近,而是与其更远的疏离。
这本二十周年纪念版的自序中,周国平絮絮地说起如何自处、说起时间和命运,谈到最后,才再次说到妞妞的事情:“我当然没有忘记妞妞,但我不想矫情地宣誓我自己仍坚守在二十几年前的悲痛之中,人不该和自己过不去,更不该装出和自己过不去的样子。人是卑微的,诸多身不由己的遭遇,诚实是卑微中的尊严。”
妞妞的确已经离开了太久。周国平在2016年写的自序中,谈佛论道,旁征博引,为时至今日的豁然找缘由,他最后说:“与不可解的难题和解,未尝不是一种觉悟。”我感受不到这些大道理的深味,只是有点伤怀地觉察到,他强打起一些精神,为了诉说而诉说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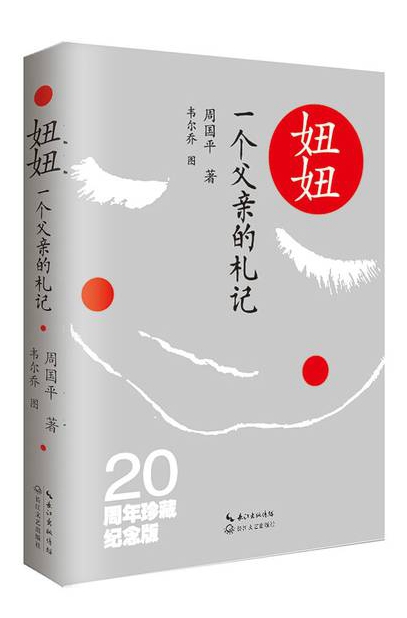
“我活着,妞妞却死了。我对妞妞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国平说。周国平在《因果无凭》一章中谈道,妻子雨儿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感冒发烧,去医院照了X光,这是导致后来妞妞患双眼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症结所在。
编剧蔡春猪谈到自闭症的儿子喜禾时说:“我在网上搜过:自闭症是一种先天脑部功能受损伤而引起的发展障碍。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就是‘先天’。‘先天’,这两个字对我特别重要,就像一个什么免死金牌之类的。有了‘先天’两个字,我就可以特别理所当然地说这句话,‘你看,我就说,儿子这样跟我带他没有任何关系的’。” “先天”二字让蔡春猪觉得庆幸,至少孩子变成这样不是因为自己没尽力。
去年年底刷屏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中,罗一笑的爸爸罗尔写:“笑笑会走路以后,我们就一直玩着一个游戏,她耍赖不想走路的时候,我就往前跑一段,然后蹲下来,张开双手。笑笑一见,就会眉开眼笑地奔跑过来,投进爸爸的怀抱。”

妞妞、罗笑笑、喜禾,包括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孤孤单单走这一遭,被成人世界的各种揣度,即便是身边的父母,也未必真的明白过他们的心灵。
周国平在《妞妞》中写: “妞妞上颌肿瘤长到快塞满口腔,右鼻孔被肿瘤堵塞,只剩下一个小孔,妞妞使劲儿用嘴呼吸,上嘴唇开裂,渗着血。”
“有一回,妞妞磕在床架上,哭了,妈妈一边安慰她,一边问:‘妞妞磕着了,是吗?’”
妞妞记住了“磕着了”这个词,到后来肿瘤向她的头部和身体扩散,妞妞疼得要命,只是一次次将这种痛苦认定为是磕着了。“磕着了,磕着了。这一声声喊叫如同节日晚宴上响起的丧钟,清楚地提示着欢宴即将结束,死神正在破门而入。”
“妞妞手握小圆板,不时举手把小圆板从床栏上方扔下,掉落在妈妈手中的玩具上,发出撞击声。她重复着这个动作,静听那声响……我想起以前在书上读的一句话:看病孩在临终前仍然依依地玩着手中的玩具,这是何等凄楚。”
妞妞用自己脆弱的、小小的病躯扛过了一年半痛苦难捱的日子,她声嘶力竭地一喊着“磕着了”;她偶尔猾黠地喊叫,希望得到爸妈的关怀;她恋恋不舍地攥着自己喜欢的玩具,就像紧紧抓住生命;她到最后一刻还是想听听音乐。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是周国平写作于妞妞过世后的一年,里面虽充斥着许多关于生命的理论,现实与梦境交叉,时间有些混淆,但还是用足够大的篇幅为我们再现了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在艰难求生。
妞妞眼睛有疾病,她像是知道自己最后会遁入黑暗一样,在她能看到光的有限的时间里,执拗地追逐着光明,她会盯着余晖、盯着婴儿床上方的灯光。当后来所有的视线只剩下眼角晃动的一小片影子时,妞妞认真训练着自己的听力,伸出手认真地触摸爸爸妈妈的脸,家里的床、地毯、家具,“她一寸一寸地丈量她生命的疆界。”
小孩子远比大人有着更强的承受苦痛的能力,他们不像大人一样善绸缪,对于一切的未知和对世界的热情,让他们满怀希望地想扛过去一次次的阵痛。大人为下一次痛苦的到来战战兢兢时,小孩子为这短暂的轻松高兴地挥臂庆祝。
妞妞患病之初,医生的诊断意见是:双眼多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建议左眼摘除,右眼试行放疗和冷冻。周国平言语间谈及:“我到此止步了,医嘱的执行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我)心想既然她活不长了,她来时一头黑发,就让她这么美丽地走吧。”“小生命毕竟出世不久,放弃她似乎并非不可思议。”“全或无!或者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宁馨儿,或者一无所有!”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周国平借着妞妞这个事情的由头,提前对生、死、爱等命题做了一番议论。

蓦然想起史铁生写自己双腿残疾以后,母亲到处求医。蔡春猪在一席的演讲《爸爸爱喜禾》中说起:“我妈因为孙子有自闭症,她就特别的上心,特别的忧伤,也特别地想做点事情,她就偷偷地背着我,去了很远的一个地方,她身体很不好,手都不能拿东西,而且坐车头晕,但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给我取回了一瓶神仙水,让我给我儿子喝,她认为喝了喜禾就会好了。”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想清楚,人和人不一样,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也不是他有意学的这么样的,而且他与生俱来就是个自闭症,这个自闭症是你没办法去改变的,它不是一个病,不是长了一个什么把它割掉就行了,自闭症就是他本身,他就是他存在本身,他就是这么一个存在的方式。” 蔡春猪说。
而对于妞妞来说,她曾那么努力地在生活,在用力地感知世界,谁知道她长大以后能不能接受她的病,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