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谭柘︱旦暮遇之:谢正光先生与他的“洋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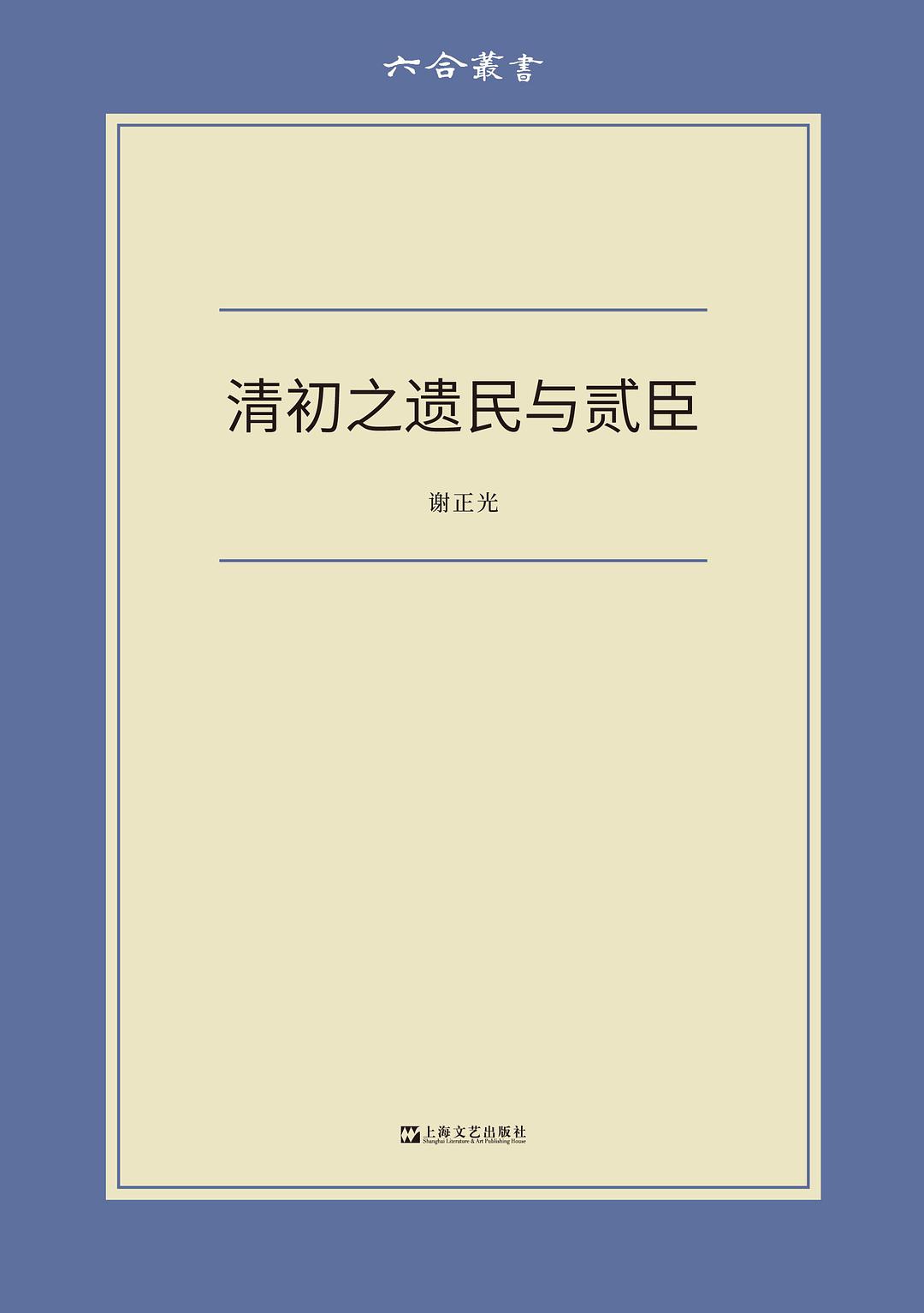
《清初之遗民与贰臣》,谢正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版,362页,5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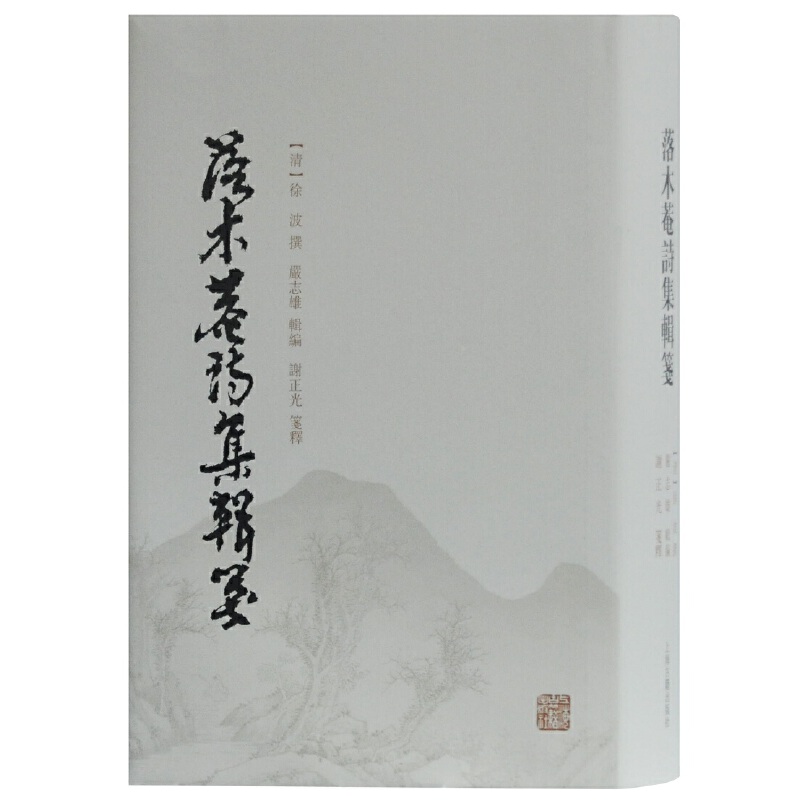
《落木菴诗集辑笺》,[清] 徐波 撰 / 严志雄 辑编 / 谢正光 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6月版,731页,118.00元

谢正光夫妇与张充和(中)先生合影
明清之际遗民与贰臣的研究本来是显学,后来不知为何似乎停顿了。美国格林纳尔学院谢正光教授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可谓倾尽毕生精力,贡献很大。
我与谢先生通信,大概始于2012年秋。谈些什么呢?主要是双方感兴趣的一些旧事。我曾对香港新亚书院感兴趣,无非政治、学术两方面,这两方面都与钱穆先生脱不开干系。谢先生于2016年8月16日来一信谈到与钱穆先生的一些交往:
我于1960年秋天入新亚书院中文系时,钱先生在耶鲁大学讲学。我升二年级,钱先生回校,且兼系主任,不管行政,也不开课。每月主持月会,全校师生恭听他演讲。主要讲“做人”、“人有人格”等等。说的是无锡话,把“人”念成“神”,听懂的人大概不多。没听他讲过有关政治的话。三年级时从台大请来郑因百(骞)先生当系主任。适逢我被同学推任系内学生会主席,要编第一期系刊(刊的均同学习作),钱先生答应为封面题字,去拜访过两三次。又因我这广西佬,居然是当时为数不多听懂无锡话者之一,所以偶然被命作他演讲的记录人。当时已有录音机,稿子又先送钱先生审核,不是难事。倒也真正学了些作文的知识。可惜钱先生改过的稿子早已不见了。
同年,校内成立古乐会,钱师母来随蔡德允女士学川派古琴,钱先生偶尔来吹洞箫,因我初中时学过洞箫,故有幸陪他合奏。听说钱先生、师母移居台湾后,二人还偶尔琴箫齐奏。
1964年,钱先生辞新亚院长,但仍在研究所兼任。我毕业后即入所,从牟先生主修历史、从潘重规先生(字石禅,季刚先生婿)副修文学。钱先生指导哲学思想,故见面不多。但研究生的月会报告,钱先生一定出席。讲话铁面无私,至今不忘。
1978年,我去台北开会,在故宫和钱先生单独见过一面。钱先生说的还是“如何做人是首要”那些话,学问和政治的事还是不说。可能是因为我那两方面都欠缺慧根之故。前些时整理书房杂物,见有钱先生手书新亚校歌的影印本,来沪时带一份送给你。
这一篇文字只有五百余,像一幅白描,单刀直入,没有形容,却富味道。我于是去信半真半假怂恿谢先生多写些回忆性文字,大有劝名人作自传的味道。谢先生当然不肯,他觉得唯有学术文字或许还有价值,其他不足作。我就说你研究的是历史,今日之新闻,便是明日之历史,有什么区别呢?且倏忽变幻,刚过去不久的事很多便真真假假难以捉摸,不应该记下一些吗?还是不写,不易说服。直到大概2019年底至2020年初才决定写一点,大概通信中胡说八道,一些问题他也生发出趣味吧?
先写什么,一部十七史从何谈起呢?我初次谒见谢先生是2012年秋于白下,问他当初如何去香港的,他说“偷渡的”,当年十岁,是家中四个孩子的老大。妈妈带了最大的,抱了最小的,抛了中间两个,离开故乡。这就是最早的一篇《容县去来》,谢先生是广西容县人,他这一篇真是惊心动魄。赴港时间与张爱玲同其前后,而波折远甚,那气氛如数九隆冬的屋子里放了一大块冰。
不知是不是故意,谢先生接下来跳过新亚书院的老师,写的是京都大学的一段经历,我只好耐心等下去。归于京都学派的学者向以考证精确著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有侵华之倾向,对中国学生不甚友好。谢先生在京都时期,即有一教授致信日本出入境事务管理所,建议拒绝延期居留,即将其驱逐。是岛田虔次先生仗义执言,为谢先生出头。这篇文章主要利用了岛田先生的三封信构成主体进行叙述,题目就叫《岛田虔次先生的三封信》。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过于依靠三封信这个现成的材料,代替了他自己的叙述,谢先生那种简练刚劲绝不拖泥带水的风格没有能得到充足的展现。
在文章的末尾,他谈到恋恋不舍地离开京都,到耶鲁求学。谢先生六十年代去日本,那时候他就觉得日本好,时隔半世纪,老先生回首东洋,不改初心。离开京都赴耶鲁,就不得不提到耶鲁的那位“洋老师”。在和谢先生谈话中,每次涉及这位老师,他总不名而只叫她“洋老师”,更没有专门谈过,所以这位老师的面目一直模糊,犹如《水浒》里的没面目焦挺,远远没有岛田虔次那么清楚,更没有牟润孙那么鲜明,甚至不如史景迁。所以我总觉得谢先生对这位老师恐怕有不足之论,故不多及。但总归要有名字吧,他在文末说:“Mary Wright(芮玛丽)教授与Arthur F. Wright(芮沃寿)教授,均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之门生”“我于1969年五月中到耶鲁报到,旋注册入暑期班进修法文阅读。”又说:“从游于两位芮教授门下前后七年,悲喜交集。他日有缘,当另作一文叙其始末。”应该说当时我已经注意到这两位“洋老师”,但我虽注意到他们,却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值得注意的。

今虞琴社欢迎美国古琴家梁铭越,前排左起:沈德皓、梁铭越、龚一、谢正光
今年搬家收拾东西时,检出很多要读而未读的书,有的如旧相识,有的如同没见过。往往站在一堆乱书间,看起了其中一本。有一本戋戋小册,是《殷海光林毓生通信集》,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与我在书尘泛起、时空漫远的老式办公楼里相见了。没想到,这一次相见,使我邂逅了谢先生的那两位“洋老师”。
林毓生1962年8月18日致殷海光函云:
Arthur Wright,见过一次,此人甚傲慢,您说的事,不便启口。(不知他给您回信否?学术上,交换通常是两方面通信联系的。第三者如不被问,除非实在是熟朋友,很不便过问,尤其是现在许多中国人寄人篱下,帮美国人搞中国东西,混一碗吃的时候,许多中国人患了软骨病,其他中国人就不得不更谨慎了。)
殷海光10月12日回信说:
你对于我托你见A. Wright而你未启齿,这种处置方式和态度,在基本上是quite proper(十分适当)的。莱特教授曾有信来,似乎很客气,而且他寄给我的东西多于我所要求的。我最近想再写信给他夫妇俩,探讨一些问题。你说“此人傲慢”,我不知道这话所指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就我所知,年来西方世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在许多方面超过中国人远甚。说句直话,大多数在美而又吃中国历史饭的中国人,至少在理解问题上,在处理材料上,是已经落人之后了。拿莱特教授做例子吧!他写的东西就非常棒,北方口语“Ber bon”。我很钦佩他。他寄给我的一篇作品“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研究),其中所表现的识度之深宏绝非胡适可比。至于才学次于胡适的徒子徒孙们,则更无论矣!目前他们比较吃亏一点的,只是中文较差,而且“体验(erleben)”不足。
谢先生的洋老师是一对夫妇,莱特先生和莱特夫人。林毓生在信中说“莱特先生甚傲慢”,不近人情,很难接近,故不愿替老师殷海光去接触他。殷海光对这个说法,一方面说你做的“基本上是十分适当的”,另一方面又好像在说“感觉他不傲慢啊”!谢先生不可能读到他们师徒的通信,但他的回忆却替我们回答了这个令殷海光疑疑惑惑的问题。
谢正光《耶鲁六年杂忆(1969-1975)》里说:
先生与夫人治学方向不同,为人处事风格亦各异。我从先生修读中国前期史研讨会,班上师生有讲有笑,气氛轻松。先生来上课前,必在耶鲁会所(Yale Club)午餐,餐前总少不了两杯餐酒,带着酒意,漫步而来。第一句对学生说:“X 先生,你对某书某章有何想法?”先生善与人交,显而易见。其组织能力亦强。三本有关儒学的著作皆集三个国际会议论文而成,功力精湛又能服众。对校内汉学发展,多有神来之笔。当年重金邀聘饶宗颐先生从香港来校当访问教授一事,世所熟知!夫人则寡言笑,全力治学。(《南方周末》2020年2月27日)
可见夫妇二人相较,莱特先生善与人交,莱特夫人倒有几分书呆子气,不易接近,显得傲慢。那么林毓生为什么会对这位只见过一面的万金油式的莱特先生产生这样深的偏见呢?具体情形很难考定,但谢先生的文章里也似乎有迹可循。谢先生初到耶鲁,跟随莱特夫人攻读博士:“瑞特夫人见面后立即吩咐我两要事:一、法文阅读课下周开始,共八周。二、选课的事,必须修她的近代中国史研讨会,此外可自由选择,但政治系的课不能修。后来才知道:当年美国汉学阵营,东部的哈佛、耶鲁属亲中国大陆派,西部则属亲台派。西部龙头名Franz Michael,传闻其研究室内,高悬蒋介石先生签名玉照一帧。”所谓“政治系的课不能修”,可知其时主流之所在;费正清亲北京,而莱特夫妇为费正清弟子,林毓生感其“傲慢”不是理所当然的嘛!何兆武《上学记》写到殷海光时感情极其复杂,其中有一段说:“那时候同学中左派多于右派,自由主义就更多,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殷海光与莱特先生短暂交流,只限于纯学术,还未深入到政治见解,故有局外之感。大赞莱特先生,说“他写的东西非常棒,我很钦佩他”。
林毓生1962年11月18日致殷海光函说:
Arthur Wright 的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大概是他最好的一篇paper,的确很棒,但此公的其他作品则不甚了了,如Confucian Persuasion(1960)的Sui Yang-Ti: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倒是他太太的同治中兴,功力甚深。)这位先生的社会科学background,我看也不见得很深,但自然比在美国搞汉学的中国老朽们要高明多了。此地靠卖汉学吃饭的中国人和国内的一批老先生没有什么两样:土头土脑,酸腐不堪而已。
这里,林毓生只肯承认莱特先生的一篇论文写得好,总体上持保留态度,还拉出莱特夫人来做陪衬。但他这次的判断,倒与谢先生不谋而合,谢文说:“瑞特先生夫妇是当时研究中国史的夫妻档:先生治明代以前史,所著《中国史中的佛教》,立论崭新,虽薄物小篇,历久弥新。惟夫人早年力作《同治中兴(1862-1874)》,则瞻前顾后,以大量文献支持其论点。证之以其后论辛亥革命之作,愈见其观史之敏锐,实非其夫君所可及!”
谢先生新亚研究院毕业后,面临一个问题,是远走他乡,继续学业,还是赶快工作,补贴家里。谢先生多年以后在衡山小馆里对我说,他妈妈去卜了一卦,得到四个字:高桥远路。于是下定决心,走下去。谢先生就给自己的这本回忆录取名为《高桥远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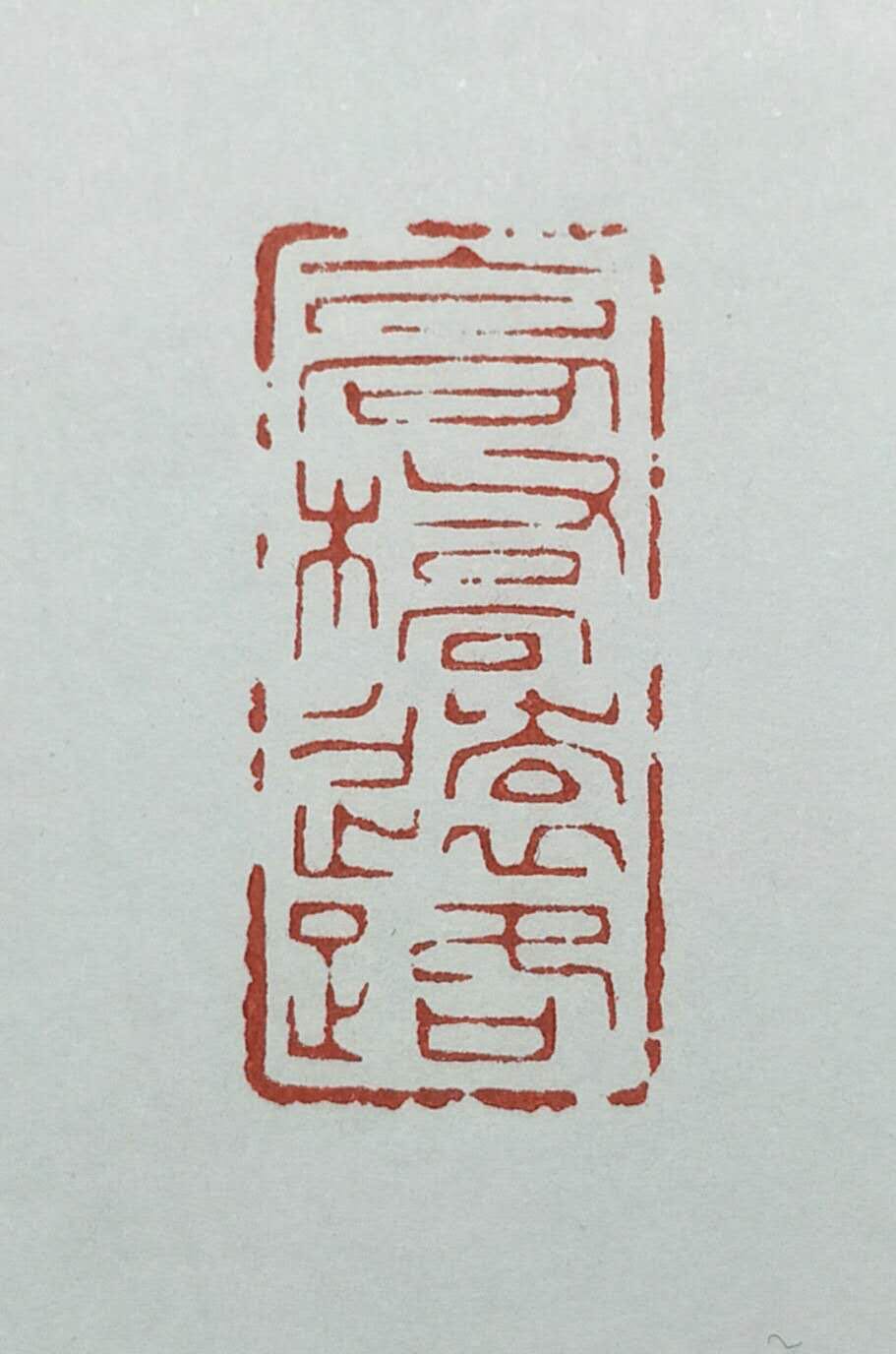
高桥路远
我有一个偏见,读书不怕晚。都知道“闻道有先后”,但一般认为还是越早越好。其实也不尽然,这是一个“遇”的问题,有时候摆在你面前,你也没有遇到,错身而过了。但总会遇到吧,《齐物论》里说的“旦暮遇之”,或许是这意思。古人著书,也喜欢用这个“遇”字,如《遇庄》,还有《四书遇》。说是“遇”,我疑心作者的心里就认为是“悟”字。“遇”要时机,“悟”更要时机,不意“兵荒马乱”、烟尘四起,是我遇到谢先生不肯多谈的这两位“洋老师”的时机。
最近看到一则书籍广告,允晨文化将于2021年11月出版《余英时谈话录》(李怀宇整理),在“耶鲁大学”那一章,第一节便是“芮沃寿与芮玛丽”,很期望读到余先生的这段文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