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远方来信丨樊再轩:我在敦煌修壁画,面壁了四十年仍想继续


在敦煌研究院做壁画修复研究的樊再轩总是很忙,忙着开会讨论,忙着奔赴现场,忙着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自1981年来到敦煌,这样的忙碌几乎占据了樊再轩的大半生。
他的微信名字叫做“面壁三十载”,点明了自己工作的性质。作为一位专业从事壁画和彩塑保护修复研究工作的老专家,到2021年年底,他就到了退休的时候。
“但是我不会离开研究院,我还要再培养一些年轻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樊再轩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说实话,我已经对这份工作和敦煌产生了不可割舍的情感。”
敦煌研究院地处偏僻,缺少都市的繁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就好像是一片历史的“飞地”,生活在这附近的人,似乎离历史比现实更近。诱惑也时常存在,据说上世纪90年代,他被派往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学习,曾有朋友劝他不如就此留下,日本经济好,收入是国内的十倍。但他犹豫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到敦煌。
“还是放不下这份事业。”四十年间,樊再轩从20岁的小伙子进入了花甲之年,并在这里结婚成家养育后代,他几乎见证了敦煌莫高窟从寂寞荒凉到游人如织的整个过程。
热闹与他无关,当一波波中外游客在莫高窟欣赏壁画的时候,樊再轩和团队思考的却是众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可能带来的危害,以及如何及时干预。
以下是樊再轩的自述。
我还记得40年前敦煌的风铃声
我成长在甘肃的嘉峪关,这里离敦煌并不算远,文革结束后,敦煌研究院在酒泉、嘉峪关、敦煌这几个地方招考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我通过考试就被选到了敦煌研究院。在这之前,我也仅仅是在书本上知道敦煌,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也并不知道真实的敦煌到底什么样子。
我是1981年3月31号晚上到的敦煌莫高窟,当时已经就很晚了,我感到一种从未感受到的寂静。我记得很清楚,甚至可以听到九层楼的风铃声在叮当作响。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了莫高窟,真的可以说被洞窟里的精美的壁画震撼到了。
最初,我来这里就是抱着找一份工作的心态,其实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对我们这些小年轻非常关心,从白天到晚上给我们上课,讲敦煌艺术史,还会讲敦煌石窟的保护,他们的坚守和奉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慢慢也有了使命感,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好敦煌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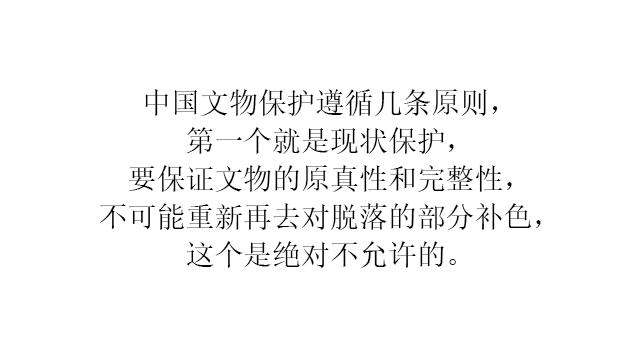
当时,国家的经济还是相对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莫高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早在1960年代,国家就对莫高窟的崖体进行了保护,修筑了让人通行的栈道,有些洞窟还安装了窟门。
我到莫高窟工作的时候,比较危险的崖体脱落和坍塌这样的问题,前辈都已经解决了。我们面临的是更细致的状况。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刚到敦煌的时候洞窟里的壁画和彩塑颜料层是有问题的,还有空鼓现象,严重了会出现坍塌;另外潮湿的空气进入到洞窟以后,地上的可溶盐潮解,酥碱的病害也比较严重。
几个月之后,我被分到了保护所,在这里我开始慢慢对敦煌石窟壁画的病害有了认识,开始一点点学习如何修复壁画。在一些人的想象里,修复壁画是把脱落和丢失的部分补成原来的样子,可能还要绘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上图:破碎壁画修复前。
下图:破碎壁画修复后。
中国文物保护遵循几条原则,第一个就是现状保护,要保证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可能重新再去对脱落的部分补色,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很多时候,我们对壁画的修复其实是通过研究解除病害,让它变得更加稳定。
莫高窟492个洞窟,
其中一部分不具备开放条件
我们对壁画的保护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技保护、日常维护和预防性保护等几个阶段,目前对莫高窟的抢救性保护其实已经都结束了,现在主要是进行科技保护、日常维护和预防性保护,将后三种相结合。
敦煌的保护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抢救性保护。之前都是无人管理,能做的其实很有限,洞窟壁画和彩塑急需抢救的部分非常多。进入到1990年代初,随着国家的发展,敦煌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成为共识,进入到了科学保护的阶段。我们主要是对每一种病害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诊断,做到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的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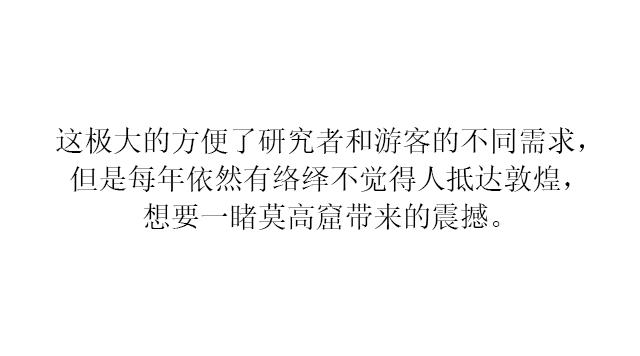
要说四十年来这里最大的变化,应该是研究保护队伍的壮大,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还不到一百人,现在有一千五百多人。我还记得当时做保护和修复的只有四五个人,现在要有两三百号人。各种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时只有很简单的几样基本的工具,现在我们拥有各种现代化的仪器。
2021年,敦煌研究院实现了258个洞窟的数字化,通过对影像数字技术、数码显微技术和三维虚拟技术的利用,我们建立了数据库,人们在网上也能很清晰地看到壁画以及洞窟的结构。这极大的方便了研究者和游客的不同需求,但是每年依然有络绎不觉得人抵达敦煌,想要一睹莫高窟带来的震撼。
目前,造成壁画损害一个是人为因素,一个是自然因素。在中国,人为因素的影响现在已经几乎降到最低了,解决自然因素的影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会观测洞窟里的环境变化,温度和湿度对壁画产生的影响等等。莫高窟的大部分洞窟里都放置了温度和湿度的检测设备,一旦数值超出或者低于控制范围,我们就会立刻进行控制。


上图:破碎彩塑修复前。
下图:破碎彩塑修复后。
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护,我们对游客也进行了管理,采用预约管理,分时间段的参观,其实这都是一种保护式的管理。说实话,莫高窟的492个洞窟,其中一部分是不具备开放条件的,因为洞窟比较小,十几个人站在里面就很拥挤了,游客进去很可能会擦伤壁画。我们选择开放的洞窟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让观众可以领略各个朝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保存也相对精美的中型洞窟或者是大型洞窟。
不仅如此,很多洞窟也不是长年开放的,我们会选择轮流开放的办法,有时候一个洞窟涌入很多游客,湿度变化的波动就会很大,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很可能对壁画也有影响,因此我们会开放一阵子就关闭,再开放一个新的,如此轮流,能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四十年了,
每一次的工作对我都是挑战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敦煌研究院同时也是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们不仅保护莫高窟,对甘肃省内外的石窟壁画,殿堂壁画,还有墓室壁画都有保护修复的责任。

樊再轩正在修破碎的壁画。
除了莫高窟,我走过很多地方。但是回头看,工作四十年了,每一次保护修复的工作对我都是一个挑战。就拿2021年刚刚完成的天梯山石窟壁画修复来说,整个保护的工作也很漫长。
1958年,为了解决天梯山附近农业灌溉和饮水的问题,政府要在天梯山石窟不远处新修一个水库。1959年开始,为了保护文物,经过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敦煌研究院(当时还叫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一起对天梯山石窟的壁画和彩塑进行搬迁,存放于甘肃省博物馆。2005年,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重视下,天梯山石窟的壁画和彩塑大部分回到了武威,只有一少部分还存放在甘肃省博物馆。
2013年,受甘肃省文物局的委托,敦煌研究院就开始对这一批搬迁壁画和彩塑进行保护和修复,我们进行了病害调查和病害分析,分析病害产生的原因,进行修复试验,经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年才完成修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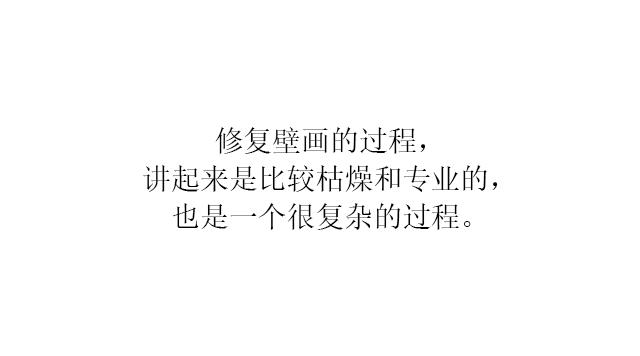
天梯山石窟搬迁保护修复的过程特别艰巨,因为当时是把壁画从洞窟里一小块一小块分割下来的。这些碎块的地仗层的厚薄不一样,切割缝的宽窄也不一样,破碎得很厉害。最终我们还是攻克了各种难关,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样的困难有很多,文化保护涉及的学科很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修复壁画的过程,讲起来是比较枯燥和专业的,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一般来说,我们进入一个现场首先是要判断病害形成的原因,如果是颜料层的问题,发生病害以后,可能就会产生鳞片状的起翘,我们叫“起甲”,那就要通过注射黏结剂的办法,把颜料均匀并平整地回贴到地仗上;还有一种叫酥碱病害,我们叫“盐害”,因为是和盐有关的,我们在加固地仗的时候,就要把地仗中的可溶盐降低,我们叫“脱盐”;还比方说空鼓壁画,是指壁画的泥层和后面的支撑体之间有了空隙,我们就要筛选出比较好的灌浆材料,注射进空鼓的部位,再把壁画回贴回去。


左图:颜料层起甲壁画修复前。
右图:颜料层起甲壁画修复后。
退休后我也不会休息
回想起来,整个1980年代,敦煌没什么游客。这些年人们在物质文化提升的同时,精神方面的追求也多了。这么些年,我对敦煌也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情感。疫情对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带来了一些挑战,每当有新的疫情出现,很多修复现场也会关闭,所以工作的进度也会被耽误。
转眼间,今年年底我就退休了,但是我不会休息,单位也早就和我打好招呼,要返聘,持续进行保护工作,继续培养年轻人。

樊再轩正在修复彩塑。
现在从事壁画修复的年轻人,学历都很高,一般都是硕士和博士,除了他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外,其实更重要的可能是要热爱这份工作。要知道,莫高窟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偏僻的,我们长年生活在一个山沟里,在这里工作要有吃苦的精神,也要有奉献的精神。
老一代的敦煌人,像是常书鸿、段文杰等人,都是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早在1940年代就到敦煌,为这里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我想,如果说他们这代人是造梦者,我们就是追梦者,年轻一代则是圆梦者,我希望敦煌之美可以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原标题:《远方来信 | 樊再轩:我在敦煌修壁画,面壁了四十年仍想继续》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