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崔之元论共和主义者阿伦特
自视为卢森堡传人的阿伦特:我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少年时代成长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那里也是哲学家康德的故乡,而数学家欧拉曾解决了“柯尼斯堡七桥难题”。阿伦特的成名作是1951年在纽约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她最具争议的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最系统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则是1958年的《人的境况》。不过,她的博士论文导师雅思贝尔斯和她的第二任丈夫Heinrich Blucher都认为她最好的书是1963年出版的《论革命》,尤其该书最后一章精彩论证了1905年至1921年间的“苏维埃”(俄语“委员会”之意)是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可行替代。
阿伦特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也常常引起人们的误解。例如,《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是她毛遂自荐担任《纽约客》杂志记者,亲自到耶路撒冷现场旁听对纳粹负责遣送犹太人到集中营的官员艾希曼的庭审而写成的报告。她认为艾希曼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即由于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盲目服从命令而产生的恶,他本人并没有“杀人魔王”的明确动机。

同时,她认为一些“集中营”的犹太领导人,即纳粹所谓“让犹太人管理犹太人”而建立的“犹太委员会”成员,其实也对犹太人的命运负有一定责任。例如,阿伦特批评柏林的犹太教大拉比Leo Baeck,他在1943年8月就知道了有些集中营是专门从企业定做了毒气机的死亡营(而非劳动营),但他没有告知其他犹太人,因为他觉得医生不应该把病情告知将死之人增加痛苦,他还给纳粹推荐犹太人担任集中营的警察,认为犹太人警察至少会对犹太人“人道点”,而1957年德国政府竟然为此人发行了纪念邮票。

阿伦特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很多人便以为她一定是“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她说“我从来不是自由主义者”,并在《论革命》中对“代议制民主”给予深刻的批判:
代议制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寡头政府……尽管不是在代表少数利益的少数统治这一阶级意义上的那种寡头政府。我们今天叫做民主制的东西,据说至少是一种代表多数利益的少数统治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是民主的,因为平民福利和私人幸福是它的主要目标;但是,在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再次成为少数特权这一意义上,它也可以被叫做寡头的。
实际上,阿伦特自认为是波兰-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继承发展者,这在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纪念卢森堡的文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阿伦特的第二任丈夫Heinrich Blucher是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1918年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团”的重要成员。阿伦特最高兴听到一个学生听课后对她的评价:“卢森堡又回来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特别强调“反犹主义”(第一卷)、“帝国主义”(第二卷)和“极权主义”(第三卷)三者的内在关系,而在第二卷中她大量引用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

在下文中,我将试图说明:理解阿伦特的复杂而深刻的政治思想的关键,是从她的犹太认同的历程入手,进而了解阿伦特从“共和主义”视角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
犹太人应该争取“整体的政治解放”,而非“个人的社会同化”
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一个“自由犹太教”的家庭,她的父母没有给她改宗(而马克思的父亲在6岁时给他改宗基督教),但也没有给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的教育。阿伦特在哥尼斯堡的自由启蒙思想氛围中长大,她的祖父书房里有康德1795年《永久和平》第一版的版本(晚年阿伦特为了支持学生“反越南战争”组织曾拍卖这个版本),1924年她先到马堡大学读哲学本科,师从海德格尔,后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师从雅思贝尔斯,192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奥古斯丁关于爱的观念》。仅从这篇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即可看出,这是阿伦特对基督教思想大师奥古斯丁的研究,当时她并没有深思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认同问题。

但是,正在兴起的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迫使阿伦特开始反思 “犹太身份认同问题“。德国的教育体制是大学教师资格需要“第二博士论文”,而阿伦特选择给犹太妇女Rahel Varnhagen(1771-1833)写传记来作为“第二博士论文”。Rahel Varnhagen可以说是个犹太奇女子,她的柏林沙龙的常客包括黑格尔和洪堡兄弟等德国文化、政治名人。她一生纠结于融入主流社会的同化愿望和不愿放弃自己犹太人自豪感之间的紧张,阿伦特的传记对她既有同情又有批评。阿伦特的主要论点是,“个人的社会同化”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政治解放”,犹太人应该争取“作为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而不可能通过个人的“社会同化”而得到解放。阿伦特认为,在犹太人“出埃及”的两千多年历史上,只有两次政治行动:十七世纪中叶的Sabbatai Zevi运动和十九世纪开始的犹太复国运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后来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区分——“政治的”与“社会的”——的端倪。
阿伦特在传记中运用了Bernard Lazare(和Theodor Herzl齐名又不同的十九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精神领袖之一)对犹太人“暴发户”(parvenus)和“被遗弃者”(pariah)的两类划分,并将“被遗弃者”又分为四类:第一类以诗人海涅为代表,第二类以 Lazare本人为代表,第三类以卓别林为代表,第四类以卡夫卡为代表。
阿伦特也自视为“被遗弃者”,她尤其喜爱卡夫卡,后来在1940年代末曾编辑《卡夫卡日记》,把卡夫卡介绍到美国。1933年,阿伦特在被纳粹拘留八天后(因为搜集纳粹反犹言论)流亡法国巴黎,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后又取道葡萄牙流亡美国。在1933年至1940年期间,阿伦特一直在巴黎从事培训犹太青年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的组织工作,因此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相识。但她逐步与犹太复国运动的主流派领导人发生了严重分歧。
犹太复国的“帝国主义上层路线”,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后患无穷
这一分歧的实质对我们理解阿伦特后来的政治思想非常关键。1919年巴黎和会后,英国获得了从前奥斯曼帝国手中“托管”巴勒斯坦的权力。“犹太复国运动”继承 Theodor Herzl(1860-1904)思想的主流派领导人(如后来以色列开国总统兼化学家魏茨曼等)走“帝国主义上层路线”,希望英国保证“托管”结束后把巴勒斯坦移交给犹太人建国,而完全无视已经世代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阿伦特则继承了“犹太复国运动”少数派领袖Bernard Lazare(1865-1903)的传统,和马丁·布伯和爱因斯坦一样,反对走“帝国主义上层路线”,而主张直接与阿拉伯人民对话,在基层共建“犹太-阿拉伯委员会”,在上层建立两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后来在《论革命》一书中论证“委员会”——包括杰佛逊的“基础共和国”(elementary republics),巴黎公社和1905-1921年间的“苏维埃”——是替代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的端倪。
1941年阿伦特夫妇侥幸避难美国成功。他们得到发放量很少的美国在马赛发的紧急签证,盖因阿伦特的前夫帮了大忙。但她的好友、著名文学理论家本雅明则没有得到法国的出境签证,他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偷渡法国-西班牙边境,在西班牙边检受阻后自杀。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希法亭也和本雅明同样没有得到法国出境签证,但他没有像本雅明那样翻越阿尔卑斯山偷渡,结果希法亭夫妇被法国维希傀儡政权移交纳粹,遭到极刑杀害。希法亭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大量引用的《金融资本》的作者。

阿伦特到美国后,仍高度关注犹太人的命运。耶路撒冷大学第一任校长Judah Magnes注意到阿伦特与自己观点相近的文章(即反对走“帝国主义上层路线”,直接进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作)。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英国托管结束后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建议分别成立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但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作为“特别国际体制”,不单属于以色列(这也是最近川普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之所以遭到70个国家反对的原因)。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单方面宣布建国。但这个分治决议遭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坚决反对,暴力冲突升级,新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安理会任命瑞典外交家Count Bernadotte为首位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协调员。Judah Magnes校长让阿伦特起草了给Count Bernadotte的建议,而后者在给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中也基本采纳了阿伦特的建议,但以色列右翼恐怖分子于1948年9月17日在耶路撒冷暗杀了Count Bernadotte,之后双方暴力进一步升级,阿伦特的基于阿拉伯-以色列基层联合委员会的两民族联邦方案也就不了了之。但这段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政治参与,使阿伦特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欧洲“民族-国家”模式的深刻弊病,以色列按照欧洲单一的“民族-国家”模式来建国,对阿拉伯人民和犹太人自身都是后患无穷。阿伦特甚至尖锐地指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种族清洗,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做法没有太大区别了。
阿伦特对犹太复国主义走“帝国主义上层路线”的批评,为她后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帝国主义作为极权主义的一个“元素”打下了伏笔。她指出,1884年由葡萄牙提议,俾斯麦召集的“柏林会议”后帝国主义各国对非洲的瓜分,强化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弱化了殖民地宗主国内部的公民权意识,为纳粹极权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德国终于在一百多年后,承认1904-1908年在纳米比亚(当时叫“德属西南非洲”)的集中营和大屠杀,并准备给纳米比亚道歉和赔偿,而当时的德国纳米比亚殖民长官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的德军将领Lothar von Trotha。纳米比亚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划给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直到1990年才获得独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阿伦特强调“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催化剂的匠心所在。

当犹太人失去公共职能,只剩下财富,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
在阿伦特看来,“反犹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另一个“元素”和催化剂。她反对用“寻找替罪羊”来解释“反犹主义”,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何是“犹太人”被当成“替罪羊”而不是别的人。她也反对所谓“永恒的反犹主义”,即把反犹主义归结于犹大对耶稣的出卖。
她认为,对理解“极权主义”起源来说,最关键的是要解释1870年之后的“政治反犹主义”和欧洲“民族-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当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公共职能和影响,而只剩下他们的财富之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
阿伦特把欧洲“民族-国家”兴衰和犹太人命运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还处于在绝对君主制的监护下,只有少数犹太人进入宫廷,替君主管理金融事务;第二阶段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民族-国家”获得了大发展,它们的公债和广义金融业务的需要,促使各国把公民权利扩展到少数宫廷犹太人之外的更多犹太人富裕阶层,并颁布了名义上适用于所有犹太人的“解放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为理解这两个阶段提供了生动的说明。第三阶段是十九世纪后期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地盘大发展时期,这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及其之间的平衡体系的崩溃的开始,此时犹太金融商业对国家的”公共职能“变得不如“帝国主义冒险家商人”那样重要了。阿伦特提到的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中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者Mr. Kurtz, 是一个极端残暴的象牙贸易商,就是“帝国主义冒险家商人”的代表。第四阶段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此时欧洲“民族-国家”及其之间的平衡体系全面解体,犹太人成了没有任何“公共职能”但又有相当一部分富人的群体,成为“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打击对象。
可见,阿伦特强调的是,“社会同化”和“经济财富”都不能挽救犹太人的厄运,只要他们没有争取到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阿伦特1958年《人的境况》一书中对公共政治参与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条件的论述。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是1970年代以后“共和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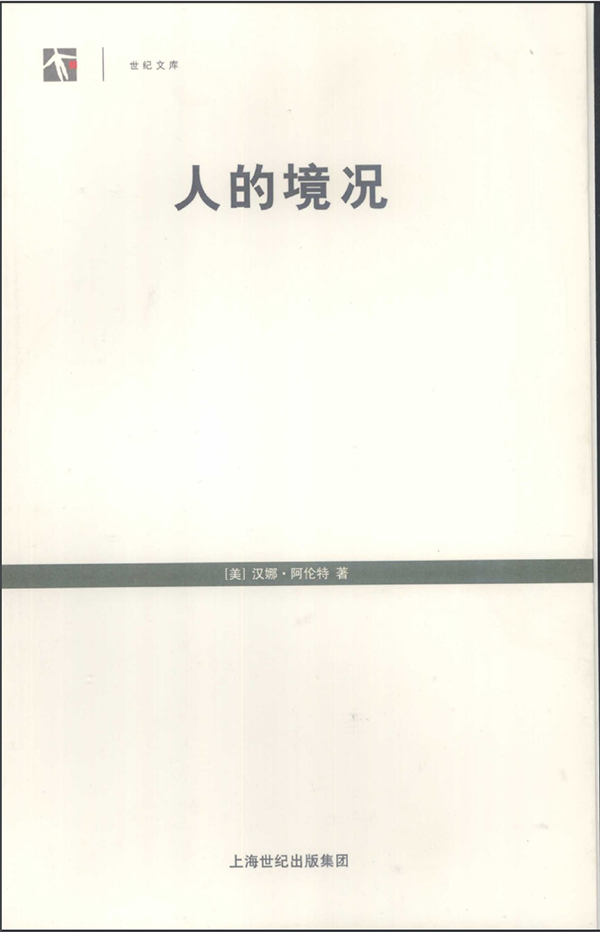
阿伦特《人的境况》是波考克“共和主义”的先声:永恒的上帝,不朽的奥林匹亚诸神
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当代“共和主义”的主要理论代表波考克对阿伦特的评价:“作为历史学家,我一向十分关注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对话,故也难怪,其著作能够引起我最强烈共鸣的,当属已故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波考克这样描述自己的这本1975年出版的《马基雅维里时刻》:“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语言来说,本书讲述的是西方现代早期复兴古代政治人(homo politicus,亦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理想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政治人通过政治行动来肯定自身的存在和美德,与他最近的血亲是‘修辞学家’(homo rhetor),他的对立面则是基督教信仰中的‘有信的人’(homo credens)”。波考克这样描述马基雅维里对“共和政体”及其公民参与的主张:
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中某些持久的模式,导致了认为共和政体的出现和公民对该政体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历史中自我理解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马基雅维里及其同代人或明或暗地坚持主张的。
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
为什么波考克说“共和政体的出现和公民对该政体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历史中自我理解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不朽”(immortality)和“永恒”(eternity)的区分,会有助于我们对波考克问题的理解。阿伦特受亚里士多德启发,区分了三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都属于“积极生活”(Vita Activa”), 与中世纪基督教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对。“劳动”是与人的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新陈代谢活动,“工作”则创造了一个非自然的“人为事物”的世界,而“行动”是在平等的公民间的政治活动,对应于人的复数性(plurality)。
亚里士多德认为,“劳动与工作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平等主体间的政治参与的“行动”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有人批评阿伦特过于推崇古希腊,不了解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理想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和“工作”基础上的,其实马克思也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处说过“在狭义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真正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自动化高度发展的今日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大胆设想,人工智能将大量取代“劳动”和“工作”,在“社会分红/基本收入“的基础上,平等主体间的政治参与的自由“行动”将获得大发展。

不过,对理解波考克问题至关重要的是阿伦特《人的境况》中的这段话: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以致于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的尊严。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被从尘世生活必需的层次上看待,以至于沉思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正是这种“沉思生活”,形成了“不朽”与“永恒”的区别:前者还是有时间性的,而后者则没有时间性。阿伦特说:“不朽意味着在地球上和在这个被给定的世界中,拥有长生不死的生命,按照希腊人的理解,这样的生活属于自然和奥林匹亚诸神……与这种在时间、生命和宇宙之外的超越的上帝相比,希腊人的神和人不仅有着相同的形象,而且有着相同的本性,是神人同形同性的。”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永恒”概念的非时间性,而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恰恰是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念的一种形式,其主旨是回答世俗时间中的特殊事件的普遍性问题。正如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中所进一步解释:
共和政体……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普遍的”是说,它的存在可以为其公民实现人们在现世生活中能够实现的全部价值;“特殊的”是说,它是有限的,它置身于时空之中。……因此,共和主义理论……的关键内容,是有关时间的观念,有关以时间为唯独的偶然事件之发生的观念,以及关于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的特殊事件之序列(称之为过程还为时尚早)之可理解性的观念。
相形之下,
基督教坚信这样一个上帝,他在过去的一个时间点上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将在未来一个时间点上拯救人类并终结这个世界……但它本身并未使特殊的事件和现象在时间中相继发生能被理解,也未赋予作为事件相继发生之维度的时间以任何特殊的重要性。
J. G. A. 波考克
共和主义正是克服基督教的非历史性的最早的现代历史主义思维方式,它首次提出了“存在于世俗特殊性中的普遍性”这一问题。波考克再解释说:
对于永恒的上帝来说,时间中的每时每刻是可以同时看到的;整个世俗模式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和命令的,因此事件序列和预见之类问题是不存在的。
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是对时间中的和世俗的历史的排斥,而历史解释模式的出现则要大费周章,它得用更具时间性和世俗性的世界观来取代基督教的世界观。
存在这一套回响于历史中的词汇,它把政治表述为“处理可能之事的技艺”,从而也是处理偶然之事的技艺;政治是统治人类的“无止境的冒险”……如果我们把偶然性的领域视为历史,……从这种政治观似乎就会产生促进世俗历史写作成长的强大动力……
那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者所主张的积极的公民生活是何以能理解在世俗时间中的特殊事件并甚至可能一定程度上控制偶然命运呢?
人文主义者都深入参与到具体而特殊的人类生活之中……让特殊变得可以理解的需要,导致了交谈观的出现,即这样一种想法:普遍因素内在于对生活和语言网络的参与之中,因此,最高价值,甚至非政治的沉思价值,也被视为只有通过交谈和社会合作才能获得。由此导致的必然结论是,社会合作本身是一种高贵而必要的善,是获知普遍性的前提,整个雅典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都强调,人类社会合作的最高形式是政治团体,是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中看到的分配、决策和行动的共同体。
共和主义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公民权”比“人权”更重要
至此,我们看到,确实可以说阿伦特1958年的《人的境况》一书预示和激发了波考克等代表的“共和主义”学派从1970年代开始的兴起。从“共和主义”视角,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阿伦特会同时批判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阿伦特强调,极权主义不仅给生活带来苦难,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政治参与权力(她用“right to have rights”一词),企图消灭人的独特性和复多性。而“自由主义”者往往只强调“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但殊不知若没有积极的政治参与的保证,这种“消极自由”弱不禁风。让我们引用一段“共和主义”学派另一位代表菲利普·佩迪特在《共和主义》中对“共和主义”的“无支配”的自由观和“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自由观说明:
(伯林)将积极自由看作是对自我的控制,而将消极自由看作是不存在他人的干涉。然而,控制和干涉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是否可以用这样一种居间的方式来看待自由呢,即自由确实是指某种阙如的状态——同消极自由观一样,但阙如的不是干涉,而是他人的控制。
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如果大家感到上述区分还是太抽象的话,我再举一个阿伦特在公民权问题上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例子。阿伦特从1933年被迫逃离德国后,曾十八年没有国籍,这使得她对公民权问题十分敏感,也感到“自由主义”完全以个人为基础的抽象人权观念的苍白无力。在《我们,难民》一文中,她明确指出,没有任何政治共同体保障的抽象的人权是弱不禁风的。因此,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权”比“人权”概念更为重要。阿伦特对“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权观念的批评,与她自身1933年后十八年“无国籍”有密切关系。纯个人的人权观念,没有国家的保护,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因此,阿伦特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公民权”比“人权”更根本的观点。1958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做出无论如何不能剥夺公民权的判决,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引用了《耶鲁法学评论》上的文章,而该文大量以阿伦特的公民权理论为依据。从此,美国黑人共产党员兼歌星保罗·罗伯逊1950年代初因来中国演唱而被吊销护照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共和主义的精神实质:从希腊城邦到“委员会”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在此,我愿特别指出,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视野非常广阔,她从希腊城邦、杰斐逊的“初级共和国”、巴黎公社和1905-1921年间的“苏维埃”(俄语“委员会”之意)都看出了 “共和主义”的精神实质,即“由革命进程本身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杰斐逊的计划,还是法国的societes revolutionaries(革命委员会),都极其匪夷所思地准确预见到了这些委员会、苏维埃和Rate(委员会),它们将在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每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中崭露头角。每次它们都作为人民的自发组织产生和出现,不仅外在于一切革命党,而且完全出乎它们和它们的领袖意料之外。……即便是那些显然对革命持同情态度,忍不住要将民间委员会的涌现载入其故事记录之中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委员会本质上不过是为了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临时组织而已。换言之,他们无法理解,站在眼前的委员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也无法理解它是一种为了自由,由革命进程本身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引自《论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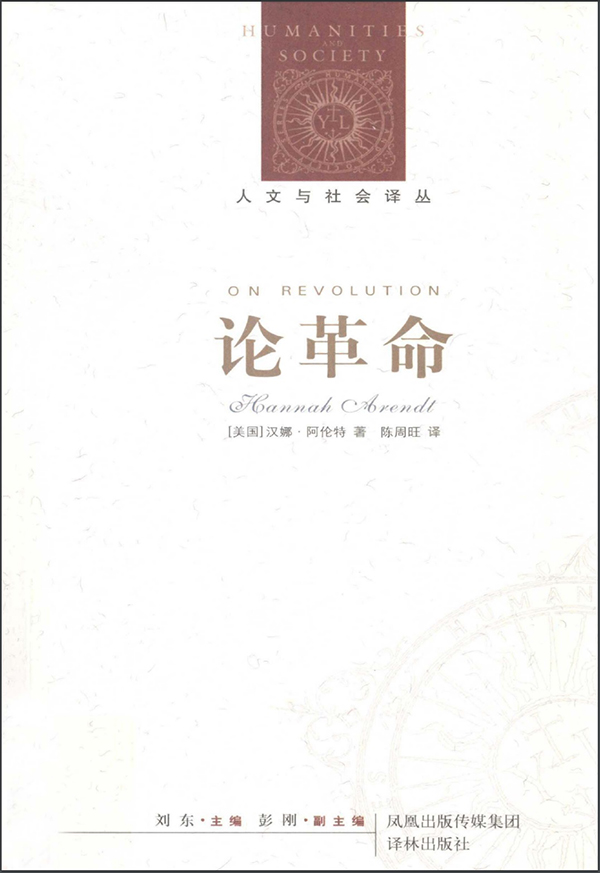
在1963年出版的《论革命》一书的最后一章中,阿伦特详细说明了她为何认为“苏维埃-委员会”体制要优于“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党:
据说,“政党最深刻的意义”必须从它们提供了“使群众从自己人中录用精英的必要框架”这一点来看。不错,正是党派率先为底层阶级成员开辟了政治生涯。毫无疑问,政党作为民主政府的独特制度,与现代的主要趋势之一是遥相呼应的,这一趋势就是不断且普遍增长的社会平等。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也与现代革命最深刻的意义相呼应。“来自人民的精英”取代了前现代基于出身和财富的精英;作为人民的人民进入政治生活,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根本就没门儿。统治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自己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少数人与生活在这个公共空间之外且默默无闻的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改变。从革命的立场和保留革命精神的立场来看,问题并不在于一帮新精英在事实上兴起了;企图否认大部分人对于政治问题本身明显无能为力且不感兴趣的,不是革命精神,而是一种平等社会的民主思维。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共空间,让广大人民有权进入,使精英从中被挑选出来,或毋宁说它在那里能够自己进行选择。换言之,问题就是政治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生涯,是故“精英”根据本身完全非政治的标准和尺度而被遴选出来。基于一切政党制度的性质,真正政治性的才华难以得到发扬,特别政治化的素质,在党派政治的鸡毛蒜皮中更难以为继,后者只要求稀松平常的推销术便足矣。当然,坐在委员会中的人也是精英,他们甚至是现代世界有史以来唯一的政治精英,他们来自人民,是人民的政治精英。但他们并不是自上而下提名的,也不是自下而上获得支持的。对于人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所产生的初级委员会,有人不禁要说,他们是自我遴选;那些将自己组织起来的人,也就是关心和拾起了创制权的人。他们是被革命公开化了的人民的政治精英。从“初级共和国”中,委员会人接着就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委员会选出了他们的委托人,这些委托人再由他的同侪来挑选,他们不受制于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压力。他们的头衔不依赖别的什么,而只依赖于平等的人的信心,这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那些投身于、现在正从事于一项集体事业的人之间的平等。一旦被选中并派往下一个更高级的委员会,委托人就会发现自己再度处于同侪之中,因为,在这一体系中,任何既定层次上的委托人,都是那些获得一种特别信任的人。毫无疑问,这种政府形式如果充分发展起来,又将具有一种金字塔形式,这当然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政府的形态。但是,在我们了解的一切权威政府中,权威都是自上而下灌注的,而在这种情形中,权威却既不是产生于顶端,也不是产生于底部,而是在金字塔的每一层中产生的。这显然可以解决一切现代政府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是如何协调自由与平等,而是如何协调平等与权威。
无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阿伦特这一具体的“苏维埃-委员会”政治制度主张,她从“共和主义”视角对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仍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最后,我热切地推荐大家观看《汉娜·阿伦特》和《罗莎·卢森》两个电影。有趣的是,这两个电影的女主角是同一个著名德国女演员扮演的,考虑到阿伦特自视为卢森堡思想的发展继承者,这样的安排是合适的。


本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改动。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