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书评︱陆蓓容:翁大人进京记
国家图书馆藏稿本《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是近来最喜欢的一部文献。它是一个矮册,封面题“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已酉正月穀旦”。若“穀旦”特指除夕之后的新年元旦,这一行字就落墨于公历1849年1月24日。其中内容确是杂物清单,并非一次写成,装订顺序恐怕也不完全正确,幸好于阅读无碍。从字迹来看,有翁氏亲笔,也有下人笔迹,还夹杂着些大大小小的奇妙单据。对照日记翻阅此书,发现这期间翁大人正好从常熟老家上了北京。那么不妨先查考事由,再顺道翻翻“杂物”都是些什么。

缘起
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督广东学政。咸丰元年(1851)以后历任工、吏、户、兵诸部侍郎、尚书等职,迁协办大学士。八年(1858)充上书房总师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他有三个儿子,长翁同书,安徽巡抚;次翁同爵,陕西、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幼翁同龢,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更兼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谥文恭。
时间倒回道光十八年(1838),翁心存从大理寺少卿任上辞职,回到常熟,奉母乡居。八年间为她送终、服丧、营治墓地。其时同书已出仕,任翰林院编修,同爵、同龢陪侍身边。他已“怡颜养志,若将终身”,似乎无意出山。
道光二十八年(1848)七月二十一日(公历8月19日),翁同书简放贵州学政,照例于次日领旨谢恩。皇帝还挂记着家居不出的翁心存,问道:“汝父岂终不来乎?葬事将以何日毕乎?”翁同书只好说,“臣父受恩深重,今葬事将毕,期以明春北上”。道光还不满足,又叮嘱曰:“汝父固当速来,汝其具家书述朕意,趣其行。”三天后,翁同书奉旨寄出家书;二十二天后,翁心存接到此信。这天的日记有云:
午初得三儿七月廿四日书,备述廿二日谢恩召见,荷蒙训谕周详,垂问微臣无微不至,敢不勉思陈力,稍申报效之忱乎?
八月十七日得翁同书信,《知止斋日记》。

于是翁大人不得不准备进京。其时葬事尚未全完,先费期月余,安排老母棺椁入土,并在墓上补种松柏冬青,然后,他终于在士绅间日复一日的祝寿、题诗、拜客、抄书之事里省出时间检点行装。这年12月10号日记,“整理大厅西厨书籍”。12日“竟日整理书籍”,至15日犹未完成。翻过年来,正月八日(1849年1月31日),还有非常令人高兴的记录。“仍料检书籍,楼上有十余年未发之箧,尽发之。得书数种,皆素以为失之者,欣如乍遇良朋也。”
也许是行期将近,朋友纷纷前来作别,翁大人已无暇应对。正月廿二(2月14日),他记下许多客人名字,因为“检点琴书”,没有时间,一概未见。约一周后,下人雇得“太平船二只”。二月四日(2月22日),翁心存与妻许氏、次女璇华、幼子同龢登舟北上,次子同爵随船送行。

据《扬州画舫录》可知,太平船是一种重檐飞栌,有小卷棚的木顶船,看来比较宽阔。《杂物目》中夹着一张船钱账单,写明“太平船户陈万全、周瑞麟”,水程由常熟至清江浦计十一站。翁家需要支付“水脚大钱”、“神福犒赏”、“灯旗洋钱”和饭钱共四十五千九百文。
此外,还有数页“托带信件”清单。过去邮传未便,寄信多靠私人关系,托翁心存带信带东西的竟有三十多位。若只寄信,就写“某人寄某人一函”。若另外捎带物件,再加小字注明。譬如“梁光甫寄蔡薇堂太史一函,外于术一匣”,薇堂二字外复有小圈,并标“绳匠”二字,料来蔡征藩当时住在绳匠胡同。郭孝虎寄沈兆霖信,附有碑刻一包;章铁珊寄吏部陈柳萍信,附送“南腿一肘,漆皮一匣”。此外尚有带图章的,带书画的,带银子、马褂、皮袍、袜子、衣料、竹篾、茶叶、水烟的,都不算稀奇。最引我注意的是“汪克昌寄潘中堂太太燕窝一匣”,不能不略为查考——“潘中堂”即潘世恩,“太太”出自吴趋汪氏,而汪克昌又是潘家的孙女婿。

燕窝
至此不难判断,这本目录是翁家进京杂物清单。但如何证明翁大人随身携带了它?“托寄信件”部分又帮了忙。在“张约轩寄但运使一函”下,写着“二月廿二日已交”。检日记,这天船才开到扬州,翁心存进城看望阮元不值,转而“晤都转但云湖前辈,谈良久”。都转、运使,都是“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这个官职的省称;看来“已交”二字应该写于见面之后。
日用品
托带之物惟恐混淆,偶尔会标出放在哪一箱里。譬如“汪墨仙寄程覃叔袍褂料一包”,注明“在第七号衣箱内”,而七号皮箱中确实有“汪寄程绸缎包一个”。可是那写“十七号衣箱”、“五十一箱”的,在存稿中遍寻不着,可证此书恐怕已非全帙。在现存部分之中,一至八号衣箱和一至四号书箱誊写比较清楚。另有“大被囊”、“木匣”、“棕帽盒”、“小棕箱”,可能也带到北京,但没有编号;至于开头的几只“新添皮箱”、“新添皮老虎”、“高州皮箱”,则由另一笔迹书写,并明言记录时间已在咸丰元年九月。
我们只翻带到京里的东西,先说八个衣箱。其实衣服衣料而外,还有书画、配饰,也偶有“桌氊”、“浴布”、“月宫帐”、“薙头衣”这类日用织物。可惜这部分页面装订舛错,只能大概罗列一二。且举内容比较完整的“陔华吟馆第六号皮箱”为例,里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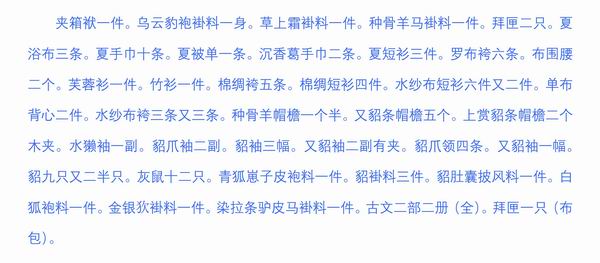

不提“上赏”,这些东西也足够富贵逼人,只是不太能唤起视觉想象。三号衣箱内的一批则要炫目得多,“二蓝”、“天青”、“宝蓝”、“月白”、“元(玄)色”、“本色”、“湖色”、“红”、“泥金”、“金酱”、“库灰”,诸色纷呈。配饰杂件则有“大荷包”、“水晶烟壶”、“玉飘风轧”、“翡翠烟筒嘴”,以及雀脑、金珀、绿松、椰子各种朝珠。又仆人所书帽盒一页,内收“四品朝顶”、“老爷帽袱二块”之类,还有“叔记金顶一个”,“叔记棉小帽一顶”,翁同龢字叔平,此次随同上京,偶有几件东西放在父亲箱子里。
二号、八号衣箱中还有些衣服,可能工艺复杂。例如“酱色湖绉大毛麦穗一裹圆”,“天青线绉小羔皮珠儿毛出风褂”——应该都是男装。整部《杂物目》中,确知属于女性的东西实在有限,三号衣箱内有“天青实地纱顾绣朝裙料一身”,小字注明“连片金全”,是一例。另一例收在“旧花布包”内,睹之不忍,是“包脚布五、脚布四”。
再说木匣,放了这些东西:
鼻烟四瓶。茶碗一只。茶盅三只。锡茶船一只。锡茶盅连底(?)盖二只。金涂塔一座。宜兴茶壶两把。宣德炉一座连底。又一个(方)。小香炉一个。自用端砚两方。磁笔洗一个。铜小椎(?)一个。
这一匣子简单的茶具、香炉和文具,恐怕不是家用配置,而是路上临时顶事儿的。在实用工具之中,纸笔簿册也与文事相关。最后一个书箱里有“诗笺二匣”、“大笔一包”、“笔二匣”、“折子一包”,也许进京后就要派上用场;“小棕箱”里则有“笔二匣”、“叔平笔一匣”。翁心存沿路不断停泊拜客,朋友也常常登舟回拜。闲暇之际,他一直在写信、写字,既了却公私事宜,又打发漫漫长途。若无茶碗香炉,再不带笔墨纸砚,这一切都无法进行。我们今天以为“风雅”的事与物,当时却不过寻常习惯无从割舍。
艺术品
行李既定,轻舟已发,终于可以暂抛尘事,看看书籍字画。这就先谈谈我较为熟悉的艺术作品。它们散在衣箱与书箱之中,但纯粹的艺术品数量实在有限,倒很有些具备实际意义或功能的作品。比如三号书箱中有“秋允公画扇面”、“迂伯公尺牍册”、“梅岑公书小横披”、“芳庵公书议单”等条目。因不便查《海虞翁氏族谱》,仅据翁同龢《石梅先祠记》探知翁振翼、翁是平两位,皆是康雍时代的翁家先人。另有《铁庵公墓志铭》一卷,则是康熙十五年(1676)探花翁叔元的墓志。先人手泽不可遗失,故而随身携带,它们的价值并不一定在艺术上。书籍方面,《家录》《家谱》《铁庵公文集》《翁氏乡会试墨》这些东西,也都是一样的道理;更有《翁氏世系墓图》,可能是一种标记墓葬所在的实用图。
在那收了两匣子笔的小棕箱里,有“赏扇六把”和“裱好对二付”,使人想起白谦慎教授的研究。他在很多场合演讲,都谈到对联与扇面是晚清应酬书法的主流。对联本身的形式带有一定的礼仪性,扇子从明代开始就几乎是士人阶层的必须品,同时也是一种礼物。晚清士大夫之所以大量地写这些东西来送人,主要还是因为快。比画画快,自不待言;比认认真真写幅字,其实也要轻松得多了。他甚至在翁同龢日记里找到材料,称其同治七年(1868)初冬某日,“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脱”。

以扇、对为礼物,不止可以送给朋友,也还能打发下人,此所谓“赏”。这些东西放在今天自是作品,可未必立即就有艺术价值。书箱中尚有成亲王、冯承辉、汪绎诸家对联,早至康乾,倒像是作为收藏品买回来的。
撇开这类东西,我们来看看为数不多的古今字画。各个衣箱中有以下这些作品:
蒋文肃《梅花》。董其昌画一轴。许南郊画一轴。蒋虎臣等条幅四轴。王麓台画一轴。王石谷《夏山图》一轴。刻丝佛像一轴。王石谷画一轴。周西村观音像一轴。马扶羲《杏花春燕》《枇杷》各一轴。乾隆御书一轴。庾唯亭《梧蝉》一轴。钱叔宝山水一轴。戴文俊山水一轴。麻姑一轴。陆包山假山一轴。
书箱中,则是:
杨子鹤花鸟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赵承旨《江山秋霁图卷》。陈居中《射猎图卷》。董文敏行书卷。元二名家墨迹卷。苏东坡《表忠观碑》墨迹卷。王雅宜行书卷。刁戴高《临千字文》册。蒋南沙书册。孙雪居画石册。潘作梅书《绵津山人怪石赞》册。成亲王临赵松雪《归去来辞》册。董文敏山水横披。陈白阳书《赤壁赋》卷。赵文敏书《景福殿赋》卷。王右军《月半帖》卷。文衡山画册。赵文敏书《老人星赋》册。黄石斋先生墨迹册。赵千里《江城晓霁》长卷。赵庭柯书卷。文伯仁书卷。陈老莲《三友图》卷。杜陵内史画一轴。覃溪楷书《密州题名跋》一轴。查士标画竹石一轴。王椒畦画红梅扇一柄。
这点东西肯定不是翁心存全部的家底。放在晚清书画收藏的大背景下,它们也不怎样出挑。可是仍然有些细节值得一说。首先是乡邦。清代作者中,蒋廷锡谥文肃、号南沙,许南郊即许永,马扶羲即马元驭,杨子鹤即杨晋,更有石谷王翚鼎鼎大名;此外,唯亭是余省的号,此处姓写为“庾”,当是误书。这些人的籍贯若非虞山,就是常熟。概略言之,两个地名都指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在翁氏家族看来,他们都是乡贤。
清初以来常熟地方画家辈出,山水方面,王翚及其弟子开数代风气;花鸟方面,有一支继承恽寿平风格的流派,又有在此基础上愈加精雕细琢的清宫供奉画家。以上诸家几乎都在这个范围里,不过彼此声望悬殊。翁大人把他们和早期名迹一起携带上路,心中恐怕很有些乡情。若再看书箱中的抄本《虞山先哲图跋》《古虞文录》《虞邑遗文录》《琴川志注》,校本《毛刻琴川志》等书,当亦能对这种士大夫间普遍存在的情感多些认识。
其次是早期名迹。以前我曾略微讨论过晚清时期的所谓宋元古画。具体情况琐碎庞杂,这里只能简单概括。相信自己的藏品是真迹,不代表它一定是真迹,这是常识;收藏某件作品,不必一定因为相信它是真迹,这背后就有错综复杂的现实。有些执念不深的文人士大夫,会因为某些作品合其眼缘而纳入囊中,可未必打算桩桩件件探究到底。也许是不能,也许只是不为。
不妨排查几幅画作。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最引人注目,只要稍微涉猎一点点书画史,就当知道它的传本非常之多,大都出自明清苏州画匠手笔,或署名张择端,或落款仇英,有的干脆无款。清初恽寿平跋一件,已称“余所见《清明上河图》凡数本”,明清诗集中题此画者亦复不少。可是目前大家认为很可能是真迹的那一件,当时已随着嘉庆四年(1799)毕沅倒台而抄没入宫了。
再说所谓赵孟頫的《江山秋霁》。考诸文献,据说郭熙、燕文贵、赵雍、王绂都曾画过,入清尚有宋葆淳、张宗苍、慎郡王诸作;征乎实迹,董其昌作品至今可见,自称仿黄公望画风。但是没有看到哪里说赵孟頫画过它。所谓赵伯驹《江城晓霁》情况也差不多,清初顾复《平生壮观》曾记一件宋人之作,附在唐人李思训条目下;晚清潘正炜则收藏了一套王翚册页,其中第六幅题名如此,此外一无可问。排查文献这件事,限于个人视野,总难免挂一漏万,但至少可说它们不是流传有绪的名作。

翁心存对收藏肯定有些兴趣。就在“检点琴书”,准备出发,无暇见客的正月廿二那天,他还在卖家手里看了一件所谓范仲淹书王建《宫词》,说原作“不敢定其真赝”,后跋“恐是作伪者所为”,两个书签“亦未必真”。看来并非全然不加讨论,只是未必想到查考流传。
我翻过晚清各家书画著录,也检点过若干并未公开的私家目录和账本,总觉得气氛有点儿混沌。这不是借着后见之明发出批评,而是要说收藏活动的边界日渐模糊。它和著录的关系已经可近可远,古今界线渐渐不存,人们讨论书画的方式也与从前不同。在这样的空气下,普通士人仍然会具备些相关知识,可这知识同样难免模糊。“不能”考察真伪,或许受限于能力;“不为”考证之事的,或许朦胧知道结果难堪。
翁大人的态度无从推知,只不过,在早期名迹最多的第四号书箱里,居然有一纸“张真人避火符”。
书籍
回过头来说书籍。翁家正经体面人家,书以经史为主,添几种名人诗集,稍加一点毫不出格的奇门遁甲。有些条目下批了一个“阅”字,不知是否路上翻读。笔记小说尚且没有,不上台面的更找不着,幸而还很有些特别的。
第一号书箱中有抄本《火龙神器阵法》一册。这是明代的火药火器技术书籍,传为洪武年间焦玉所作,流传甚稀。这一本该是亲自抄成,只因抄件现存国家图书馆,且有翁同龢题“先文端公手钞,子孙谨守”字迹一行。书虽不大,内容不少,有兵器名目、火药制法,有托名姚广孝制的行军保命丹方子,还带着些独特的插图。据翁同龢跋,道光庚子(1840)兵事骤起,六月间洋舰进犯福山港,兵未登岸而市井一空。翁心存束手无策,抄了这书,是泄愤,是寄望,恐怕也是一个赋闲文官谈兵报国的心志。

《火龙神器阵法》里的图和翁同龢跋
这一号书箱里神奇之物实在不少,譬如《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两个抄本静静挨在一起。检日记,均是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廿八日(1848年6月28日)从湖州书估手上买得,只写“旧抄本”三字,或非名贵,后来似亦没有再谈起。此外又有《契丹国志》校本一部,不知是否亲自为之。
但凡略知一点乾隆修四库的八卦,恐怕都听过这两个题名。乾隆四十六年(1781),文渊阁四库全书誊写将毕,皇帝抽阅《契丹国志》,顿然触动神经。辽金史问题关乎大清的正统性,那是万万错不得的。当下《大金国志》也受牵连,两种书都被抽出来单独改纂。我查了查这两种书的传世善本。在清代,前者至少有一个元刻旧本,又有毛氏汲古阁抄本;后者至少有明天一阁抄本。到翁心存的时代,两边版本数不胜数,各有许多明清无名抄本,又都还要加上四库本子,再加流波广被的扫叶山房刻本。虽然清中期怀挟禁书有些危险,可是,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之下,仍旧想猜这两个抄本未必遵从四库官书。毕竟,同为禁书的“待访录”抄本也安居书箱一隅。
替翁大人翻检书籍实在不易,只是话头远远没完。二号书箱里收有不少书,大都难得。譬如《重续千字文》,写明“影宋精抄”。此书宋人撰,仅汲古毛氏著录刻本,后亦不传,但毛抄尚存。嘉道间虞山陈揆稽瑞楼又抄两本,其中一本再转归铁琴铜剑楼。这三种在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里都能查到。翁家部分书籍原是稽瑞楼旧藏,不知此本是否也在其中——很可惜,资源库中三种似乎并无翁氏印记,而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称翁同书曾抄此书,亦未知是否曾经目验。

稽瑞楼、铁琴铜剑楼递藏影宋精抄《重续千字文》
另一种残宋本李德裕《会昌一品制集》,非常出名,许多版本学家与文学研究者都已讨论及之。此书可能由翁心存传给翁同书,转翁同龢,经翁曾翰、翁安孙、翁之廉而入美国翁万戈手,并于2000年4月28日随另外七十九种翁氏藏书一起入藏上海图书馆。在窥探翁心存进京之旅的过程中,它对我产生了莫名的吸引力,只因许多人记述翁氏文献,都说一百五十年间,它曾是“存没难知”。
如今翻翻《杂物目》,再翻翻日记,却能看到它怎样安坐箱中,从常熟上船,渡过长江,渡过淮河。在淮阴王营登车,由山东德州,经河北沧州。直到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六(1849年4月18日),“发黄村,过丰台,入右安门”,来到宣武门外兵马司中街。终于在官房寓邸里住定,陪翁大人继续下半场宦海生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