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年度阅读︱在“例外状态”中寻找知识的“稳定之锚”
疫情后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状态》(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所讨论的情形来形容。所谓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者用一个更常见的说法——“紧急状态”,指的是权力在一般性的秩序被悬置起来后恢复了其完满的特性,而秩序与法则变成空虚的状态。疫情这只“黑天鹅”所导致的“例外状态”是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人们在回想起2019年时,仿佛在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这或许就是“例外状态”对我们身心造成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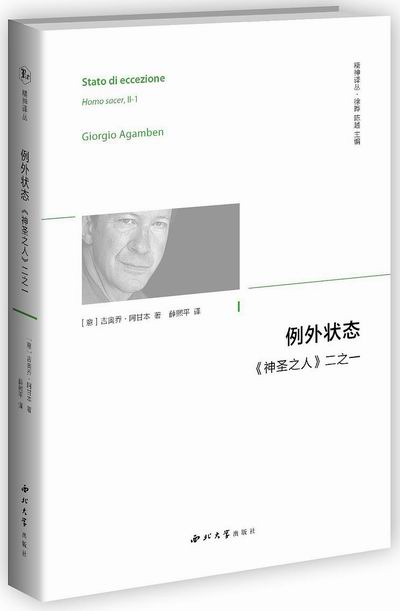
尽管“例外”是“常态”的对立面,但是当“例外状态”持续到第二年时,所谓的“例外”本身也就成了“常态”了。2020年若尚给人某种“新鲜感”的话,那么2021年的生活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内外的重压。这种重压不仅仅是经济压力下物质生活层面的“消费降级”,还表现为在急速变化的局势中找不到稳定精神依托而导致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在这兼具旧秩序崩溃所带来的混乱与新世界诞生之可能的例外状态中,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又应当如何行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理解崩溃中的旧秩序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最长远和宏观的角度看,旧秩序首先是14-15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可以算是对此最凝练的概括之一,他对“万物商品化”过程中充满辩证意味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讨论发人深省,也对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中家庭支持下的青年劳动者的行为模式具有启发意义。华勒斯坦的作品固然精要但也失之过简,扬·卢滕·范赞登的《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更为细致地从利率水平、市场环境构建、出版业、婚姻年龄等社会层面描绘出中世纪的欧洲如何走向工业腾飞的“漫长跑道”。当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时,才能理解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的论断“资本主义并不根植于某种超越历史的自然规律”。伍德在书中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史讨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靠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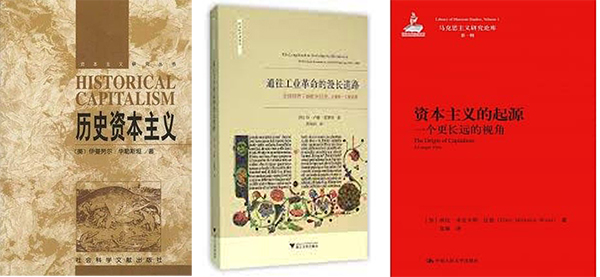
上述作品关注的都是宏观过程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劳伦斯·斯通的《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商务印书馆,2017年)则聚焦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探讨了中世纪彼此关系疏远的开放世系家庭如何在宗教改革时代完成“圣灵的家庭化”,并最终形成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重视成员纽带的“封闭的核心家庭”。这一过程不仅是观念的转变,更是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迈克尔·米特罗尔在《欧洲家庭史:中世纪至今的父权制到伙伴关系》(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就强调,生产过程从家庭手工业转向集中的大工厂加速了家庭的小型化和成员关系的紧密化,这种紧密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代死亡率,进而为工业化提供更充足的劳动力。家庭模式的变迁便以此和生产方式联系在了一起。Keith Wrightson的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J. A. Sharpe的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Arnold, 1997)则将家庭、人口、土地、犯罪和贫困等要素编织成一张相互作用的紧密网络,为我们理解英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度转变为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俯瞰的视角。

同一时代的中国也绝非一成不变的“木乃伊”。易劳逸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重庆出版社,2019年)以优美的文笔概述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面向。高王凌在《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则着重讨论了乾隆在控制粮价问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手段,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前现代国家遇到了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在此展现的活力绝非一句“封建社会”可以抹杀的。事实上“封建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形而上的概括,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就极为细致地分析了“封建”这个词是如何被泛化乃至滥用的。若结合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中对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的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许多我们今日熟知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

资本主义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资产阶级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维度:从近代早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最终成型的现代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尽管宣扬“主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却从诞生始就充满了地理空间上的霸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色彩,正如刘禾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中所总结的那样:“人类社会的空间差异被整理为时间(历史)差异,而文明使人类社会趋向于一致(这同时也是资本的要求),这导致一种全球行为准则的诞生。比如在边界问题上,军事手段被条约所取代,模糊边境被精确边界取代。”

在新的理念指引下,如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所描绘的那种充满幻想与奇异关联的中世纪世界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近代大帝国永无止境的掠夺与扩张。在海洋上,有桑贾伊·苏拉玛尼亚姆在《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实践;在陆地上,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两卷本《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则是描绘帝俄兴衰的恢弘巨著。俄国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就几乎可以与领土扩张画上等号,这一趋势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才真正得到实质性的遏制。奥兰多·费吉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极为细腻的笔调为我们呈现了这场充满了狂妄、愚行与肮脏的战争。英、法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却不过是用自己的拙劣表现成就了世人皆知的南丁·格尔,但南丁·格尔很大程度也不过是沾了英语话语霸权的光。人们只记住了南丁·格尔,却不知道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他发明了“伤员分流系统”并且广泛地采用乙醚麻醉,使自己手下的伤员存活率高出英法两倍有余。克里米亚战争所象征的西欧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对抗不仅是政治-外交层面的,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奥兰多·费吉斯的另一本作品《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就着力描述了俄国文化中“西方性”与“俄国性”之间持久的冲突,到了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对冲突中又加入了俄国的“亚洲元素”,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俄国文化永恒的内在张力。

当然要论帝国扩张史之最,俄国还是难以和大英帝国相比。一般而言,人们把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看作是英国取得海上霸权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加勒特·马丁利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华文出版社,2019年)却告诉我们,事实上英国海军不仅在质量上,甚至在数量上都强于西班牙海军,所谓的“无敌舰队”更多的是西班牙人讽刺的说法。只是英国人自我包装的能力太强,才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以弱胜强”的印象,这也是英语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有太多的作品致力于将不列颠民族崇尚的实力政治包装为正邪斗争,如巴巴拉·W.·塔奇曼的《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本·威尔逊的《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的《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都是类似的作品。尽管我们在阅读时应批判其中关于英帝国描述虚伪一面,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书籍如何将霸权构建得“合乎道义”,对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而言,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课。

要从学理上理解英帝国的扩张,Ronald Hyam的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Palgrave Macmillan, 2002)和C. C. Eldridge 编纂的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4)是更好的选择。前者是关于英帝国扩张原因和特点深入浅出的总括,后者是分析这种扩张对英国社会与殖民地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对于英帝国而言,印度无疑是其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然而在英国殖民之前,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曾有着辉煌的历史,贾杜纳斯·萨卡尔的《皇位之争:奥朗则布和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生动地叙述了莫卧儿极盛时代的君主奥朗则布青年时代直到掌握权力的精彩故事。然而奥朗则布自身的赫赫武功却反而成为其统治印度之薄弱的证明,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各处平叛以及抵御萨法维波斯的入侵,这种高度不稳的统治结构在奥朗则布死后导致了莫卧儿的分裂,英国才能以东印度公司为媒介趁虚而入。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是了解东印度公司的浅显入门作品。那些在印度成为暴发户的英国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的政治,这与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对商人通过捐纳而进入中国政治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在东方掠夺的不仅有财富,还有艺术品,马娅·亚桑诺夫的两卷本《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就生动地告诉我们那些大英博物馆中的藏品到底是怎样用各种暴力与卑劣的手段运到英国的。

英帝国的模式既吸引了崇拜者也造成了敌人。沃尔弗拉姆·希曼在《梅特涅:帝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就指出了英国模式对于这位奥地利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强烈影响。而安德鲁·罗伯茨的《拿破仑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则是这位英国人最大的敌人的上乘传记。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敌友,我们也应当关注更为隐秘层面的抵抗。例如迈克尔·卡瓦斯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就讨论了走私者如何抵抗本垄断与国家专卖的研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讨论了地方结构对政府权力扩展抵抗。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亦可视作近代社会面对不断扩张的“大政府”的反弹,无论这个政府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这些抵抗者所代表的暴力传统与鲁大维在《神武军荣耀天威: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和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结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所强调的那种崇尚荣誉、服从、等级与秩序的官方暴力文化迥然不同,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对抗冲突也是18-19世纪社会秩序演变的重要议题。

历史最终证明,有组织的国家暴力终究是更胜一筹。但是暴力作为手段则必须服从于更高层面上的价值理性,否则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便很可能如韦伯所担忧的那样是理性本身走向其反面。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所描绘的战前欧洲社会就如同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一样陷入非理性的残忍狂喜之中,是人们成为祭品而不自知。这种癫狂既是心灵层面的,也有赖于药物的使用。诺曼·奥勒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中就指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从元首到普通士兵都大量依赖被称为“帕飞丁”(parvitin)的冰毒才能维持战争所需要的亢奋状态。然而纳粹的暴行却又是高度理性化的,克里斯托弗·吕康在《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就以葡萄酒为例为我们呈现了高度理性化与系统性的战争掠夺是如何实践的。

正是纳粹的这种疯狂与理性的两面性,才使欧洲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毁灭。也正是这样彻底的毁灭才使战后的反思如此深刻。基恩·罗威的两本关于二战的反思与总结《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和《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我读过的同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罗威这本书几乎全面地网罗了二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经历战火的亚非欧到间接参与的拉丁美洲,从超级大国到流散的个人。罗威记录了许许多多人的故事,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流畅叙事,为我们带来剥去了神话色彩后“平衡”的真话,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我特别强调“平衡”是因为罗威叙述中无与伦比的对称性。他在解构战胜国的“英雄神话”的同时也不忘重审战败国的“妖魔神话”,在讨论战后的科技乌托邦设想时,也关照了社会治理中的乌托邦实践。最后再将镜头由远及近,从国家组织和超级大国一直到一般的个体,使得战争带来的影响得以层次鲜明的铺陈,其文笔的精巧令人叹服。

然而二战结束后人类构建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下被无情地击垮了,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维度,20世纪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与美国的单极格局。新自由主义如同麦克·布若威的《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群学出版社,2005年)的书名所形容的那样,不断利用人类的贪婪本性“制造甘愿”,并使人异化。这种异化既造成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提出“虚假的阶级意识”,同时也如乔治·里茨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提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而甘愿受到物的奴役,进而成为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贪婪滋养出了最令人炫目的企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大概就是那些所谓“军工复合体”。尼克·图尔斯在《复合体:军事如何入侵我们每日的生活》(后浪出版集团,2021年)中指出,这些复合体不仅制造了最具毁灭性的武器,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日用品的供应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才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大到不能倒”的超经济影响力,同时这种影响力也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但仅仅是暴力绝无法成就霸权,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学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麦克尼尔的《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就以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为案例,为我们勾勒出美国大学在二战期间如何从老欧洲手中夺取学术领头羊的地位的过程。对于挑战者而言,了解对手,学习对手的优势并最终超越对手乃是必由之路,美国是这样崛起的,那么后来者也理应如是。

知彼还要知己,超越对手之路上的困难不仅来自对手的打压,也来自于内部的挑战。例如人口问题与城乡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或者个体经历的层面理解是难以得出答案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陈剑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非常详细而客观地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政策的得失,熊易寒的《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讨论了现代化运动中的城乡居民的认同是如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代际撕裂也是如今普遍存在的问题。刘岩的《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则从文化角度切入,将赵本山现象与东北不顺利的市场化改革联系在一起。赵本山所塑造的那些“丑角”身上的笑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边缘群体“跟不上时代浪潮”而造成的尴尬。许多人对于这种尴尬感同身受的体悟才使赵本山的小品借春晚这个舞台获得了“共时性”。在诸如《卖拐》这样的小品中,关于市场化的黑幕的揭露以及言语间对过去的社会主义风格的语言的戏仿让人们得以在“消费共有的过去”的同时,也意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契约理性精神和传统农村的朴素正义观之间的某种张力(这在《马大帅》中也有体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能够消费的“共同过去”越来越少,社会的分化也使人们共享的话语日益消失。春晚也因此失去了世纪初的那种影响力。

尽管我们相信新世界终究到来,届时“例外状态”也就自然解除。但这究竟需要多久,哪怕最优秀的学者也难以回答。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或许只有不断地阅读才能抓住维持自身稳定的“知识之锚”。令人欣慰的是,许多人已经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或者韦伯的经典作品,但是更多的人还是苦于缺乏必要的时间和知识储备去钻研,所以在最后,我想再推荐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尚·纽曼·杜康吉的《沙滩上的马克思,生活中的资本论》。(台湾商务,2020年)这本书以相当轻松而易懂的语调带领人们走入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没有晦涩的语言,没有冗长的书单,只有咖啡馆漫谈式的娓娓道来。若这本书能够带领人们真正走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而通过阅读原典而真正理解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那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