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玲娜贝儿们的“钞能力”,把我整不明白了 | 湃客Talk
2021年的进度条到了末尾,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习惯回顾自己错失的机遇,忍耐父母的新一轮催婚,咽下上司的新年大饼,一句“我emo了”,框住都市年轻人的万千愁绪。
当年轻人emo了,他们的情绪出口在哪里?《湃客Talk》年终特别策划,联合优质创作者和资深学者,探求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学历、住房与婚恋难题。

滑至文末查看播客时间轴
出道还没三个月,玲娜贝儿愈发膨胀的“钞能力”,已经把不少人整emo了。
12月17日,玲娜贝儿的限定款补货发售。“好妈咪”们携着钞票奔向迪士尼,终于买到原价219元内的“宝贝儿”。然而黄牛蹲守店外,打算以8倍价格收购,再以10倍数额卖出。
在过度营销和炒作之后,川沙女明星的新一轮“下头”风波正浮出水面。雷同的热潮今年还有很多,盲盒、球鞋和国货,都重复着相似的巅峰和低谷。我们试图回归玲娜贝儿的本质——消费品,以及孕育它们的消费主义。
让我们上头的消费浪潮,背后的精神诉求是什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非要靠买来获得满足?《湃客Talk》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和湃客号·新消费智库创始人王静静。他们认为,痴迷消费品的本质是社会公共性的衰落,人们投射情绪并建立身份认同。而资本在刻意制造成瘾产品吗?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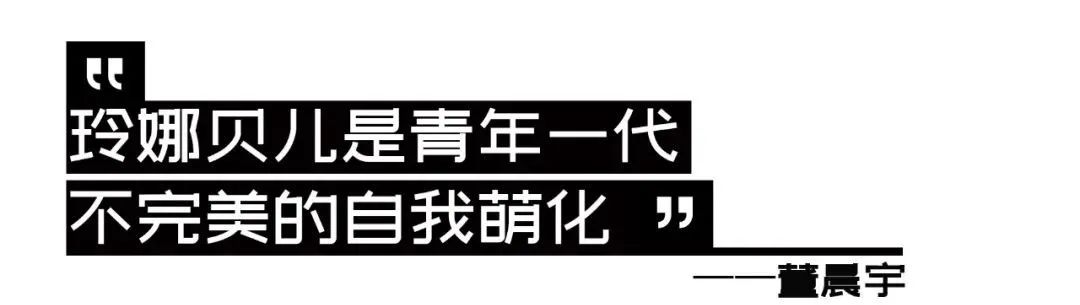
实话实说,我是因为参加《湃客Talk》的节目才开始关注到玲娜贝儿。这几年特别火的消费品,或者说消费形象实在是层出不穷。作为一个研究者总感觉在被新现象拽着走。
以前戴手串代表着一个北京老大爷的形象,玲娜贝儿就是青年一代的手串,只不过换了一个样子,意味不完美的自我萌化。
为什么不完美?玲娜贝儿不是以一个很乖的形象出现的,她有自己的脾气,甚至有缺点。中国青年群体希望看到的是不完美的东西,不完美意味着真实,真实意味着离他们更近。
“自我萌化”也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每年六一儿童节,很多成年人拼命地把自己和这个节日联系在一起。这也回应了一种社会心态,他们有焦虑感,不想长大,借节日契机把自己重新领回童年。

上海迪士尼乐园里背着玲娜贝儿周边产品的女士,还抱着另一位达菲家族成员“杰拉多尼”。
把情感投射到玲娜贝儿身上,在社会学的研究当中也被称为“物作为一种自我的延伸”。当我们和玲娜贝儿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放纵自己成为与她相似的一个存在。这是很重要的购买、消费以及占有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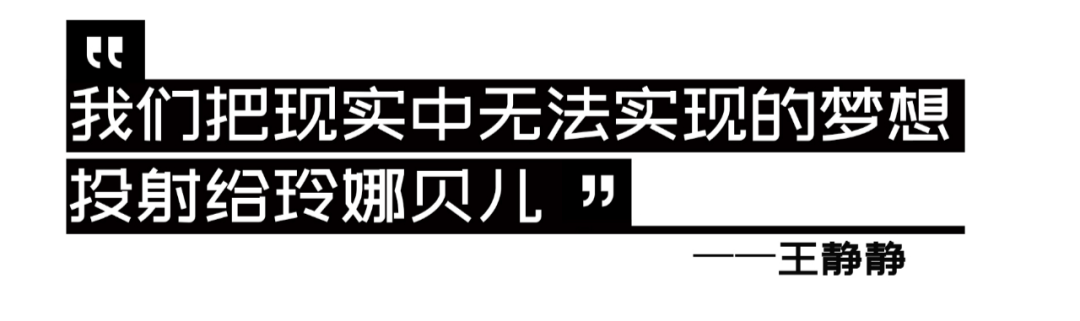
今天的年轻人在社交关系里比较孤独,需要一个东西给予陪伴感、治愈感。
在现实中找不到像玲娜贝儿这么可爱的事物。你对现实世界里的人抱有想象,但是这个人不一定给你正向的反馈,刚好这个虚拟形象能满足自己的期待,无时无刻都按照你设想的方式回应,就可以把很多的爱释放在这个形象里面。
所以人们就把很多的情感投射给“玲娜贝儿”们。就像我买艺术画的朋友,画中是个非常悲伤的人物,我问为什么,他说最近情绪状态不好,而画里的人物好像是自己的一种情绪表达。

2021年12月17日,上海迪士尼玲娜贝儿节日系列产品发售,引起哄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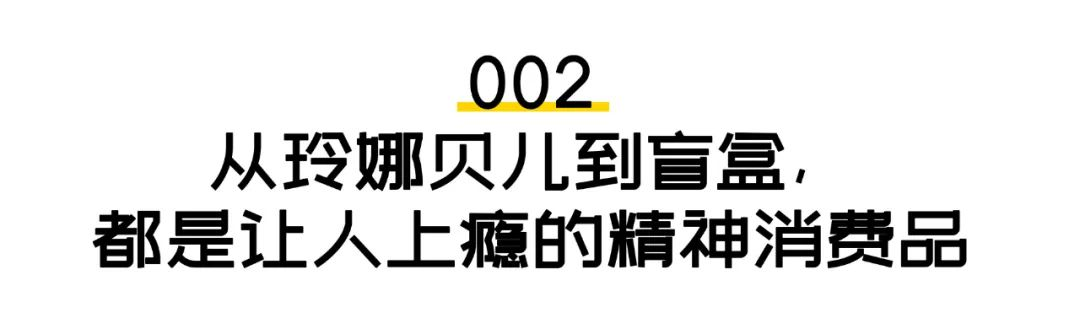

除了为玲娜贝儿上头,还有很多年轻人热衷于买盲盒、炒鞋、买艺术品,本质都是感兴趣,有钱就去买更贵的。
进一步研究,我们也会发现这些人买完盲盒会干嘛?现在流行一个生意叫“盲盒柜”,把买来的所有盲盒都通过柜子展示起来。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有一定的社交属性,或者叫社交货币的属性。通过购买这个东西来达到个人价值的彰显,显示我是有生活情调、有艺术品味的,我要去收藏这些东西。
而且每一种精神消费品里都有部分“炒家”,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有升值空间,可以赚钱,类似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所以这个市场里面有一部分是兴趣用户,一部分是投资用户,剩下的是兴趣混合投资。

2021年4月,一名音乐专业学生展示她收集的“盲盒”玩具。

盲盒和玲娜贝儿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购买盲盒的时候,你不知道买的是什么。它通过非常精妙的设计,把购买和赌博机制放在了一起,使人变本加厉地上瘾。
我们研究圈里的曾新老师写了一篇关于盲盒的论文,他引用了《追忆似水年华》的一句话,“唯一有吸引力的世界,是我们尚未踏入的世界”。打开一个盲盒之前,我永远觉得它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就是在这种期待当中,而不是你获得盲盒里的玩具之后,你的多巴胺的分泌是最旺盛的,这种快感不断驱使人们去回购。
购买行为背后还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可以从“身份认同”和“参与式文化”来看。举个例子,娃圈的人,会把彼此称呼为“娃友”。这种称呼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可以归类为一种认同标签。
一个人去买盲盒,我无法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有很多人跟我热爱同一个东西,就造成身份的认同感,买这个产品会从个体的消费行为变成集体的文化行为。
还有一些盲盒艺术家热衷于“改娃”。这种人其实也并不新奇,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很多美剧观看者热衷于做周边,比如把美剧里的人物做成画册,然后去卖,这其实是侵犯版权的,但也这体现了用户的能动性,我们称之为“参与式文化”。随着互联网时代Web2.0的普及,参与式文化已经成了常态。

2020年上海第26届上海同人展(CP26),众多动漫迷参观购买手办。
一个产品想要在一个圈子里激发起更大的共鸣,要给使用者变成创作者的可能。一些盲盒经过改造之后,能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交价值。


当公共性衰落的时候,人们要逃离在家和工作场所之间来回加速的倦怠感,消费主义就出现了。
不仅是中国,全球都是如此。《The Great Society and the Good Society》里面说,社会存在三种场合,第一场合是我们的家,第二场合是我们工作的地方,第三场合是公共交往的地方。但是现代都市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被困于家和工作单位之间,在第一场合和第二场合之间来回加速运动。而第三场合,公共交往场合越来越少,这就导致了公共性的衰落[1] 。
我们通过“买买买”来去化解公共性的缺失,导致的也许是更大的孤独感和倦怠感。
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这本书中,认为早期奴隶主在不用干活的时候,要做的事是就是和奴隶区分开。为了表现阶层和品味,奴隶主吃饭用银汤勺,奴隶用铝汤勺[2] 。

古罗马时期,上层阶级向奴隶分发食物,Heinrich Leutemann (1824-1905)彩色雕刻。
所以我们要看到商品背后隐藏的阶层属性。譬如时尚往往是上等阶层来创造的,中产阶层负责追随,消费能力较差的底层负责仿制,因此有很多A货,它们的主要职责是摧毁。底层社会摧毁之后,上层阶层要开始一个新的时尚,时尚的循环圈就这么绕起来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购买产品的符号价值。

很多品牌也在营销中塑造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商业里面统统把这种品牌叫作“生活方式品牌”。
一些消费品牌只满足于一个功能属性。举个例子,我和董晨宇都戴眼镜,眼镜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看得更清晰的工具。所以一个眼镜品牌可能不会有态度的表达,它要强调的是功能、质量和性能。
但是随着市场供给越来越充分,有一类品牌不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买一个奢侈品包包真的是用来装东西的吗?为什么不买一个编织袋去装东西?买它其实是为了证明我的社会地位,证明我有财富获得的能力,有一处优于别人、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日本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疯狂的消费主义,无印良品这样的品牌是在那一波风潮后诞生的。逐渐地,大家不要消费主义了,不去买特别贵的奢侈品,而是去买平价替代,买价格便宜的平价服装,这也是一种消费的“反向彰显”。

2021年,驻足日本大阪市中心的女士。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轻一代出现“低欲望消费”的趋向。
不是没钱的人才会去买优衣库,很多有钱人也去买优衣库,他们为什么不去买奢侈品呢?因为很多人会给一个负向的评价,“你只知道买奢侈品”。这个时候他又需要用不同的观点来彰显自己。

有一些行动者希望做到No-brand,没有品牌,发现这件事情是无比之难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符号性的经济体系里,你要与它割席,无异于寻找桃花源。
王静静提到的“反向彰显”,传播学里称之为“文化杂食”,上层开始杂食中产或者底层的消费品。这种杂食或反向彰显,往往是上层对下层的。比如说我很有钱,买得起不知道多少个LV,但是我穿一身优衣库。下层对上层是无法反向彰显的。
我们看似从消费主义过渡到极简主义,如果消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极简主义又何尝不是呢?当你抵抗消费主义、选择极简主义的时候,你又何尝不是被极简主义所收编呢?
约翰·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写道,他问学生为什么穿牛仔裤,学生说因为它象征着反叛和自由,尤其对商业主流文化的反叛。Levi's看中了这个机会,开始把牛仔裤的生产品牌化,因此反抗变成了收编。但反抗和收编是一个不断的循环,这其实反映了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之间不断的博弈[3]。

1983年,穿着牛仔裤跳舞的英国青年。牛仔裤曾是反叛与牛仔精神的代名词,今天被作为基础款的时装搭配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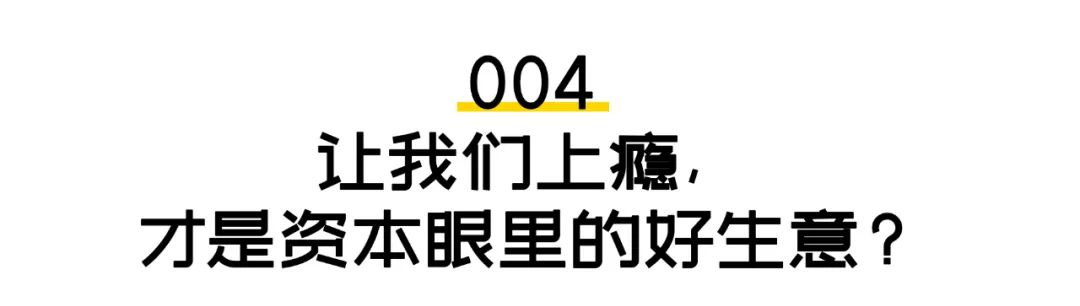

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客观存在的,我不太喜欢“商业塑造了上瘾世界”的说法。
首先说企业的本质,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做商业肯定要赚钱,它需要通过利润扩大生产,再有更大的资本去改良它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
营销学的理论开创者菲利普·科特勒提到“扫描市场环境”,他首先说的就是政策的影响、社会的影响。企业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天然承载着一部分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所以要接受社会对你的批评,也应该去承担部分的社会责任。
但是企业承担的责任有一定的边界性,到底要承担多少,哪一部分属于是企业的责任,得先框定边界值。如果说企业做了社会应该做的部分,或者是社会反过来,做了企业应该做的事情,都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匹配和交易效率。
我自己还很喜欢一本书,叫《上瘾五百年》,讲了人类几千年来就有烟酒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4]。

1933年的美国,人们为禁酒令解除举杯庆祝。
这些产品诞生的背景有各种各样的逻辑,比如咖啡在最初被作为药物使用,在宗教仪式里喝它,能让大家有一种精神上的提升感,然后人们慢慢发现咖啡是可以上瘾的。
我们为什么会上瘾,是由于这件事带来了快乐,人分泌多巴胺或者获得快乐的方式非常不一样,有人通过烟酒茶,有人通过刷抖音。我认识的很多新消费公司创始人对经营公司上瘾,认为挑战这种高难度的事能获得巨大的快乐和价值。
上瘾这件事涉及到未成年人会不一样。青少年的思维模型还没有定型,玩游戏、玩抖音、买潮玩过多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危害。这需要国家更好地去规范,不太可能靠企业自身的道德感去约束核心的用户客群,因为他们还是以一二线城市的白领为主。
所以我觉得例如“建议限制未成年人购买盲盒”这个措施本身的出发点很好,可能会让行业更规范,不一定是坏事。

我不喜欢“上头”或“成瘾”的概念,为什么我们不担心大家学习成瘾?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家长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管一管,读书上瘾了。
我更愿意把“上瘾”替换成传播学研究中的“问题性使用(Problematic-Use)”。你的使用方式有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比如说我逃避现实,整天泡在网吧里是一种问题性使用,资本可能鼓励这种行为,至少希望通过过度使用(Overuse)来增加流量。很多年前,谷歌就已经爆出这样的丑闻,它声称自己不作恶,但却不愿意改变Gmail使用中的成瘾机制。
资本所需要的是流量,而流量的基础就是用户要投入、要沉浸。政府部门为什么要求王者荣耀实行青少年模式,要求抖音实现青少年模式?因为我们无法放任企业或者资本来去追逐利益,即使它是合法的。

2019年12月24日,深圳,瘫坐着玩手机的青年。
社交媒体提供给我们自我表达和交流的机会的时候,也完全没想到会有大量的人互相谩骂、憎恶。
社会性规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从来不会投入到对“问题性使用”的抵抗之中。这是我们无法期待的一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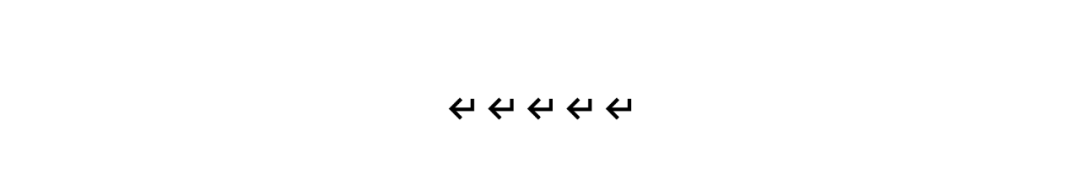
2022年,不想再为“钞能力”浪费生命?
来看看两位嘉宾摆脱emo的小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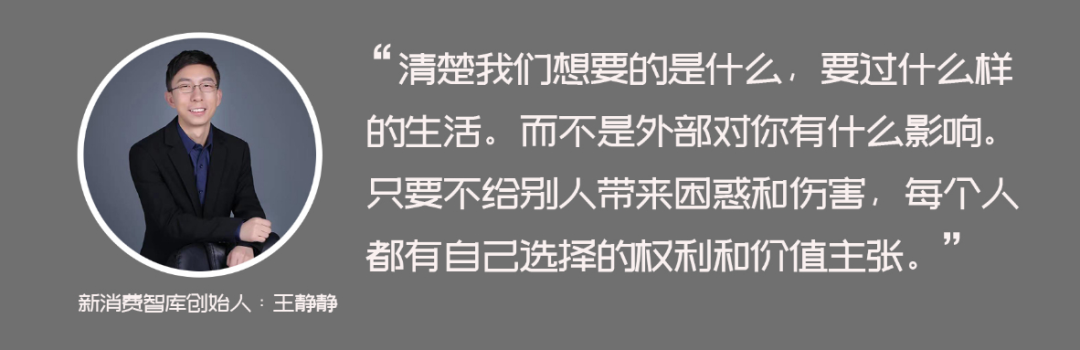
【时间轴】
03:25 现实中哪里找玲娜贝儿这么可爱的“人”?
05:56 我们爱玲娜贝儿的“不完美”
07:25 盲盒、炒鞋、艺术品,拆解年轻人的消费心态
10:11 怎么合理化花钱的行为?找同好,搞同人,个体消费变成集体文化
12:35 添加赌博机制的盲盒,让“上瘾”变本加厉
14:45 人类天性追求快乐,商家察觉大家对多巴胺的渴求
17:06 传播学概念里,“上瘾”是一种“问题性使用”
24:00 互联网带给我们什么?
25:51 社会公共性缺失,“买买买”无法化解大众的孤独和倦怠
31:05 商品也能区隔阶层:上层制造,中层追随,底层仿制
33:44 平价替代也是一种“反向彰显”
36:30 用极简主义抵抗消费主义,何尝不是被另一种主义收编?
39:27 企业承担的是有边界的责任
40:58 资本解决社会问题,也带来更多“负”产品
42:18 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才能更好地做出选择
43:12 延迟满足会带来更大的价值感
注释:
[1] Qualter T.H. (1980) The Great Society and the Good Society. In: Graham Wallas and the Great Society.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 凡勃伦. (2011). 有闲阶级论. 商务印书馆.
[3] 约翰·费斯克, 费斯克, Fiske, 王晓珏, & 宋伟杰. (2006). 理解大众文化. 中央编译出版社.
[4] 戴维·考特莱特. (2014). 上瘾五百年. 中信出版社.
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在小宇宙·荔枝·喜马拉雅APP,
搜索“湃客 Talk”关注我们
主播、撰文 / 胡雅婷
后期、监制 / 徐婉
海报设计 / 白浪
实习生 / 李小庆 吴宇迪 张之钰
运营 / Yatiti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