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马子木:诗文中的明末清初政治史
因研究方向之故,本年阅读书目中最受教益的几本著作,基本集中在晚明清初政治史方面。近年来明清政治史领域颇觉黯淡,学者反复呼吁重提政治史研究,这几本著作或可为我们思考如何更新政治史的研究路径提供一些参考。
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此前早已翻过,年初又仔细重读一过。邓之诚治史的理路大抵仍侧重于传统学术,也不仅限于某一断代,但明清史,特别是明中期至清前期的历史,则始终是其用力最多且成绩最为卓著的领域。他在抗战时期因仰慕义士与遗民苦节,遂留心收集清初集部,累积至七百余种,其中不乏罕密之本。这部《清诗纪事初编》,写定于1950年代,是邓氏生前手定的最后一部著作,可以说是积二十余年之功所作,而小传部分尤其值得重视,考证、评论以及对重要史料的提示皆在其中。原书涉及范围极广,胜义迭出,无法一一举述,在此仅以两方面为例略为说明。
其一是遗民事迹的考订,这是遗民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由于文献禁毁,遗民事迹往往晦暗难明,特别是矢志抗清者,因其大多都是地下活动,尤难获得确证。不过诗文集中尚有线索可循,邓氏花费极大精力钩沉发覆,如其最先注意到吴祖锡抗清始末,徐枋佯为隐居,而与祖锡配合,“实有大谋,用心良苦”(26页)。顺治十六年的魏耕通海案是清初东南一大案,大族被牵连者甚多,邓氏据魏霞、杨宾、朱彝尊所撰传状及魏耕《雪翁诗集》详考其事,举凡魏耕行踪、同谋之人及孔元章首告缘由,皆一一得其本末(247-248页)。后来何龄修先生在此基础上阐幽发微,网罗诗文集、方志与官书档案中的史料,对通海等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又发掘出李长祥、黄毓祺、杨鹍、陶汝鼐等人的抗清事迹(各文均收入何龄修:《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东南抗清史的疑案方在数十年的学术接力中逐渐廓清。
其二是对清初中枢政治的考察。党争首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邓氏看来,“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臬,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徐)乾学、(高)士奇,嗾郭琇劾罢之。”用徐乾学辈,不过“欲倚之为搏击之用”(364页),要之,“党争固烈,而操纵者则人主也”(940页),这可以说是对清初政局演变极为清醒的把握。当然,党争并非政治史的全貌,如李天馥等政事鲜有建白的大臣,邓之诚注意到他们是京师文人活动的核心,“结纳名士、竞尚诗文”(555页),其社会网络、交游唱和未尝不是一个新的考量角度。政治史的曲折隐晦,必有待于诗文集中发掘,邓之诚在《初编》中留下了很多未能完成的线索,如称清初中书舍人权重,“多擢卿寺方面”(475页);康熙朝多以侍卫传旨,“与南书房缮拟谕旨,同属机要”(663页)等等,均值得续作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初编》所试图呈现的,正是以政治过程中参与者“个人”的视角来观察清初政治。
“诗文证史”或“文史互证”本是古典学术中常见的路数。邓之诚的旨趣与厉鹗、陈田诸家专重艺文不同,他完全是以史家的眼光选录诗篇,“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讲求“以诗证史”而非“以史证诗”。相较于诗文的艺术性,邓氏更看重其史料价值,“但取其事,不限名家”,甚至一度拟将此书更名为《顺康诗史》,以配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

此书内另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新君旧主与遗臣——读木陈道忞〈北游集〉》(179-215页)。木陈忞的《北游集》本属禅宗语录,且于雍正朝遭禁毁,清人鲜有见者,经陈垣先生的重新发现,已为学者所熟知。不过由于木陈自述较为零散,除了少数治宗教史的学者,自陈垣以后,很少有人利用此书讨论顺治朝的时局与人物。所谓“新君”自然指清世祖,旧主为明思宗,遗臣则为崇祯朝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清世祖对明思宗怀有一种极深的认同、同情式的怀思,顺治十六年,世祖亲祭思陵,据说在陵前失声痛哭,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李清:《三垣笔记·补遗》,中华书局1982年,90页)李清虽然隐居江南兴化,这一记录却非空穴来风,亲历其事的王熙,便有“翠华凭吊处,也为一潸然”之作。晚明之“有君无臣”在清初士林中是相当流行的看法,不过此语从世祖口中道出,与士人所言,意义自有不同。作者在此文中引述木陈忞的记述,勾勒出世祖对思宗的认同与怀思(190-196页),借用木陈的话,便是“异世知己”。稍有遗憾的是,作者的论述到此为止,清世祖何以同样会有“有君无臣”之叹、何以会对思宗产生如此深的认同,文中并未涉及。其实厘清此类问题,对于今日重新理解顺治政局甚有裨益,譬如有学者便认为,世祖之叹,与其晚年推行汉化改革失败、遭到满洲贵族的孤立有关(参见姚念慈:《评清世祖遗诏》,连载于《燕京学报》新17、18期)。此文的另一要旨是考订曹化淳的事迹。张汉儒之狱,牧斋得曹氏之力而幸免,思宗亦因曹氏之奏而疑温体仁。甲申京师陷落,皆谓由曹氏开门迎降,是以时人对其多无恕辞。但其生平却不甚清楚,可以说是明清之际一个若隐若现的人物。作者通过《北游集》中的零散记录,勾连以诗文、方志、石刻史料,详考曹化淳于顺治元年最先倡议修建思陵,并捐资董理其事。作为崇祯朝颇受信任的宦官,曹氏入清后虽十分低调,却非默默无闻。其人“珠玑满腹”(引木陈诗中语),世祖幼年未受到系统的汉文化教育,亲政后乃从曹氏读书(188-189页)。曹化淳对佛教也颇为亲近,甚至在宫中亦有“法社”,故木陈入宫后多与往还。不过,曹氏在顺治宫廷的地位究竟有多高?木陈与曹氏唱和,诗中不乏虚誉,方志传记,更不可全信,作者遂称曹氏“俨然国师”(186页),甚至认为世祖之奉佛,最早也是受到曹氏的影响(206页),未免推求过当,事实如何,恐仍需讨论。

今人谈及清代文字狱,往往理解为政治威权与文化专制的迫害,这固然不误。但如此简单化与概括化的论断,或多或少会忽略案中之“人”。涉案者、首告者、审讯者以及各自背后的家族、师友、僚属等等社会网络,都因其各异的利益诉求而产生不同的应对策略。雍乾以降的文字狱,因档案俱在,供招、转审大多历历可考,但行政文书的格套化书写不免隐没“人”的主体性,更不能排除审案官意志的作用,表面的“案情”似可一目了然,但其周边与背后却一无所知。就此而言,相较于档案,诗文、笔记或可提供另一幅不同的图景,这也是此书的价值所在。庄氏史案在现已公布的清代档案中几乎未存下片语,亲历者和清初地方史家却留下或隐或现的记录。如被庄氏列名参订的范骧,其子范韩为救父奔走于京杭间,晚年撰有回忆一篇,对于整个营救过程有详细的记述,如述及夜见巡抚朱昌祚一节,朱氏一方面对朝廷旨意揣测不定,另方面又对世族曲为保全、不欲兴起大狱,此种微妙的情态,非由亲历者的记述绝不可得之。黄裳曾得其稿本,题为《私史纪事》,这篇文字在清代当然不可能付梓,民国时周延年纂辑南浔地方文献为《南林丛刊》,始以《范氏记私史事》之名收入,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著录的便为后者。此文梓行已八十年,就目力所见,也只有白亚仁此书能够系统利用,足见作者对清初江南文献的熟悉。此外,作者大量引用了史案亲历者、幸存者以及众多悼念者的诗作,虽未必在探明史事上有多少助益,但对于理解时人的“心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全书引用清人别集、总集近百种,其中不乏稀见者,如中科院图书馆藏钞本《范文白(骧)遗诗集》、浙江图书馆藏吴农祥稿本《梧园诗文集》、上海图书馆藏钞本《査继佐诗》等。另如作者所引张岱《喜査伊璜对簿昭雪》诗(110页),仅见于本年刚刚公布的沈复粲钞本《琅嬛文集》,作者蒐求文献之勤,由是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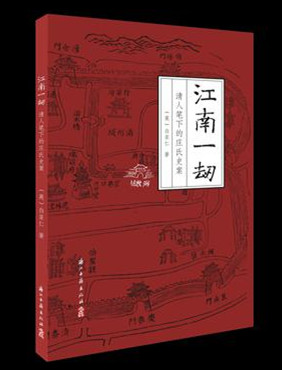
(本文原题《2016年读书札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