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年度阅读︱日本学者眼中的日本,中国学者眼中的中国
一年好景君须记。一年读过的好书,更是让人留恋。

4月初在“燕京书评”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颗“炸弹”》,谈的是章益国教授的《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读得还算认真,借机结识新知(如张荣华、张寿安的论文等),重温故旧(如钱穆、余英时、王汎森的论著等),总是很惬意的一件事。《道公学私》的脚注很丰富,也很有读头,最近想到一个问题,或许可以藉此做一点补充。书中提到陈垣、余嘉锡等近代学人对章学诚的批评,作者认为:“以陈垣的路子和口味,对章学诚的高明处可能体会不深,对其凿空蹈虚处却看得清爽。陈垣的心头好是钱大昕,我们很难要求一个人同时喜欢《十驾斋养新录》和《文史通义》……”这个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不过似乎也应注意到,胡适等人对章学诚抬举太过,恐怕也会引起一些学界同仁对章学诚的不满。这就好比,某人突然大红大紫,旁人趋近一瞅,觉得固然有其优胜,但又没有达到众人吹嘘的那般地步,不能不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以表持平,在这种情形下说一些重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各家秉性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可能大相径庭)——这些板子打在研究对象上,其本意或有几分是对吹捧者的“抗议”。如果我们把这一层考虑进去,也许可以对学界一些现象有更深一层的把握。当然,这种“默证”有其限度,不可过度推衍。

丸山真男
暑期主要读了丸山真男和立花隆。丸山真男(1914-1996)是战后日本重要的思想史家,近些年他的著作陆续有中译本刊行。巧的是,苅部直的《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唐永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丸山真男的《忠诚与反叛: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先后面世,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丸山真男:“开国”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发表在“澎湃·思想市场”上。

立花隆生于1940年,是战后日本著名的学者,早年以《田中角荣研究》《日本共产党的研究》等深度调查广为人知,后来出版的《太空归来》《濒死体验》也是好评如潮,影响甚众。立花隆兴趣广泛,嗜书如命,他在东京文京区著名的“猫楼”就是一间小型的图书馆,从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环境论到宗教、哲学、宇宙论,应有尽有,据书中照片说明,光是关于“共产党研究”的参考文献就有700册。立花隆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被誉为“知识巨人”,因病于2021年4月30日去世。我是6月下旬一天夜里在朋友圈看到立花隆的死讯的(立花隆去世的消息是他家人6月23日告知媒体的),国内几乎没什么动静,但在日本,报纸、电视节目都有报道。

我主要读了《立花隆のすべて》(书名直译,即《立花隆的全部》),准确地说,是书中的部分文章,尤其是《毛沢東の徹底的解明》一篇,反复读了多遍,还把24页的全文录进电脑——当然也是为了学习日语。这本书由文艺春秋社1998年出版,主要收入了立花隆在《周刊文春》和《文艺春秋》上发表的重要作品,以及一些社会名流(作家、教授、媒体人、律师)关于立花隆的印象记和读后感,其中包括舞台美术家妹尾河童的《梦幻般的“立花小报”》(幻の『たちばなしんぶん』)、哲学家梅原猛的《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人》(ソクラテス的意味における哲学者)等。

今年9月,文艺春秋又推出了《「知の巨人」立花隆のすべて》,与1998年版有部分内容重合,但全文收录的《田中角荣研究》,以及司马辽太郎、山中伸弥和立花隆的对谈,都是旧版所没有的。如果想对立花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两版“全部”值得参考。
对我而言,立花隆《透彻了解毛泽东》一文虽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事实,但生动流畅的叙事、鞭辟入里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在阅读的过程中,早年零星读过的关于毛泽东的一些纪录,像通了电似的,猛然从记忆之海浮出水面,比如青年毛泽东坚持洗冷水澡,偏爱在闹市中读书,以及“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之类的名言和掌故,零零总总,不一而足。而作者驾驭有度,行文不疾不徐,引人入胜,充分展示了其高超的谋篇才能和精湛的剪裁技艺。上面说该文没有什么新材料,那是就现今的立场而言的,遥想当年(本文发表于《文艺春秋》1970年11月号),中日还没有建交,作者却能“彻底”解读毛泽东的功过,除了他本人的博学多闻,也跟日本坚实的中国学研究积累有关。

这一年,日本有立花隆这样的“知识巨人”辞世,中国学界也有多位著名学者驾鹤西去,如章开沅、何兆武、余英时、李泽厚等。这四位先生中,除了章先生的论作较少接触外,另三位先生的大作我都尽量阅读,近两年机缘凑泊,不时重温一二。最近从图书馆借出《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回想初读,大概是在鹭岛上大学期间,一晃将近二十年了。当然其中有些篇章,后来读过不止一遍。此处只谈重读之后几点琐碎的感想。其一,当年读书肯定是跳着读的,像《〈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一文,我就完全没有印象,这回粗读一过,感觉很有意思。比如,文中推论说,“司马光也许是刘歆伪造(《周礼》)说的始作俑者”(150页),而“司马光是最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联想到北大辛德勇教授《制造汉武帝》一书所引发的学术公案,对王安石变法的重大影响(不只是政治事件,其对思想学术上的刺激或有深入研讨之余地),以及《资治通鉴》的史书性质(光从书名即可看出司马温公此书的指向,但后来的学者大都从现代史学的立场出发,这个前提很可能成为一个陷阱),有必要格外留心。其二,《犹记风吹水上鳞》《一生为故国招魂》等已成为名篇,自不消说,单是书中附录的钱穆几通论学书简,尤值吟咏再三。实际上,据我观察,确有学者从钱穆的“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出发,成就自家论著,且颇有影响,也算善于读书、敏于撰作了。其三,《〈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是一篇“少作”,1954年8月和9月分三次刊发于香港《人生》半月刊,这大概是余氏平生最具争议的论文之一。恰好《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发表了华东师大李孝迁教授的《〈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从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的学术论辩这一角度分析《十批判书》的写作,与《互校记》对读,颇可玩味。

夏秋之交断断续续读了《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卷《东洋学的磁场》,(岸本美绪编,岩波书店2006年版)打算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顺带一提,最近因查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发觉他在1925年7月14日写的自序中说:“……稿凡五易,时阅四年。中间复得一九二〇年南京黄教士中西年月通考。又得一八八〇年日本内务省地理局所编之三正综览,备载中西回历。参互考订,始行写定。夫日本民族,固无回族也,然四十五年前,日人已注意及此。”关于日本人对回民、伊斯兰民族的关注,此前读《东洋学的磁场》时深有体会,因为其中就有一篇论文专门讲述二战前日本学界对“回教徒问题”的研究。

如果说这一年有哪本书最使我感到“刺激”,约莫要属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某个傍晚,在研究室沙发上休息,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翻读了几页,我就被“抓住”了,或者说,我强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间汩汩涌动的热力,由不得我不往下看。“以战败为契机,把学问确立在对战前的学问方式进而是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总体的‘反省’之上,意在重新恢复学问和文化的总体性;而这种志向本身,同时又是在精神深层来接受战败这一事态,并且以面向重建新日本的实践性(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国民的)热情与希求为主题。”(40页)——后来,我冷静下来,努力回想那被“抓住”的瞬间,这句引文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一种学问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直面时代的问题,直面内心深处的迷惘,何况日本战败这样巨大的劫难。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以后又该如何走下去,千疮百孔的现实迫使有良知的知识人不断自我拷问。战后日本为什么会涌现丸山真男、鹤见俊辅这样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出现立花隆这样的“知识巨人”,我似乎找到了解答问题的一条线索。与中国的情形相对照,这不能不使人陷入沉思。
回到《鲁迅与终末论》,书中写道:
说到我自己,如果借用中野重治的话,那么就是“两个青春”重合在一起的时代,即“战后”这一日本的青春和我自己的“第二个青春”。我在这当中与之相遇的《现代中国论》和《给日本的遗书》,通过对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所分别象征的两种近代的比较,对日本近代给予了总体性的彻底批判,这也逼使我自己的民族主义产生“回心”。就是在这个时候,鲁迅作为对我构成威胁、不肯接受我的一种完全异质的精神原理,也与《旧约圣经》一道不时地叠映在我的脑海里。(41页)
抱着这样庄诚、恳切的态度,这样勇毅、执著的精神,以鲁迅为镜像,“死磕”日本的近代历程,大概是本书激动人心的一大缘由罢。“鲁迅在日本”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日本学者通过阅读鲁迅把握时代脉搏、造就时代精神,产生了一批富有解释力和思想冲击力的作品,国内多有引进,但在整体上如何认识“鲁迅在日本”的意义,似仍有待开掘。另外,本书的翻译非常体贴,为便于读者理解,补充了很多必要的译注,借此机会表达一个普通读者的感激之情。

对战前日本的学问方式进行剖判的当然不止伊藤虎丸一人,譬如,梅原猛(1925-2019)在《日本文化论》中也对明治以来日本的教育展开了批判。《日本文化论》是非常薄的一个小册子,100页都不到,这回翻看笔记,才知道是去年10月读的,记忆中却一直以为是年初的事。为写这篇小文,我又从图书馆借来《美と宗教の発見》。(《梅原猛著作集》第三卷,集英社1982年4月版)《日本文化论》虽然仅占该书(500页)十分之一的篇幅,却让我初次领略到日文的美,而且其内容颇有启发,便在此略作介绍。
《日本文化论》是梅原猛在1968年一篇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次年初版,题作《日本文化的过去与未来》。1976年改题《日本文化论》,由讲谈社再版,此后一印再印,到2002年12月20日已达41刷,足见其魅力匪浅。虽是戋戋小册,视野却很宏大,立意也很高远。梅原猛一上来就表示,要谈“日本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就不应局限于日本一隅来理解日本文化,而要在世界整体的视野下思考日本文化。从世界文化的立场出发,梅原猛认为最具参照意义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而到了作者演讲的年代,欧罗巴全盛时期已然落幕。根据汤因比的观点,16世纪欧亚大陆上有六个文化圈,即西欧文明、拜占庭文明(苏联是拜占庭文化遗产的继承者)、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文明(以大乘佛教思想为基干)。不过,与另五个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是否可以算作一个独立的文明,尚存疑问。16世纪到19世纪的世界史,就是欧洲文明征服世界的历史。然而,欧洲文明只是“力”的文明(科学技术),缺乏“精神原理”——欧洲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过去的灵魂。进入20世纪,其他文明逐渐苏醒,开始反击欧洲的霸权。但是纵观当时各大文明,只有日本吸收了欧洲文明,并大获成功,甚至比欧洲还欧洲。对于中国文明的现状,梅原猛有一个新颖的看法,他说中国在历史上两度遭遇外来文化,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一次是西欧近代文明,而中国的应对,其最终结果是将对方语录化——与佛教融合,创造了独特的禅宗,其表现就是禅宗语录。而语录的祖宗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言行录《论语》。接着梅原猛讨论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否定就是一项重要内容,雅思贝尔斯、汤因比堪为代表。以上大体为开篇“世界史的动向”的梗概。
第二节转入批判“日本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梅原猛认为,虽然明治日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教育方面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弊病,基本上是以英语和数学为中心,而英语、数学只是“技术之学”,并非“精神之学”——德川时代,官方学习儒教,民间学习佛教;中国人考科举,其中心是文章;欧洲有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教养”。明治之后的日本“国学”,无非是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修身为名,实行一种技术性的教育,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神由此遗失殆尽。比如说,日本学校讲授国语(也就是日语)的时间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10世纪的法国还是野蛮人,而日本在11世纪初就诞生了《源氏物语》这样的优秀作品。构成日本人精神基底的亲鸾、道元、日莲在国语教育中基本上是缺席的,战前学生读的是《徒然草》《方丈记》——在梅原猛看来,这两种书虽然不能说无聊,但《徒然草》里的“退屈男”和《方丈记》里的“无常男”至少远不是一流人物无疑;吉田兼好(《徒然草》作者)也罢,鸭长明(《方丈记》作者)也罢,可能是很有情趣的人,但绝非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因此,梅原猛认为,国语课应该读亲鸾、道元、日莲、空海等人的文章,感受生命的热情、思想的雄浑。一句话,佛教不仅对日本文化有很深的影响,对日本文学也有很深的影响。
在演讲的1968年,梅原猛深刻地意识到,历史又一次迎来了转捩点:欧洲强国主导世界的时代结束了。欧罗巴的思想是“力”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已无法解决时代问题。接着,梅原猛从宗教思想的角度分析东西方的差异。他说,作为欧洲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其根柢都是“力”的思想,表现在神话上就是宙斯那样怒气冲天的复仇之神,而日本神话里的神都是非常平和的。再者,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临终的姿势迥然有别,基督之死是很残忍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释迦牟尼之死则是安详的,在寺庙里涅槃。苏格拉底是被毒杀的,而孔子和释迦都是寿终正寝,尤其儒家思想,基本上不涉死亡。最后,梅原猛提出,应该继承圣德太子提倡的“以和为贵”,“和”是日本的立国之本。至于欧洲的科技文明与东方和平、慈悲的文明如何共存,则是人类发展的大问题,亟须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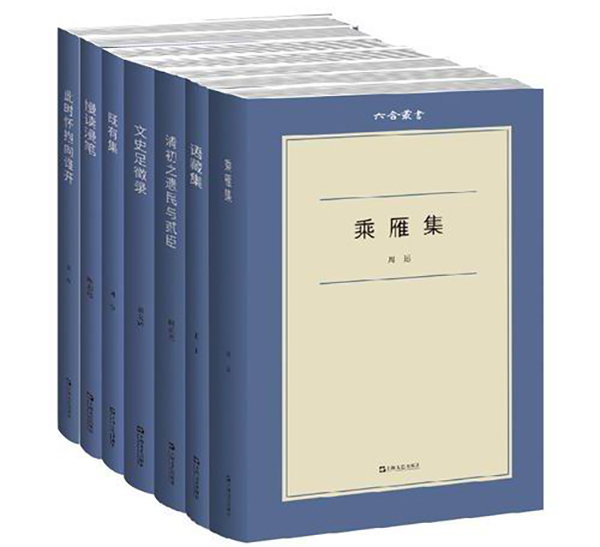
其实,本文的写作提纲上还列有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周运《乘雁集》等书——好在这些都是新作,国内读者很容易入手。最后提三篇读后记忆犹新的文章,以结束小文。巧的是,三位作者都是女性:一是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岸本美绪教授的《“风俗”与历史观》,(台北《新史学》第13卷第3期,2002年9月)像这样朴实、简明而通透的论文,多乎哉,不多也。二是台湾东海大学陈以爱教授的《胡适的〈水经注〉藏本的播迁流散》(分上、下篇刊于《九州学林》2006年冬季号和2007年春季号)——因《乘雁集》里用400页的篇幅追踪周作人的藏书,蓦地想起暑期某个周末独自一人在研究室读罢胡适藏书的故事,不禁掩卷长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三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孙歌教授的《哲学的日常性》,(《读书》2021年第1期,后作为“中文版序”收入《鹤见俊辅传》)套用作者的话,“即使是不研究日本,甚至不从事学术文化事业的读者”,也可以从这篇序文中获益。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