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意大利修宪公投:留给欧洲队的时间不多了
继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后,本周“黑天鹅”事件再现:12月4日,在意大利现任总理伦齐发起的修宪公投中,反对派以平均56.7%的比例压倒赞成派。
当然,这并不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黑天鹅”(指概率极小的事件),因为在公投前,民调已经显示反对阵营将以约55%的比例领先。因此,公投失败本来就是大概率事件。但毫无疑问,它在人们心头笼罩的是黑色的乌云。公投结果公布后欧元的应声大跌,就是最好的证明。
意大利2016年修宪公投结果,图中红色程度越高的地区,反对的比重越大。
其实,意大利的这次公投,与它是否留在欧洲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这次修宪公投是现任总理伦齐赌上自己民望和政治生涯的一次冒险:意大利政治向以混杂纷乱著称,议会中小党林立,立法机构效率低下,政府决策多有掣肘,官僚体制颟顸透顶,以至于意大利人爱讲的政治笑话是:只有墨索里尼在位期间,才能让意大利的火车准点,让意大利的黑手党伏法。伦齐两年前在大选中获胜,以三十九岁的年龄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府领导人,当时他一定意气风发,想放手做一些事业。然而两年来与议会、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无数的扯皮似乎已经让他沮丧。于是他奋而决定推动修宪。
伦齐发动的公投修宪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削减参议院人数,让众议院成为意大利事实上的权力决策机构;二是削减地方政府权力,以助于确立中央政府权威。从历史沿革来说,意大利立国实际上可以看作北方诸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地区联合教皇控制区(罗马)形成的北方王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之间的统一过程,地方主义在意大利政治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伦齐试图扮演的角色与日本重建中央权威的明治天皇相似。然而,明治天皇最终因获得倒幕派的支持而成功,伦齐却因失去意大利普通民众的支持而失败。
人们恐慌于此次意大利公投的结果,原因在于,如果伦齐按照之前的承诺,公投失败随即辞职,那么,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是现在意大利的极端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五星运动党被人视为民粹主义政党,以反精英、反欧盟、反移民为纲领,承诺若2018年大选获胜将举行退出欧盟公投,伦齐的失败,让五星运动党提前获得了执政机会。鉴于五星运动党的创立者格里洛是个喜剧演员,由于他曾经涉嫌一起谋杀案,按意大利法律他不能担任公职,现任众议院发言人的迪马伊奥成为炙手可热的总理候选人。

是谁在反对伦齐?
仅仅在两年前,伦齐还是以“政坛局外人”和“改革者”的形象赢得广大选民的支持,而在此次公投中,他已经被五星运动党塑造成建制派、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五星运动党号召人们投票说No,反对修宪,就是让伦齐下台。
看起来,这又是美国大选反建制派胜利的一次重演:丈夫曾为美国总统、自己也长期担任要职的资深政治家希拉里失败,而我行我素,一向以大嘴巴形象示人的特朗普上台。美国大选的结果已经跌破了很多分析家的眼镜,有许多人也把这归为民粹主义的胜利,然而事实如此吗?
笔者在学界的朋友圈中流传一份关于美国大选的民调数据,根据这份数据,在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群体中,希拉里赢得的支持率远高于特朗普。如果按照民粹主义的经典定义,似乎希拉里才是民粹主义的代言人。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政治现实已经推翻了学者长期奉为圭臬的定义和概念。如果仅从收入水平来看,在美国中产阶级群体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基本持平,这意味着收入水平已不足以划分不同阶层的价值观与政治倾向。因此,单纯指责说特朗普支持者是民粹分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特朗普的获胜,恰恰在于他把握住了中产阶级中的关键少数。
早在英国脱欧之后,一位长期在中文知识平台知乎上发声的英国人(知乎ID:Lightwing)就指出,旧有的阶级划分标准正在失效,更合理的划分方式是按照所处行业在产业革命中的进程来划分:以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之间的产业革命为界,在此之前出现的行业(如农业、资源采集业、各种部门的工业,以及医生和律师)为旧,在此之后出现的行业(如投行、互联网、新媒体)为新,则可划分出新旧资产阶级、新旧中产阶级和新旧工人阶级。其中,旧产业从事者多半支持脱欧,而新产业从事者多半支持留欧。这是因为,新产业从事者所在的行业多半受益于全球化和资本、技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他们切身体会到维持与欧盟的关系有多重要;而旧产业从事者还习惯于民族国家时期的产业供给关系,他们的利益反而因为全球化造成的产业转移而受损。
这种新的阶级划分方法在美国大选中尤其具备解释力:许多传统行业的精英从业者成为特朗普的拥趸,论收入,他们也许跟从事金融与互联网行业的多数白领差距不大,然而他们访问不同的新闻网站,关注不同的Facebook主页,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跟不同圈子的人聊天交流。一句话,他们的信息来源彼此隔阂。笔者许多在美国读大学的朋友得知特朗普获胜后感受到了世界观的崩溃,因为在他们接触的圈子中,没有人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绝料想不到,这个国家有一半人生活在他们完全未曾想到的信息世界中。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意大利。笔者接触到在米兰等大城市读大学或工作的年轻人中,伦齐的支持者不在少数。然而在传统行业更为发达、同时也在全球化浪潮中受损更大的意大利南部,则清一色都喊出了让伦齐下台的声音。当然,意大利的公投制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律规定参与投票者应当回原籍去登记投票,异地投票需要经历复杂的登记手续,然而许多在大城市读书工作的年轻人觉得登记太麻烦而放弃了投票。这与部分中国农民因为回乡太麻烦而放弃村委会选举类似。但问题在于,民主制度的支持者觉得投票恰恰是国家主人翁意识的体现,如果伦齐的改革如此重要,为什么主人翁却纷纷放弃了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呢?
民主的失败,还是精英的失败?
民主制度一直没变,但2016年一年我们连续目睹了各国人民通过选票作出让精英惊讶和惋惜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出问题的恰恰是一直没变的民主制度。现行普选制诞生于19世纪晚期,在20世纪经历了三波大的扩散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很多国家广泛推行的制度。然而,在这项制度诞生初期,许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政府职能,例如通过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为不同的产业制定分门别类的引导发展计划,以及配合私营投资机构影响国民经济……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出现,或者只是以极其粗糙的方式运营着。但今天,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已经成为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问题。不信,就请问问基层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开那些“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文件。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期就指出,现代社会专业分工的发展,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中的人关在不同的“铁笼”之中。每个人只熟悉自己熟悉的那一块专业领域,对其它领域的知识不感兴趣也没有精力去了解,因此只能靠着直觉和想象去判断。这就是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和意大利公投发生的事:我是一名精通如何提炼原油的工程师,我有硕士学位,因为我的专业技能,我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我对欧盟、移民和全球化这些议题不感兴趣,我看到的是在那些种族、肤色、信仰都与我不同的移民进入我的社区之后,治安变差了,工作机会变少了,那么,为什么我不能投票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我堂堂一个硕士毕业生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却要被所谓的精英斥之为民粹?
这就是政治精英的问题所在。他们在大学中接受过的专业训练告诉他们世界只能是这样,全球化只能向前不能后退,自由、平等和开放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些意见已经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结果就是他们误以为身边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这些当作共识,意识不到他们和这些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一个的铁笼之中。

现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就在于:普选和公投打破不了笼子的铁栏杆。它们最多让笼中的我们惊醒过来,然后更加厌恶我们自己笼子之外的其它笼子。希拉里和特朗普几乎不在大选中解释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些东西对他们自己阵营的支持者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解释的共识,而在对立阵营看来则完全是疯言疯语、不值一驳。伦齐和他的反对者也是如此:意大利的主流政党攻击五星运动党是民粹,而五星运动党动员其支持者的方式也很简单:对公投说不,就是让伦齐下台。
先天不足的一体化
也许欧盟不会在瞬间崩溃,也许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没有画上句号。但目前的事实是,欧元和欧洲一体化从根子上就出了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就是讳疾忌医。
已经有很多知名经济学家指出,欧元从诞生之初就有先天性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欧元的发行权归欧央行所有,但财政政策的决定权却在每个国家自己的政府手中。这意味着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权责不统一,各国政府很难把货币政策当作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这个先天不足与另外一个事实结合起来,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摧毁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础,那就是:尽管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但它们的经济社会结构有很大区别。例如,德国人口年龄结构偏老龄而西班牙偏年轻,老年人倾向于储蓄而年轻人倾向于消费,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德国人储蓄起来的财富通过政府间的借贷关系发放给西班牙人消费,对此,德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就不具备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的能力。然而,德国财政部为什么要为西班牙人的借贷消费负责呢?

欧元自成立之初就不乏批评者,但欧元区还是建立起来了。毕竟,这对一个经历了四百多年高烈度战争和国际冲突的大洲,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文明而言,是多么弥足珍贵!法国和德国这对历史上的冤家而今居然能够实现货币的统一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黎塞留、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和威廉一世这些政治家泉下有知,搞不好会被吓活过来。也许正是这样的理想前景让欧元区的创立者决定学习一下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争论。然而,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其底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欧洲呢?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用简单暴力的逻辑指出美国在19世纪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以几乎为零的价格,获得了大量的资本要素——土地。如果把这个逻辑套用到上世纪90年代的欧洲,我们也会发现,当时的西欧,尤其是德国,同样也获得了大量廉价的资本要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产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那些被贱价折算卖出的产业资本。换句话说,造就今天德国在欧洲地位的不是什么日耳曼人的严谨精神,而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财富的吞并——所幸,那些还对此愤愤不平的东德人,今天都已垂垂老矣,行将就木,这段历史也会被人遗忘于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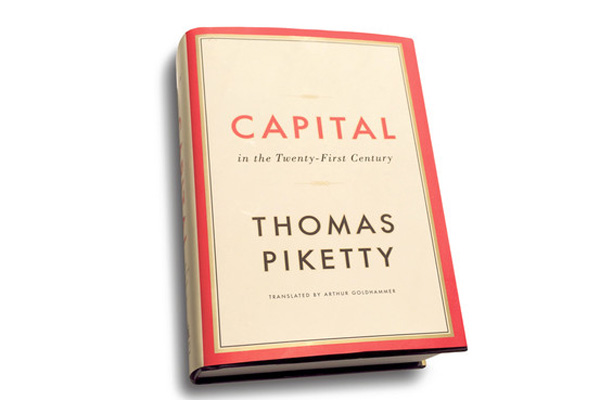
然而活着的人必须面对现实:天下大同的一体化前景很美,但今天欧洲经济衰退和社会撕裂的程度,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美好理想继续向前了。如果政治精英依旧用各种空头支票来维护一个摇摇欲坠的大一统欧洲,而不是直面问题,那么未来最可能的结果,套用一句中国格言来说,就是老房子着火,烧得更快。
欧洲的未来会怎样?
从目前的新闻来看,伦齐的辞呈已被意大利总统“留中不发”,但留给建制派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了。好在,五星运动党尚无独自组阁的能力,而退出欧盟对于意大利这个眼下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18%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不能承受之重。也许为了跟其它政党合作取得联合执政地位,五星运动党会对此作出妥协?而且,意大利宪法规定,国际条约是不能通过公投废除的。因此,即使在事情演化方向最符合五星运动党预期的前提下,也就是17年提前举行大选,五星运动党获胜并按承诺举行公投的情况下,建制派依然有机会通过议会政治让意大利继续留在欧元区,从而能够理直气壮地接受欧洲其他国家的救济。换句话说,这只靴子直到大概2018年才会落地。
意大利之后是谁呢?是17年4月份将举行大选的法国吗?然而熟悉法国政治的人都清楚,极端主义政党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娜·勒庞在大选中获胜的概率很小。首先,就法国目前的大选形势而言,左翼社会党基本上没有获胜希望,更有可能的对决状况是中右翼政党中选出一个人与极右翼的勒庞对决。在中右翼政党初轮选举中,无论是菲永还是朱佩,其民调都大幅度领先勒庞。

此外,与公投和美国大选不同,法国大选采取两轮选举制,也就是如果第一轮选举中未能选出获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那么得票数最多的前两人进入第二轮角逐。可以想象的是,朱佩或菲永的支持者在自己心仪的候选人失败后也不会投给勒庞,而如果勒庞在初选中赢得首位,则会有更多人出于惊讶和恐惧出来投票给勒庞的对手。想想看,如果美国大选也采取两轮制,特朗普还会获胜吗?
2017年7月,德国也将举行大选。不过,默克尔妈妈在这次选举中仍然没有对手。尽管默克尔民调因为难民事件一直下滑,尽管德国极端主义政党新选择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但它依然是联邦议会中的小党,本身无力与基民盟这样的大党去抗衡。而法国总统候选人菲永本身跟默克尔之间就有合作经验,朱佩与德国也持合作态度。如果届时出现这样的结局,那么,德法之间也许会再度出现“默科齐”这样的搭配,为摇摇欲坠的欧元区和欧盟延长其续命的能力。
然而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权责不匹的状况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欧洲议会和欧央行的决议对各国政府缺乏约束力,如果南欧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依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难道默克尔大妈要勉为其难再连任一届吗?毕竟,举退欧大旗吸引选民的各极端主义政党用了不超过三年时间就在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骄人战绩,就算建制派政党撑过了2017年,2021年大选又该怎么办呢?

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欧洲因为一体化受挫而出现严重衰退,世界和中国都不愿意看到。这意味着寒冬更冷,而我们更加缺乏来自有力伙伴的炭火。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体化的梦想不会在不付出代价的前提下就能达成。我们不是欧洲人,无法越俎代庖地去告诉欧洲人该怎么办,我们只能用一句中国球迷们耳熟能详的话,送给默克尔、菲永、朱佩以及许许多多希望看到政治一体化进程有更光明未来的政治精英: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本文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