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173
莱布雷希特读阿伦特传记︱男人因恨她而团结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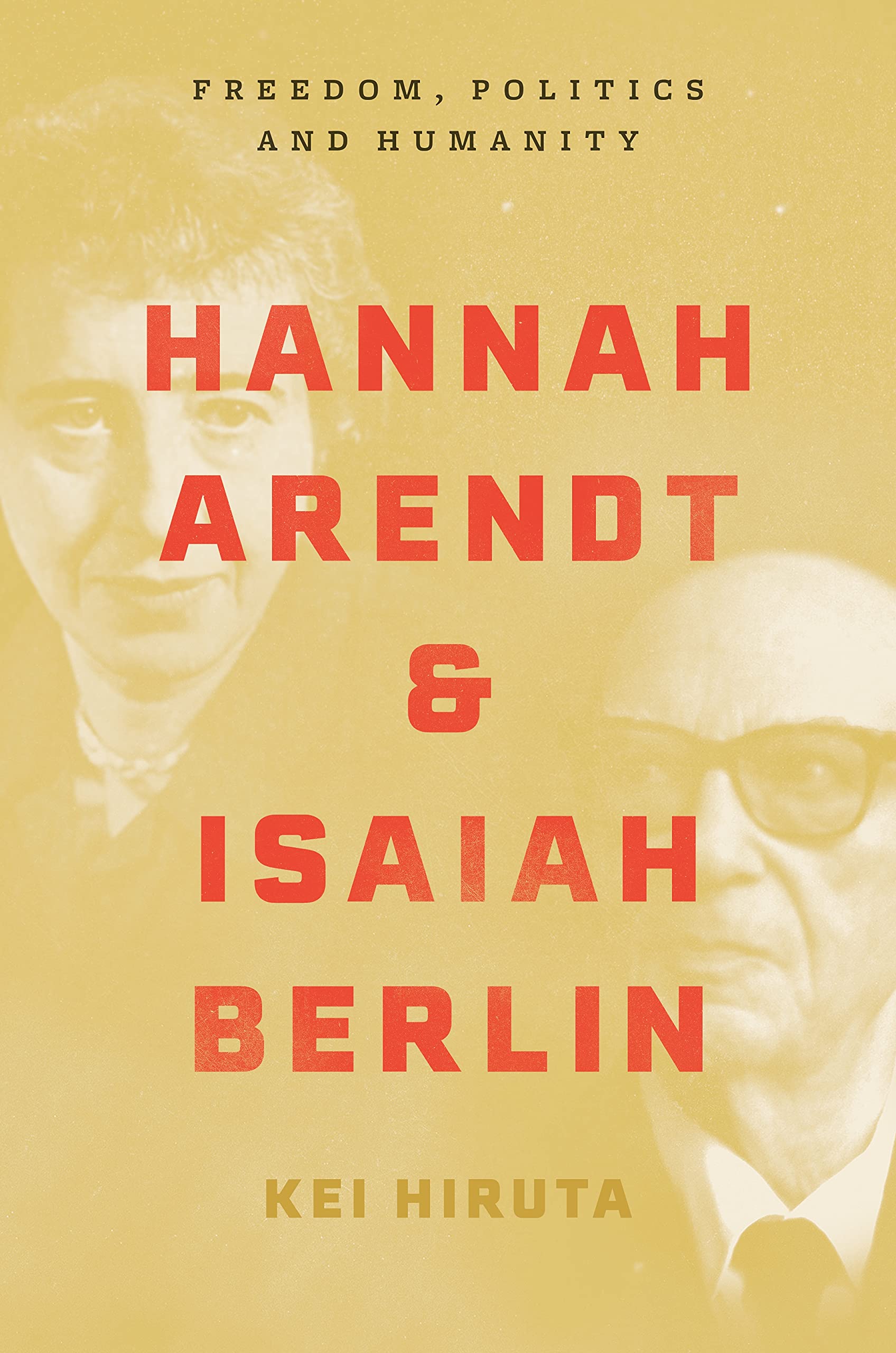
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 Kei Hirut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1, 288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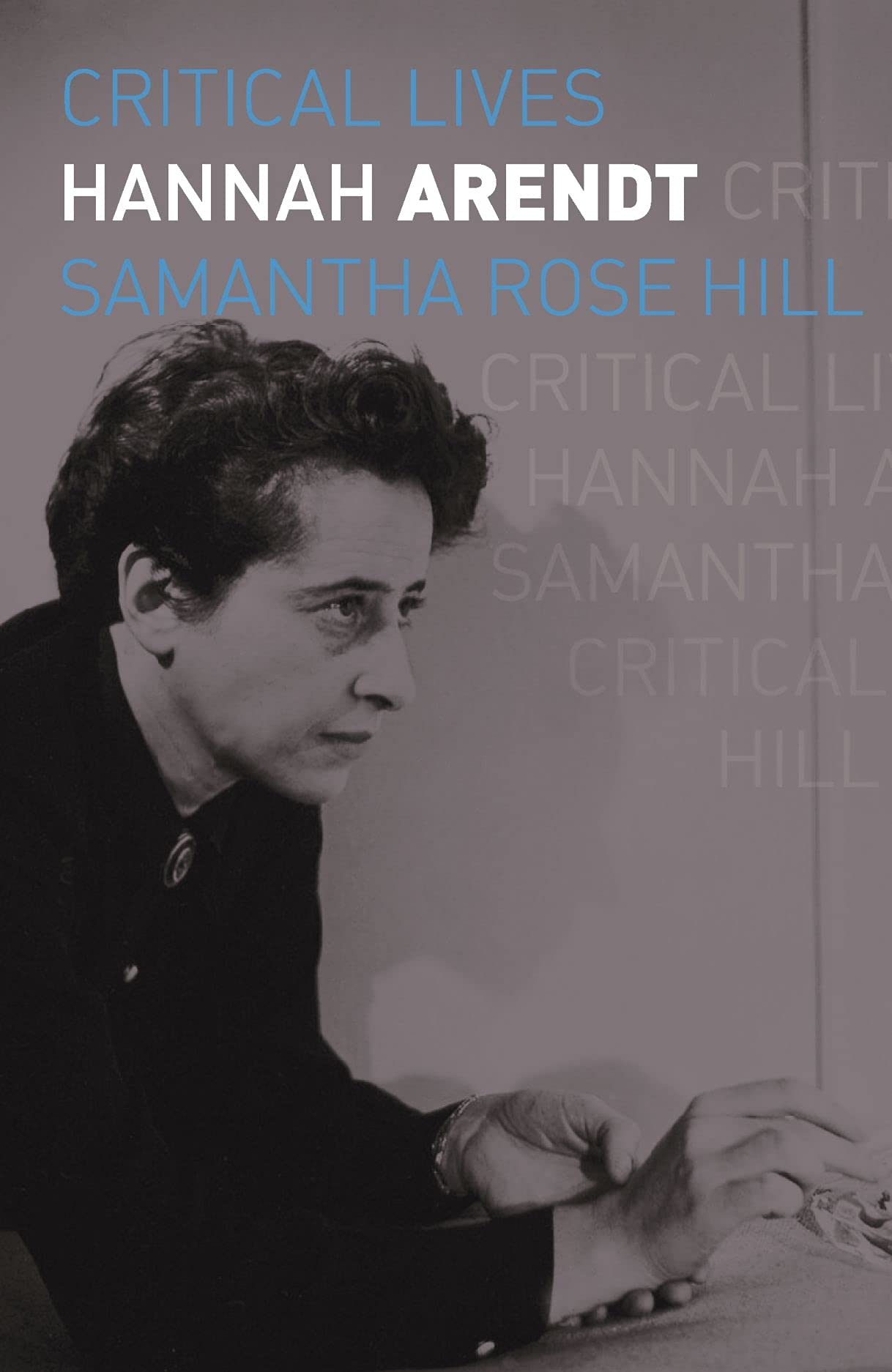
Critical Lives: Hannah Arendt, Samantha Rose Hill, Reaktion Books, October 2021, 230pp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静好时代,我曾经飞去一座德国小城看一部描绘两位哲学家之间爱情的歌剧。这段爱情绝非柏拉图式。汉娜·阿伦特当时十八岁,没有父亲,尚是处女。马丁·海德格尔已经三十多岁,已婚并有两个儿子,是他所在学科的领军者。在现代话语中,这是一个发生于校园中的典型#MeToo场景,是对信任和责任的滥用。
阿伦特并未如此提及此事;实际上,她成功保证了让这件事在她去世之前无人知晓。但这场老师对学生的性掠夺给她留下了终生的影响。现如今我们对她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是时候重新评估阿伦特了,在极权主义研究领域她是一位主要的哲学家,其影响力塑造了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她又堪称一条出色的变色龙,会将自己转变为纳粹的智性辩护人。
海德格尔在生活和思想之间划分了一条界线。他告诉学生,“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然后死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思想”。艾拉·舍里弗的歌剧《平庸的爱》投射了他的一些观点,即人类个体,哪怕是怪物,也是无趣的。
平庸是一个关键词,这个名词使阿伦特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她为《纽约客》撰写了记录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的冗长报道,标题为“平庸的恶”。艾希曼是希特勒大屠杀的首席执行者,一个将数百万男女儿童送入死亡集中营的官员。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即使以希特勒时代逃离德国难民的角度进行观察,艾希曼的形象,只是一个无聊的官僚,一个无名小卒,“既非变态也不暴虐……正常得可怕”。她认为,根据法律和逻辑,他不值得被逮捕、审判或处决。
她的立场激怒了道德哲学家,使她暴露在一群前互联网时代的抱持着不成熟观念的私刑暴徒之前。阿伦特既没有退缩,也没有回避。她对她的挚友玛丽·麦卡锡这么说:“痛苦,只是存活的另一种方式。”
萨曼莎·罗斯·希尔的新传记将阿伦特重新定位为现代的女权主义英雄,“高标准、不退缩、有主见”,随时准备在她进入的领域中对抗男性的统治地位。从她在美国的学术生涯中期开始,她开始将自己描述为一名政治写作者,而非哲学家。
她会说:“被人称赞是件好事,但被人理解就更好了。”希尔博士是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中心的助理主任,她认为,“阿伦特的作品如今已经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其中参考考证,以帮助我们达成理解”。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评价。
即使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她所点燃的怒火仍然会烧着人的眉毛。一项新的哲学研究审视了她与文雅有礼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关系,描述了他们1941年在纽约的第一次会面,可谓一见成仇。而这关系还会变得更糟。伦敦的费伯出版社在1958年询问伯林,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推出新版的阿伦特著作《人的境况》,伯林的回答堪称经典的拆解。“我不推荐任何出版商购入这本书的英国版权,”他如是答复,“对这本书有两点意见:它不会畅销,而且它也不是本好书”。而这仅仅是用来热身的开场白。在将这本书的内容一一粉碎之后,在报告的最后,伯林又回到了对“好”的确切含义的沉思。他继续写道:“阿伦特博士在谈到道义德行时写道(第75页),‘基督教对好的要求’是‘荒谬的’。那么要求一本书是好的也同样‘荒谬’吗?让我们希望她也这样认为。那么有人告诉她的这本书不好的时候她也不会在意了。”在由写作者遭遇到的各种拒信组成的漫长而有趣的清单中,这封回信也堪称是所有拒信中最为斩钉截铁的一例。
这两位创造性思维的巨人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仍然少为人知,但十分令人着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激烈对立,还因为把他们对比来看,就能发现他们既相似又相悖。他们都来自于波罗的海之滨的犹太家庭,阿伦特在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在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伯林来自拉脱维亚的里加。阿伦特的父母对宗教漠不关心,而伯林则知道他祖上有参与路巴维茨运动的拉比。阿伦特的父亲死于梅毒,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件事打乱了她的少年生活,并使她迁往柏林。
伯林在圣彼得堡时目睹了窗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满怀喜悦地漂流到伦敦的一所私立学校。阿伦特先后在马尔堡和海德堡大学深造,只讲德语,流亡异国后努力学习英语。伯林除了作为母语的俄语,也纯熟于拉脱维亚语、德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浮华使他愉悦,在出任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董事会一员时,他曾写下关于威尔第歌剧的博学论述。阿伦特不曾有过这种琐碎爱好,也不好闲言碎语。伯林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而她是西北大学和瓦萨大学的讲师,从未获得过终身职位。他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天造地设,针锋相对。
日裔丹麦学者蛭田圭对这两位1941年的纽约相遇进行了出色的分析,阿伦特当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难民,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那里领取津贴,与她没有工作的丈夫和受抚养的母亲住在租来的两间房间里。伯林在当时则是丘吉尔政府的特派代表,被派往华盛顿和纽约去施加影响力,并收集信息。两人在握手之后,阿伦特就针对伯林所谓的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缺乏承诺的问题对他加以批判。身为哈伊姆·魏茨曼(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长期朋友,伯林不屑一顾地说她太疯了(“fanatical”)。
八年后,阿伦特的著述已经被广泛阅读,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也即将完稿。1949年春季的一次会议上,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以他与肯尼迪的关系而闻名)促成她与伯林再度会面,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误判。施莱辛格总结说,她“对他来说太庄重,太有预示性,太过日耳曼,太过黑格尔”,伯林后来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把阿伦特列为本世纪最被高估的作家之一,小阿瑟·施莱辛格还为此恭贺伯林。伯林在第二次见面时震惊地发现,阿伦特反对新成立的犹太国家:“她批判了以色列。”
如果没有对艾希曼的审判,这一切本应逐步偃旗息鼓,只剩在学术期刊上的零星交锋。以色列情报部门(在联邦德国的帮助下)追踪艾希曼的足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那里将他绑架,押上前往以色列的飞机,并指控他犯有种族灭绝罪。阿伦特在1933年曾经身陷盖世太保的牢房,后来又险些没能将她的母亲从德国解救出来,面对“最后一次目睹纳粹头目真身的机会”,她就此采取行动。

汉娜·阿伦特
那场审判为时八个月,而她只在1961年4月旁听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她将她所看到的大部分内容贬低为“廉价的把戏”,并质疑这一过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整个事件是如此该死的平庸,难以描述地低级与令人厌恶”,她回家后对丈夫如是说。经过两年的酝酿,她的报告于1963年2月和3月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不久后结集成书。由此引发的反应可谓爆炸性。两位犹太文学活动家欧文·豪和莱昂内尔·阿贝尔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组织的讨论会,被玛丽·麦卡锡形容为“大屠杀”,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将其比作“对家族中的一个被抛弃的成员施以石刑”。以色列负责起诉艾希曼小组的一名成员发表了长达四百页的反驳意见。
在阿伦特的各项声明中引起最大反感的是:她声称如果没有犹太政要在各地提供协助,艾希曼无法屠戮如此多的人,这个根基不稳的主张忽略了艾希曼对那些人及其家属的完全控制。
阿伦特一如故我,坚守自己的每字每句。她在十年后表示:“我对(艾希曼)身上明显的浅薄感到震惊,这使得我们无法追溯他的行为的无可争议的邪恶,去发掘任何更深层次的根源或动机。这些行为是可怖的,但其执行者——至少是现在受审的那个卓有效率的执行者——是非常普通的、平凡的,既非恶魔也不可怖。”
我怀疑,在这样的认识的背后,隐藏着别的东西——海德格尔的沉闷学说。希尔写道,阿伦特曾经在1946年飞往德国去见她的老师,而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正名,海德格尔提出要离开元配妻子与她结婚。尽管阿伦特拒绝了,但仍在他的控制之下,无法承认她的那位杰出的施虐者曾为希特勒唱赞歌,并将优秀的同事喂饲给纳粹的狼群。她从未摆脱过他的魔咒,还为他八十岁生日发表过一篇洋溢赞美的文章。海德格尔的败坏道德蒙蔽了她的思维,并在面对艾希曼审判时严重歪曲了她的判断。
当那场风波爆发时,伯林并未批评阿伦特,他在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还私下对她的想法表示了某些同情。但他也鼓励《文汇》杂志发表了阿伦特与犹太神秘主义学者格朔姆·肖勒姆之间的尖锐笔战,后者指责她对自己的人民缺乏爱。阿伦特的回答是,她永远不可能爱某一群人民,只能爱她的朋友。伯林最终同意了肖勒姆的观点,认为她没心没肺,而她对艾希曼审判的记述“几乎以讥讽和恶意的语气”为特征。
我们在此可以见证阿伦特的非凡能力,男人因对她的憎恨团结在一起。在一组那些男人间的信件的新译本中(Polity Press, Cambridge),肖勒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阿多诺通过他们对阿伦特共同的抵触实现了完美的和谐,因为阿伦特曾写过一篇关于这两人的共同朋友本雅明的有趣文章,并希望被承认为研究本雅明的权威。阿多诺咆哮:“在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上,我是不会妥协的,不仅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位女士不屑一顾,我觉得她就是个老洗衣妇,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本雅明如何看待她。”
在这里我们是否能发现某些其它东西?在哲学的世界里,阿伦特是一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的局外人,最好是被隔绝在外,而以赛亚·伯林以及他那些穿着长袍的快乐男同行们则在高桌边笙歌畅饮。如此交流中的性别恐惧症有时相当令人窒息。
在一切都结束后,阿伦特将永远因为那个可怕的词“平庸”而被牢记,事实上她已经在所有的时代中改变了这个词的含义,使之与邪恶一致。就伯林而言,他留下了大量经久不衰的作品,从他作为基石的《卡尔·马克思》到《自由论》。他的刺猬和狐狸的寓言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晚餐聚会游戏而经久不衰。他的低吟“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会萦绕不绝。尽管阿伦特是个刺头,但她可能确有一大知——个人的自由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即使此人不可原谅。伯林尽管对犹太复国主义、英国和歌剧的忠诚毋庸置疑,在艾希曼的案件中,他还是准备以目的为手段张目。在这个故事里,狐狸并不总会占上风。





- 下一个千万人口城市会是谁
- 真鉴定证书“护航”下的假黄金暗流
- 河北、山东回应“狐貉胴体黑市”报道

- 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加大包括直播带货在内的网售产品抽查力度
- “砍头息”再现!315晚会曝光电子签高利贷,电子签放款人竟不是活人

- 秦朝大一统政策中要求书同文,秦朝的统一文字为
- 中国知名企业家雷军创办的互联网大型公司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