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书城》专稿|内山书店:鲁迅与内山完造兄弟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都,古书店大多偏居一隅,店面宽敞的已是屈指可数,坐拥一整栋大厦(ビル)的,恐怕就只有内山书店了。在整整三层店面中,中国和日本的新书种类齐全,更新速率也很快,但古书却着实不多,质量也一般。仅有的几十部线装书,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的新影印仿古版,和多有明清甚至宋元刻本、存货深不见底的山本书店和琳琅阁,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但内山书店在中国仍然非常知名,其原因当然是鲁迅。只可惜当年位于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早就在日本战败后翌月关门歇业,从此不复存在。内山完造一开始还没有打算离开上海,甚至不顾当时的混乱局势,试图在义丰里的自宅重新开业售书。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他被国民政府强制遣返回国,书籍及财产也被悉数“接收”。邮轮上的他身无分文,爱妻亦病逝,三十多年的中国岁月,宛如黄粱一梦。

今天东京的内山书店,其实是由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夫妇一九三五年于世田谷创办,一九六八年才移至神保町现地址。嘉吉比完造小十五岁,由于三岁时就被过继给叔父家,远赴四国生活,故两兄弟关系并不密切。似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自一九二七年起,完造几乎每年都邀请弟弟来上海过暑假,嘉吉因此自然而然地认识了鲁迅、郁达夫、郑伯齐等左翼文人。
一九三一年夏天,三十岁的嘉吉已是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教师,一边教授工艺美术,一边研究雕刻。正好当时鲁迅因受柔石等“朋辈成新鬼”的刺激,开始嗜好木刻版画,认为其风格冷峻,成本低廉,更利于革命宣传。嘉吉应鲁迅之邀,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间为上海“版画讲习会”授课,向十三位中国学员传授技法,由鲁迅亲自担任翻译。一九三二年他携妻回国时,鲁迅特意手书欧阳炯之词相赠,曰:“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引春风相对语。”
回日本三年后,内山嘉吉也辞去小学教职,创立东京内山书店。他效仿哥哥完造以学生为主要顾客的经营策略,最初的店址选在祖师谷大藏站前,因为这里是中国留学生的聚居区。与上海内山书店相似的是,嘉吉与日本左派作家保持着密切关系,竹内好、小野忍、冈崎俊夫等人,都是店里的常客。
完造和嘉吉,一个在中国卖日本书,一个在日本卖汉学书,犹如两翼颉颃。战后虽顿失一翼,但因为他们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东京内山书店备受新中国政府关照,连店名也是四十周年店庆时郭沫若所题——上海时代的另一位常客。内山完造自己也枯木逢春,相继担任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等要职,并发起“中国漫谈巡回行脚”,演讲八百多场,遍至九州和北海道。一九五九年他访华时,在北京的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意外病逝,遗体被运至上海,葬在万国公墓,与妻子团聚。

一八八五年出生于冈山县的内山,与书之间的缘分,最开始没有任何迹象。因为他小学四年级时便辍学,赴大阪大塚商店当学徒工了。完造之父是当地村长,算有钱有势,故此举绝非家庭经济所迫。据完造自己所说,他做出这个决定,纯粹“是为了反抗在家中只有父亲才能吃白米饭,其他人都只能吃半麦饭的压迫。因为如果去大阪工作的话,每天就能够三餐吃白米饭了。所以我决定远走高飞,业若不成死不还”。
“白米饭出走论”乍看有些可笑,但当时的内山,反权威的人格特质已经成型。刚到大阪时,因为能够自食其力,他顿觉如鱼得水,工作得非常卖力。但几年后,就因为带头要求店长改善员工待遇而被解雇。十六岁那年,走投无路的他被迫还乡,向父亲借了五十日元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大阪,成为眼药水生产企业“参天堂”的一名员工。
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青年时代的内山完造一度沉迷于运命学:“四柱推命、墨色、方位、方角、手相、姓名判断、八卦等等,几乎什么都信。”后来因为受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鑑三的感化,才渐渐转变成为一名基督徒。基督教特有的超世俗、同情弱者色彩,后来贯穿了内山的一生,成为其不易的底色。
所以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可能都误解内山完造了:他后来在书店二楼,屡次不计安危地庇护中国左翼联盟的成员,并不是因为他立场偏左、同情革命,而是他基督教的博爱、反暴力、反权威精神的体现。出于基督徒悲天悯人的性格,内山书店不但允许穷知识分子欠书债,甚至对偷书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先偷,等以后手头宽裕了再付款,不是跟借钱一样的嘛。”
内山书店最初的顾客,也是上海地区的日侨基督徒,渐渐扩展到正金、三菱、三井等日资银行的员工,最后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为主。以培养中国通为目标的东亚同文书院,其每届学生在毕业之前,都要在中国境内进行“夏季大旅行”,并选取一处撰写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涉及金融、民生、地理等方方面面,涵盖中国沿海、内地及边疆,可以与著名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相媲美。
因公或因私,内山完造自己也经常在中国游历。但从其回忆录《花甲录:中日友好的桥梁》中可见,最初他对中国底层的印象并不好。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一样,他也屡屡提及中国人的“不洁”,如上海饮水状况之恶劣、绍兴民居之肮脏,等等。偶尔他还会对比一番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诸如:“日本人的思维偏抽象,中国人的思维偏具体。中国人易冷易热,情绪起伏变化之快,犹如线香花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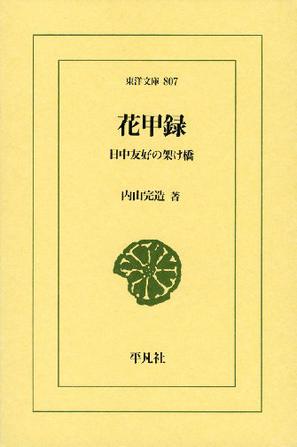
等到一九一七年内山书店开张,完造广泛地接触中国上层政治文化精英后,鄙夷中国的观点才悄然改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还没认识鲁迅之前,他通过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MCA)上海地区的活动,就已经认识汪精卫、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名人。
一九二一年谷崎润一郎来华时,也是在内山书店二楼会见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中国作家,显示此时在上海地区,内山书店不仅是与日本堂、申江堂、至诚堂书店并列的日本“四轩”之一,也是重要的中日文化沙龙。一九二七年,一位穿白麻长衫的顾客慕名来到店里,购买数本书后,用日语与完造说道:
“老板,这些书请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
“好的,请问尊姓大名是?”
“叫周树人。”
“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啊,久仰久仰。早听说您从广州回上海了,刚才没能认出来,失敬失敬。”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来店里,据完造白描式的回忆:“抽着烟飘飘而来,买几本书后,又飘飘而去。”后来鲁迅经常带几个年轻人一起来,他自己朝门坐在藤椅上,一边与他们谈话,一边观察外面的情况——若有异常,就立即起身转移。一九三一年“龙华事变”后,胡也频、柔石等二十四人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里被枪杀,风声鹤唳之下,鲁迅干脆搬进书店二楼。
即使如此,鲁迅对于内山完造本人,恐怕也未必完全信任,他曾说过:“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另一则史料则显示,日本共产党员尾崎秀实(1901-1944)寄居在内山书店二楼期间,与鲁迅多次彻夜长谈,但两人使用的却是德语,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尽管不无防备,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还是成为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日本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本思想界反思侵略战争,马克思主义席卷全国,《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刊物畅销,内山书店、极东书店、大安社等左派书店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期。但进入到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爆发后,日本左派运动式微,相关书籍也受到冷落,内山书店也难以恢复昔日的盛况。
晚至二〇一〇年,内山书店才被迫转型,开始出售中国以外的亚洲相关图书。但每次去店里,我都感觉整栋大楼(ビル)里顾客寥寥,颇为冷清,毕竟现在日本人文学科研究整体上都在退化,更不要说经营范围狭窄的内山了。即将迎来创业百年的内山书店,在店里自由取阅的宣传单上这样介绍道:“通过书籍,内山书店不仅将继续推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亦为加强全亚洲人民的联系而不断前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