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立新:历史学者应该如何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选题
10月23到24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主办了主题为“理解国际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历史经验”的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论坛。此次论坛由四十余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硕博士研究生分组报告自己的研究课题,再由北大、华东师大、首师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对报告内容进行点评,主办方期望以此促进年轻学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成长。
硕、博士阶段是学者进入研究领域的起步阶段,要想在以后的研究道路上走得长远,扎实、规范的学术训练是不可缺少的。在24日下午的会议上,主办方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做了题为《史学论文写作漫谈》的演讲,就年轻学人在论文写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如何选题,是很多硕、博士生常有的困惑,王教授在演讲中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记者整理相关内容,与读者分享。

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
学术研究是以问题为引领的,一个好的历史作品要提出、回答和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significant problem)。现在有不少论文就事论事,学术论文写成始末记,历史学者成了说书人或讲故事的人,这是不应该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问题的作用是根本性的,不同时代会对同一个历史现象提出不同的问题,所以历史的书写没有止境,历史学才能常新。王教授引用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的话说,“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当问题被更新了,空白有时候不用填就消失了。”
那么,在历史研究中,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呢?王教授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有三个标准:一是要探究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对现象(事件、过程、人物、政策等等)进行叙述,这种联系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如果在考察冷战兴起历史时仅仅叙述从富尔顿演说到NSC68号文件出台的过程,那就没有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如果我们通过比较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试图阐释“为什么美苏之间在二战时期能够进行有效合作,而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年就走向对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国的对抗无法避免”,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正是冷战史研究中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二是要触及历史现象和过程背后的深层动力,而不仅仅是过去史实的重建。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供历史的细节,当然细节很重要,它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带来愉悦感,但最重要的是揭示深层次的动力——那些在历史过程中长期起作用,会重复出现的要素。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是诸多因素“碰巧”汇聚在一起发生作用(contingency)的结果,因而具有特殊性,因此现象和细节是不会重复的,没有两种历史现象是完全一样的,重复发生的是深层次的动力和长期起作用的力量。解释这种动力是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第三,“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阐释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无论是史学学位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应该提出并回答前人没有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研究生在讨论自己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通常会讲自己要研究某个问题,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指的是“题材”(topic),比如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生会说,我想研究人权问题、越南战争或尼克松对华政策。这些都是研究题材,或研究对象,而不是这里所说的“有意义的问题”,提问是必须就这些题材或对象提出一个你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前人没有回答或回答得不好)来,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才可以说论文选题工作做完了,也就是说,题材(topic)不等于问题(problem),论文选题是题材和问题的结合,选题的关键是就一个题材(研究对象)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王教授进一步举例说:“比如,我的一位博士生要研究20世纪的人权史,这是研究对象,仅有这一想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就20世纪人权提出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来。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之后,人权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兴起了国际人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联邦政府和NGO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就是有意义的问题,其论文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即考察人权国际化的过程与动力。到了这一步,其选题工作也就大体完成了。”
怎么提出一个好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呢?很多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在研究中都有这样的困惑,似乎提不出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很多论文,只是通过材料的爬梳和解读,把历史事件来龙去脉或政策过程描述清楚了,而未能通过提出和解决问题来提供洞见。提出好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教授在发言中与年轻学人分享了他的个人思考,指出了四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途径是了解学术史。通过梳理学术史可以从四个方面找到有意义的问题,实现学术创新:一是发现前人没有关注的新问题;二是对前人研究进行深化;三是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四是挑战前人研究,提出对立的观点或挑战成说。学术的更新、史学流派的演进,往往是从发现和研究新问题开始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视野的变化意味着一系列前人忽视的新问题的出现。比如,随着6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过去被史学家忽视的底层社会的经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进入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新题材和新问题。80年代以来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史的兴起导致了大量新题材的出现,比如非政府组织、国际体育、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传播等,研究这些新题材和新问题就是创新。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让我们对前人研究进行深化。一些前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可能受时代的局限,材料没有完全解密,或者受研究者个人学养的限制,导致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通过对该问题的深化,实现学术创新。比如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在冷战兴起后不久之后就有人研究,但那时候没有档案资料,只能靠公开出版物和当事人的一些回忆。而随着冷战的终结,美苏双方的大量档案资料被披露,学者们可以运用更加丰富的材料、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新研究和阐释这个问题。实际上,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冷战史新研究”在这方面涌现了很多成果。
另外,还可以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任何一个史学作品都是从某个视角对历史现象的进行研究,很难囊括所有的视角,所以不可能穷尽和终结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而不过是对某个问题的阶段性报告,后人都可以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补充性解释。在美国外交史领域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对美西战争起源的研究。关于美西战争的起源,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解释: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美西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美国的经济扩张和寻找海外市场;地缘政治学的解释认为美国是为了获取海外军事基地、扩大海权;社会心理学的解释重视90年代美国的心理焦虑和精神危机对海外扩张的推动;还有文化的解释,探究美西战争背后的思想观念,包括帝国主义思潮、新天定命运论、种族优越感、家长观念等等。而哈佛大学的厄内斯特·梅教授则引入跨国和国际的视野,认为美国之所以发动美西战争,是因为受到欧洲追求海外殖民地、建立帝国的“国际时尚”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海外殖民地、“教化”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大国的标志,是大国的“标配”,是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票。而当时美国已经崛起为强国,渴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承认,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正是在这种“国际时尚”的影响下,美国决定兼并菲律宾。厄内斯特·梅的这一研究不是要推翻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为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无疑也是一种学术创新。
当然,你的研究也可以是直接挑战成说,推翻既有的研究本身就是重要的学术创新。
第二个途径是现实关怀,在过去和现实之间建立关联性,以此发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提出新的看法。历史学家要关注现实,历史学家不是古董迷,要有现实关怀。如果对现实一无所知,想要了解历史也是徒劳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可以帮助理解历史现象,纯粹的好古主义是没有办法造就伟大的历史作品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托克维尔撰写《论美国的民主》就是基于作者的现实关怀:法国为什么历经多次反复的革命和动荡,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于是,他去美国考察,成就了一部经久不衰的名著。“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观察、对有关中美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忧虑的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一战前德国和英国的关系,理解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霸权转移’过程。有人说,英美之间可以实现和平的霸权转移,为什么中美之间不能?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类比,我并不主张简单的历史类比,只是想说,对现实的洞察和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进行分析;反过来,对历史的理解也会启发我们思考当下。”王教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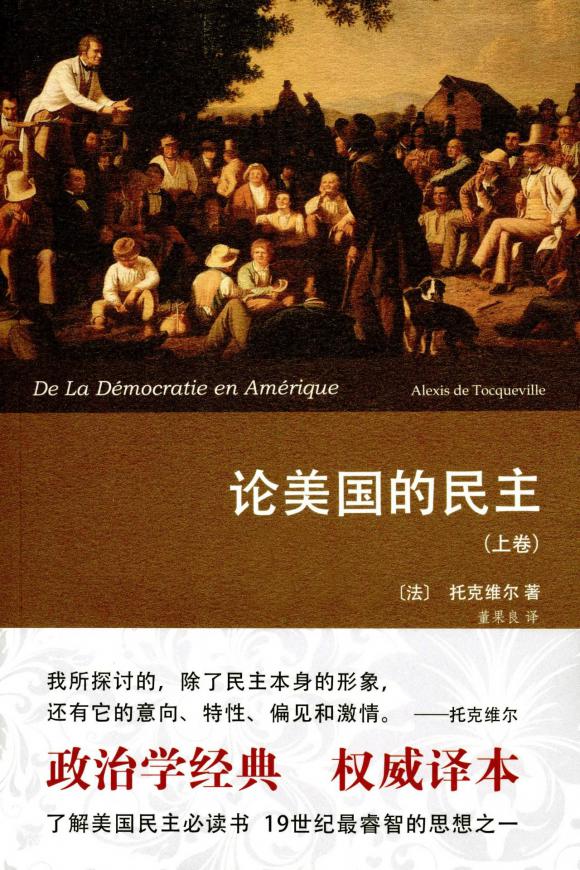
第三个途径是培育自己跨学科的素养。跨学科的知识对我们发现选题,提出有意义的问题非常有帮助。比如耶鲁大学教授、冷战史研究权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有很精深的国际关系学的素养,在70年代初借鉴了“安全困境”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思考和阐释冷战的起源。在此之前,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已经有正统派和修正派,前者谴责苏联的扩张和意识形态导致美苏无法继续合作,后者指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认为其要为冷战的兴起负责。而在加迪斯看来,关于冷战起源的探究不能局限于道德的谴责,还应该看到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特性对美苏行为的制约和塑造。二战后出现严格的两极体系,在两极体系下,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使美苏两国各自的防御性行为被对方视为进攻和扩张性行为,其结果是相互误解、猜忌和敌视不断加深,进而导致对抗的螺旋式上升,使冷战不可避免。这一解释借助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安全困境,这超出了我们常识和经验的范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也丰富了关于冷战起源的解释。王教授又举例说:“有的学者用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研究美韩关系、美日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台关系。‘同盟困境’理论是指,结成同盟的国家是不平等的,大国担心被小国牵连,小国担心被大国抛弃,从而引发二者之间的猜忌和矛盾。这一理论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历史上的同盟关系。”
第四个途径是多读深思。要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刨根问底,不要轻易认同前人研究。例如,关于美国革命的起源,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史学界大体上已经有共识,认为是英国的高压政策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导致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哈佛大学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却没有简单地接受这个观点。他通过考察英国议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税率发现,殖民地人民承受的负担其实远远低于英国本土,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也超过了英国人。但为什么殖民地人民还要追求独立?他利用前人没有使用的革命者的宣传品作为基本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阴谋假说”,认为革命者反抗英国主要不是因为英国的政策真的严重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而是由于革命者认为英国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一旦被落实,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会遭受践踏,被剥夺殆尽。主要是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而不是现实的损害促使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这就是批判性的阅读。批判性阅读的另一种方式是探究既有结论与经验事实是否一致,我们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与既有结论不一致的史实或现象,就说明既有的解释出了问题,需要有新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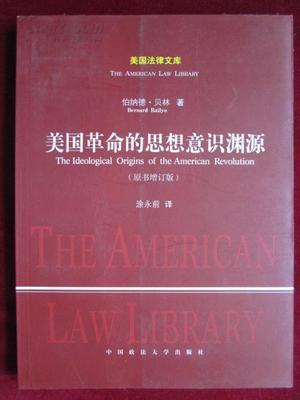
学位论文的选题原则
王教授从自身指导学生的经验出发,针对硕、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提出了几点技术方面的建议。首先,选题大小要适中,不能太大,太大了在有限的时间(博士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无法完成,太小则学术价值又不易挖掘出来。当然,选题的大小是相对的,这跟学术潮流和学术观念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次,选题不能过难,自己要能驾驭。“过难”是指涉及太多理论问题和知识领域,超出研究生的思维能力。研究生的学养毕竟有限,不能把资深学者才能驾驭的问题让研究生来研究。再次,要“以小见大”,即题材要小一点,资料搜集容易,在有限的时间可以完成;同时又要有宏大的视野,从小问题中阐发出大的意义来,把小问题和更大的历史进程、更有意义的大问题联系起来。最后,选题要有进一步拓展和进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王教授说,学术研究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多博士生毕业后还会继续学术研究,选择一个有拓展空间的选题无疑更有利于作者以后的学术发展。
最后,王教授说:“历史研究是一门技艺,技艺是需要工具的。这里的工具既包括史学的基本技能,也包括跨学科的素养和各种理论知识。工具箱越丰富,学养越丰厚,越能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在常见的史料中发现新意义,为老问题的解释找到新视角,从而写出优秀的史学论文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