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首师大同侪悼念青年历史学者孔源:一个纯粹的知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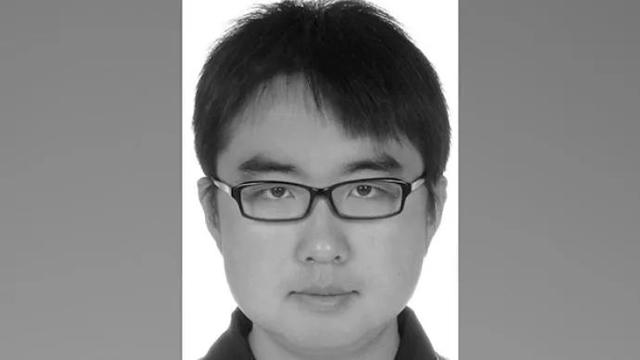
青年历史学者孔源
青年历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孔源于11月13日去世,年仅36岁。消息传出之后引发国内历史学界众多学者的哀悼、惋惜。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学科官方微信公众号11月16日刊文《缅怀孔源老师》,集纳了翟韬、于展、陈志坚、李永斌、姚百慧、王超、李建军、倪玉珍、乔瑜、崔金柱、蒋家瑜等多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对于孔源的悼念文章。
文章写道:孔源热爱工作,关爱学生,为培养学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同事认可和学生爱戴。孔源心如赤子,纯正善良,心诚行笃,关心父母,呵护妻女,生活朴素,乐善好施,爱好文艺,长于歌咏,恍如误入人间的天使。而立存自性,才华常夸师友口;卅六人生旅,黾勉永存父母心。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翟韬在文中追忆:老孔在首师大,我是他交往最多的同事,他信任我,愿意在班主任工作上“请教”我,愿意和我聊聊学术规划,我也愿意关心他、“指导”他,把他当弟弟看待,愿意关心他照顾他。这两年我愈加地忙了,有时甚至忽略了他,现在想起来心如刀割。老孔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特别牛,五门外语(可能不止),数次学术交往让我感觉他几乎无所不知,提什么都懂,讲课点评论文从来不看稿,智力超群。我常和学生说孔老师讲出来的只是他学问冰山的一角,而跟他比起来我跟文盲一样。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于展追忆:孔老师刚到首师大,分到和我同样的办公室里,因此有时间我们能聊一会天。孔老师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人,学识十分渊博,研究具体问题又非常精深,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无疑需要超常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因此和孔老师聊天总能获得很多收获。
陈志坚副教授追忆:骤闻孔源老师离世,我不敢相信。因为前一天中午在文科楼一层大厅还与孔老师打了个照面,当时他正往外走,我则是进文科楼,因为我们之间隔着很多赶饭点去吃饭的学生,只能彼此点头致意。不想这竟是与孔源老师的最后一面,悔恨当时没能与他说上几句话。平日里,因各自忙于工作,办公室也不在一个楼层,我与孔老师的交往并不多。
李永斌副教授追忆:(孔源)他是一个“讷于言也讷于行而敏于思”的人,在吃饭、逛街这些俗事方面,他经常有些无所适从。但是一旦到了博物馆,他立刻轻松自如起来,对阿斯摩林博物馆藏的中国瓷器如数家珍,对这些瓷器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有非常深邃的见解。在科技博物馆,他对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了解之深,评论之深刻,让我大为震惊。
公开资料显示,孔源,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是早期近代欧亚史、中俄关系史、内亚研究等。他在《俄罗斯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主要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大众文艺里的苏修形象》、《近代呼伦贝尔地区俄罗斯人经济文化区发展与形态》、《清代以来达斡尔族跨兴安岭贸易及其地理基础》、《从‘dergi’一词看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等。
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方面介绍,受到家庭影响,孔源从大学起就开始发表俄罗斯地缘相关文章,一直比较关注苏俄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孔源在北大英语系、俄语系、历史地理,社科院近代史等专业方向辗转修学期间,关注的重点一直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中俄关系、中俄文化交流等方面上。
孔源除在英语、俄语方面有良好基础,研究东北史地之时也学习了满语、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多次到俄日美等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也对东部内蒙古等地区进行了若干次田野考察。另外孔源还曾自修德语。
孔源的父亲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凡君。孔凡君,笔名孔寒冰,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东欧政治与外交”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孔凡君已出版过相关著作有《寒冰访罗明》《从华学博士到驻华大使》《中罗两国的桥梁》《执着的汉语史学家》《“黑脚”的汉语之路》《在历史与现实中探寻中国》《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发表的相关学术文章几十篇。
孔源去世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义军等学者也在微信公众号、微博撰文悼念,表达哀悼。
以下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几位教师的悼念文章:
忆孔源
孔源离开我们已经2天时间了,我仍然是恍恍惚惚宛若梦中,不敢相信这是现实。昨天在家里躺了一天,头晕地厉害,孔源离世的消息像是一场噩梦把我魇住了,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我称孔源为“老孔”,这个称呼在我们首师世界史青椒群体中叫开了。老孔喜欢这个称谓,也称我“老翟”,甚至称倪玉珍老师为“老倪(老尼)”,听着别扭又好笑。如今老孔不在了,我没法在当着他的面叫一声“老孔”,何其悲也。
老孔在首师大,我是他交往最多的同事,他信任我,愿意在班主任工作上“请教”我,愿意和我聊聊学术规划,我也愿意关心他、“指导”他,把他当弟弟看待,愿意关心他照顾他。这两年我愈加地忙了,有时甚至忽略了他,现在想起来心如刀割。老孔最大的特点是学术特别牛,五门外语(可能不止),数次学术交往让我感觉他几乎无所不知,提什么都懂,讲课点评论文从来不看稿,智力超群。我常和学生说孔老师讲出来的只是他学问冰山的一角,而跟他比起来我跟文盲一样。
老孔还是个正心诚意的君子,和他交往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异乎寻常的炽热热情。他和我郑重大声表示要为首师大、要为北京基础教育贡献一份力,他说父母都当过教师,他有这情怀;他在首师大世界史学科开会时当众以朗诵腔宣布,一定要把在北大开设的中俄关系史文献课开回首师大,铿锵坚定;我负责协调一些基础课程的开设和规划,找到老孔,他从不拒绝,荆腾没入职之前,他还主动倡议几位老师先把德国史开起来,别让学德语的同学没有国别史课程。
老孔后来担任了18级世界史班班主任,他孩子般地兴奋,如获至宝、无比投入,看到他发的朋友圈和同学们的朋友圈,能感受到他的心和同学们在一起、兴高采烈。常感到18级学风端正朴实,我感觉老孔热情投入的学术态度和对同学的关心厚爱作用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正像同事乔瑜老师说的,老孔有赤子之心,感召着有慧根的学子们。老孔走得匆匆,没有一声告别,但我觉得他也是很幸福地走的,他最终从事了最钟爱的学术事业,他有着爱戴他的学生,有着温暖的同事情谊。这一切都给了这个腼腆羞涩、不善言辞的大男孩以莫大的慰藉,他也是幸运的。老孔,期待来生还能做兄弟,多听老翟再唠叨几句……
(翟韬/文)
孔源老师千古
听到孔源老师突然去世的噩耗后,几天时间里一直处于恍惚的精神状态中,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我的心脏也常感到难受和疼痛,第一次深刻体味到痛心至极的滋味,脑海中不时回想起一些孔老师生活中的片段。
孔老师刚到首师大,分到和我同样的办公室里,因此有时间我们能聊一会天。孔老师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人,学识十分渊博,研究具体问题又非常精深,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无疑需要超常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因此和孔老师聊天总能获得很多收获。后来每次开学术会议,也非常喜欢听孔老师发表他的高见。当时学校工会每年发蛋糕券,孔老师还没有孩子,就常把蛋糕券赠给我,他的一些书我翻看时,他见我喜欢也常慷慨地赠送与我。孔老师很追求上进,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付出巨大的努力,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正是他大展宏图之时,没想到天妒英才,痛呼哀哉!
孔老师千古!
(于展/文)
忆孔源
骤闻孔源老师离世,我不敢相信。因为前一天中午在文科楼一层大厅还与孔老师打了个照面,当时他正往外走,我则是进文科楼,因为我们之间隔着很多赶饭点去吃饭的学生,只能彼此点头致意。不想这竟是与孔源老师的最后一面,悔恨当时没能与他说上几句话。平日里,因各自忙于工作,办公室也不在一个楼层,我与孔老师的交往并不多。但我素闻孔老师不仅做事认真,还是一位热心肠的人,非常愿意帮助别人。记得有一次与孔老师一起在北一区阶梯教室监考本科生教师资格考试,在发完试卷之后,我便走到教室后面躲清静,孔老师则闲不下来,不仅主动承担了整理所有监考文件的劳动,还不时地提醒学生各种注意事项及考试剩余时间。又因考试要求最终的试卷须按照考试号从小到大排序,孔老师索性守在讲桌那里收卷子,学生每交一份卷子,便仔细地将其插入一大摞试卷中,并确保它在应该在的位置,认真至极,可爱至极,让人忍俊不禁。另外,我还特别敬重孔老师的不断学习,勇于进取的精神。孔老师在其学习、工作的任一阶段都能注意学习新语言以利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我所知,孔老师精通英、俄、德等语言,并可阅读蒙、满等语言书写的碑刻、文书、档案,实在是令人佩服。之前我还想着有机会去听孔老师的文献课呢,没想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愿孔老师安息!
(陈志坚/文)
沉痛悼念我们的亲密同事孔源老师
孔源离开我们已经三天了,这几天一直心里阵阵悸痛,晚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仍然不愿意相信如此年轻的优秀同事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恍如昨日。
我第一次和孔源有非常深入的交流是在2017年10月。当时他偕夫人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学,我在牛津大学古典学系访学,我们相约在牛津见面。我们一家四口和他们夫妻俩,还有我的一位师姐,一行七人浩浩荡荡地去吃著名的Cosmo自助餐,然后去逛街,参观阿斯摩林博物馆、科技博物馆、自然博物馆。他是一个“讷于言也讷于行而敏于思”的人,在吃饭、逛街这些俗事方面,他经常有些无所适从。但是一旦到了博物馆,他立刻轻松自如起来,对阿斯摩林博物馆藏的中国瓷器如数家珍,对这些瓷器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有非常深邃的见解。在科技博物馆,他对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了解之深,评论之深刻,让我大为震惊。
后来,我多次和他一起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一起带学生去天津交流,组织学生去西安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世界史专业论坛和“海国图志”奖。去天津交流的时候,他会用天津话给大家介绍天津的各种历史遗迹和历史典故。去西安考察时,我负责整体的前期组织工作以后,就放心地让他自己和崔丽娜老师带着世界史班的学生,和学院其他老师带队的大部分一起去了,但是我一直在带队老师群里交流。大家在酷热的暑期里奔波于各处参观考察,一些同学出现了轻微中暑等状况,孔源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忙前忙后,既要负责同学们的起居、饮食、出行,又一直关心照顾身体微恙的同学。他指导的杜俊超同学获得了“海国图志”奖二等奖,我们祝贺他和学生,他却表示,“主要还是学生有潜质,他的论文是我改得最少的”。我经常说,如果说世界上有真正纯粹的“赤子之心”,那非孔源莫属。
我们痛失一位如此优秀的年轻同事,在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手指发抖,思绪也一片混乱,甚至都不敢回看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就此罢笔,惟愿真有天堂吧!
(李永斌/文)
追忆孔老师
孔老师来首师大世界史,已愈五载。五年多来的接触,我的一点体会就是,孔老师在积极地融入我们世界史团队,尤其融入我们青椒团队。虽然担任班主任是几乎每个青年教师都要做的,但孔老师非常积极,来后就主动找我们、找学生口负责人,后来是成为2018级班主任。教授课程是教师的天职,但孔老师在上课上异常主动,除了《世界近现代史》通史课程,以及世界史专业特色必修课程《世界历史要籍选读(俄语)》、选修课程《俄国史专题》外,他自己主动提出开设《满文历史文献入门》,为历史学院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不熟悉在全国这门课的开设情况,但类似课程在首师大是独一份。本学期孔老师正在上《满文历史文献入门》,随着他的离去,该课程竟成绝响。我作为学院的督导,今年3月曾有幸听过孔老师的《俄国史专题》,当时该课正讲古代罗斯部分,孔老师对古代罗斯的相关概念、时空范围、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化特征、宗教与社会、交通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孔老师做事认真,无论是做班主任、上课、指导学生、参加学院、参加团体活动的会议,他都是一丝不苟。我们都作为团队成员参与教学改革项目“面向基础教育的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建设”,其中一个是编写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图片说明。孔老师撰写的《新型航海图比萨图》,对该图的馆藏、演变、历史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得到项目负责人徐蓝教授好评,作为样章供大家参考。
(姚百慧/文)
回忆孔源老师
对孔老师的印象,首先是他的热心。刚来首师的时候,我分到和他一间办公室。记得刚见面,孔老师就说要让出自己的书柜。我自然不愿夺人所爱。可谁知过一阵再回到办公室,柜子已经摆到了我的一侧。他把自己的书都搬出来,一些带了回家。剩下的,只是又用一个简易的新书架,临时放了起来。
后来学院安排我和孔老师合上世界近现代史。为了衔接顺利,孔老师的部分我时常会去听听。如果两个人都有空的话,也会约着下课后在一处吃饭。孔老师喜欢去清真食堂,南门外的披萨店还在的时候,也进过一两次。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听孔老师谈天说地,那样的回忆,至今依然生动。我对于俄国史纯然是外行,因为要备课的缘故,常会趁着这个午饭的机会,问问孔老师的看法。记得有一次,说到为什么1905年之后的俄国似乎已经在向上走了,却还是抵不住1917年的革命。孔老师只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句,因为沙皇的帝俄太反动了。顿时于我有一阵冲击。如今想来,那话语里面的力量,大概不仅出于孔老师对俄国历史的熟悉,更有一部分当是他对自身信念的执着。
孔老师出事的前一个下午,他的课刚好接在我的课后面。我还和他发微信,请他帮忙拿一下我忘在教室里的东西。现在睹物思人,却没了和他道谢的机会。还有我内心的歉疚,也无处开口了。接下去,只有继续地上课,继续地教好这班学生而已。青青校树有一日长成栋梁之材,孔老师知道了必定欢喜。那时我们会用丰收的号角向你致意,愿你在天国里安息。
(王超/文)
忆我的同事孔源
这两天,悼念孔源英年早逝的信息铺天盖地的袭来,难受之余,我也写下零星文字,表达对孔源的怀念。
我和孔源虽是同事,但是因为我经常在首师大本部办公,与他交往不多。说实话,因为共同的研究领域,我与他的父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孔凡君老师更为熟悉。每次我和孔凡君老师在会场相遇,就会谈到同事孔源。我告知他虽然我和孔源交往不多,但是大家公认孔源是一个学识渊博、学问扎实的青椒。记得一次孔凡君老师以无奈、苦恼又包容的语气揭秘道:“你可不知道,为了一篇考证性论文,孔源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是的,孔源就是这样纯粹的学术人,在追求学问的路上倾尽全力。
虽然我与孔源互动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件事非常值得追忆。那就是孔源教我如何直播。2020年春,因为疫情的关系,教学改为线上。开始大家对五花八门的直播软件并不熟悉,孔源的直播课用的是企业微信,于是想使用企业微信的我便发微信向他咨询。孔源担心文字回复得不够清楚,直接用企业微信直播的形式从头到尾给我演示了一遍如何上课,如何让学生发言,如何生成回放视频,并嘱咐我直播要注意的细节。这次线上演示让我发现,孔源虽然老是一脸严肃,但其实是一枚暖男。他的热情和细心至今让我依然感动。
11月13号上午梁占军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孔源在参会期间猝然去世。我无比震惊,一再和他确认这个消息。我和梁老师马上前往现场,看到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的孔源,听到了孔源妈妈撕心裂肺地哭喊“你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和孔凡君老师心痛、不舍又压抑地呼唤“源源,源源……”我们心里难受极了,难以接受孔源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我们。
世事真的无常,我们甚至还未来得及彼此熟悉,睡梦中的孔源就这样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惟愿你安息!
(李建军/文)
怀念“孔孔”
在米兰·昆德拉所区分的“轻”与“重”的两类人里,孔源显然更多地属于后一种。他珍视某些事物的价值,并且认为它们是不容亵渎的。对于别人给他的善意,他也异常珍重。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帮助,他也会用一种过于庄重的方式,表达感激。
在学院里见到孔源时,他多数时候是行色匆匆,神情严肃,若有所思。我总感觉他身上背着重负,却说不出它们是什么。或许他渊博的知识,也是其中一个吧。他像一个知识收藏家,头脑里储存着丰富的、各样的知识。如果他能安适地、自足地待在他的精神王国里,取用和享受这个丰富,那他会是很惬意的。然而他却很渴望他的精神世界能和他人的互通,于是他就有了一种孤独。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况且当他滔滔不绝地数着他的家珍时,也没什么人能接住他打过来的球。
孔源的心思敏锐且敏感。或许因着这份敏感,他偶尔会为一点事情激动起来,甚或有点小脾气,但在学院的“青椒”群里,大伙儿都挺爱护他。因为谁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心中住着一个孩子。私下里,我们都叫他“孔孔”。记得2017年11月的一天,他在青椒群里发信息,说他明儿生日,问谁有空来学校,和他一起过生日。第二天中午,我们四个青椒奔过去,在首师大南门陕西菜馆和他一起过生日。他像一个孩子似的,高兴得眉飞色舞,时而说两句逗趣的话,时而“飚”几句他热爱的学术。还记得2019年11月的一天晚上,孔源在青椒群里发了一个“34岁生日大红包”,催大家领红包,“我先领为敬啦,祝我生日快乐!”现在想来,那天孔源或许一直在等着大家和他一起过生日。
孔源有着渊博的学识。可是我明明地看到,这些知识,并没有叫他那样一个敏感的心灵得饱足。他是一个有着深情厚意、也渴望他人有同样的深情厚意与他相往还的人。然而在这个各种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压力驱使着人们忙忙碌碌的时代,朋友和同事的一点点善意对于渴望同伴和爱的孔源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还记得他曾把我拉进一个“PKUer香山凤凰岭奥森及远足群”。然而在我的印象中,这个群并没有成功地组织过一次远足。孔源渴望的深厚、真挚、亲密的友谊在这个时代,注定是一件奢侈品。
在孔源短暂的一生里,人没能给他足够的爱。愿他的灵在天国得到安息,愿天国里,他能得到丰盛的慈爱。
(倪玉珍/文)
忆老孔
孔源老师与我同岁,比我晚两年入职。我和同事们一起参加过他的入职面试,尽管能看出紧张、但很容易就被他的睿智渊博所打动。入职后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来学校的时候一定会来串门,平日里大家都跟着资深青椒翟韬老师称他为老孔。有时候翟老师亲昵的唤他wuli老孔。老孔可能挣扎了一段时间,就默默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接触稍多一些,就会发现老孔和我们中很多人一样,是社交恐惧症和社交牛*症的双相患者,腼腆又炙热。
2017年5月,在刘文明老师的支持下,我和老孔以“边疆、生态与文明”为主题一起张罗了一个小型工作坊,期间交流很多,老孔几乎视俄罗斯研究与边疆史研究为生命的执着让人动容。再后来一起监考、出题、参会,也经常能感受到老孔对学问和知识的认真,甚至较真。他也从来不“放过”学生,我旁听过一次他的《世界名著导读》课,那堂课讲的是《历史的地理枢纽》,老孔旁征博引,开阔天空,学生在底下奋笔疾书,临了还不忘给毫无准备的我布置个任务:给学生介绍特纳的《美国历史中的边疆》。2020年初的研究生复试线上进行,老孔和我一起负责英语复试,老孔的问题都不容易,我提醒他可以降低一点难度,老孔沉默一阵不忿的看我一眼。今年,我的研究生刘岳着手俄罗斯环境史的研究,老孔得知后慷慨的提供了资料援助。
在生活中,老孔也有格外特别贴心的一面,他会在外出归来后给同事带回各自适配的礼物,然后热切又拘谨的拿给大家,他也会因为一句半年前的玩笑话,坚持驱车送同事回家。老孔爱歌唱,学院的联欢会上他表演过蒙语、俄语歌曲。他那高速运转的cpu里应该还装着海量的曲目,一次从良乡校区监考回来,路上聊起各自的家乡,下了校车他颇有兴致,唱了一首他认为我应该耳熟能详而我闻所未闻的苏北抗战革命歌曲。
重新分配办公室后,老孔距离我们办公室远了一些,仍时常可以见到他在楼道里踱步。和我们中大部分一样,老孔也有他的困顿,但稚气又炙热的他比我们更加激烈。三年前他有了心爱的女儿,疫情期间他开始健身,体重也降了不少,我们都以为一切会比以前更好。与老孔相识不过数载,他就像蒙古骑兵一样,乘风而来,又潇洒离去。这两天走进文科楼四层,历史青椒的大本营,一切看起来并无变化,只是大家都知道遍插茱萸已少一人。
(乔瑜/文)
悼孔源兄
2021年11月13日,学友孔源兄以36岁英年早逝,沉痛万分!自2016年秋成为首师大世界史团队的同事以来,孔兄总用略带天津口音的语调唤我“劳崔”,我则一直称你孔兄。以社会常识论,我们已是中年,但在大学科研及教学工作中,我们还是刚刚起步的“青椒”,远未到被回忆的年龄。我们的人生交集不算长,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纯良、热忱,共情力强,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孔兄学识深厚,当聊起专业话题时,一直以“话痨”自居的我永远只有听的份儿。孔兄热爱天空,时常看到你拍摄的清晨月、黄昏霞,那里也许是你的自由精神家园。
这两天总是想起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时而又会冒出一个念头——若是30年后为荣退的孔兄撰写贺文该多美好啊!以孔兄多语文能力与广博的专业积淀,定能在内亚史、中俄关系史等领域作出更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天妒英才!孔兄,你离开得太早了!
愿你安息!
(崔金柱/文)
忆老孔
孔兄长我两岁,来到首师大世界史学科后,我们青年教师之间都戏谑地给对方加了一个“老”字,故我喊他“老孔”,他屈尊唤我“老蒋”。记得有次他与我在学院里偶然相遇,因双方都蓄有胡须,于是笑称我们二人才真正地无愧于“老”字。初识老孔是2013年,我那时仍博士在读,冒昧地去复旦大学“跨界”参加了历史地理学的会议,但当时交往并不多,仅仅是闻其大名而已。2017年来到首师大并逐渐熟络之后,才惊觉世界竟如此之小。我们的亲朋好友网络里充满了诸多的重合,我们都和北大外院以及北大的历史地理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因为以后会同在一个小区而相约要一起遛娃。由于我们正好是前后脚担任了17级和18级本科生的班主任,所以工作上几乎一直都在交流着各自当班主任的心得和经验。显然,老孔是一个认真且心细的班主任,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班里每位同学的状况,积极为同学们的切身利益而奔走呼吁,这都让我敬佩不已。在学院新年晚会上的才艺展示显然就是他跟学生们打成一片的最好证明,我们甚至还曾相约要为新年晚会献上一段京剧合唱。然而,遛娃、京剧合唱等等约定都随着他的突然离去而无法实现了,那个认真且充满生活感的老孔也就此定格在我心中。老蒋终将老去,但老孔却永远不会老了!
(蒋家瑜/文)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