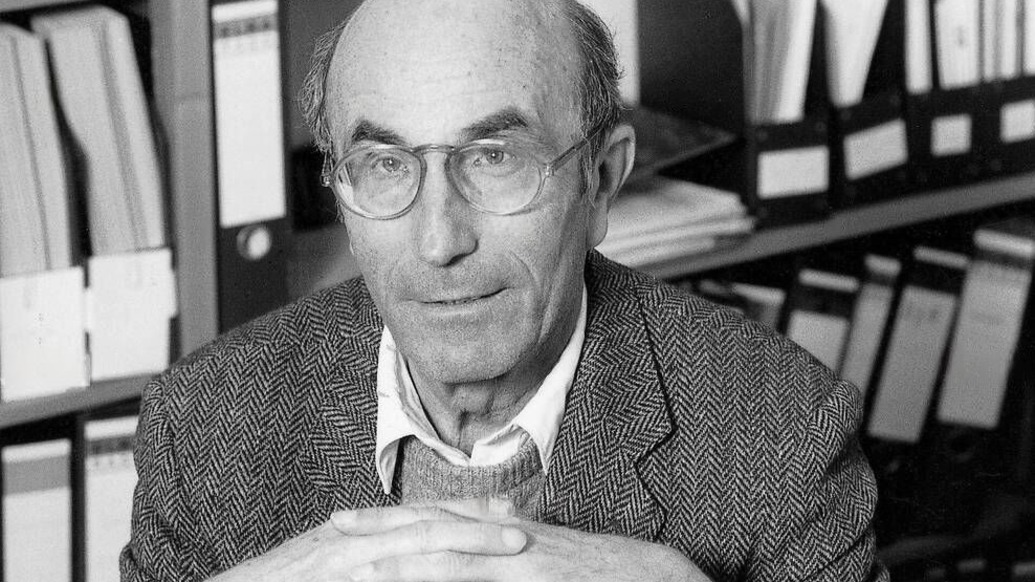- 47
- +157
“学术小时代”来临,年轻学者失去了大关怀吗?
本月初,笔者旁听了“现代性的质疑:近代中国的新传统主义”学术研讨会,从这个会议主题就可看出,这是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大议题。而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年长一代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讨论长时段的问题,而年轻一代的学者基本上走的都是以小见大的路子——从某个人物、思想或事件切入讨论某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历史学界,这不仅是这次研讨会上呈现出来的代际差异,也可以说是当下年长学者与年轻学者在研究旨趣上的差异。

第一代关心政治,第二代关心文化,第三代关心学术
此次学术研讨会,最后安排的是一场圆桌会议。年长一代的学者率先发言,谈及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启蒙时代的大主题,而年轻学者一开始并没有加入讨论。会议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自我调侃道:“现在似乎开启了‘老年频道’,有些年轻学者可能在想,你们这些老人啊,还就是那样,想着做‘帝师’,整天在思考救国大方案,恰恰天下就是被你们害的。”
许教授继而提到了他在199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这一划分,具体来说就是: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那么各代知识分子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在许教授看来,主要是体现在具体关怀上:
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
很明显,当下的历史研究也已经走到了第三代。套用一个流行语,许教授将这类研究旨趣概括为“小确幸”,即专注于做确定的学术,追求确定的社会目标,对宏大叙事不感兴趣。所以,年长一代学者习惯于将问题还原为政治和思想问题,而年轻一代学者更愿意将宏大问题分解为一个个学术问题。
不过,许教授在发言的最后总结道:“老了的标志是话多,这一定要警醒,一定要给年轻人腾出空间,节制是老一代学者最大的美德。”
年轻学者为什么没有了大关怀?
既然讨论到了这样的代际差异,年轻学者便开始踊跃发言,似乎要为自己“辩白”。
《学术月刊》编辑张洪彬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到:“青年学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间也就十来年,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够多,不太敢说话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遇到自己还没下过工夫的议题,更是如此。这又跟学术竞争有关,即便是仅考虑现代学术,也已经有一百来年的积累,已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那里,你要涉足某一题目时,必须要正面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就会发现自己的施展空间很可能其实很小,在此情况下,要在学术竞争中取得成绩,往往需要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做专深的研究,而不是就已有许多成果的问题做大而化之的发言。也就是说,学术纪律在客观上会推进专门研究的发展,而不太容易催生通人。”在他看来,通人之学尽管值得向往,但在现代知识生产的大环境中,已不太可能。他转而强调,更应重视跨学科研究,因为研究对象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复杂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现代学科范围。比如我们要理解章太炎,若不能理解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佛学义理,就很难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一个思想史学者越能全面理解思想家的知识背景,就越可能理解思想家及其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瞿骏分析了这种学术变迁背后的时代因素。1980年代颇近似于“五四”时代,那个时代关注重大问题,饱含激情,富有关怀,但提问和写作的方式也多和“五四”一样,传统与现代并举,中国与西方对峙。无论是谈传统,还是论西学,都相对不那么透彻和精致。但也正因为不囿于透彻和精致,往往会产生一些大的、跨学科的、可以有持续性思考的洞见。放眼今日,年轻学人因学院之严苛规训,恐怕很少敢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样的方式来提问或做文章。他们经常追问自己的是,说传统,究竟说的是哪个传统,你有足够的水准来谈这些个传统吗,西学也类似。这种心态的好处是能够更精细地处理传统的复杂性和西学的多元性,有助于跳出那些二元对峙、非此即彼的惯常想象,但弊处则在相较1980年代离“通人”之学就更远了一些。因此年轻学人或一方面仍需去追寻中国传统中“通人”之学究竟所指为何,另一方面要通过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对1980年代的时代气氛不断重温与回味。心态不妨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可能会比一意沉迷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精耕细作,收获要更多一些。
的确,时代变了,传统也在远去,当下的研究者如何重新进入传统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高波就说道:“年长一代或多或少都见过老先生,亲身接触过民国范儿。而我们一代人则跟活生生的传统比较陌生,需要靠艰苦的研究工作才能重新进入传统。”在他看来,转折时代大关怀显露较多,而当下是一个常态化社会,改良是常规手段。年轻一代学者的大关怀是潜藏的,表达方式更为迂曲。这既跟生存压力有关,也跟当今社会的需求相关——整全性的思想不是当下的首要要求。所以,还是胡适先生的那句老话说得好:“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章可则从当代知识人的身份定位入手分析了这个问题:“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也可以被看成是某种商品,而知识分子只是知识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如果从这个角色定位来看自己,那么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会降低。修齐治平在古代社会有价值,但现在已经是专家治国的时代了,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在文化领域、公众舆论方面发挥影响,但要把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古典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接续上,已无必要。”
说到知识生产,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的彭春凌看到,现在越来越是全球融合的时代,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这对研究者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语言、认知、材料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使研究者埋头于个别问题的深挖。
大关怀在“学术小时代”如何可能?
既然很多人都谈到了通人之学,关注儒学的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展良最后总结道,他并不反对专家之学、分科之学,这种清晰的定位是应该的。但通人之学与专家分科之学应该互相尊重,它们其实是可以互补的。在吴教授看来,通人之学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只是更侧重于探究当今世界的根本性问题。
面对这场争论,笔者不由想起了日本著名佛教史学者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在今年6月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谈到的一番话:
比我年长的、“文革”前就开始佛教研究的学者,或者跟我同年代的学者比如葛兆光教授,虽然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很宽阔的研究视野,试图在研究中把握全景和全貌、抓住大的脉络。而现在的年轻学者,人数是变多了,但他们把研究范围变得比较小,可能是希望在限定的领域中更快地拿出更多的成果。所以,我感觉,这使得最近的研究成果对整体的把握不像以前那么充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日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细节进行深入研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些细节的研究是在接受既有的整体理解下展开的。举例来说,佛教有各种各样的宗派,但这些宗派原先是没有的,到江户时代后才逐渐产生,宗派的门户也逐步建立起来,而且彼此之间越来越泾渭分明。日本的宗派思想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中国也接受了各个宗。那么,现在的研究如果都以这些宗的构造为前提的话,就不能突破各个宗之间割裂的局面。这些细节研究是无法对整体理解提出质疑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佛教的整体变化,恐怕要突破这个前提。细节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对整体的构想和把握,恐怕只能在小范围内打转,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可见,这种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学者在研究旨趣上的差异,是当下历史研究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公允地说,没有细部研究的广发展开,我们可能无法更好地推进对整体的认知;而如果没有整体性的关怀,细部研究“恐怕只能在小范围内打转,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所以,用许纪霖教授的话说,再好的微观研究,也需要一个整体的“认知地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学术研究,皆不可取。

- 巴基斯坦被断水
- 外交部回应美称中美仍在谈判
- 全国贸易摩擦应对工作会议召开

- 美股开盘:道指开盘跌0.1%,标普500涨0.1%,纳指涨0.1%
- 三六零:一季度净利润亏损2.73亿元

- 动物体内的一种脂类化学物质,能引起动脉硬化或胆结石
- 中国的一位著名建筑学家,是林徽因的丈夫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