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勇:坚持发展本位,重建合乎时代的新儒学体系
马勇:坚持发展本位,重建合乎时代的新儒学体系 原创 陈菁霞 中华读书报
20多年前,马勇应庞朴先生的邀约,参与其主持的四卷本《中国儒学》的编写工作,其中,第一卷《儒学简史》由马勇独立撰写,在30多万字的篇幅中,将三千年儒学史做了系统、概略、完整的描述,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该书能够清楚儒学发展历史的整体框架。最近,该书的修订扩充版《中国儒学三千年》由孔学堂书局出版。马勇自言,写作这本书是想从一个比较宏大的视野检讨儒学三千年历史,最大限度地摆脱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污名化,也最大限度地与“尊儒者”疏离,取历史主义立场探究事实。而对于儒学内部分歧也作如是观,既不绝对认同师祖(章太炎)的古文立场,也不认同太老师(周予同)的今文家言。“我试图超越今古、融汇今古,择善而从。”“此前几十年,儒学史、经学史也出版了几种,与这些作品比较,我这本属于一个人的写作。一个人的写作固然有很多局限,但其好处是逻辑自洽,首尾一贯,不会自乱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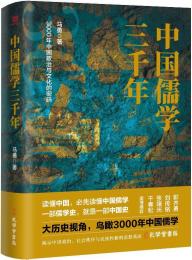
马勇向以研究近代史而知名学界,不熟悉的人乍一看到这本《中国儒学三千年》难免讶异。实际上,如果了解他的学术履历,他对儒学的研究和情怀其来有自。1983年,马勇从安徽大学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以《汉代春秋学研究》为题的硕士论文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誉为“儒家经学研究领域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出版20年来一直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和广泛征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儒学初现复兴之势的时候,马勇即多次陪同导师到曲阜参加关于孔子的会议,参会人员中有杜维明、庞朴这些享有大名的学者,籍籍无名的学生马勇,会参与一些整理会议纪要的琐细工作。“从孔子被批向获得正统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中,我算是个经历者。”
1986年,已经拿着工作派遣证准备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报到的马勇,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了近代史所,从此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将主要精力放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研究上,数年间即拿出一系列有分量的著作。前些年,他参与汝信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世界文明研究系列”,撰写其中的“中国文明史”板块,他因此又回到古代史,接续之前的研究。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非常时期,长达半年的居家工作,我唯一下功夫的事情就是整理了这部书稿,做了很多修订工作。而这部书稿,我多年来一直希望修订再版,毕竟它涉及我的专业,也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在。”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围绕儒学自身的现代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儒学如何如其过往一样,适应时代,开出新局。

马勇
儒学内部并非缺乏更新机制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国儒学三千年》序言里谈到,历史上“殷周之变”产生了儒家,“周秦之变”遏制了儒家。至晚近的上世纪初,因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变局给儒学带来了根本性冲击。萧功秦先生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中认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马勇:前辈学者郭沫若、范文澜等建构的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至今已经七八十年了,影响深远,几代人得益于此,我们一直延续他们的模式在解读。这些年我在做中国文明史研究时,一直思考如何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修补、完善中国文明史解释体系。
王国维最先发现殷周之际的变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农业文明凸显。周人的农业文明与殷商时期的商业文明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周人的几个制度性安排,对于我们讨论儒家学术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据《汉书·艺文志》,以及后来学者的研究,夏商时期,学在官府,有欲学者,以吏为师,一方面在各衙门打杂,做着日常事务,一方面阅读文献,追随长者学习。到了周人建政,实行封建制度,各个诸侯国成为政治实体,独自处理各自国内事务,周王室中央政府层面渐渐成为一个虚置的机构。周王室与诸侯国这种二重政治架构,在学术史上的体现,就是人们都知道的“官学下移”,原来在中央层面的官学分散到各个诸侯国。而各个诸侯国又根据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导致“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儒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发生。
在轴心时代,儒家和其他学派始终处于一个竞争的态势,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思以其道易天下”,用自己的思想、主张影响各国统治者,孔子和其他各派领袖无不风尘仆仆,游说诸侯。百花竞放,诸子竞争。到了战国中晚期,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让各国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特别是涉及中国历史的母题——如何治水,以邻为壑的诸侯国体制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从小共同体走向更大的共同体成为思想者的必然选择,统一,甚至说“天下定于一”,在包括儒家在内的各派中都有或显或隐的表达。但统一的手段,各家很不一样。儒家主张仁政,主张“不嗜杀人者一之”;而法家自商鞅以来在秦国的实践,就是以国家主义整合资源,富国强兵,用竞争,用实力战而胜之。
历史事实证明了秦国路径走到最后,秦国征服了东方六国,这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征服六国之后如何重构社会组织方式。儒家并不反对由周变秦,它所反对的只是秦统一之后的政治架构。按照儒家的观点,如淳于越在秦始皇御前会议上的看法,统一之后秦王朝应该继续周朝分封制度,继续实行中央与诸侯国二层政治架构,中央由周王室变为“秦王室”,其功能依然如周王室一样为王朝的象征,其功能是协调各诸侯国,平衡各国之间的利益,率有道伐无道。诸侯国是政治实体,依据各国情形决定社会经济方面的政策。儒家的方案并不被秦始皇选中,李斯在御前会议提出的绝对中央集权方案成为秦朝的实践。儒学在此后的秦朝也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所谓焚书坑儒,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秦朝的政治实践以失败而告终,“二世而亡”是一个惨痛教训。刘邦建政前后,儒家学者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不断影响君王,不仅让君主明白马上可以打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而且让他们亲近儒者,尊重儒生。儒生也对新朝统治者给予善意回应,诸如叔孙通为刘邦演练礼仪,重整纲纪,其意义就是用儒家的礼仪制度约束、规范统治者。
经过几十年发展,至武帝即位,汉朝已经露出繁荣景象,先前几十年“无为而治”的黄老学似乎已经无法满足汉武帝日趋膨胀的帝国野心。汉武帝为此专门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董仲舒适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这是中国历史一次巨大转变,儒家思想由诸子之一上升到统治阶级唯一思想。此后两千年大致不变,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皆然。所以两千年中国进亦罢退亦罢,功与过,均可归于儒家。
过去的研究以为儒术独尊是中国文化独断主义,严重伤害了社会活力。其实从历史发生的实际情形看,儒术独尊并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儒学获得了唯一地位。此时的儒学,经董仲舒重整,已不是孔子的体系,甚至也不是荀子的体系了,而是把阴阳五行、刑名法家全都包容其中。所以董仲舒的思想能够一直传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占据几千年思想意识的主体,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包容性。萧功秦批评儒学内部的僵化性,其实儒学在面对异质文明的时候,比如面对佛教,面对明末传入中国的西学,有本能性的抵抗,但经过不断调适,最终走向了融合。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乾嘉汉学的排外性,忽略了汉学家的包容性,乾嘉汉学对西学的吸收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的如《几何原本》,以及那些收入到《四库全书》中的作品;暗的则是明清之际,尤其是汉学家所承袭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所以我在做文明史的课题时,认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说法是不合乎中国历史实际的。
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与多数人面临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真正解决,导致欧战爆发。严复在欧战初起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资本主义三百年发展,只是落了“杀人利己,寡廉鲜耻”八个字。他在那个举世绝望的时代,大胆呼吁重新理解儒学,重新理解孔子,孔子与儒家义理必将给中国、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机会。很多年前,没有人觉得严复说的有道理,但是历史发展昭示,欧战中不仅中国人梁启超、梁漱溟、胡适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西人罗素、杜威,也有向东方寻找解方的意思。
到了二战,儒家思想再经冯友兰、贺麟、张君劢这些受过西学训练的一批思想者的重新解释,至抗战结束,我们重读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读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读张君劢对现代政治的新解释,很容易感觉到儒家学术不再是中国落后的原罪,儒学应该如其过往一样,依然会适应时代,开出新局。事实也正如此。二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儒家思想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重回世界中心,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联合国所体现的现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儒家的思想,儒家告诉世界,纯粹的物质财富增加是没有意义的,仁者爱人,对人的关怀,可能比物质丰富远为重要。
由此可见,在20世纪转折过程中,儒家不仅得到了很大的调整,而且对世界有突破性的贡献。所以我这本书里讨论了儒家在三次历史大转折中,如何调适自己。孔子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儒家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会看到趋势,他按照趋势去走,而不是和趋势相抗衡。先前以为儒学内部缺乏更新机制,可能是不准确的。
重建合乎时代的新儒学体系
中华读书报:自近代以来,中国几代学者都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化。时至今日,您认为收效如何?无论是制度儒学还是儒家宪政,无不显示出将儒学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观念进行对话的努力。对当代儒学的发展现状,您是什么看法?
马勇:对新儒家的这些讨论,我很赞赏,但他们只是就儒家思想讨论儒家思想,没有放到一个大的脉络中去。另外,应该保持传统儒学那样的相对的独立性,在现代政治架构中,儒学不能过度政治化。
宋明以后的儒家都很包容,不再竭力排斥其他流派。宋明理学家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里的西方尽管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西方,但真正的儒家应该是通古今中西,别人的好的东西我都应该接纳,自己的好的东西也应该说出来。换言之,真正的儒家怎么会有意识地反对政治现代化?20世纪这几代儒学者非常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执着地要表达出来。梁漱溟在不太那么自由的环境中,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尽管使用了许多现代词汇,其实真实意思还是在寻找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从现代学术的架构当中,新儒家从上世纪80年代被激活,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儒家的面貌以及在中国政治语境、文化生活中的处境发生了极大改变。现在的讨论,应该接续历史,抱持一个开放的现代心态,对包括儒家思想资源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大度吸收。假如真有当代儒者的话,至少应该像董仲舒、朱熹那样,包容各家各派,不断扩大儒家思想体系的内涵和外延,进而重建一个合乎这个时代的新儒学体系。
上个世纪初,陈独秀的困惑是,孔孟之道如何合乎现代生活?将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倾向。由此讨论,进而认为,即便儒家有某些合理性,也只是留存于私人生活领域,而无法继续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对,儒家思想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如何能够在私人领域继续存在?好的学术,当然是在所有领域中发挥功能,比如儒家的正义感、浩然之气,当然应该在公共生活当中发挥作用。到我们这一代人,更应该具有包容性,不仅让别人包容儒家,儒家本身也应该有意识地去包容非儒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中西交融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儒家文化在世界思想格局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马勇:应该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亨廷顿的分析是,人类文明可能最后形成就是三大思想架构: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文明,以古兰经为主导的伊斯兰文明,以儒家主导的东方文明。
从学术的观点看,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内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极大改变了中国文明的面貌,是一次凤凰涅槃。中国文明、儒家思想可以接纳马克思主义,这个事实证明中西文明的整体性融通并不是痴人说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学理上证明了人类文明不仅有冲突有摩擦,更有融合、汇通的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上,反对佛家最激烈的莫如韩愈,但韩愈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他之后两三百年,佛教就内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佛家的方向就是西方文明未来在中国的方向,只有内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才能对中国文明真正发生作用。
外来文明的内化,离不开中国文明、儒家文明的接纳、包容。在这一点上,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儒学并不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滞碍。儒家文明背景的诸多国家地区照样可以实现政治、社会生活现代化。马克斯·韦伯原先的预设事实上已经不再成立,新教伦理之类的前置条件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我个人的猜测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仍将处于儒家“三世说”之“乱世”。但人类的发展终将沿着东西哲人的共同期待,随着物质增长,社会进步,逐渐从乱世中走出,进入升平世,进而太平世。儒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并不是儒家的私产。全球一体化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历史终将如长江三峡,不论如何风高浪急,曲里拐弯,最后结果仍是世界大同,全球一体化。
全球化发展至今,还没有遇到真正的挫折,适度的挫折、回调,也并不是异常。从历史的观点看未来,强调的是趋势。从趋势上看,全球化不会停止。随着全球化进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这三大文明会朝着趋同的方向行进。先儒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真是神一样的预言。
往前看,总是有不安,有困惑,但是回望历史就不一样。孔子的时代,举目所见皆夷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短短几百年,至秦汉,后世中国境内诸族先后完成“中国化”过程,中国境内不同文明整合到了一起,多样性、地方性构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色。这个例子,或许对于我们观察世界文明的未来,观察儒家思想的未来,具有些微启发。
中华读书报:按照胡适对儒学的思考,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中国哲学,虽然有不少新的创造,但在根本上都不可能突破经典儒家哲学的束缚,创立新的范式。对照今日现状,您如何评价胡适的观点?
马勇:这是胡适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看法。这篇论文以《先秦名学史》为题出版了中文本。胡适在导言里谈及文化发展趋势时,认为儒家文明有一种内在的缺陷,没有逻辑,没有实验,不能转化为现代科学。因而胡适竭力提倡从中国内部寻找嫁接西方科学的因子,从而减少科学进入中国的阻力。胡适的思路当然是有意义的。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应该转换思考的视角,儒家、中国文明确实没有西方意义的那种科学、逻辑,但是问题在于,儒家是否排斥科学?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固然不在中国文明既有框架中,但儒家并不排斥科学的进入、落地、生根。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明史上不胜枚举。中国文明如果剥离了外来文明的进入,还原到周初原生的儒家,还原到孔孟荀时代的儒学,那确实只是利玛窦看到的儒家,除了伦理信条,既没有试验,更没有逻辑。儒家的伟大就在于自己没有并不反对有,因而短短两千年的发展,儒学就是不断学习、汲取外来文明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然赞成胡适的态度,继续寻找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同构关系,最大限度接纳其他文明的成果,充分世界化。
儒家的黄金时代属于历史
中华读书报:近代以来的学术方向是以科学为普遍的价值尺度,所以近代中国知识界主要是接受一些西方的逻辑思辨成果和科学成果,以及一些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未能足够重视生命的问题,结果导致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常常停留在一些器物的层面,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当年牟宗三指出的这些问题,当今社会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
马勇:牟宗三讲的这些其实是延续严复的观点。欧战一爆发,严复就讲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很早就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问题,《资本论》中就讨论了这些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问题是通过二战之后几十年社会发展政策来进行调适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历史主义地观察。从严复到牟宗三,包括梁漱溟,所思考的问题有一个交集点,就是随着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发展,人们究竟是更幸福,还是更孤独、更不幸?梁漱溟年轻时几度自杀,都是因为他感到社会不公,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分享发展的好处,反而承担发展积聚出来的弊端。当然,儒家并不主张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承认人和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而不是墨家的普遍的、无差别的爱。儒家从来强调要从自我开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修身,是内圣功夫,是儒学的根本;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因而儒学的人文情怀,既是对人,也是对己。一个好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社会。没有物质的社会绝对不会有幸福,只有物质而缺乏情怀和关爱,也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社会。近代以来世界都忙于物质的发展,确实忽略了人文。西方在先发之后,注意到了这点。中国由于最近两三百年内忧外患各种因素,耽搁了发展,因而也就极大影响了人文关怀。物质化、功利化,绝对不是社会常态。严复、梁漱溟、牟宗三以及一切具有儒学背景知识人所忧虑的,都值得我们深思、矫正。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提到,比起某些国人毫不拣择地接受西方的心态,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更担忧那种执迷于西方思想的皮毛表象。很多学者认为,对西学的采纳,必须与中国价值的重建相结合。这也是儒学当下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马勇:从陈独秀开始,就把儒家看作中国落后的根源,甚至原罪。这个思想影响深远。到了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主流依然以“五四”全盘反传统继承人自居,于是打倒孔家店,破“四旧”,废止一切旧的东西,成为20世纪中叶几十年的主题。改革开放之后有所调整,但是仍然很不够,儒家思想还没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自由地发挥功能。儒学虽然成为一部分知识人的信仰、工作,但是相对于更广泛的人群而言,儒学其实还是一个工具,用则举起,不用则闲置。儒学应该重回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无须意识的自觉。
前几年,山东推广乡村儒学,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但是光靠官方的力量推动也不够,重要的是如何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意识。面对西方文化,面对任何异质文化,只要有自信,就应该开放地讨论、融合。这就是儒家的观点,不必一定分出个彼此来。
中华读书报:历史上儒学并非一成不变,从先秦原始儒学,到董仲舒的政治儒学,到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每次的变化都很大。晚清乃至“五四”以来,儒学经历重大挫折乃至至暗时刻,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迎来了再起、复兴的过程,如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特别是学界,儒学的境遇都是很积极的,儒学有无可能再锻造出朱子儒学、阳明儒学那样的新范式?
马勇:历史地讲,儒家的黄金时代不可能再现了。因为人类社会处境不一样,我们看过去的几百年,到最近这一百年,中国现代化的趋势很清楚,中国不必一味地固守儒家传统,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世界越来越接近,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思想能够容纳异质的东西,历史上儒家几次这种颠覆性的变化,都是因为接纳别人。今天的中国要从发展本位,去把包括儒家在内的思想熔为一炉,重构一个包容性的体系。儒家在几千年的发展中,虽然一直还叫儒家,其实早就有别的东西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是变动的,是趋时的,儒学不会和时代别扭,识时务是儒学的真精神。这个时务是历史大势,不是蝇营狗苟,不是利益勾兑。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相信儒家思想一定会跟进时代,过去变,未来还是变。观察历史的好处,就是看趋势,至于趋势是什么,就靠见识了。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原标题:《马勇:坚持发展本位,重建合乎时代的新儒学体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