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解构康德的美学观
本文来源于哲学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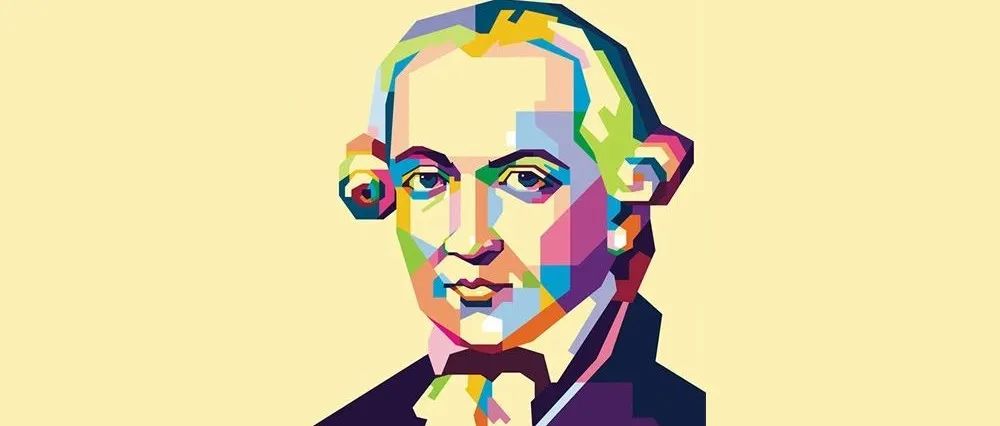
解构康德的美学观
尚杰
作者简介: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国哲学、后现代思潮。
人大复印:《美学》2021 年 05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21 年第 20211 期 第 59-66 页
关键词:解构/ 艺术/ 绘画/ 框子/ 先验/
摘要:德里达对康德美学观的解构,认为康德把“先验判断”视为一个已存的框子,这个框子与具体的审美经验脱钩,在美的分析四个方面,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参与无概念的审美愉悦。但是,解构的艺术认为,框子并不是中心,而处于边缘,它的审美趣味并不遵循康德的演绎逻辑,而是处于“延异”或增补性的逻辑过程。在此,德里达与康德的争论,代表了后现代哲学向德国古典哲学的挑战。
德里达极少专门用一本书的篇幅讨论艺术,因此他的《绘画中的真相》一书,是了解解构艺术最重要的著作,它不属于通常所谓的艺术评论,而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是一本讨论艺术的哲学基础的书。该书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康德的美学观的解构,它是一场发生在德国古典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激烈辩论,但却是以阅读理解的形式实现的,显示了德里达的一贯解构式阅读风格,就是让被阅读的本文自己解构自己的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含义的消解与转向。
康德的美学观,集中体现在他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内部,我们的判断能力是在先验原则之后出现的。“判断力”被单独拿出来写成《判断力批判》,虽然表面上是在讨论美与艺术,似乎与认识论脱钩,但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种假脱钩,在这部著作中,康德实质上仍旧以“认识论”的姿态讨论艺术,它是康德纯粹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中的矛盾,在“第三批判”中最为明显,就像他关于美的一个著名定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一样,“目的”被说了两次,仍旧是目的,所谓与前面的目的不一样,显示了康德想使美脱离认识的愿望。理性与认识脱钩,却又保存着理论性话语的基本姿态,即抽象的普遍性(话语)。这已经是矛盾。另一处矛盾就更为明显,美或艺术无法回避愉悦与愿望的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使康德考虑到它们不属于认识论,但他为了保持哲学体系的一致性,绝不肯把愉悦问题还原为纯粹经验体验,而要纳入先验哲学之内,但是一旦这样,愉悦的问题就悬在空中了,它只涉及美的形式而回避关于美的内容,德里达对康德美学观的解构,正是由此出发的。
在最短时间内
饱览人类知识精华
最新106册
《牛津通识读本》
长按二维码了解
德里达写道:“欲望、愉悦与不愉悦,这些问题也正是脱钩的问题,它本身就是表示脱钩。”①这里所谓脱钩,就是说美的体验的本质,对于美的具体对象本身不感兴趣的态度。现在有两种可能性:实存的可能性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康德用建筑艺术作比喻: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应该认为形而上学的工作就相当于有才华的建筑师,有出色的建筑技术,绘出一个艺术空间,而这首先要打好地基。在康德看来,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说我们的判断力要根据先验原则建立起来,先验原则就是地基。但是显然这里出现了某种不协调,美的判断不属于认识判断,而原本对认识论有效的先验原则,现在如何对于美的判断同样有效呢?如果同样有效,不仅需要重新理解先验原则,而且康德陷入了某种“没有脱钩的脱钩”的困境之中,但康德强意为美学设定先验基础,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暴力,它来自一种任意的虚构。也就是说,审美的基础来自一种先验的判断力,而先验绝不同于经验,可是先验原则或者范畴只是某种形式,那么审美判断只停留在形式,并不提供审美经验的具体内容。
德里达对康德美学观的质疑,就是质疑作为地基的先验形式,这种先验的普遍性原本来自康德的一个隐喻或者类比——建筑。在之后的分析中,德里达认为这个地基绝非清晰可辨,它是一个无底深渊。隐喻,或者说整部《判断力批判》(艺术哲学)相当于建筑艺术。在康德那里艺术的愿望成为构建基础的愿望,理性的愿望,不是经验的愿望,因为经验的愿望之危险性,就在于纯粹经验杂多导致某种任意性,就像是经验的无底深渊,因为它没有先验性作为前提或者地基,从而无法掌控。但是,就像德里达在其《哲学的边缘》中曾经尖锐分析过的,概念起源于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柏拉图的“理念论”来自其著名的“洞穴之喻”,这就像说形而上学只不过是抹去了原本存在着头像的硬币,变得光秃秃的看不出硬币上原本具有图案,从而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就像是蘸着白墨水书写的“白色的神话”,这种批判也适用于康德:所谓普遍的先验原则其实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深渊就是隐喻,康德自己已经把艺术哲学比喻为建筑艺术,德里达称之为“理性的隐喻”②。它是康德先验原则的愿望中的愿望——地基的愿望,这就使得愿望具形化了。“理性的愿望就是作为被奠基的(建筑)结构的愿望。”③
在康德的知性理解力中,我们发现了先验概念,而审美判断力使用—应用先验概念,但这是一些空的概念,它并不实现认识。先验概念为审美判断力提供使用规则,这些规则不包含任何对象性。在德里达看来,这属于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不仅黑格尔甚至海德格尔,都没有脱离这个传统,这是从询问“美的方式”看出来的,他们的艺术哲学是“关于”美的话语,问“什么是美”或者“艺术作品的起源”,在这里的“什么”和“起源”都属于广义上的观念性的询问,标志在于它们只是形成判断,受困于“对立概念”,而没有进入美的艺术自身。受困,就是认为难题在于回答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但在德里达看来,无论回答美在于主观还是客观,其实它们所遵循的普遍原则在性质上一样,也就是为美下一个定义,它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美,而美的多样形态只是美的定义之下的例子,而例子本身是无所谓的。
更大的困难在这里,德里达写道:“尽管审美判断不属于认识,然而作为判断,它们只属于认识能力。审美判断根据先验原则,和愉悦与否之间建立起关系。”④那么,康德事实上将认识与愉悦与否联系起来,而这违背了他的本意,也许正是由于看到了这样的困境,才想尽各种办法加以摆脱,其中著名的就包括美在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但“无目的”或者“无概念”就能摆脱认识论的嫌疑吗?12个先验范畴已经作为工具思考审美判断了,但是困境在于康德认为:“如同审美判断表明的,我们不能将美交付于概念规则……而要分析形成审美判断的可能性、普遍的什么对象的可能性之条件。”⑤在这里康德说的很空洞,这空洞,德里达换一个词说康德审美判断的先验性,它是一个框子(cadre),留下的是空白(lacunaire),它涉及审美快感,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快感——它不是私人的亲身体验,而是某种可以普遍传达的快感之纯粹思想,纯粹快感不过纯粹思想而已。说它是快感的快感,也于事无补,因为其中抹不掉判断系词“是”(being)。这种古怪的难以理解的快感既不能与身体的快乐挂钩,也不能与概念挂钩,它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那么它在哪里呢?它是一个谜,它被写出来、被读到、被理解,如此而已。这种快感存在着,但并非像一本书的实存。如果说我沉浸于一本书的装潢颜色,这在康德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把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消解了,使两者彼此相互包含—给予。
德里达问道:为什么要把美的感受称为判断呢?即使是趣味判断,也还是停留在判断。这就好像在说“这朵花是美的”,但这句话并不美,我们从这句话里感受不到花的美。美不需要作为间接性的判断横插过来破坏我们的兴致。康德将类似“这朵花是美的”当成审美感受,并且古怪地认为它不是认识判断,与逻辑无关,但实质上,它印有认识与逻辑的深深烙印。康德审美判断的古怪,还表现在他对于事物的实际存在不感兴趣,是某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对于枯燥的先验形式本身的兴趣。德里达尖锐地指出:“兴趣总是将我们引到事物的实际存在。”⑥而对此不感兴趣的兴趣,是难以理喻的兴趣。我在形成康德式的审美判断之前,就已经享受过实际存在的愉快,这种愉快并不会由于被称之为美或者丑,而有丝毫改变。这种愉快沉浸于事物的实存(l’existence de la chose)而不是面对事物(la chose),更不是“关于”事物即所谓判断。康德式的审美判断之愉悦使我面对事物的非实存(non-existence),不实存的美怎么会诞生愉快呢?就像没有色彩的画或者没有头像的硬币只是“白色的神话”,没有物质性的实存,就没有快感可言。康德用“先验”诱惑我们,对实存做了“了断”。
德里达举例说明:如果我面对一个宫殿,人们问我是否发现了宫殿的美。如果我说这宫殿很美,这涉及的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判断,这里的问与答,都是以陈述形式做出的,但这并不能还原出美的感情——无论对“宫殿是美的吗”做出什么方式的回答,它们都是“关于”艺术的哲学话语,都停留在观念自身,而没有沉浸于实存,在这个意义上说,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没有最终摆脱的形而上学的痕迹。
在康德那里,美的判断不涉及外(le dehors),例如色彩、声音等物质性的实存,经验的现象、感性的动机、经验的心理活动,但是去除了这些因素,何谈审美感受的纯粹主观性呢?这主观性其实就是普遍的先验形式判断,是没有享受的主观性,满足于没有满足,没有这儿或者那儿的满足,没有琐碎的犄角旮旯的满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愉悦享受是发生在具体时空之中的场景,它拥有时间,时间在这儿或者那儿,就像与人约会在某时某场所,而相比之下,康德的审美判断是超时空的纯粹形式,它“没有”时间,无法拥有感受的细微差异的改变,用德里达的解构术语,就是没有“延异”(différance),只剩余空洞的“美”的词语或概念,它是“关于”美的,它所求助的不是实存而是判断,德里达称之为“自爱”(l’auto-affection)的词语结构(例如“花是美的”)、没有满足的“满足”,因为关于美的词语自身并不美,就像“树叶有美丽的绿色”这句话并不是绿色的,因为没有享受绿色。而享受的元素,是特殊的、经验的、实存的“异样的爱”(l’hétéro-affection),在这里说什么理论与实践,都纯属多余。异样的爱拥有“外”,从而与纯粹局限于沉思的自爱区别开来。
由上,康德的审美判断具有这样的危险,它培养起某种对实际的爱与不爱漠不关心的古怪的爱,就像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者都说“爱人”,但他们彼此之间其实并不爱,甚至仇恨。它止步于“应该爱”,而一遇到具体场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呢?就像在康德那里,德里达写道:“经验的快感是不可能的,我不能采用它、接受它、退回到它那里,不能给予它,它也不能给予我,因为我绝不以如此方式接近美,我绝没有作为实存的纯粹愉悦。”⑦当美的对象是一本书时,德里达问到,就像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是一部艺术品,这时美的实存在何处呢?这就像是一个深渊里的问题,它是存在于空间的一个对象。一座雕塑,可以从上下左右去欣赏,但是一本哲学书呢?也可以从任何一页切入它,因为就像康德说过的,这书就像是一座建筑。德里达说,任何角落都有这座建筑的出入口,无论是阅读还是康德写这本书的顺序,康德是写完这本书的正文之后才写序言的,我们究竟应该相信事实的顺序还是盖起一座建筑的逻辑顺序呢?如果把作为基本观点总括的序言比喻为这座建筑的地基,难道能首先盖好房子再打地基吗?这显然违背康德的教诲,但康德写此书的实际操作顺序,却是地基在后,正是如此。但倘若不首先阅读序言而从该书任何一页开始读,人们就会说这不是正经的读学术书,但康德并没有按照“正经的”逻辑顺序写这部书。
德里达认为康德的审美判断其实就是某种反思判断,“我称它是最贫乏的普遍性”⑧。如何理解它呢?德里达说既然康德可以先写正文后写序言,那么读这本书也可以不按照顺序读,先读康德列举的例子,而非序言。康德先立法,再寻找例子。德里达先解构康德立的法,解构的方法就在于琢磨康德的用词造句,注意那些似乎非主流思想的“边边角角”,就像欣赏一幅画时,不能忽视画框,画框或者边缘也是这幅画的一部分,但传统艺术哲学从来不曾像德里达这样欣赏艺术作品,似乎框子在绘画之外,是附属的、增补的,甚至是多余的。乍看起来,似乎确实如此,有谁只是为了欣赏画框而去看画展呢?“哲学话语一直反对装饰物(le parergon)。”⑨画框是绘画作品的“外”(le dehors),想一下前面说过的,康德认为美的判断不涉及“外”,例如色彩、声音等物质性的实存,经验的现象——德里达就是这样思考解构的,他迅速类比两种看似无关的现象,从中发现和发明新思想。在这里“外”或者框子、边缘、装饰物,都是新思想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就在于消解或解构了“内与外”(我们自然会由此想到形而上学将概念双双对立统一起来的传统,例如主观与客观之间,这种思维方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登峰造极)的对立,因为框子或者装饰物也是绘画作品的一部分,它既在绘画之外,又在绘画之中,内与外的断然区分是对作品人为的粗暴干涉,它限制了我们对于作品的浮想联翩的能力。
要注意作品中那些附加的装饰物,欣赏可以将这些增补的装饰物连接起来,目光从一个装饰物到另一个装饰物。这种方法甚至与词源学方法相似,也就是思考相似词。当相似词多起来的时候,会猛然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脱离了词的“本意”。单独一个词,是无法形成句子的,而只要词语动起来就一定会发生脱离本意的消解过程,这是语境在时空中的差异造成的。在《绘画中的真相》中,德里达经常采用如上方法,他先写出一个词,例如“边框”,然后在该词旁加个括号,括号里面写着“装饰物”“外”“边缘”。最为惊奇的,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判断,其实也相当于一个框子或者“外”——这个思路是揭示事物真相的语言还是隐喻性语言呢?两者都是,于是就这样,德里达消解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走在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
以上是横向的串联方法,德里达的“解构”也被人叫做“后结构主义”,相似于拉康说的“漂浮起来的能指”——意谓中的意谓,而德里达的“延异”永远推迟了所指对象的实现,所谓对象自身总是一个他者,就像血液在血管(vaisseau)里流动。按照以上“相似中的相似”方法,于是就有血管—沿岸—沿路,如此等等。对此,传统哲学家会严重抗议,因为沿路绝不同于血管,这是对的,因为在不知不觉之中,血管已经在沿路途中被消解掉了。
作为装饰物,画框是绘画作品的补充,它提醒细心的观赏者注意,相当于一封信原本已经写完了,又补充说“又及”(它同时在信的内容之外与之内),这里德里达使用了“remarque”一词。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哲学家会使用“又及”的方式写书,但是德里达的所谓解构,就是这样写哲学书的,他写出了《绘画中的真相》,它填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缺失。作为“又及”,它扭转了欣赏美的方向,康德的纯粹理性无力观看的沿路风景。就是说,美超出智力判断,在智力界限之外的神秘享受与感受能力。“又及”转移注意力到别的地方,就像是画框。“Remarque”不仅是注解,一切注解都增补了新内容,它填补了内容的缺失,移植到新的领域,形成一种寄生效果。
画框—装饰物使绘画有了更多东西,“外”的东西嵌入了“内”并且发挥着作用。康德的审美判断只局限在智力,排斥“外”,理性遭遇自身的界限,或者说是自身的匮乏,满足于没有满足的状态、“这朵花是美的”状态。装饰物不仅有画框,还有衣服,就像一座殿堂的柱子是人体雕像的石柱,它既是柱子又是雕像,而雕像同时在柱子之内与之外,装饰物自身已经是内容。如果没有雕像,柱子自身就不复存在了。就是说,现象已经是自在之物,康德的区分是不必要的。
德里达继续写道:“装饰物意味着特殊、异乎寻常。”⑩让我们返回上述人体石柱雕像,它加之于自然材料但雕像自身就已经是自然材料组成的,就像音乐的乐音是物质的声音但已经添加了作曲家对于声音的改造。离开乐音本身音乐将不复存在,就像是一旦脱离雕像,石柱将不复存在。雕像脱离了又没有脱离石头,乐音脱离了又没有脱离自然音响。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无从区分内与外。这种不能脱离的脱离,就像上述“意谓中的意谓”,一种既增加又减少的艺术效果,但它不是“关于”艺术的,因为“关于”相当于说“什么是艺术”或者“艺术作品的起源”,也就是艺术作品之外的词语,而德里达认为,词语应该成为艺术作品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关于”艺术的——如何能实现这种效果呢?就像德里达在本书开头引用的塞尚的一句话“我对绘画语言感兴趣”(11)的解构,例如“‘绘画’中的语言”,就是说在绘画中已经在消费语言,而不是“提到”语言。所谓“提到”相当于从作品外部对于作品自身不感兴趣的旁观者的中立态度。例如“什么是艺术”或者“艺术作品的起源”,而“使用”或者“消费”相当于词语已经成为绘画作品的一部分,例如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一幅逼真的烟斗画下方写着“这不是一只烟斗”——这句话当然不是烟斗,但也不再仅仅是一句话,因为这句话自身已经是画的一部分了。
人体雕像和音乐,把石头和自然声音缺失的成分显示出来,这种发明的技术,我们叫它艺术。它们把石头和自然音响,装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它们是外部赤裸裸的现象,而不是康德审美判断局限的“内”,这里已经有新的艺术哲学,它不同于康德的哲学。解构的艺术哲学唤醒崭新的自由想象力,它的效果是惊讶与惊喜,一种突然插入或者萌发的恍然大悟,就像领悟到画框也是绘画作品的一部分,而作为装饰物,画框就像是绘画中的他者。画框既在作品的边缘又处于作品的环境之中,画框是作品的背景却又没有脱离作品。总之,画框不是画框自身,它的价值在别的地方,就像人体雕像还是这座建筑的石柱。一个善于鉴赏者应该浮想联翩,而不仅仅只是“画框就是画框”,画框是别的,是作品的一部分,就像人体石柱雕像。
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区别于德里达的解构式的艺术哲学,主要在于两人的提问方式不同。康德总是问“什么是”或者“是什么”,系词“是”不仅在他所谓“分析判断”,更在连接新含义的“综合判断”之中。德里达这样写道:“例如,康德把装饰物称为框子,可是框子在哪里发生呢?它得有一个场所。框子在哪里开始呢?又在哪里结束呢?”(12)在这里,德里达不问“什么”,而是询问从哪里发生?问时间与场合的问题,相当于询问“如何”,它是具体行为的细节,已经包含着界限或者边缘域的思想。界限,比如上述“既是……又是”的亦此亦彼的情形,这里就像是一个可以四处转弯的十字路口,集聚着巨大的精神艺术的发明能量。它比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想象视野。这里马上就有德里达的想象力的例子,本文以上的内容也是他如此发问的背景:“我不知道是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就发生在说明装饰物本身就是装饰物。”(13)德里达这句话很费解,需要澄清的是:(1)如上所述,“装饰物”与“框子”近似,而康德的先验判断,就是审美体验的框子。(2)康德是在某种场合下想出(发明出来)《判断力批判》的,它有自身的界限或者局限,但在书中,康德宣称先验判断具有普遍必然性,全部时间与空间都囊括其中,因为时空就是先验判断的框子。
也就是说,框子原本在边缘,但康德却将它当成正午的太阳了,即所谓“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解构这场革命,德里达将艺术情趣的目光朝向边缘,转向即刻的场景而不是永恒。目光不是朝向基础,因为不存在基础(这里连带质疑海德格尔追问艺术作品的“起源”),“基础”或者起源,其实是无底深渊,它经历着“延异”或者“解构”,这里遵循“增补性的逻辑”(la logique du supplément)。
德里达继续写道:“装饰物(框子、衣服、柱子)能增强愉悦的趣味……”(14)它是康德普遍抽象的先验判断形式无法提供的,因为这个“标准的思想框子”并不存在于真实的时空之中。康德普遍的审美判断的危险性还在于,他可能是用“正确思想”取代具体艺术鉴赏享受的做法的近代鼻祖。就是说,用理性取代非理性、用形式取代内容、用逻辑取代任性。
康德“美的分析”(趣味判断)包括四个方面:“(1)根据质,(2)根据量,(3)根据目的关系(在这里装饰物发现了自己的居所),(4)根据样态(la modalité)。”(15)根据质,美被定义为某个不动心的对象;根据量,美是无概念的普遍愉悦;根据目的关系,美在于没有呈现目的的合目的形式(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根据样态,美作为必然对象,被无概念地辨认。
德里达说,以上“就是美的分析的范畴框子,然而这个框子出自哪里呢?谁提供了这个框子呢?谁构造了它?它从哪里引进的?”(16)德里达的回答是:来自逻辑。审美判断的分析来自“强行给予非逻辑的结构,给予实际上与作为认识对象无关的对象的关系结构以某种逻辑的框子”(17)。只是为了逃避明显的不协调,康德才说审美判断与认识论意义上的判断无关。如果说每个艺术作品都有自身的特殊结构,那么如上所述,这些结构在具体的时空场景中自行变化着拓扑学形状,在效果上就是解构,德里达所谓“增补性的逻辑”(它显然不是康德所理解的逻辑)就如此解构了形式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的困难,在于它无法应付感性(包括感官)的逻辑。“在第一页的头一个注释中,康德说逻辑的作用在于给自己指引方向。”(18)逻辑给美的趣味以方向吗?这个说法当代艺术家肯定不会同意。与其说趣味及其鉴赏力来自逻辑判断能力,不如说来自对于美感的敏锐感受能力,这种感受极其多样,根本就无从束缚。
无从约束的感受性,具体在哲学思考,例如类比、说“好像”、隐喻手法——对于德里达来说,不能问“什么是解构”,而要观察解构式操作如何进行。例如,如何解构康德的美学观?是这样:先验判断是一个框子,那就去发现框子的相似物(词),除了以上讨论,德里达还仔细观察康德著作的细节。例如,德里达提到康德经常在正文的某个句子后面加括号,这些括号相当于以上提过的“又及”,这种中途插入“既不在内容之中,又不在内容之外”(19),这个意思和“既在内容之中,又在内容之外”其实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咬文嚼字”式的品味意谓是解构的手法),处于“之中”与“之外”之间,括号或者框子似有还无,这很像是双关语:框子是必须有的,但它却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能起到框子应该起到的作用的“框子”,这就是解构的基本思路,或者说是操作手法,因为德里达有很多类似的表达,例如:翻译是必须做的,但却是不可能的;过生日是纪念不是今天的今天,如此等等。如上,也是意谓的意谓,意谓无法完全落实,一个意谓总是飘落到另一个意谓,推迟意谓的实现,这就是解构的关联词“延异”。这里通行“自由增补式的逻辑”,而不是康德的演绎逻辑,这两种逻辑的重要区别在于思路的顺序、写作与阅读的方法,德里达是片断的、插入式的、发散的、即兴的、隐喻的、“咬文嚼字”式的一词多义,把重复当成差异,而康德式的思辨逻辑根本就不可能重视德里达上述的“哲学边缘”思想。
康德的先验“框子”—画框—装饰物—衣服—人体石雕像—写作过程中加括号的修辞手法—文章的注释……”这就是德里达的解构思路,没有结构的游牧式“结构”——它并非毫无根据的虚构,就像生活世界的事实告诉我们,文明就是开拓陌生的世界—领域—陌生人,理解就是向陌生词开放。传统哲学像古代社会重视血亲关系,而现代—后现代哲学认为与陌生人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血亲,网络世界无限开放。德里达重视康德著作中的括号与注解,因为在康德感到困难之处会偶尔流露出德里达所需要的解构思想。与理解力“连接”,与趣味判断连接,不一定非得与康德式的演绎逻辑连接,还可以与自由增补式逻辑连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还”,朝向各个方向的愿望。
在最短时间内
饱览人类知识精华
最新106册
《牛津通识读本》
长按二维码了解
康德关于美的分析的四个方面,都是先验分析的框子,它们为所有情趣判断提供框子。但是,原本并不存在框子,先验框子是康德的思想发明,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从中衍生出众多概念并且在其间搭建了一座思想艺术建筑,就像是在大框子里搭建小框子。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也是在创作一部思想作品,但思想作品还可以是别的样子,例如德里达的《绘画中的真相》。框子是必需的,但不要将它看成现成的、普遍的、永恒的,就像牛顿发现的物理定律。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哲学思想是发明出来的,这种发明的性质是艺术的,框子以艺术的方式产生。
在大框子里搭建小框子,在框子里写框子,但是框子并不位于中心的位置,并不存在围绕一个中心搭建框子的情形,就像宇宙并没有中心,因此“地心说”和“日心说”都不完全对,康德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亦然。更重要的在于,按照德里达以上的分析,框子并非位居中心,而是像画框一样位居边缘,而所谓“中心”,其实并不真实存在,根据上述“既在……又在”的增补式逻辑,“中心”既在内容之内又在内容之外,而每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人都可以这样看待自己而实际上又做不到,例如“以我为中心”——引号里的这句话不可能真实实现,但它实际起作用,可是德里达的意思却是说,我们要是真的相信它,就等于进入康德式的古典哲学。解构式的哲学,就是相信思想事实的效果,边缘式的、增补衍生式的写作思想,属于思想的事实。康德哲学是自身封闭体系性的,这从黑格尔哲学看得更清楚,而德里达的哲学是解除边界的,开放的,这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相符。
德里达用“边缘”(框子)解构康德的“先验”(中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它是后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区别所在,是《绘画中的真相》与《判断力批判》的区别所在。就是要解构框子,朝向思想的缺失,即在古典哲学看来不在场的思想。“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康德)反思式的操作是在框子上书写”(20)。德里达也“在框子上书写”,但是他把框子理解为边缘,而康德却将“框子”视为中心。似乎是中心的,其效果原本在边缘——这就是德里达试图反复告诉我们的真相,包括了绘画中的真相。
于是,出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节点:尽管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独断论,但是他的先验哲学中的“先验”作为“批判哲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却陷入了新的独断论,因为康德并没有做到使之公正合理:“康德的动机隐藏在他的哲学命令的任意性(l’arbitraire)之中。”(21)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新词“任意性”,它回答了以上“先验审美判断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康德哲学排斥纯粹任意性或者纯粹自发性,但他的“哲学命令”或者说“先验”,却来自某种纯粹任意性。这从他发明的作为思想图式的12个先验范畴表,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就像叔本华对康德的批评:为什么一定是12个呢?因为康德有一种将概念一一对称起来的思想癖好,而对称就得是双数。但就像德里达在这里敏锐察觉到的,这来自康德的任性,因为概念的对称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在此,德里达对康德的批评与叔本华异曲同工:“列表是从两组数学范畴开始的(量和质),为什么不从两个动态的(dynamiques)范畴(关系和样态)开始呢?为什么没有遵循范畴列表原有的次序(量在前,质在后)而是颠倒了数学本身的范畴次序呢?”(22)这里指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同样12个范畴图式列表中,量在前,质在后。为什么运用到审美领域,次序就颠倒了呢?因为需要,康德是这样说的:“这后一种颠倒肯定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即认识不是趣味判断的目的和效果:数量(在此即普遍性)并非趣味判断的第一价值。康德在注解的结尾处写道‘我首先考察质的范畴,因为质是审美判断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为何首先……然而,如果逻辑次序的颠倒在此却是源自非逻辑的原因,为什么就不能追寻呢?”(23)康德是出于临时的需要而忘记了逻辑吗?康德在此遵循了怎样的逻辑规则呢?德里达咄咄逼人的追问,暴露出哲学思想的溯源,那第一原因就是某种独断,但它的含义并非贬义,它是“自因”的,来自纯粹的自发性,或者说任意性,它有元哲学意义上的“公正性”,给予自由意志以一针见血的新意。
某一种规则原本被认为在一个系统内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德里达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发现了自相矛盾,这种无法自证的情形,会使我们不由想到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对于数学与逻辑学的里程碑意义上的革命,这种类比更加凸显了德里达解构哲学的重要意义,它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它洞察了思想事实的真实可能性,就像“不完全定理”变革了逻辑的可能性。
以上康德认为“质是审美判断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但质的特性,竟然是对于享有不感兴趣,他在愉悦与亲自物质性的享有(jouissance)之间,划出界限。艺术家和美的鉴赏家听了之后,会感到不以为然,康德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艺术,而是哲学,他把哲学思考混同于艺术鉴赏了。一个画家不可能对色彩无动于衷,而色彩是物质的。同样,我们在康德的道德命令中,也只能收获抽象空洞的不动心的感情,真实的感情一定有生理因素的参与。康德声称美的愉悦行为没有概念参与,但是他却是用概念分析方法描述“没有概念参与”。“康德把概念分析强加给无概念的过程。”(24)
康德把概念与无概念的趣味情景(例如,大自然里的一株郁金香)收集在一起,这就好像处于思想转弯的十字路口。在这个路口,德里达注意到康德审美判断的关键词“无”与“和”,这两个词也成为解构艺术的关键词,就是连接差异——延异,就是搁置同一性的“意谓中的意谓”过程,例如上述先验“框子”—画框—装饰物—衣服—人体石雕像—写作过程中加括号的修辞手法—文章的注释的过程,它们是即兴冒出来的相似性,一边写一边涌出来的思想发明,而不像康德的先验哲学书的写法即事先就有了思想框子。综上所述,德里达的《绘画中的真相》比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更像是一本思想艺术著作,一本走在哲学与艺术之间的书,更与当代艺术的观念化切合,是后现代艺术哲学的经典之作。
注释:
①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p.46-47.
②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p.48-49.
③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49.
④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50.
⑤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50.
⑥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52.
⑦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57.
⑧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59.
⑨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63.
⑩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67.
(11)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5.
(12)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p.73-74.
(13)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75.
(14)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75.
(15)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79.
(16)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79.
(17)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0.
(18)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1.
(19)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2.
(20)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5.
(21)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6.
(22)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6.
(23)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6.
(24)Jacues Derrida,La vérité en peinture,Paris:Flammarion,1978,p.87.
原标题:《解构康德的美学观》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