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杨明读《文学的艺术》|呕心沥血,独树高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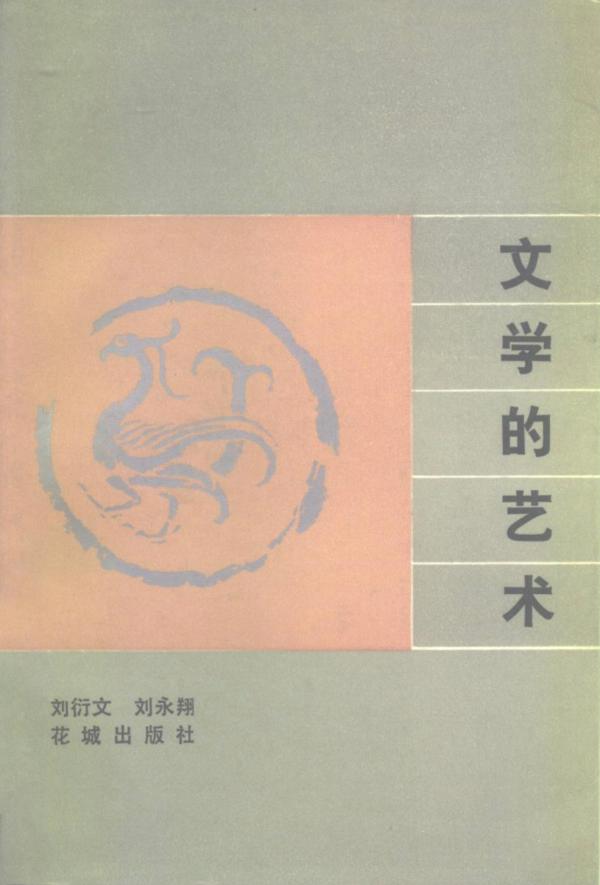
《文学的艺术》,刘衍文、刘永翔著,花城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475页,2.85元
刘衍文先生、刘永翔先生父子所著《文学的艺术》,享誉学林,乃是一部极有价值、独具个性的文学理论著作。早在六十多年前的1956年,衍文先生便完成了《文学概论》一书,不胫而走,先生却精益求精,决心重写。不幸成为僇民,而于艰难竭蹶之中,明知无从问世,却仍以惊人的毅力,重新写就一百三十万字的巨著。不幸又在“史无前例”的红羊劫里化为乌有。劫后重生,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先生以历尽磨难的病弱之躯,再次重新执笔,但终因体力已衰,只能与哲嗣永翔先生一起,先写就这部《文学的艺术》奉献于读者。同时还共同撰写成《古典文学鉴赏论》,可谓《文学的艺术》之姊妹篇。前后三十年的著书历程,颇令人想起谈迁著《国榷》的故事。
一百三十万字的书稿分五个部分,全面论述文学的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为何重写时首先论艺术呢?《文学的艺术·后记》说,那是因为艺术性问题,向来是一般文学理论书籍谈得很少很粗疏的部分,也就是其薄弱环节。但其实艺术性、技巧对于鉴赏和创作是极端重要的。确实如此。在笔者看来,一般书籍之所以少谈艺术,固然有种种缘由,而著书者的修养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二位刘先生不但精于鉴赏,而且擅长词章,沉思翰藻,自有亲切的体会,那是一般空谈理论的作者所难以企及的。
重视艺术性,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我们试看魏晋以来的诗文评著作,包括后来的诗词话、文话以至评点,虽然不乏明诏大号标举“载道”大旗的,但毕竟以谈艺术者为其主体,也以谈艺者最为丰富多彩。只是古人谈艺,零碎者多,有条理成系统者少,《文学的艺术》则秩序井然,而且除大量引证我国古典作品和文论之外,还结合外国的作品和批评,融会贯穿二位先生自己的心得,上升到理论,形成一部面目全新、独树一帜的著作。笔者拜读之下,深感获益良多。而限于水平,这里只能谈一些片断的理解。
首先,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形象”的问题,这部著作给我们很多启发。
我国学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凡言及文学的特征,就总要突出所谓“形象”。《文学的艺术》指出,那是源于俄国十九世纪的评论家别林斯基关于艺术的论述。别林斯基说,艺术与科学的区别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处理内容时所取的方法;文学家是以“形象和图画说话”,“运用生动而鲜明的现实的描绘,作用于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画面里面显示”现实。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衍文先生在《文学概论》里也采用了。该书给“形象”下定义道:“文学的形象乃是具体的、感性的、综合的人生图画;这种人生图画,借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创造出来,给人以一种鲜明的、印象一致的美学上的感受”(刘衍文:《文学概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33页)。但是,到了《文学的艺术》里,却对别林斯基的观点表示异议,把这个定义也自我否定了。《文学的艺术》认为别林斯基的说法嫌片面、简单,似乎文学是表达某种观念的,只不过采用了“形象化”的表达方法而已。这可能使人以为文学艺术只要根据某种思想观念甚至政治意图来具体化、形象化一下就行了。事实上文学艺术虽然可能表现某种观念,但它是那样丰富、多样、复杂,绝不仅仅只是表现观念而已,也绝不是根据观念来创作的。刘先生的这一改变,想来和对某种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思有关。在那种思潮鼔荡之下,“主题先行”,使得文艺花园一片黄茅白苇。至于对原先“形象”定义的否定,则是因为那个定义仅仅强调画面感,那便“把文学或文学作品的范围,弄得越来越狭隘了”(《文学的艺术》,26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数)。这一点颇为重要。
今天我们讨论“文学”的定义,或许可以拓开一些,不一定将“形象”列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年学界的情况,如上所述,是深受别林斯基的影响,以“形象”作为文学的首要因素的。《文学的艺术》也是这样,但是却对于“形象”作了十分宽泛的定义,不像一般著作那样,强调其画面感。书中这样说:“反映生活而能够综合地给人的思想和感情以新的感受和印象的,就是形象。”又说,文学作品是以“具体的、富于联想的、或者是概括的、合于修辞法则的、充满情绪色彩的语言”作为工具,来完成形象的创造的(28页)。这里强调的是“感受”和“印象”,而不再提画面感;又强调语言对于形象创造的重要性。“概括的、合于修辞法则的、充满情绪色彩的”与“具体的、富于联想的”相对而言,就是说,即使不是具体地写,不描写细节,但是只要具有语言文辞之美,鲜明地传达出作者的心态、情绪,那也是“形象”。这与一般对“形象”的理解迥异,也就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范围。
书中借用《文心雕龙》的话语,进一步作具体的阐述:“文学的形象化或形象思维的进行,是通过形(色)、声(音)、情(性)三方面来完成的。而这三方面,既可各自独树一帜,也可彼此结成一体,而其中最主要的,还应该是情(性)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其所谓理,应即寓于情之中,而情乃由性感物而发。”(51页)这就是说,在作家构思过程中,形色即画面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作家本人感物而发的感情、情绪、感受、心态才是最主要的,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甚至说理也可以包括于其中,只要其理是通过情表现,亦即与情结合着,就也属于形象化或形象思维。
书中举出许多例子,让我们拈出数例体会一下吧。
杜甫的《蜀相》,前四句写诸葛亮祠堂的柏树、草色、鸟声,很有画面感;后四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则并无画面,“三顾”二句高度概括,“出师”二句长言咏叹。若依通常的“形象”概念,后四句是缺乏形象性的,但其实后四句体现了诗人深沉的感喟,“千载以来,最感动人的、最能起作用的,却莫过于最后一联”(52-53页)。按照刘先生的定义,后四句也是形象化的,也可说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
又如高适的《咏史》,咏战国时须贾、范雎之事:“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出之以议论,并无具体画面,但议论中体现了诗人深深的感触,暗含着怀才不遇的愤激和抑郁。因此,“不失为较好的形象思维的产物”(47页)。
《文学的艺术》借用《周易·乾》孔颖达疏的“用象”一语,强调形象思维也可以是高度概括性的,关键在于这样的概括以感触、感受为基础,表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心理状态,而不是纯粹理性的思考。如刘禹锡的《蜀先主庙》:“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此诗首联、尾联颇有感情色彩;而中间两联,特别是“得相”两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体现出深深的感喟和惋惜。看似议论,但议论中实含深情。这样的概括,仍然是“形象”的、文学的语言。刘先生对此首评价很高。
不仅诗歌如此。《文学的艺术》指出,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散文、骈文,属于应用、实用的文字,如诏策、檄移、章表、奏启、书记、铭箴、颂赞、碑诔、吊祭等,它们不合乎今日一般所谓“形象”概念,但我们不应将它们排斥在“文学”的范围之外。此点很值得深思。我们知道,不少实用性文章,是具有比较强烈的抒情性的,如唐人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清人袁枚的《祭妹文》等,那当然属于“文学”,而有的虽不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却还是能让读者感觉得出某种心理、态度,某种活跃生动的神情语气,我想那也还是属于“文学”。试举一两个例子。汉武帝的诏书:“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诵之不难体会那种对人才的渴求和居高临下的自信。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读来深感那种剀切陈言的鲠直和忠悃。“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对比鲜明强烈,环环相扣,步步逼近,不说太宗当日,就是今天,读来都感到凛然悚惧。举此二例,不难三反。这样的文字,如刘先生所说,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情绪、心理,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感受,我们应该置之于文学之列。
从《文学的艺术》的论述,我们也可以明白:要说什么是文学,不该拘泥于作品的体裁,而应该看作品的性质。即使是实用性、应用性的文字,只要符合上述情况,便也该视之为文学;即使是押韵的文字,如果毫无美感可言,不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心理、情绪,那也谈不上是文学作品。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现代的“文学”概念只是包含诗歌、小说、剧本和抒情写景的文艺性散文等等,不能笼盖那些实用性的散文、骈文,也不能涵盖历史、哲学等著作里的篇章,于是以为现代的“文学”概念不符合我国的传统。其实若不拘于体裁,而是从性质着眼,就没有什么扞格之处了。现代的“文学”观念,体现了文学的独立性;运用这样的概念,是学术的进步。
所谓“从性质着眼”的“性质”,便是指上文所述《文学的艺术》里所说的那些特征。说得更笼统一点,可以说就是具有美感,由语言文辞所体现的美感。昭明太子的《文选序》说,《文选》的收录标准,乃着眼于作品是否“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亦即是否很好地运用、组织美丽的文辞。如果作者在这方面很用心,“事出于沉思”,那么就“归于翰藻”,符合他的收录标准了。因此《文选》是收录了许多应用性文字的。我国传统的许多文章选本,都是这样做的。这样的文章,从体裁、从写作目的说,是实用的,但照萧统的说法,它们也都是“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是具有审美观赏价值的。
上文说过,《文学的艺术》将“形象性”亦即文学性概括为形、声、情三个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对于“声”给以高度的重视:“声音与形象表现关系重大”“形象思维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声调来完成的”。甚至说:“文学的形象思维……不一定有形有色,但却会是‘音’和‘性’的某一方面的特殊表现。”(51页)声音的地位甚至在描形摹状之上。又说:“说到声文,当代的人似乎不十分注意……但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上却最为重视。”(53页)这是非常正确、完全符合我国传统文论的实际的。《文心雕龙》有《声律》篇专论作品的声音之美,且置于论各种修辞手法的篇目的最前面。《神思》篇说:“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构思的过程,也就是“刻镂声律”的过程。这不就是刘先生说的,形象思维通过声调来完成吗?刘勰是骈文家,后世古文家也莫不强调声音之美。韩愈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桐城派主张从字句音节以求神气(见刘大櫆《论文偶记》),都是如此。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有句云:“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一般都说“虎狼之秦”,王氏却说“虎豹”,就因为“豹”字更响亮,且“豹”与“秦”一仄一平,有抑扬变化(参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曹致尧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62页)。笔者曾读一文,说鲁迅《伤逝》的开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两个介词结构倒装在后面,长短错落,而且“够”“哀”“君”“己”四字,仄平平仄,抑扬顿挫。以上声字“己”结末,传达出压抑的情绪;若说“为自己,为子君”,结束在高而平的“君”字上,就没有那样的效果了。优秀的作家,是一个字一个字考究的。这是我国古来文章家的好传统。《文学的艺术》将声音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完全符合我国传统文论的实际,这大约在当今各种谈文学原理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吧。
从上面所述,该可以见出:《文学的艺术》关于形象性、文学性、文学范围的思考,是与我国传统诗文的创作、鉴赏实践紧密结合的;与一般的文学理论书籍相比,是很富有个人色彩的。
《文学的艺术》的大半部分,是具体地论述作品的艺术技巧、表现手法,占了全书十分之七的篇幅。其所取材料,大多来自传统的诗词话、文话、评点之类,也注意与外国的、现代的文艺理论著作相比照,同时列举大量诗词、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加以阐发。此点十分重要,因为谈艺而不结合具体作品,便很容易流于虚浮,也很容易郢书燕说,产生误解。
我国古代的诗词话之类,多结合具体作品,且多真知灼见,体现了鉴赏者艺术感觉之敏锐,颇富于启发意义。但常是点到即止,明而未融,又多漫无统绪。二位刘先生的工作,首先是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沙汰提炼,获取有意义的材料,然后予以解释阐发,最后分门别类,纳入“语言”“描写”“结构”“情节”等项目之下,使之有条不紊,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又往往抓住古代文学批评中常用的语词概念,如炼字炼句、夺胎换骨、宾主、疏密、虚实、方圆等等,探究其涵义,融入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论述,结合具体的鉴赏和批评,落到实处,可说是对于传统谈艺资料的发掘整理、归纳总结,而又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不事空谈,而以有利于鉴赏和创作为鹄的。这也是本书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书籍的鲜明特色。二位先生本精于赏鉴,而且本就是诗人作家,自然不同于纯粹从理论角度思考问题的撰述者,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二位先生的《古典文学鉴赏论》之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材料更多,分析更细致)。
下面不揣浅陋,略举数例,谈谈笔者的点滴体会。
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之句,“绿”字几经改换始得,其事传为佳话,其诗也因此而备受赞誉。本书则指出:前人早有“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春风已绿瀛洲草”等句,都是将风与“绿”相连,故王诗实在算不得十分新创。而细究之,毕竟有所不同:“绿”字在“秋草萋已绿”之中,乃用作自动词,在王诗中却是他动词;在“已绿湖上山”和“已绿瀛洲草”中虽也是他动词,但“山”和“草”与绿色的关系比较直接,容易联想到春风吹绿,“岸”字则不那么直接,“春风”与“岸”之间多一层转折,一时就不易想到用“绿”字。因此,王安石此句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这样论述,颇见用心细密。刘先生又说,这首诗也算不上王安石的上乘之作。若不是熟稔王集,确有会心,是下不了这样的断语的。
崔颢的《黄鹤楼》,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浑成一气,今古传诵。而本书指出,崔诗八句之中,开头用了四句,只在一个仙人乘鹤的传说里翻来覆去打滚,显然比重失调。刘诗也是一半篇幅只写了王濬伐吴之事,后半首也嫌空泛落套。又说李白拟崔颢的《登金陵凤凰台》,在内容比例上实胜于崔,但若以后来日趋精严的诗律论,则还未免有率意、松散之感。(笔者体会,此首失粘姑且勿论,其颔联、颈联较为落套,尾联“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似与前三联不够融会。)又举出宋人郭祥正次太白韵和施逵《感钱王战台》与崔、李、刘之作加以比较,认为郭、施之作构思严密紧凑,有胜过前人之处。这些论述,让读者扎扎实实地体会到篇法、结构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论篇法比重时还举出王昌龄的七绝《出塞》为例,认为王夫之“未免有头重脚轻之病”的批评“独具只眼”(343页)。王氏此首为其名作,但我们试看,起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何等莽莽苍苍,给人以阔大雄浑的历史感,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也感喟深沉,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却意思平平,显得空泛。这也是一种头重脚轻,比重失调,不过不是句数比例的问题,而是气势方面的问题。
“方”“圆”二字,是古人评说作品时常用的语词,钱锺书先生曾举出大量的实例。《文学的艺术》在论篇法时专列一节,从句圆、声圆、语圆、体圆四个方面加以阐发,又阐明“方”“圆”对举时的特殊意义,非常细致周到,让读者得到具体扎实的理解。黄庭坚的“换骨夺胎”之说,历来未见有人作过中肯的解释,只是笼统地说是“点化”“敷演”前人诗句,往往举例差池,令人迷茫。本书则指出“换骨”“不易其意而造其语”,属于炼句;“夺胎”“窥入其意而形容之”,属于炼意;又各自举出恰当的例子。前人于“换骨”所举例子多不恰当,本书则以黄庭坚“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当之。这样,便把二者的区别说清楚了。凡此都可见用心之细密,理解之准确。类似情况,书中所在多有,于读者极有助益。
论篇法时,有“疏密”和“虚实”两项。刘先生说此二者“同属于我们民族特有的美学观”(382页)。这一判断也来自对于古典文学和批评的真切体会,一般文学理论书中是见不到这样的论述的。
关于疏密,指出不仅文学,古典书画、园林等也都十分讲究。文学上的疏,作为一种美学风格,主要因作家的生活、气质所造成,但是与构思用笔也很有关系。疏的表现,是用笔放得开,似乎任意任情,不甚经心,有时宕到别处,有时似不大连贯,而不是拘泥窘束,一步不敢离开。但是,又自然合宜,绝不是松散繁冗。书中举出司马迁、韩愈的文章为“疏”的典型,又说《庄子》之纵恣,《离骚》之反复,李白之飘逸,“忽离忽合,忽断忽续,忽起忽落,忽往忽复”,都是“疏”的表现。这样,读者就颇能体会“疏”的涵义。又论疏密相间,指出同为桐城派,方苞谨守“义法”,能密而不能疏;刘大櫆颇具才气,略有浪漫主义气质,贵疏贵变;姚鼐则觉得二人各有所偏,遂变而通之,能做到疏密相间,交相为用。三人的创作如此,理论主张也是如此。这确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刘先生独特的心得。
关于虚实,刘先生说其概念与疏密有些接近,却又完全不同。在列举、分析古人关于虚实的种种说法之后,指出传统中属于正宗的美学观之虚实,乃是“以叙写为实,抒情为虚;推理为实,翻空为虚;直陈为实,假借为虚”(378页);并举昔人评论杜甫《缚鸡行》、柳宗元《桐叶封弟辨》和《小石城山记》的话作为例证。
刘先生特别提出清人唐彪《读书作文法》的观点:“文章非实不足以阐发义理,非虚不足以摇曳神情,故虚实常相济也。”实意既尽,似可“言尽而止”,但是“体裁神韵之间,犹似未可骤止”,故不得不长言咏叹以“虚衍”之。“文之动人,反不在前半实处,而在此虚处矣”。刘先生对此甚为欣赏,说:“这种‘虚’再往前推进一步,就能做到言有尽而意味无穷,有所谓‘弦外之音’和‘象外之旨’,真能使‘虚室生白’,笔未到处,包孕无穷。这种趣、韵、味和神,它所潜在的力量,决不是‘含蓄’的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的。”(380页)
唐彪的虚衍以摇曳神情之说,使我们想起《世说新语·文学》所载的一则佳话。桓温命袁宏作《北征赋》,赋成,在桓温座前诵读。叙及孔子泣麟故事云:“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接着便转韵述他事。座上有人提出意见,说“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袁宏应声揽笔,添加两句:“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众人皆称善。这正是以虚写足其神韵的例子。
刘先生说言有尽而意味无穷,其趣、韵、味和神,乃是“含蓄”的概念不能概括的。笔者以为这是深有体会的话,非常重要。所谓“含蓄”,指作者欲说还休,半吐半吞,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捉摸那未直接说出来的意思;那意思还是实在的,可以说明白的,只是故意不说而已。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曾提醒我们须明白寄托与含蓄的区别。而刘先生这里更进一层,所说的趣、韵、味和神,该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虚的东西。宋人周煇《清波杂志》称秦观《踏莎行》、毛滂《惜分飞》“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按秦词结末云:“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可说是“假借为虚”;毛词下片云:“断云残雨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可说是“抒情为虚”。周煇体味到难以言说的一片深情,故有此评(周氏系用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语)。永翔先生在其名著《清波杂志校注》的《前言》里特地指出:“‘意’外拈出‘情’字,可谓中的。”
对于文学作品的虚灵的情味、神韵,古人也是早有体会的。如东晋阮孚读了郭璞的两句诗“林无静树,川无停流”,便说:“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林逋的“疏影横陈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朱熹说:“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须要自得他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朱熹说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那种难以言说的韵味,只是他还只是笼统地说“意”,没有如李之仪、周煇那样有意识地将“意”和“意外”之“情”加以区别而已。周煇之后,元人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说“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韵”,明人陈子龙说“五七言绝句,盛唐之妙在于无意可寻而风旨渊永”,他们所说的“意”都指比较质实的意指,“味”“韵”“风旨”则指虚灵的美感。欣赏此种虚灵之美,确实是我国传统文论的一个特色。其实唐人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宋代严羽的“兴趣”,以至近代王国维“意境”“境界”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都是这种美感的表述。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盛唐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无非就是形容其“无穷”之“意”——也就是“兴趣”之虚灵、难以把捉罢了。
《文学的艺术》强调“这种趣、韵、味和神,它所潜在的力量,决不是‘含蓄’的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的”,这便将古人的一些明而未融的表述说得十分地明白透彻。而在强调这是我们民族一个审美特色之时,又指出不应该以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算得诗家的绝诣,才是最高的境界,才是最合乎艺术的形象”(26页)。这真是通方广恕,十分宏通的见解。
以上是笔者学习二位刘先生这部大著之后的片断体会,不揣浅陋,希望得到刘先生和读者的指正。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