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患阿兹海默症的奶奶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患阿兹海默症的奶奶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 三明治 原创 聆雲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 #短故事学院 216个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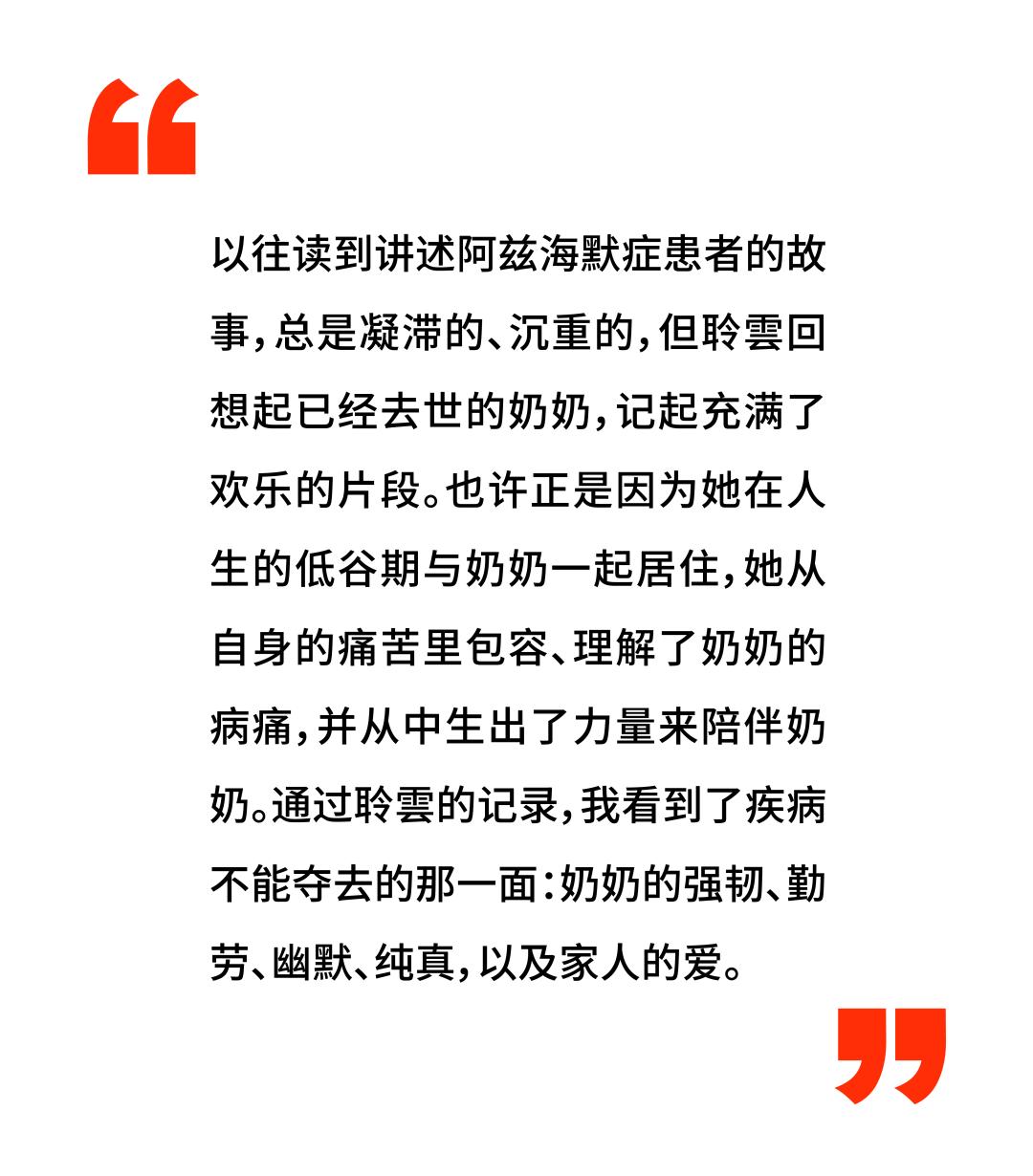
作者|聆雲
编辑|恕行
2016年5月底一个夜晚,我带着一只近二十公斤的旅行箱,独自坐上了由北京城东南角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几分钟前,我打电话给母亲,报告了我和前夫离婚的决定。
“知道了。”
母亲的反应平静得如我所料。也许是为了避免尴尬,我们没有探讨任何细节。
“那你住到奶奶家去吧。”
“好。”
“……不用和她们说什么……”
“好。”
一个半小时后,我突兀地出现在了奶奶面前。母亲显然和保姆小红打过招呼,她什么也没问,只是热情地招待我。爷爷生前用的单人床被仔细整理过了,洗得发白的绿色条纹旧床单上,新的毛巾和牙刷摆在一起。我扶着床沿疲惫地坐下,准备歇口气,才注意到对面椅子上的奶奶审视的目光。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来陪您住两天不行吗?”
我懒得和她多废话。奶奶作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天晓得她要重复多少遍同样的问题。
“好是好,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像好奇宝宝,观察着一个刚到手的玩具,随时准备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你不是老嫌咱们这儿太冷清吗,有人来陪你不好吗?真是,这老人。”小红憨笑着,适时地插嘴,并借机把我推去洗漱,这才让我躲过一场盘问,得以度过了一个还算安稳的夜晚。

次日的晨曦来得有些晚,睡得本就不甚踏实的我忽然被一通呵斥声惊醒,睁眼时一个胖墩墩的黑影站在我床边。
“你怎么睡到我们家来了。”
“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吧。”
是奶奶。我翻过身,不想理她。谁知她越说越严厉,连小红都揉着眼睛、穿着睡衣跑出来调停,可她说什么也要我离开。小红好言相劝不见效,和她争吵起来。两个人谁也不肯认输,嗓门一个赛着一个洪亮,音量从低到高。
“是她爸爸不要她了吗?”
“告诉我,不要紧。我给她爸爸打电话去!”
“我说话还是算点数的。”
说完奶奶气呼呼坐在电话前面。我们都不理她,半晌只听她自言自语道:“我忘记我要干什么了。”
奶奶在20年前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即俗称的“老年痴呆症”。经过一段时日的药物治疗,她的病情趋于平稳,可是记忆力、理解力、脾气秉性和生活习惯都有所改变。在她患病的这些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看望她,和她聊一会天。和她对话辛苦而且单调。
“云云,你在哪儿工作呢?”
“你结婚了吗?”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
“结婚了吗?”
……
同样的问题不重复上一百遍不算结束。虽然我大部分时间有问必答,可是内心不免烦躁,经常找借口岔开话题,避免口舌之劳。
这次入住奶奶家,相当于送上门去听她唠叨,躲都躲不过。每天凌晨三四点,奶奶会准时把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叫醒,开启各种我不愿开口的话题,絮絮叨叨说个没完,直到嗓子都哑了,才自行倒上一杯浓茶,结束“审讯”。而我每每被诘难到流泪崩溃,她却又没事人似的喊我吃饭。
在爷爷的床上住了半个月,被奶奶折磨了半个月。我徘徊在被侮辱、被抛弃、生不如死的心理边缘上半个月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住进了奶奶隔壁的小房间。躺在隔壁的床上,我像好几年没见天日的囚犯终于刑满释放,呼吸到久违的自由空气。
奶奶虽然没把我忘记,每天仍要来“敲门”问候,可终于不骂我了,而且每餐都会专门来喊我吃饭。有时我在做自己的事情,只是口头答应,并不动弹。她就慢吞吞走开,过两分钟又来喊我。
离婚后不久,我辞去事业单位的稳定工作,开始了异常艰难的创业。奶奶显然不知道什么叫创业,事实上,她对于新鲜事物一无所知,看见我的破洞牛仔裤非要给我新买一条,还好没说给我缝上。
她没再打听我的婚姻状况、工作单位,只顾日复一日,每餐按时叫我过去吃饭。这成了她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和爷爷已经双双离休。小时候,爷爷是家里绝对权威的大家长。他喜欢阅读《人民日报》和各种政治书籍,给儿孙们做思想工作,每周一小会,每月一大会。
我至今眼前还能浮现出当年的场景:全家十口人团团围坐,大大小小或坐在板凳上,或沙发上,或床上,听爷爷给我们解读最新政策动态、国内外政治形势。大人们轮流发言谈体会,小孩们则抓耳挠腮、不知所云。在这样严肃的会议上,没有人可以享有“除外”权,只有奶奶是唯一有特权睡觉的人,我们的学习和论谈,通常伴着她均匀而柔和的鼾声。我因此把她看作家里最“落后”的分子。
小时候,大人们很少对我说起奶奶和她的经历,她自己也绝口不提,所以我对她的过往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离休前是中央电视台的小干部。
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她有点古怪,喜欢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靠在墙上打盹,头油甚至把白墙浸染成了乌黑色;喜欢把茶叶根趁人不备泼在墙角,弄得墙角总是汪着一滩茶水;喜欢把各种零零碎碎收进不同的地方,连她自己的假牙丢了都找不到……后来从父母的口中,我得知这是疾病的表现。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老年痴呆”这个名词。
在奶奶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不久,体弱多病的爷爷又一次生病倒下,不幸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时日无多。在爷爷最后的年岁里,除了保姆,只有奶奶陪伴在他的身边,寸步不离。
他们经常坐在二环路边有树荫的长凳上,爷爷看报,奶奶看马路上往来的汽车。爷爷经常温柔地摸着奶奶的头发,一脸爱怜和不舍。连去银行存钱这样的小事,爷爷都不肯让奶奶做,她根本不会存钱。爷爷只要手头有钱就会跑去银行,以奶奶的名义存起来。为了身后给奶奶多留点钱,爷爷省吃俭用,虽然离休金不低,却从不肯大手大脚。
2004年2月15日,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现在,马上来,人民医院,快。”
从父亲急切的语气中我有了不祥的预感。当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抢救室,爷爷已经需要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了。全家人围成一圈,唯独不见奶奶。父亲冲我点点头,我们低着头走出抢救室。片刻的沉默之后,我突然想起什么,忙问奶奶去哪儿了。
“你奶奶丢了。”
“什么?!”
“已经报警了。”
父亲的语气中只有无奈。一个多小时后,奶奶出现在医院门口。我跑过去拉着她,生怕她再走丢。她的眼神涣散、焦急而又茫然。我们无从得知她是如何找到医院的,不晓得不会打车的她是如何走来的,更无法感同身受她的心情。只是爷爷已经被推到太平间了……
爷爷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了。告别仪式后,奶奶坐在自己平时的座位上,却不肯打瞌睡。她迷迷糊糊问我:“老头儿呢?”
“他怎么还不回来?”
然后看到柜子上的遗像,恍恍惚惚又问:“老头儿去了八宝山吗?”
恍然大悟之后,一会儿又问:“老头儿呢?”
……
日复一日。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理解了这件事。她没哭也没闹,但是心里好生糊涂了一阵子。
每每看她坐在遗像前发呆,我们都很担心她病情加重。但是事情出乎意料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药物和心理治疗的双重作用下,奶奶心态慢慢恢复了平稳。

距离爷爷去世已过去整整十年,我住进了奶奶家,虽然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但很意外地——不知是我变了,还是奶奶变了——我开始慢慢享受这样的日子,不再嫌弃奶奶,并喜欢上和她一起谈天说地,“忆苦思甜”。
“奶奶您出过国吗?”
“我出国不多,没去过几个国家。”
“您去过哪国呀?”
“不记得了……大概去过日本吧,忘了。我主要是抗战打日本来着。”
其实奶奶并没有去过日本,她一生梦想出国看看却未能如愿。老来这个未完成的夙愿经常被她“梦想成真”。一会儿是日本,一会儿是德国,反正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终于看见了外面的世界。
当年身为开明地主的太爷爷让四个女儿全部参加抗日,于是奶奶14岁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成为一个抗日小兵。太爷爷毕业于保定军校的表弟抗战中战死沙场,他延请老师写了一篇文言悼词,要四位不懂事的女儿背下。
在我的要求下,奶奶当场给我背诵了悼词全文。她半闭着眼睛,拖着长腔,就像教书先生给私塾里的童子念蒙学课本一样熟稔,不知在心里背记过多少万遍了,虽然她的深县口音外加艰涩的文言,让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可那时我仿佛触摸到了奶奶内心一点真实的情感。
住到奶奶家之后,我发现她是院子里的大明星,谁都说她年轻时是有名的美人。可是从她布满岁月沧桑的脸上,已经看不出曾经的美丽。她一年到头把自己裹在大棉袄里,走路拖着不利落的腿脚,矮矮胖胖的看上去像一只大熊。
自从生病以后,奶奶更不爱下楼了。她一年一年地待在家里读书看报,困了打个盹儿,醒来又接着看。我经常和她坐在不开灯的房间里,直至窗外的天空慢慢暗下去。有时奶奶会捧着一本奇怪的书长时间沉浸,比如《瓜类蔬菜周年生长技术》,我问她看的什么书,她看看我、看看书:“我也不知道。”
又有一次,她拿着一本《深县县志》看得认真,我知道她是河北深县北部地区的人,就问起她老家的情况。她却好似终于逮着了话头,数说起太爷爷的种种不是来:“……吃饭时他就训我,他打我手板……”
作为家中的长女,奶奶的童年并不快乐,无论家里哪个孩子犯了错误,太爷爷都要拿奶奶是问。饭桌上太爷爷为了训斥奶奶,经常一口饭都不让她吃。
当然,奶奶童年的回忆除了悲伤,偶尔也有欢乐。
奶奶跟我提起她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二婶教她唱歌的事,被我引以为家庭“重大历史发现”。奶奶五音不全,从不肯当着人唱歌。但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她经常哼起同样的曲调,虽然调子平淡无奇,但是我却觉得有趣,留意歌词,发现那是一首老歌,《渔光曲》。奶奶经常手脚并用,打着拍子,轻轻哼唱,我仿佛一眼看到了当年奶奶学歌的情景。
还有一次奶奶不知从哪儿找到一包大虾酥,她瞌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吃一块糖,再睡再醒再吃。一块接一块,掉了一身渣子不说,还把糖纸扔到不被人注意的书架缝隙里。
奶奶得意地告诉我:“小时候谁给我一个大子儿,我就拿去买糖,大块的糖一个大子儿能买一块,小块的糖可以买两块,如果没人给钱,我就去找我妈要。”
她笑着,仿佛回到了妈妈身边,刚买到一大块糖。她大方地冲着我伸出手:“给你吃一块,吃吧。”
除了爱吃糖,奶奶还爱吃烤鸭和饺子。姑姑每次带她下饭馆吃烤鸭,她都像个小孩子一样开心地拍着手:“今天有鸭子吃,你知道吗?”
每逢周末,全家聚在一起,都会包饺子,奶奶总是争着擀皮儿。而逢年过节,爷爷不在了,家宴上讲话的人就变成了奶奶。奶奶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几句话之后就词穷了:“……我祝大家吃好!喝好!”
最后结尾的音调和音量还要来个拔高儿。尽管缺少政治高度,她的发言却总能引起我们的齐声喝彩。而她自己也会开心地给自己拍巴掌。

2012年9月4日,又到了奶奶的生日。爷爷去世后,每年这个日子,全家人都会尽可能齐聚一堂。只有三个人例外:三叔在银行做监理,常年驻扎在外省,很少有空回北京;堂弟和表妹则远在大洋彼岸留学。
他们仨也成了奶奶最惦念的人,没事总念叨:“三青呢?”“川川呢?”“鹤鹤呢?”而他们虽然人不在北京,却总会准时送上祝福。一通电话后,奶奶就会乐得眉花眼笑、心满意足。
三叔由于工作繁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每次他回来,都会第一个来看奶奶,准备一桌子家常好菜,让奶奶高兴高兴。
我父亲排行老二,为人低调,由于身体原因早早下岗,是默默无闻的老好人。三个哥哥之下,老姑也非常受宠。只有小时候调皮捣蛋、最让奶奶头疼的大伯,长大后“不受奶奶待见”。不管大伯怎样表现,怎样“拍马屁”,奶奶都会及时送上一个大大的白眼。
那天赶上电视台播放南京的专题片,大伯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南京待过,最近又去了一趟,完全找不到以前的影子……”只听奶奶悠悠地插嘴道:“你忘了中国是发展的了?你忘了解放后的中国是发展很快的了?”
大家都笑了,鼓掌叫好。大伯连连点头,承认了错误。
这个生日又是张灯结彩、无比欢乐的一天。按传统习俗,逢九的生日要大操大办。那天,大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三叔、堂弟和表妹照例打来电话庆贺。奶奶特别高兴,使劲拍着巴掌,为自己又多活了一岁开心。
“我都快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年,就要去八宝山了。”
我们都说她胡说:“您能活到一百岁!”
她似乎想象不到一百岁是什么概念,说:“一百岁,那我得老成什么样啊?”
我们虽然有些伤感,可是看着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她,我们都默默祝愿她,即便到不了一百岁,也尽量活得越久越好,我们离不开她,她是我们家庭的主心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奶奶生日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远在武汉的三叔晨跑后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距离他退休回京只有一年的时间。北京家里的新房子刚刚装修好,远在新西兰的儿子和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回国。
大家默契地对奶奶隐瞒了这个噩耗。从此奶奶提起三叔,大家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而过了很久很久——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奶奶终于不再提起三叔。
有一天,天气有些阴霾,她一个人坐在爷爷的旧书桌前看旧照片。她是那么沉静而专注,仿佛陷入了许多回忆……我从照片背面分辨出那是一张小宝宝百天的黑白照片,边角已经打卷了。我没有去特别打扰她。
那年,奶奶八十九岁,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

四五年过去了,奶奶依然活得精神矍铄,离我们给她定下的百岁目标,越来越近了。我们此时理所应当觉得她应该能再活很久。而我和她一起的生活,也越来越和谐而愉快。
平时,奶奶和小红的对话就像脱口秀节目,拥有无数逗乐的时刻。
“奶奶,人是什么变的?”
“人是什么变的?你说人是什么变的。人……是人变的呗!”
“人不是类人猿变的吗?”
“类人猿,有这个词,意思是说那时候的人长得跟猴子有点像。但不是说人是猴子变的……人是慢慢慢慢改变形状,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小红还不甘心:“……进化论您肯定没学过,人是猴子变的……”
“哦,那你是猴子变的,我们不是。”
奶奶能做的事情都尽量自己做。她自己手洗内衣,从不让小红碰,还喜欢帮厨给小红择菜。有次我和小红不在家,回来时见她抱着一只锅。她看时间不早,就下厨给我们煮“粥”,可是仔细看那米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原来是一锅白芝麻。
生活点滴充满数不尽的欢乐,然而事业上,我却遭到重创。由于缺乏经验,我的创业失败了,半生积攒的金钱和许多心血付诸东流,在家赋闲了好一段时日。
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收集奶奶的生活点滴,准备给她写一本回忆录。我经常没事就观察她,向她提问,给她拍照片、录视频。而她时而配合,时而则让我哭笑不得。
上午是零食时间。奶奶爱吃甜食,嘴里不闲着。何时何地,她都在不停地吃东西。她摊开手管小红要零食:“我要两块点心。”“你先吃完这块,就再给你。”她仍然不缩手,“我要两块点心。”
下午是睡觉时间。每天她可以从正午一直睡到日落,有时在椅子上睡着,手里还举着半块点心。
晚上的吃饭时间,我经常趁机问她各种奇怪的问题,她每次都认真回答;有时我们也很沉默,只顾默默吃饭。而饭桌上,小红每端来一道菜,她都不厌其烦地说一声谢谢。吃饭时玩手机是我和小红的保留节目。有次吃饭,我听着乱序播放的音乐。手机里突然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正在喝粥的奶奶猛地抬起头,我抱歉地看向她,她也定定地看着我,然后她笑了:“我这粥里头有葡萄干,你那里有吗?”
夜晚的固定节目还有看新闻和电视剧。有次我看见奶奶对着电视鼓掌,觉得这个场景有趣,就拿出手机,打开拍照,让她再鼓一遍掌。她不配合,说,“该鼓掌的时候鼓掌,不该鼓掌的时候不鼓掌。”
她就是这样睿智又糊涂,可爱又执拗。她享受着自己的世界,很少与外人交际;偶尔去院子门口看风景,无论我和小红怎么规劝,她也不肯回家,哪怕家里火上还坐着高压锅,她就那样对着二环路上的车来车往,一动不动地看。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她和爷爷就是这样,在二环路边,爷爷看报,她看车。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很少有奶奶的位置。唯一记得的场景是半夜醒来,她坐在我的床边,一手拎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抓着我的长头发。当时头发是我的命根子,看到她这么狠心,我也不客气地大哭大闹起来。吵得爷爷都过来批评奶奶,说她做得不对。
这个场景我总是难以忘记,以至于总觉得自己当年一点也不喜欢她。除了这件事外,我对她年轻时的印象几乎是零。
患病后,奶奶喜欢趴着阳台窗子往外看。尤其是送别时,她每每趴在阳台的窗沿上,冲离开的背影使劲挥手,直到小黑点消失在院子的拐角,她还要再挥一挥手。我在她身后看着,突然脑海里闪过了许多画面。原来在我小时候,是有奶奶的存在的。
有一年春节,我和奶奶趴在阳台上,看向楼下人来的方向。堂弟的身影突然出现,让我欢乐起来,我撒欢儿似的跑下楼,蹦跳着冲向他们。不想脚下一绊,摔了个大马趴。我爬起来,低头看到新裙子下面,两个膝盖全破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是奶奶第一个跑下楼,把我抱起来哄我的。她又翻药箱找到一瓶紫药水给我涂满了两个膝盖,还在伤口旁边画了一个紫色的笑脸,惹得我破涕为笑。
回忆新鲜,仿佛发生在昨天,当年的她还没有患病。
可是如今……早晨的天色还未亮,奶奶趴在阳台上,犯病了。她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你们都起床了吗?”
“没起赶快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喊声中气十足,拖着尾腔,划破了早晨安静的空气。小红嘟囔两句没有理会,她就那样足足喊了半个小时。院子里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吭声。大家都对她保留了最大的宽容和足够的善意。

有一天奶奶迷糊得厉害,下午我早早回来过去看她,只见她眼神迷蒙,躲闪着我。我走上前去,突然发现她捂着额头,额角血肉模糊。我连忙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不知道。
小红买菜回来也吓了一跳。我们连忙打电话叫来了我父亲,拦了辆出租车赶往人民医院。经过各种细致的检查,奶奶身体无大恙,只是眼眶上方缝了多针。
有了爷爷和三叔的前鉴,我一直担心奶奶会突然离去让我过于悲伤。然而,除了偶尔的小伤小病,她似乎活成了一个神。身体越来越硬朗,连精神状态也很高涨,我开始相信那个一百岁预言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新冠疫情悄悄降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小红因为回老家过年无法回到我们的社区,于是父亲母亲入驻进来顶替小红的工作。他们多次努力让小红回来却无果,只能接受了这个现实。
有一天母亲在写毛笔字,奶奶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在我的要求下,她拿起毛笔,欣然为我们写下了“中国加油”四个大字。她的笔反复在纸上描画着,脸几乎要贴到宣纸上了。我突然意识到,奶奶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上一次我向奶奶求字还是在一两年前,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我抄写了圣经诗篇第一篇,当时她的眼睛还可以看得清。
我看着奶奶的样子,感觉有些忧伤,有一种不知名的东西在我心里流过。我不想看她费力写字的样子,但又想留下些什么,无论是字迹也好,记忆也好,总之我觉得有些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抓紧时间完成计划中和奶奶相关的每一件事。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她写字。
两天后,她的左手疼得抬不起来,涂了很多红花油也不顶事;又两天后,她的舌头也不好使了,再也说不出逗人的言语。于是,我们叫来了救护车,把她送往医院,虽然查不出任何的急症,可她就是这样再也站不起来了。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奶奶无法进入三甲医院的高干病房,只能在一家无法探视的二甲医院治疗,准确地说,维持生命。
几个月后,在97岁生日前夕,奶奶在这家老年医院溘然长逝。陪伴在她身边的,只有医生和护工。
在进入老年医院病房之前,我整夜在留观病床前陪着她。我在她耳边轻声说话,她却嘴里含糊着大叫起来,我按着她的手,泪水润湿了眼睛。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奶奶的骨灰被装进了一个盒子里,和爷爷的放在了一起。盒子里,还装着她的一块金属股骨头。她最心爱的手表也和她长眠在了一起。看着爷爷奶奶多年前的合影,我想说点什么,却终于只说出了一句:奶奶,再会了。
相信我们会在天堂重聚的。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 “短故事学院”


奶奶去世一年有余,可是我总觉得她还在我身边,熟悉的床、熟悉的椅子、那些旧衣物、落土的破皮箱,我都舍不得让母亲扔掉,我喜欢一切都保持着她走时的样子。奶奶虽然离开了,可是她的故事留下来了——这个我长久以来想写又不敢写的故事。时间时常会来敲击我的心门:“再不写出来也许你会忘掉它。”
14天的短故事写作,有爱的导师和小伙伴给了我最好的指导和陪伴,没有他们,甚至我没有勇气下笔去写。中间因为各种原因,我割舍了部分我喜欢的内容,也许最终呈现的这个故事它不是完美的,但它包含着我对奶奶深切的爱和思念,我希望她在天有灵,可以看见——知道她的孙女在想念她。
原标题:《患阿兹海默症的奶奶冲着窗外大喊,“哎——你们好啊!”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