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与文学二十年:沉浮与坚守
文 | 南希 (纽约)
十年的远离,十年的回归。纵观自己的文学创作历史,大约就是在时代变化中,怎么样观察时代,迎合潮流,又放弃潮流,坚守初心的一个过程。
网络文学的影响
早年,我在《北京日报》社做记者。我热爱写作,除做记者和编辑外,业余时间写作,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纪实文学、评论、随笔和诗歌。本来以为会顺利地写下去,出国留学使我的中文写作被迫中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2年我以陪读身份踏上美国新大陆,写作中断,事业转向。特别是来美国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是我在文学写作上失语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新移民在陌生的处境里,每分钟都在经历惊吓、羞窘、颓丧或欣喜若狂,几乎是在几个月内完成正常人十来年的成长,现在想来也真是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国内读书期间,学的是俄语,到美国后从英语的26个字母开始学起。对比熟练掌握英语的新移民,我一度站在大陆与海外生活的双重语境、双重经验交集的起点上,也许在精神和文化上受到的冲击更强烈,倍感蹉跎。可以说,这是我人生里最大一次重创。当一个移民独立而自尊地立足于别人的国土时,其短时期的经历确实使内心变得极度的敏锐和丰富,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洋插队”的生活经历,就像当年的上山下乡的“土插队”一样,让我收获另一种语言和写作的养分。但当时,我却无暇顾及这些,连顾影自怜的时间都没有。在最初的艰难创业时期,我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求学,做各种工,像一个埋头推磨的人,在磨盘边上转啊转。在求学时期,我努力攻关。毕业之后,工作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喘息……就这样过了“埋头推磨”的第一个十年。
最初拼搏的十年,是与母国文化脱落、沉浸异国文化的十年,是努力摆脱中文、学习英文的十年。有两件事,刺激了我回归中文,一个是回国,一个是网络。
时空变化,会使人非常敏锐,我在阔别中国十年后回国探亲,第一次走出北京机场时,记忆霎时劈面而来,突然撞见了十年前的自己,猝不及防,瞬间泪流满面。我仿佛第一次“看生活”,而不是“过生活”。第二天,我在长安街边上一家餐馆买早点。坐到二楼临窗的一张八仙桌旁,突然被一股熟悉无比的气息笼罩了。我好像站在时光的“窗口”——窗外是长安街繁忙的街道,而我年轻时的背影匆匆掠过,我从这里去上学,去工作,去恋爱……光阴在我心里打了个结儿。这时眼泪突然奔涌而出,心里涌起了汹涌的波浪。我发现大陆的生活和意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十年是中国巨变的十年,我在恍惚之时,站在了三种文化的窗口:记忆中的和现实中的中国文化,还有西方文化。我多了几重视角,在语言之外,听到了多维空间的声音。
这实际上是文化的冲撞。我后来几次回国探亲和出差,都有同样的感觉,每一次在飞机上,我的思绪是最活跃的,时空的每一次穿梭,都激发心绪的激荡。每一次往返,都产生经验的改变。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笔,急切地记下飞溅的思想火花和佳句,我往往能写出很多平时写不出来的文章。我的邻座都睡着,黑暗的机舱里,只有我拿一支笔拼命地写,怕赶不上我的思想。
第二个影响是网络。在网络文学出现之前,海外华人面对的是一片文化沙漠,没有中文报纸,没有中文语境和文化环境,没有中文书,所以更谈不上写作的机会。最初我在德克萨斯州,基本上没有读到什么中文书籍,到纽约求学后,才在小书摊看到一些报刊。可怜的几本《新华文摘》和其它的非文学刊物。偶尔在理发馆看到的报刊都是繁体字,竖排版,很多繁体字我都不认识,拿起来读一下,很生疏,不敢相信我自己曾是靠文字吃饭的大报记者。而报上的内容乏味低级,都是三流港台小报写的艺人八卦,和令人作呕的夸张照片。
当时与大陆家人通电话很贵也很困难,记得有一种100分钟的电话卡,捧着话筒还没开口,眼泪先掉下来了,说了还没20分钟,就会听到“请重新输入你的号码……你的卡内余额不足以支持通话,请稍后再拨……”。真是乡音隔万里,家书抵万金啊!
请自行脑补一下,什么是文化沙漠?没有电话,没有书刊,没有报刊,更没有文学作品,在一片文化沙漠中又聋又哑。有的朋友打趣说,你要学好英文,必须忘掉中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新事物出现了,它就是网络文学。新世纪以来,新兴的科技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和思维带来巨大变化。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汉语文学的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从传统的书写模式,进入了全新的网络化写作环境。各大网络文学平台也应运而生:文学网站,文学论坛,文学博客等等。其间的风云变幻,因缘纠葛,是一波世界大潮,也对我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总是后知后觉,它出现了很久我才注意到,主要是因为自身太忙,无暇顾及。
从2006年才开始“触网”,读了很多网上文章。那时候网络很活跃。后来,博客出现了。人们可以面对面地系统地读一个人的文章,甚至是日记,连家里的鸡鸭猫狗都能看见,天涯海角一键相连。这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网络文学热形成一个新的百家争鸣、人人参与的热闹状态,它模糊了文学与出版的界限。它是海内外信息大爆炸大交流,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激荡。它使人感到,要跳入这个大潮,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可是脱离时空和大洋板块的束缚。可以说,有了网络,有了中文语境和各种文章与思想碰撞,这是我回归写作的外因。
造成回归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内因,即自己的内心需求的变化。生活变化了,学业结束,事业打拼,生活稳定起来,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写作这个事情慢慢回到了我心里。
“网络文学”初期,文章多是对生活的感悟。见到周围海外的文友写作上有了进步,我慢慢地又拿起笔,开始了散文写作。开始写作时是很困难的,由于十多年没正式写作,要启动时觉得写作的机能都生锈了,就像一台多年没开的老爷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我和自己作斗争,利用了一切空隙时间去写。更糟的是,我不会用中文软件,在国内没用过,到国外现学英文打字,所以面对英文字母的键盘,不知道怎么变成中文,因为一个滑稽的原因——我不会汉语拼音,在小学学汉语拼音时我生了一场病。我用了一个笨办法,把一本从中国带来的小小的《新华字典》,拆开,贴墙上,背。
真正触动我,使我回到写作的还是我的父亲。2003年初,我父亲因胆囊癌去世,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我至今对非典全无印象,因为担心父亲病情恶化,在当时非典最严重的301医院跑上跑下,心力交瘁。他知道我出国是不得已的选择,知道我历经很多,当时他可能也以为我不会再写作了,有惋惜。他也不说。可以说,他的去世让我思考很多从来没有考虑的问题。我父亲总是让我去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他问了我三次,你想做什么?每一次他都全力支持我。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恩。
写作原本是我的理想,但是生活并没有按照我计划的轨道运行。在我经历了一系列意外、压力和曲折,蹉跎了很长一段宝贵的时间之后,痛感“生命有限”。我觉得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作,我得好好把这件事情想明白。所以父亲去世后,写作开始回到了我的心中。当然,不是马上,而是走了一段弯路——我回到了美国,心里空荡荡的,对命运的绝望,使我抑郁、空虚、徘徊、冷漠,自我囚禁,几乎什么都干不了。连英文写作班都退了,老师来问,我都懒得搭理或解释。我沉寂了很久,有一天突然打开文档,写下一些回忆,然后是爆发倾诉,然后进入深思。突然,我找回了自我,发现我的笔变得沉重了,加入了以往没有的视角,即对生命的思考,让我决定开始写点文学作品,而不只是小文章。因为生命的意义不一样了。
我有一个特点是改文章,像得了“强迫症”,可能跟我做编辑的习惯有关,我还很注意文章的思想性和意象,所以落下一个“追求完美”的毛病,所以我的文章往往费时很久。比如《天禽如人》这篇文章,我写了半年多,当时拉拉杂杂写了上万字,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撂下来。有一天读《庄子》,突然受到启发,又联想到卡夫卡的一篇小说,就翻出这个文章把它重改了一遍,找到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角度。文章的思想性早已潜伏在那里,只是等待着一种合适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篇文章从一万一千字改成七千字,就又放下了。后来看到美国汉新文学奖在征文,要求三千字,我又把七千字删了很多,寄出后,没想到《天禽如人》获得了美国汉新文学奖的散文一等奖。陈蘅瑾教授评论说:南希的散文在干练的文字中透出真诚与大气,《天禽如人》这一篇散文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视角非常独特。朱云霞教授评论说:“现居美国的华文作家南希,是近年来在海外华文文坛非常活跃的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初她放弃了国内报社记者的职业,远赴美国留学。出国之前,南希已经发表大量的纪实文学、散文和随笔评论,然而生存语境的转变让她在异域无法继续中文写作。异质文化空间中的“失语”感、边缘感是很多新移民作家共有的经验,这也培育了海外华文作家跨语境、跨区域创作的独特性。在美国沉淀很久之后,2006年南希从散文创作开始,重新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世界,无论是观察角度、生活感悟还是生命体验,都在跨文化之后有了新的表现视域,获得美国汉新文学奖散文一等奖的《天禽如人》正是如此。
这个阶段,是散文阶段。在这个阶段其实我感受到的是学习如何逐渐靠近与回归源头,并且如实地去做出语意的调整。这时收获的是喜悦与感恩,是多么难得的心情。我在海外新兴的中文网络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还有评论和诗。我分享自己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心得体会,很多文章获得了读者积极的回响,让我感到兴奋。
我虽然写了很多中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我最喜爱的,其实是散文。散文的写作是我文学回归的第一步,是对现实的抵抗,散文就是生活,散文就是悟。一篇好散文应该像陈年老酒,有沉淀的过程,耐品、耐读、有回味,集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其实这就很难写了。在写了一阵子散文之后,开始注意写作视角,从开始时只注重一己之感悟,到后来换了观察角度,关注一些共性的厚重复杂的东西。
多视角创作的短篇小说期
2005年到2006年的网络文学阅读,对我是一种文化冲击。同时也引发了我的新思考。
在思考中,我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字,二是主题。
首先是文字。网络文学的海量作品,拥有民间的气息、野性的力量,但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读多了,我意识到网络文学的庞杂,有些网络作品,用糊涂不清的态度去写作,文章晦涩而又杂乱。有些文字偏离文学的标准,跟纸媒刊物作品有差距。过去,我因年轻又阅历浅,在写文章时把文辞漂亮当作工巧。到了年纪大一些,才知道文章是用来阐明内容的,因此不再轻率地讲究形式的美观、追求辞采的华美、炫耀声韵的铿锵,而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才能了。又因为我做过报社的文学编辑,这给了我一个标准,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标准。于是,我对自己开始有自律,不再漫不经心,避免浮滑而不深刻,改变以前为了更新而更新,为了连载而连载的偷懒取巧的写作,防止文章松散而不严谨。我希望文章明快,而文气流畅,于是反复修改,进行精简,希望文辞凝练,这点对我是一个提高,修改多遍后,才能凝聚保存文气,使风格庄重不浮,文章才能让人读得舒服明白。
另一个问题是主题,我看到网络文章的主题,很多欠思考,欠调查研究,为了博眼球,为了追求网络效应而赶时间,赶话题,赶时髦,赶风潮,而缺乏内容和深度。于是,我的阅读回到了书本上,回到了以前的阅读水准,要读就读那些真正的大师。我发现好的文章都有主题,好的主题都是言而有物,言之有道。同时,好的文章首先有好的文字,才能让人读得舒服明白,于是我开始有系统、选择性地读书,读现实主义的作品和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有针对性地深入地思考现实。
对网络文学,我也还继续阅读,但我放弃了海量阅读,改为重点阅读。我发现了一些少数写得极好的人,文字非常自然,具有自然性的力量和真诚的力度,人性的深度,既丰沛茂盛、元气充沛,令人回味;有的气势磅礴又精致婉约,具有古典美学价值。有一天,一位纽约博友对我说,我发现有两个国内博友文章写得很好,你跟她俩很相像。我跑去看这两位博友的文章,果然有文采,这是有天赋的真正的作家。文字在她这里全都飞了起来,她热情洋溢,诗意比别人多,见解非常透彻,很有见地。我的天呀!这个人的美感该有多么丰富!她有一颗多么细腻、多么敏感的诗的心灵!这类作者都是我重点阅读的对象,后来有幸因文结缘,成为文学之路上并肩前行的朋友,对我促进很大。
我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但也发现自己的优势:两种文化的经历,中性的笔触,比较庞杂而厚重,具有多层次的视角,对中国的基层较深入的了解,职业造成的较宽泛的观察面,对海外移民生活的了解,以及几种职业带来的细腻特质,使我有更多的题材可以写。
我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2008年我转型写作短篇小说,放弃在网上发文,转入小说的文学创作。我知道博客文字和文学文字的区别。小说的叙述角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这对我是一个有意思的挑战。短篇对一个作家的训练是最严酷的,对短篇小说的写作,我现在仍是一个学习者。我写的是社会类型的小说,不是自传式小说。我写我知道的东西,我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加上我的想象。我觉得,写散文多数是以自我倾诉为满足,但小说创作应该很快转入书写他人经验,尤其包括其它族裔的经验,关注生命体验和感悟。这也是小说更迷人、也更难写的地方。
我在英语环境中从事多年服装设计,同时持续地在业余时间写作,幸运的是,我的作品在海内外中文媒体还算比较顺利地发表,大约有十几年时间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并获得一些奖。开始,我以海外新移民为主要描写对象,反映自己能够驾轻就熟的移民生活,即“他国故事”。最初,被倾诉的渴望所驱使,从生活经验和在场经验出发,写下了短篇小说《沙丽的晚餐》,后来又开拓疆界,写中国故事长篇小说《娥眉月》等。但我很快随着阅历的积累、个人心智的逐渐成熟,开拓了一些视野,心态也变得淡定,写出了更厚重更丰富的长篇小说《足尖旋转》和短篇小说《邂逅》等。
回归内心的长篇小说创作期
写了散文和一些中、短篇小说后,由于年长,也由于对生命的感悟,我进入长篇小说写作,这是跟我的生命直接对话的文学,有了生命感悟后,应写出更厚重更真实的作品。对我来说,长篇小说提供了回归内心的写作,但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首先,长篇小说对时间的要求严苛,我这样的业余写作者无法做到。短篇小说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还可以进行一些语言和风格上的尝试,可以在感到疲劳之前就结束。长篇小说就太难了,创作时间、创作心境、创作中的自律程度、工作以及家庭生活等,任何一个点都会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我有工作,早出晚归,朝九晚五甚至朝九晚九,还有家务和生活……我被钉在一条小绳做的平衡木上,跳舞,不能越界,只能高空翻。晚上吃饭洗完碗,推开一切,打开电脑,在一团糨糊的状态下写一个小时,幸运的话,写一个半小时,是我的最佳成绩,不幸运时,15分钟,还没酝酿出一个字,关电脑,准备明天的上班,结束冥想,回到硬邦邦的现实。
其次,长篇小说要求完全的沉浸和专注。写长篇小说,要求作者长期高度集中精神,几乎与世隔绝,需要比常人更平静的精神状态,如驾驭一匹马在瓷器店里遛达,不能猛也不能出错。写长篇,是用一颗心作舟、作浆、作罗盘、作翅膀,赤手空拳在空气和时间里滑翔。
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娥眉月》是从2008年开始构思的。《娥眉月》写了前几章,中途母亲去世,我心情不好,搁置了很久,后来强迫自己在写作中恢复,前后加起来写的时间大约一年,到2010年10月写完初稿。其实我写得很慢也很少,常常感到很绝望,简直不自信到极点。我写长篇的原因,并不是自认为短篇小说已经写得很好了,而是想要尝试不同的创作形式。我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容量的体裁,容纳我从容的转身,也需要它能承载厚重的历史和情感,短篇小说则很难实现。同时,我早年做编辑的经历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后来移民经历中切身感受不同文化的碰撞,让我不再满足只热心描摹、记录生活现象而没有精神提升的小说。在一种更开阔、深远的人生视野中,我觉得人的信仰包括我自己的信仰, 在消失。陈衡槿教授讲得更通透,她说,南希在移居美国十四年后重新拿起写作之笔,在逼仄的时间和世俗角色的重重围困中,开始有计划地写作散文、短篇小说直至长篇小说《娥眉月》《足尖旋转》等的创作。文学成为她在异域生活的必备武器和自愈良药,也是她乌托邦式理想的承载之所。
现在回头看,最忙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最多。我每天利用上下班时间,用尽心思设计小说的章节,脑子里一直会转着小说里的场景,我随时带了本子在身边,写完下车的时候,在车窗上看到有一个人,耳边插一支铅笔,脖子上挂一条长尺(这是我在上班画图纸时的打扮),顿时哑然失笑,赶快拿下铅笔,假装理理头发……有时下班晚了,我又专心写作,半夜里忘记倒车,坐错车,把自己封在车库里面,差点夜里回不了家。说起来可笑,我有时会魔怔似地在梦里写作,最近也发生过,我第二天醒来,常常会懊悔忘记了梦里的佳句妙思。
我虽然在十七岁就发表作品,但之前都是业余写写,没有条件把写作当成最重要的事。而自从出国之后,有十多年完全终止了写作。现在我也没有条件把写作当成职业,但是,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的日程表几乎是计算到了每一分钟,用来写作的时间经常是几分钟的片段,有20分种就是奢侈的。没办法,也是由于我的条件太艰苦了。为了专注,也为了时间,我果断“断网”。我不上网,不写网络日记,不写时政评论,不聊天,不追星,不快速靠近人群。包括后来微信刚兴起时,我决定暂时不安装微信(有几年时间)。不学习任何手机上的新知识。这个是比较反常的,属于对新技术的抵制和不接受。这也是由于性格造成的,我是一个非常有自我意识的人,自律的人,所以我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就自我封闭。就这样我连续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长篇小说都用了三年时间,处于“地下状态”约有六年时间。我工作很忙,常常被迫加班,很晚到家。所以我没有任何空隙去进行社交。除了工作和生活的时间之外,我只有占用自己的睡觉时间,来充当创作时间。所以这是我为什么停掉微信的原因。
算起来,我是两次摆脱网络。第一次是摆脱“网络八股文”,向严肃文学靠拢;第二次摆脱,是摆脱网络(包括社交媒体和微信)对个人时间的侵占和独立思考空间的侵占。这就是我与网络文学的“恋爱,交往和分手”的“历史”。我是喝了网络文学的奶复苏,但是我又跟它分道扬镳。是基于个人的成长和清醒。
《娥眉月》是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带着强烈的“网络文学”的色彩,点击率特别高,就像现在的“10万+”帖子,在网上几个文学网站连载多时。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
长篇小说《足尖旋转》是我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写作中,孤独是我最为关注的主题。开始写《足尖旋转》是在2013年底,当时我第一部小说正在出版社的流程中徘徊,我无暇喘息,马上就开始了第二个长篇小说的写作。原因可能因为我写完《娥眉月》,还意犹未尽,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跟第一部长篇一样,这部书的很多段落都是在通勤的地铁上完成的,每周末固定两三个小时全身心的写作,对我来说是就是最幸福、最放松的时刻。
《足尖旋转》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始终没有后续,也总达不到我脑子里想象的标准。它沉默着,沉默了多年,直到有一天,因为某件事的刺激,它“啪”一下就蹦出来了,成为这个小说的种子。一件事触发了这个素材,这个故事活了,开始发酵。故事在孕育成长,它曾经瘦弱、蹒跚,但是后来越来越强壮、成熟,它的体积膨胀起来,我有点控制不了它了,后来它又生出一些原来并没有的人物。它一路使我惊奇和难以控制。这部小说完全不同于第一部小说,它也出乎我的意外,以一种妖娆的姿态自由生长起来。
朱云霞教授读了我的两部长篇小说,并进行了比较:“从《峨眉月》到《足尖旋转》,我们看到南希的长篇小说容量越来越丰厚,由个体的情感、成长和流动建构起复杂的社会网络,但青春和爱情都只是故事的开始,孤独、流浪和漂泊才是她表现的关键。在南希那里,漂泊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具有双重意涵:从现实指涉来说,既写出上世纪末期青年人向外走的出国冲动,也写他们回返当下中国的平常与热诚;从精神隐喻来说,这种流浪和漂泊涵括了不同种族的人们,是对生命和自我探寻的象征。流浪和漂泊,是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在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中,这样的主题与过往的离散情绪和失根感不再相同,新移民作家往往在家国之外进行超越性思考,他们更关注人类共有的情感诉求与内在的精神向度。
文学是渡过苍凉人生之舟
有人问我,我一直从事设计工作,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
真正的鼓励来自我写作的过程中,在网络上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一路扶助我前行,成为我的知音和良师益友。没有他们,我不会有今天的收获。也包括鼓励我的师长亲人,比如我的父母,还有在我年少时对我有过期许的人们,尽管他们不在了,我是为他们交出的作业。写作对我有治愈作用。文学是渡过苍凉人生之舟,文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简单地消极避世,而是进入了另一套生命程序,另一种层次。孔会侠教授说的很准确:南希的生活阅历很丰富,既在国内插过队、做过《北京日报》记者、又移民美国了二十多年,她对生活的体悟可谓多而深。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写作是个人精神的需要,也是时间给予的良策。”为什么写作会是“个人精神的需要”?我想,主要就在于写作对作者自己心灵的作用。小说的文字是作者灵魂流淌出去的真实,表露的是作者的人生认识与精神气血,以附着于情节和人物身上的方式。
回顾2019年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坐在郑州“纸的时代”书店里,面对一屋子的新朋旧友,讲述自己的文学之路。这是我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新书发布会。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大幅活动招贴上,“旅美作家南希老师再次携新长篇小说《足尖旋转》,前来坐客纸的时代书店”,醒目字样标示出,它是一本新书的分享活动,又是一次重逢。两年前也在这里,做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娥眉月》的发布会。从一楼入口处到楼上的活动厅里,一路有鲜花和笑语,长长的一个大桌面上和书架上堆放着我出版的几本书。
“纸的时代”书店,漂亮得像植物园一样,从门口的广告牌到讲台上的巨幅照片,走进店门口,扑面而来一大屏有如温带植物园的满墙绿植,到处鸟语花香,流水潺潺,偌大的空间坐满了可爱的年轻读者。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网上的朋友,见到了旧雨新知,感到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网友陪伴了我十几年,有的专门从武汉跑到郑州参加我的发布会。在长长的书架上摆着我出过的几本书。有一瞬间,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网络让我们像亲人一样相聚,像亲人一样互相鼓励,让我们获得了温暖的友情。当我拿起话筒的时候,当我握笔为读者签名,当我意外见到可爱小读者排着队买书,当我和小读者合影,当我与在网上神交多年,未曾谋面的朋友合影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无比的充盈、温暖、幸福和踏实。这是由文学创作和网络的神奇美妙的结合,使我们的心灵碰撞,使我们连接在一起。
从我开始小说创作的2008年,到出版两本长篇小说,这十年,是我从网络文学写作起步回归文学的十年,与第一个远离中文文化的十年相比,我感到心灵相通的感觉,很幸福。感谢网络文学,它起到了唤醒、激发、震荡的作用。我只是一个文学森林中的远足者,常常迈出千百步,才望见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最悦目的风景是我的读者,我始终记得那一个像花园一样美好温馨的下午,和读者在一起的令人感动的情景。它将永远地激励着我,在孤独的写作道路上前行。这是美好的开启。让我们凭靠信念与劳作,凭靠彼此的爱,在世间存在。
我在《足尖旋转》扉页上写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这也是我对自己写作的信念和期许。
作者简介:南希,原名王燕宁,旅美华文作家,原北京日报记者,现居纽约,从事服装设计。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美国、中国大陆、香港等地报刊杂志。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娥眉月》《足尖旋转》。多篇作品入选各种精选本和选集。长篇小说《娥眉月》获得新语丝文学奖二等奖,散文《天禽如人》获美国汉新文学一等奖,短篇小说《多汁的眼睛》获美国汉新文学奖一等奖,短篇小说《谢丽一家的晚餐》 获美国汉新文学奖二等奖。
本文原刊于《向度》2021年秋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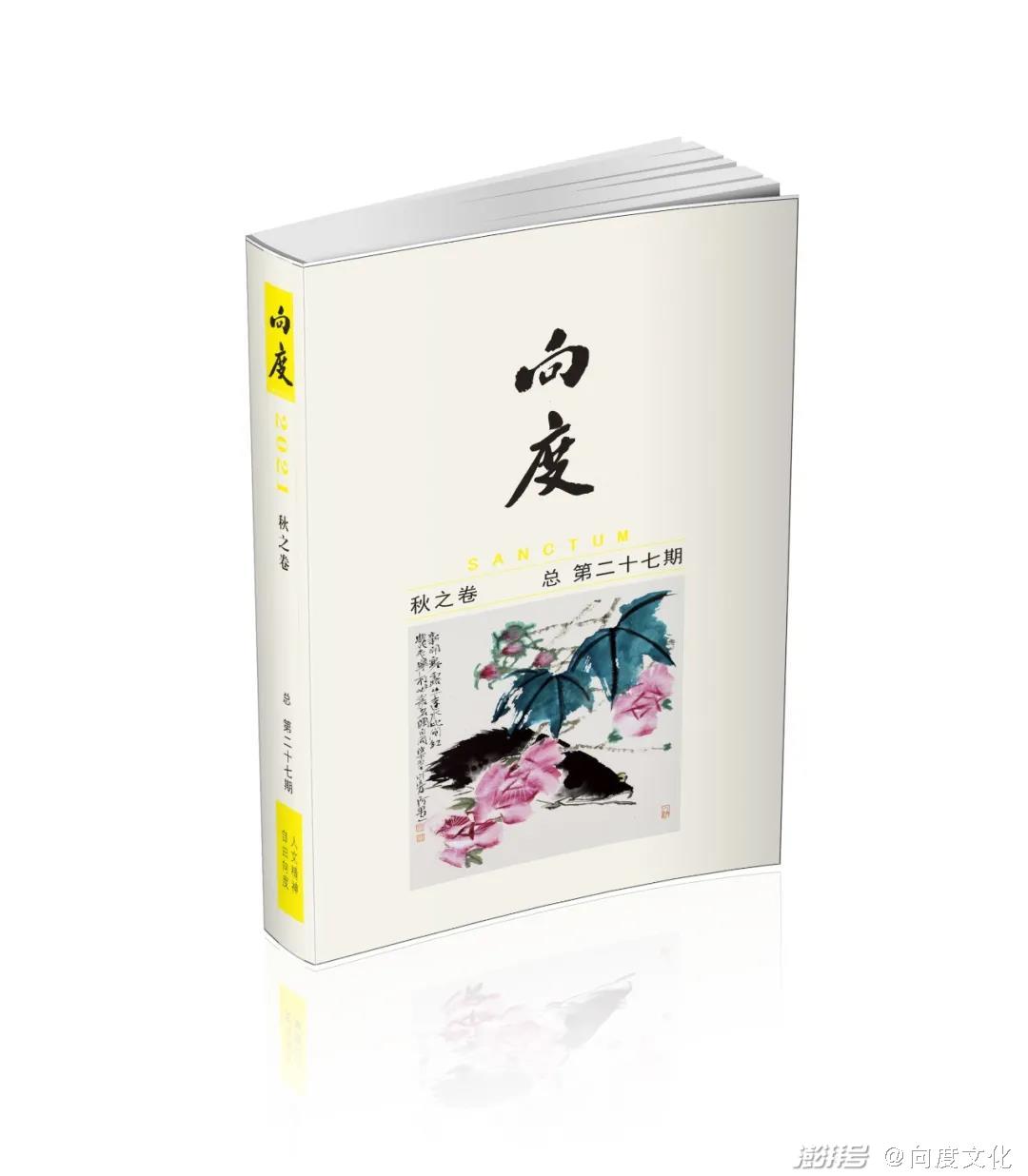
《向度》2021年秋之卷 总第27期 2021年九月出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