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余世存:一个五四的受益者,现在观念上已经超越鲁迅胡适
2005年,余世存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出版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些读者至今还记得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影响。《非常道》有着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了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孙中山、胡适、陈独秀、钱锺书、陈寅恪等多位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有人说《非常道》出版后,开创了一个小的文化产业,甚至开创了互联网中的微博体,是中国文体的一种先河。余世存说他看到很多跟风《非常道》的书,“但十年过去了,这些书都不在了,但是《非常道》还在,还是得益这种青春写作和五四精神的相通。”
十多年过去了,余世存说他写《非常道》的时候,自己可能还是“五四”的学生,或者说鲁迅的学生,现在可能有些不同了。“十多年过去,我自己又容纳了更多的东西。我从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受益者,到在观念上超越了鲁迅和胡适,在生活方式上和他们也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中西方的紧张是一直存在的,但在我这里,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包括现代化,没有那种过于紧张和冲突的关系。”
近日,《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由上海三联书店再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因此采访了余世存,请他谈谈如何看待互联网“绑架”的生活以及现代人的焦虑感等问题。

澎湃新闻:有人觉得我们被互联网、手机和各种讯息绑架了,而您却更看重互联网的创作力?
余世存:对的。我觉得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不是很多,我不知道西方人的研究多不多。我们的网络生活包括互联网阅读,肯定要比传统的阅读要更精彩、更有意义,也更全面一点。当然我们还是离不开传统的、纸质的阅读,而现在网络阅读的巨大创造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但我相信它的创造力迟早有一天会让我们惊艳。
我曾经遇到过一些网络作家,撇开质量,借助于网络,他们的规模是惊人的。从创造性上讲可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互联网阅读,可能写不出这么多书来。比如在过去的话,可能三五年才能出一本有质量的书;如果以我们现在对互联网的理解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半年、一年内出版一部有质量的著作。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乐观,也是非常期待的。更多的年轻人要善用、用好互联网这个工具。
澎湃新闻:互联网会促进作家的创作力吗?
余世存:互联网给写作者提供了更好的阅读和写作的条件,让他们和过去相比得到更多的便利。比如说我有次到东北的一个图书馆进行交流,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馆藏的图书已经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给研究者和写作者提供了方便。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所有馆藏书里的条目都能呈现,这是一个很大的便利。我当年编写《非常道》的时候没有这个便利,那时候只能用传统的方法,比如说抄卡片,抄了几千张卡片才有这本书。现在应该是很容易了,除非是特别生僻的书。比如说你要查一个民国的人物,他的很多生平事迹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只要你善于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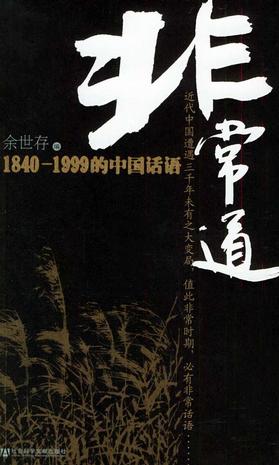
澎湃新闻:就是说互联网在技术上提供了更多便利?
余世存:对。当然它在思想上对作者的要求也更高了,否则的话你跟读者的沟通就会非常尴尬,因为读者了解的材料和你一样多。我有时候觉得这也是对知识分子的挑战。我很难想象以后我们生活在穿戴式的网络和嵌入式的网络中会怎么样?假如一个嵌入式的工具放到我们的手臂里面,或者放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比如说我们聊着聊着,眼前的网络上就出现我们需要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作家和学者更应该去实践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精神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当作生存和写作原则的,比如说万物相互链接,我们不应该用某种传统的标准去看待,我们必须去实现某种有效的链接,这当然不是生拉硬扯地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像我看网上把有位学者将王阳明和马云放在一起研究的文章拿出来讽刺,那样的链接就有点过分了。
澎湃新闻:您在讲座中谈到李泽厚所说“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这种“救亡的必要性”可能不仅在五四时期或者辛亥革命时出现,自古以来我们就比较崇尚救亡式的英雄,比如说文天祥和史可法。那这种救亡的焦虑是怎么遗传下来的呢?
余世存:你这个发现非常对。以中世纪论,中国的中世纪在宋代,在宋代中国很糟糕地遇到了北半球一个小概率事件,那就是气候变冷,这就导致北方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地来到中原寻找生存空间。所以宋代立国后不久就要面对来自北方的压力,在这种压力面前它就要救亡,正是因为如此,在发掘个体生命价值上就做得不够。
我记得多年前韩少功和我写信讲过这个问题,很可惜这些信现在已经丢失了。他和我提过,西方人从中世纪走出来后,尊崇个人来排斥宗教,但中国是相反的,是“舍人以奉国”,宋代理学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即牺牲个人来成全国家,而西方中世纪是“舍教以立人”。这就是你刚才提出的,中国的救亡意识好像源远流长,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你看从宋朝开始中国就一直有外部环境的压力,在外部压力面前,人很容易让渡个人的权利来保存种族。
民国时代类似的口号就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鸣。中国人没有从宗法、宗亲的农耕文化中走出来,农耕文化就是要讲集体主义、宗亲观念,而在这种宗亲观念中个人的价值和地位是比较低的,没有把个人上升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价值高度。虽然中国的圣贤经典中也能看到他们对人的尊崇,但这种尊崇是抽象意义上的。比如说中国人讲“人与天地参”,“一贯三为王”,好像把人的生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安排中却并没有把人抬到这个高度,反而把人放在一个既有的秩序中,无论是自然秩序还是人间秩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老一辈人对中国文化的判断是对的,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伦理之中,而不是生活在自己独立地与这个世界互动并建立关系当中。
中国人没有生活在自然状态。如果用我刚才的那个世界观讲,世界有春夏秋冬,世界有东南西北,世界也有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少年是春天,在东方,中国人就一直被当作孩子在管理,中国人还没有长大,一直依附于某个亲友团、某个朋友圈子、某个管理机构。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某个地方的人、某个时间段的人或者某个国家的人。我觉得这是世界文明给大家的福报,人必须成为人,甚至首先要成为人,其次再打上时间和空间的烙印,比如说在空间上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生长在东方大陆这片土地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个地方习俗、文化的影响;在时间上我们生活在21世纪,不是17、18世纪,也不是宋代和唐代。我们没有必要在精神谱系上只认儒家传统,就像唐诗宋词是现代人类的遗产一样,在我们的精神遗产里还有希腊,有荷马史诗,有罗马法,我们也有古兰经,有圣经,有印度文化,这些都是我们的精神遗产。
澎湃新闻:我们现在也有某种发展的“焦虑”,比如我们最好的大学都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余世存:对。就像我曾经讲的一样,包括我之前上北大的时候,北大的口号就是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好像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还在喊。这种对“一流”的寻找好像成为了每一代人的一个梦。但是我们很少反观自身,很少考虑我们究竟获取了什么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如何摆脱“焦虑”,我觉得首先需要有人有这种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能够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安身立命的方式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典范,或者提供一个参照物。就像我讲的,如果知识分子自己也以出国访问为荣,也以旅居国外为荣,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以出国定居甚至移民到国外为荣的话,那内心还是会没有归属感,还是在赶时髦,自己就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自己不自信,不踏实。
假如真是按孔子的教诲来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东西方的文明当中都有比较好的教导我们生活的参照。比如孔子讲的“知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如果真的是知者、仁者、勇者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这么匆忙,没有必要这么焦虑,也没有必要这么紧张了,也没有必要拼命追赶别人,别人毕竟是现实的存在。如果我们只知道追赶别人,那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要求就还是工具性的。
一流大学也好,西方发达社会也好,最重要的是它们体现的精气神,人类的那种创造活力,我们只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种创造活力就行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流大学有那么多的硬件有那么多的科研经费、高楼大厦,就把这些学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这种精神是什么,时时刻刻拷问自己有没有这种精神,这是需要少数人带头的。
我们的前辈们,像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出的方案,虽然被称为改良方案,比如说“好人政府”,比如说在道德上严格约束自己,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值得去效仿,去实践的。这是从贵族时代、士大夫时代以来一个社会精英人群的责任或义务,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示范健康的人生;但现代以来,随着权力、资本乃至知识信息大规模地下移,转移到平民大众这里来,上层精英们的责任感降低了,他们与某种下流的东西同流合污,失去了健康的心态,变得偏激、片面。
太过激进要不得,我有一个说法,如果一个成年人还是很愤世嫉俗很偏狭很有戾气的话,那他就是不正义的,这是我的新正义论。我说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身心相貌负责,应该对自己的精神状态负责。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健康,很通泰,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人而去追求到伦敦去、到纽约去。其实那里的人也活得很焦虑,大家都被现代性的列车绑架住了,被技术绑架住了,上去了就下不来。
现代性也有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必须跟着它走,紧跟技术文明的升级换代,但我们的心态不能也这么浮躁。所以就像很多人讲“革命”,似乎只有激进的才叫“革命”,这其实是一个错误。只要一个人的存在本身是开创性的,有创造力的,那这个人的任何言说都是“革命”的。我们现在对“革命”的理解、对现代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是反革命的、反现代的。我们没有理解到现代性的本义,没有理解到“革命”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原来以为的现代性是反传统的,经过了这么久到现在我们才慢慢意识到所谓的现代生活它是包容传统的,甚至传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用我的概念讲就是要拥有全部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现代。我们这几年有点提倡家室、宗亲的观念,追问你从哪里来,这种血缘意识又起来了,但这种血缘意识只是人的少年阶段,这不是现代,现代包容了你的少年阶段,但你也要展示你的青年阶段,也要展示你的中年阶段。青年阶段你要去寻找世界的本来面目,要追求终极目标;然后中年阶段你要对这个社会尽义务,这些东西都需要,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好像把自己活好就好了,把自己活好其实还是停留在孩子的阶段,自己会照顾自己而已。
澎湃新闻:和您同时代的人其实都遇到了很好的机遇,他们的焦虑多在自身的发展。
余世存:是呀,但是也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1980年代所受的教育,所感受到的开放的气息是最难得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应该回馈社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和产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但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下岗了,退职了,不参与建设,只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在过日子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被这个社会裹挟而去,大家没有改造这个社会,反而被这个社会改造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惜,这有点像那个西方诗人艾略特所感叹的:我看到这么多人被死亡带走了。
我有时候在想,1980年代这批风华正茂的人,可以用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不再表达他们的存在,不再表达他们的创造力,外在因素让我们这代人不再有文化,这是很惨烈的事实。现在看西方的书,或者回过头去读读经典甚至佛经,还是因为自己内心没有东西,只好去依附经典,依附圈子,好像只有靠经典才能活得踏实。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普通人也能活得很好,活得踏实,活得有价值,那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精气神,而不是每天在人面前开口闭口说圣经、佛经,说孔子、《论语》。
澎湃新闻:那您怎么看待近年新儒家在舆论上活跃的程度?
余世存:现在这一批新儒家和港台那些老一辈的新儒家学者们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国内这批活跃的儒家信奉者的姿态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类现代化的潮流,有些逆时代而动。当然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他们,但是无论是站在人类的立场还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我们都不应该将儒家的经典那么神圣化。

澎湃新闻:您曾讲到目前家庭教育的缺失状况,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又有脱节的地方。那对于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怎么办?
余世存:现在的父母,学校的老师还有社会对个人存在的判定是不够完备的。我们整个社会还是过于把人当成工具了,虽然我们喊得很高,好像生命重于一切。但事实上通过房价涨价就可以看出人在中间扮演的工具性角色。比如说房价政策一改,很多夫妻就要求离婚,因为离了婚就可以买第二套房,里面确实有合理性的成分,要理解人性的庸俗化;但这样的事如果成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就可怕了。那么学校也是如此,学校也是把孩子的培养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并没有把学生当作一个有无限创造力的人去尊重、激励和鼓励。有些学校看不起学生,但是学生的头脑看起来空白,一旦激活了就有无限的创造力。
“尊重生命”、“终身学习”等这些口号很容易提,但是我们怎么在日常细节里让人觉得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确实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完成?这一点我真的不太清楚。以我自己举例,我这么多年在体制外生活,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想问题,它既是在挑战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在挑战我作为中国人、作为人的一员的心智。这个问题诱使我去读书去探索,使得我这么多年还能得到一些东西。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去见一个知名的文化人,我和他聊天的时候和他说自己最近没什么书要看,希望他能推荐一本书,他居然很郑重地说:“现在还读书干什么,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几十年书还不够吗?就应该赶紧去工作,赶紧去挣钱,赶紧去创造。”他还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排比句,我都觉得很纳闷,大家把读书看得如此功利化,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自我教育是要伴随我们终生的。
我经常看到周围的人吹牛,说自己大学的时候对哪本书是下过大工夫的,就好像靠当年下过的工夫就可以玩一辈子一样,用我们现在的概念这也是违背现代精神的。学习是终生的,而且需要和身边的人、和亲朋好友一起互动。我经常拿哈佛大学的黄万盛教授举例子。他曾经跟我讲,现在西方研究哲学的很多转向价值哲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加有效的、可以安顿生活的价值。我后来就问那有哪些价值呢?他说有四大价值:其中第一大价值就是学习,西方人现在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在社会中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其实和东西方的文明教育是不矛盾的。你看你读孔子的《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也是要推崇学习。那么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孔子的情境,因为论语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结集的,孔子死后这么多年弟子们把他们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放在前面,放在前面的就是“学而时习之”,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孔子,孔子最重要的理论不是仁爱,可能是学习。
孔子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一辈子也有好几个阶段,年轻的时候他提倡礼学,克己复礼;中年的时候他提倡仁学;但到了晚年他又提倡易学。我们不要把仁爱看成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是看作生命价值中的一个维度而已,孔子还有很多维度,其中学习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把学习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顶多是急着要用的时候才去买点书看。我们在朋友圈、餐桌上聊的内容大多是作为炫耀的工具,我们很少将其内化为我们的精神信念。这是我们学习不够造成的。
所以你说现代人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完善起来而不是缺失?就是要终其一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你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保持足够的开放,才能有更包容的心态。就像之前有个年轻人对我说虚构类的东西他是不看的,他先天给自己规定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都给自己设限,然后又以为这是最重要的,以这个限去干预别人,就像很多儒学的人看不起信佛的人,看不起基督教一样。我们应该更开放一点,因为互联网精神的本质就是零和一,零和一不是完全对立的,从数学的角度零和一是互根的,互为根本,同我们《易经》里的阴阳一样。中国人爱讲“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画地为牢,不与外界打交道,这既违背古老的东西方文化的教导,也违背技术文明带来的互联网的内在精神。
(实习生陶越彦对本文亦有贡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