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图腾制度》到《菊与刀》: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
【编者按】
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历史学教授,专攻情感史、感官史等,在《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一书中作者梳理了从启蒙运动到大众传媒时代,从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到奥巴马写给女儿们的信,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斯皮尔伯格的《人工智能》、梦工厂的《怪物史莱克》的情感史历程,情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催化作用,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情感的处理方式亦存在差异。本文摘编自该书《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虽然涂尔干的确探讨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长途的旅行。他的研究建立在现有的人类学研究之上。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表征”(包括仪式及其功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1912年,他写道:
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的表达。亲属们流泪、悲伤、虐待自己,并非是其本人感受到了死去亲人的影响。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其表达出来的遗憾之情。但一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情感与参加仪式时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并没有什么联系。当失声痛哭的人完全被悲痛所占据时,倘若有人向他们说起一些带有世俗趣味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即刻换了一副面孔和声调,开始谈笑风生,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因此,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一个人流泪,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悲伤,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出于对习俗的尊崇,他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仪式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他的感情状态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义务经由神话的和社会的惩罚做了规定。例如,他们始终确信,如果某个亲属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恰如其分,死者的灵魂就会步步紧随着他,直到把他置于死地。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点,就会发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对社会面具和“真实面孔”或个性的区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体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而且,如果没有涂尔干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情感的仪式化解读,当今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我们回到涂尔干和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他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在促进共同体发展的固定社会规则下的运动。宗教也意味着宗教仪式和集体情感爆发的“沸腾状”。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
20世纪法国人类学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和马塞尔· 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一样,他也受到涂尔干和德国传统的影响,因为在1941—1948年,他在美国期间受到了弗朗茨·博厄斯的影响。此外,他也受到了卡尔·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他在纽约时曾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密切合作。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结构主义教父索绪尔的作品。
在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法国后,列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图腾制度,进而研究宗教和情感。在他之前,不同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基于“原始”民族和图腾(通常基于动物起源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发展出宗教理论。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图腾表明,宗教生活始终与共同体有联系,涉及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图腾的使用并不代表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认知操练,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抽象化是罕见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所有关于图腾的重要作家—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克罗伯(Kroeber)——都把图腾追溯到情感,也就是认知的对立面,因此放弃了任何提出一个科学解释的机会。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由于感性是人最捉摸不透的方面,所以才会有不断诉诸感性的诱惑,而将那些其实并不适用于解释,所以也将不能解释的东西遗忘掉了。
涂尔干认为人类通过情感构建动物图腾,是为了与他们已逝的祖先建立联系,而列维—斯特劳斯反对这种“神圣情感理论”,他认为:
实际上,冲动和情绪什么都解释不了:它们往往都是结果,或者是体力的结果;或者是精神潜能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是后果,而不是原因。
就情感而言,列维—斯特劳斯被证明是众多实验心理学家中又一个唯物主义者,卡尔·朗格(Carl Lange,1834—1900)和威廉·詹姆斯根据他的思想提出了最有前景的理论。他们认为情感不是身体内部的东西,相反,肢体语言本身就是情感。后来的社会建构主义著作对《图腾制度》(Totemism)中关于冲动和情感的这段文字给予了不同的重视。有人认为斯特劳斯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家,为某种程度的评价或意图主义创造了空间。也有人认为,他将情感明显地简化为肢体动作,这足以让他成为心理学家西尔万·S.汤姆金斯(Silvan S. Tomkins,1911—1991)的帮凶。汤姆金斯是所有社会建构主义者最讨厌的人,也是保·埃克曼的精神之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人们最早感觉到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是最突出的代表。马林诺夫斯基从1914—1918年在新几内亚的研究,在英国开启了基于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和学习原住民语言之上的20世纪的社会人类学。马林诺夫斯基坚称,他关注的是亲属关系,但他的日记雄辩地表明了人类学家在从事田野调查时的感受。即使在澳大利亚,他也有这种感受:
对热带地区充满了恐惧;厌恶高温和闷热——想到遇见去年6月和7月那样的高温就一阵莫名的恐慌……非常沮丧,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前面的任务……我在1914年9月12日(星期六)抵达新几内亚……我觉得很疲乏并且内心空虚,以至我对此地的第一印象不甚清晰……10月31日……因为当时那里没有舞蹈或集会,我就沿着沙滩一路走到了奥罗柏(Oroobo)。非凡的旅途。这是我第一次在月光下欣赏这里的植被。非常奇妙和富有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轻轻地撕破了熟悉事物的面纱……走进了丛林。突然觉得很害怕,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试着省视内心:“什么是我的内在生活?”毫无理由自我满足。
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也是情感人类学反思的奠基文献。后来,人类学家们开始认为,他们自己的情感构成了收集“数据”的基础。因此就有了在与观察对象进行接触时的情感,因为被观察者的情感总是会与观察者的情感进行对话。
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另一位先驱是威廉· 哈尔斯· 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1864—1922),作为人类学家,他一直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战争期间,他对医学产生了兴趣,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为遭受“炮弹休克”(shell shock,即今天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士兵服务。其事迹因为派特·巴克(Pat Barker)的《重生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1991—1995)而名传后世。里弗斯与西格夫里· 萨松(Siegfried Sassoon)以及苏格兰克雷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精神病院的其他病人之间的通信,已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史料之一。他的创伤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田野考察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里弗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 Brown,1881—1955)在1922年对安达曼群岛居民的研究中,将“情感”定义为“以某一对象为中心的有组织的情绪倾向系统”。他还认为,“一个社会的存在取决于其成员思想中是否存在一个特定的情感系统,通过这种情感系统,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需求的调控”。“这种情感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社会作用于个人而形成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在1931—1937年在美国教书,因此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因此,当德国的人类学陷入相对默默无闻的境地时,巴斯蒂安通过博厄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对美国的人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通过巴斯蒂安的“儿子”弗朗茨·博厄斯,这条线索可以延伸到他的“孙女”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她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马上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菊与刀》,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民族的心理学群像。本尼迪克特不仅让日本的“羞耻文化”与美国的“内疚文化”之间的区别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她考察了指导日本人社会生活的情感观念,并将其与类似的北美观念进行了比较。例如,日文中“恩”的概念支配着一切。它是“爱”和“尊重”的混合体,也意味着责任和对某人的感恩。“我们重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的价值,越是无条件越可贵,而在日本则必然附有条件。”在“人情的世界”那一章中,本尼迪克特概述了日本人对五种情感的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实践。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是本尼迪克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此或多或少算是巴斯蒂安的“曾孙女”。米德对美国人类学和20世纪美国文化史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她在1925—1926年对萨摩亚群岛的实地考察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对美国教育和种族关系的重组做出了贡献,而且她对波利尼西亚人(尤其是妇女)的描绘也为性革命奠定了基础。她观察到波利尼西亚人:
对感情表达方式的态度同对行为举止的态度一样不同寻常。各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被区分为“情有可原”或者“无缘无故”。易动情感、喜怒无常、忧郁寡欢的人被说成是无缘无故地笑,无缘无故地哭,无缘无故地泄怒、好斗。“无端暴怒” 一词并非意味着脾气坏,后者是由“易怒”一词来表达的;同时也不意味着对合理的刺激产生一种不成比例的反应;它只能按其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即无缘无故地愤怒;用不太严谨的话来表达,即一种不因任何表面刺激而产生的感情状态。
总体来说,米德认为“萨摩亚人更喜欢中间路线,即情感的适度”。和其他人类学家相比,米德更加明确地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向美国社会举起了一面镜子。她指出,在美国核心家庭中,“情感的专门化”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一个包括几位成年男女在内的稍大一些的家庭共同体,似乎保证了孩子们不致发展出某些残缺性态度,诸如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等等”。
后来有许多人类学家追随米德,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情感人类学研究都建立在对南太平洋岛屿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非洲、南美或北美印第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人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学流派,他们尤其与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这对夫妇有关。我们只有一些来自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情感的评论,比如“不仅思想,还有情感也是文化的造物”,以及“为了下定决心,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为了知道我们对事物是如何感受的,我们需要感情的公开形式,这只有仪式、神话和艺术才能提供”。在探讨情感表达仪式特征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作品经常被引用。他的第一任妻子希尔德雷德更加注重情感。在20世纪50年代,她指出每个人都具有表达文化普遍性的情感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文化变量的改变,这些文化变量使其受到不同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有的文化鼓励某种特定的情感,而有的文化则往往会压抑它们。希尔德雷德·格尔茨倾向于在一种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过时的普遍意义上谈论爪哇人,即使与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相比也是如此。她认为,“他们不喜欢任何强烈的情感表达,几乎没有真正的友谊或爱情关系。爪哇的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安静和顺从,她们更善于表达情感”。她还谈到恋母情结的冲突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她还对当地人的情感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所有这些概念都以某种方式与尊重发生关联,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传递给他们。她由此得出结论,“儿童训练程序”不仅是情感社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对内心情感生活所做假设的内在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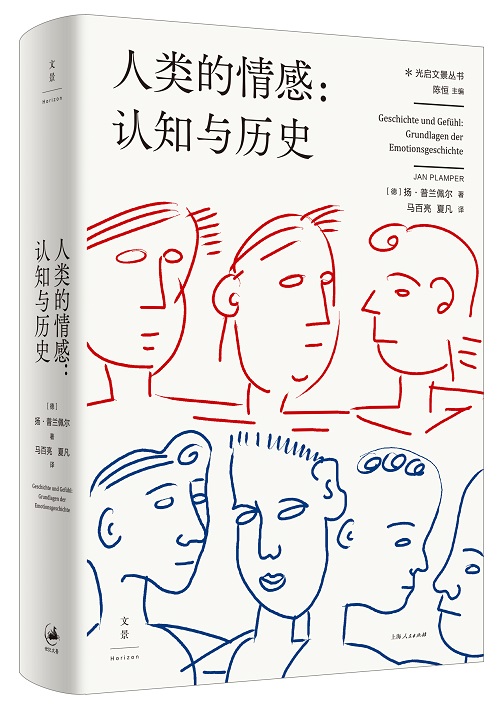
《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德]扬·普兰佩尔著,马百亮、夏凡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