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狭间直树:康梁关系演变背后另有一层围绕谭嗣同的纠葛

【编者按】
狭间直树是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者,被誉为当代日本梁启超研究、京都学派的领路人。狭间直树2012年在日本在清华大学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系列讲演,力图通过精细的历史文本比较分析,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近日经整理结集出版,是为《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本文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教授张勇对系列讲座的评议,此次亦收入集中,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载。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部分发布,此为下篇,评议范围涵盖前三讲,探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梁启超与康有为关系以及梁启超思想如何走向独立之过程。以下为正文:
狭间直树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其曾经主持的梁启超“共同研究”班,一度名闻遐迩;该研究的结集之作《梁启超· 明治日本· 西方》,也已经成为梁启超研究“必读书目”中的一种。2012年秋季学期,狭间先生应邀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纪念讲座”,承蒙刘东教授等推荐,我有幸以“评议人”的身份,全程参与了狭间先生的讲授,就近请教,获益良多。值此狭间先生讲稿付印出版之际,特追记当时先生讲授答问及课下交往之种种片段,以资纪念并应刘东教授嘱文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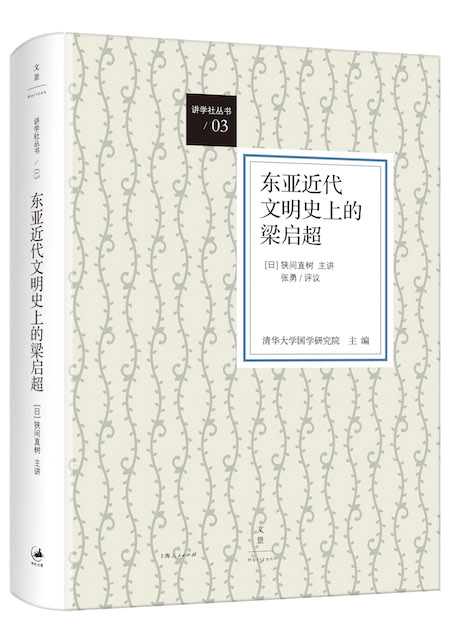
一
狭间先生此次讲座的总题目是《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由八次独立演讲组成。讲座进行中,对原拟演讲内容作了部分调整,其实际演讲的内容为:
第一讲: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世界史的近代与东亚;
第二讲:身为康有为的弟子——以接受西方为目的的“康学”和西学;
第三讲:梁启超思想的独立——《清议报》时期;
第四讲:梁启超的“辉煌期”——《新民说》等;
第五讲:“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
第六讲:民国初年的梁启超;
第七讲:梁启超与历史学——1920年代东亚人文科学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
第八讲:《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梁启超年谱在近代东亚文明圈中的意义。
调整后的讲题,涵容更广,增加了一般知识的内容。
也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讲座的内容,《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这一总题目下,还有一个副题——“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的关系为中心”。饶是如此,这里所谓“东亚”“文明史”的确切含义,似仍有待说明。所以,在第一讲时,我提给狭间先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东亚’?为什么是‘文明史’?”我的问题似乎振振有词:既然中心主题是梁启超与近代日本的关系,即中日关系,为何要用“东亚”的概念?怎样看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等对“东亚”一词的意识形态含义的解构?子安提出的日本近代知识体系(即“文明”)形成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否应当予以关注?以先生对“文明史”之“文明”的说明,应主要是指包括学术、思想、道德、艺术等在内的“文化”概念,并因此明确将梁启超与日本的政治交往(如特别指出的护国战争期间梁氏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排除在讲授之外;但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对学术的态度始终不脱“经世致用”的范围,这正是其“善变”中之不变所在;如是,在讨论梁氏的“文化”言说时,如何处理其必有的政治用意和政治关怀,是否应当将其纳入考量的范围?综上,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需要双重关照的问题:日本近代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梁启超与之互动时的政治关怀。
狭间先生对此问题似有几分不快,他的回答也颇简要(大意如下):东亚既是文化的(汉文化—儒家文化—朱子学等),又是地域的(日本—韩国—中国)。这里说到的文化,首先是东亚文化,再是西方文化,但又不赞成“新儒家”的文化观。“文明史”的定义尚无定论,但明治时的“文明”,大正时的“文化”,似都还没有“意识形态”的解说。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梁启超的影响,以后还会说到。
我感觉到先生的些许不快,应该是由于我提问的“孟浪”,或许也有责怪对其所讲内容未能领会的意思。在狭间先生第一讲的讲授提纲中,对“文明史”和“东亚”都有简略的说明,比如指出“东亚”曾经是以中华文明居主导地位的区域等,但讲授提纲更着重的还是“近代东亚文明”的问题。狭间先生这里所说的“近代”是一个世界史的概念,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与国民经济的时代),政治上的民权主义时代(万国共存与国民国家的时代),文化上的科学主义时代(客观知识与国民教育的时代),亦即西方文明领先并影响世界的时代。由此,则“东亚的近代始于1840年清朝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而所谓“东亚近代的文明史”,以“语言接触史”(词汇和概念的交流)为例,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分为四个时期:始发期即1840—1860年(从鸦片战争到北京条约):清朝占主动的时期;发展期即1860—1895年(从北京条约到下关条约):日清两国各自发展的时期;成熟期即1895—1919年(从下关条约到凡尔赛条约):日本占主动时期;决裂期即1919—1945 年(从凡尔赛条约到日本投降):日本侵略时期。狭间先生在讲授中,对前两个时期日本的情况有较多的介绍,但落脚却在第三期,即作为讲授内容主角的梁启超与日本发生关系的时期;由此,讲授的主题—明治日本文明对梁启超的影响乃至日本对近代东亚文明的影响—也就呼之欲出。如此明晰的逻辑叙述,却得到上述我提出的颇有些“惺惺作态”的问题作为回应,先生之不快,实属自然。
其实,第一讲的内容中,我更感兴趣的却是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来源问题。作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前的日本知识,狭间先生讲到乃师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并顺便提及有关其来源的最新研究。多年前我就曾关注此问题;先生所述仍未完全释疑,当时未及请教的问题,借此写在这里。
关于《日本书目志》的由来,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政变考〉序》中有过明确交待:
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政变之勇猛,而成效已甚著也。
这是一条关键材料,几为研究《日本书目志》者所必引用,但对其的释读却有错误。所误在于时间的判断,所谓“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向无例外被指为光绪元年即1875 年,并由此认为康氏此说有夸诬之嫌。但实际上,此处“御极之时”非指光绪帝即位之时,而应为亲政之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而“琉球被灭”,亦指是年,即1887年,而非通常以为的1875年或1879 年。正是在光绪十三年八九月间,康有为作香港之游,得识其居港的“乡人”陈焕鸣,于是有见识“日本书目”之因缘。康有为于《延香老屋诗集》中曾自记其事:
乡人陈焕鸣乞书扇,君通英文,甚才,曾为日本使馆翻译,弃官隐于港。吾读日本书□假途焉。于陈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书、派游学,因缘实自陈君来也。
由此,则《进呈〈日本明治政变考〉序》所记,与《自编年谱》(香港之游)、《延香老屋诗集》所记,相互印证,若合符契。明确康氏接触日籍的最初时间及因由,或有助于对《日本书目志》之编纂依据的判断。最初看到《日本书目志》,就由其每书标明价格而猜测其或为书商提供之书目;排比上述材料后,则以为《日本书目志》所依据者,或即陈焕鸣所提供而为康氏所惊叹的“日本书目”。王宝平教授新近研究指认《日本书目志》所根据者为明治二十六年(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出版的《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王教授考证细密,但将此《总目录》与《日本书目志》相较,终有所收书籍数量(《日本书目志》少收2398种)和编排、分类的不同;且不能确知康氏得到《总目录》的渠道。王教授文中亦指出,此《总目录》为先已存在的各家会员书肆书目的总汇,那么,在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之前,将《日本书目志》所依据的“书目”暂认为即最初得自陈焕鸣的日本书肆书目(不早于1887年),或亦可聊备一说。
二
自第二讲开始,狭间先生进入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讲授,讲述以时序为先后。
第二讲的讲题是“身为康有为的弟子”,内容主要涉及梁氏早年所受的教育和学识(尤其是康门学术对他的影响),以及戊戌年逃亡和初到日本的情况。
狭间先生将康梁之间的师徒关系分为三个时期:1890—1898年,梁为名副其实的弟子;1899—1920年,梁对与康的思想分歧保持克制,仍声称为弟子,但在清室复辟问题上,与康“产生决定性对立”;1921—1927年,恢复师生关系,但保持距离。关于这一划分,可再斟酌的是第二期,现在的划分,时间相对较长,或可考虑划成几个段落,比如以民国成立为界划为两段。但这毕竟是枝节问题,可以提出讨论的,还是第一期梁氏所受“康学”的具体内容。狭间先生似乎接受了梁启超在《三十自述》里的说法,即从康所受者为“陆王心学”和“史学、西学”。但任公这一事后的回忆,是有问题的。
首当其冲的是,所谓“陆王心学”,究竟在康学和康门教育中处于什么样位置的问题。任公在《三十自述》前一年,于《南海康先生传》中,首揭乃师“独好陆王”,正与其自述于康门所受为“陆王心学”相互为证。但在康氏众多的著述中,其实少有特意表彰陆王心学者,关于宋明理学,康氏本不以为是孔教正宗,且于其中毋宁更重朱子。就康门教授而言,查康氏《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等,以及戊戌时期梁氏的《读书分月课程》《时务学堂日程》等,皆难见“独好陆王”的所在。其他康氏及门弟子所记,如陆乃翔、陆敦骙之《南海先生传(上)》、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卢湘父《万木草堂回忆》等,也都难以落实康氏“独好陆王”和草堂以“陆王心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之说。狭间先生在讲授时曾言:“或许当时康有为已经了解到一些表彰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的事情”,只是猜测,并无根据;但这里说到的日本的“阳明学”,或许正是梁启超“陆王心学”说的由来。狭间先生曾有力作《关于梁启超称颂“王学”问题》,指出梁氏于《新民丛报》时期提倡王学,实受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日本伦理汇编》(1901)的影响;而“阳明学”在当时的日本亦是“新学”,即明治三十年代出现的“国粹”思潮的一部分。所以,可以推论的是,万木草堂和戊戌时期,康梁师徒似无从得知所谓“阳明学”推动明治维新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才得到的。而他对王学的认同和提倡,如同狭间先生所说,是在转向“国家主义”后,借鉴作为国粹主义的日本“阳明学”的结果。其提出早年受教“陆王心学”和乃师“独好陆王”的《三十自述》《南海康先生传》,正是其转向国家主义初期的作品。
其次,所谓“史学、西学”,亦当有具体的分析。在前述《长兴》《桂学》及时务学堂诸学记、课程中,“史学”都在“经学”之次,所谓“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故“经学子学尤要” ;类如后来所谓“新史学”之对于“史学”的认识,实不在草堂、戊戌时期的论议之内。至于“西学”,则更是有限,此由康氏《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中有关西学的内容及梁氏《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可知。要言之,草堂、戊戌时期,梁任公所学所述,主要为中学之经、子学,其有限的“西学”(政学、公法学)亦是通过附着于其经、子论述——如《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而得以表现,即以经学、子学附会西学、西理。由此,所谓“陆王心学”“史学、西学”,乃梁氏三十之年(1902)所看重的学问,而非草堂时期受之于康氏的课业。
虽然第二讲的主要内容是梁启超所接受的“康学”和西学,但狭间先生提示:本讲最有价值的内容在“日本支持者”一节,所用文献多不易看到。所谓“日本支持者”,指的是梁启超到达日本初期即迅速进行的“求援”活动,在日本所引起的积极回应。狭间先生所列举的文献,一是作为个人的内藤湖南在《日本人》《万朝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声援康梁变法事业及支持梁启超对变法的解说的文章;二是作为团体的“东亚同文会”通过其机关报《东亚时论》所表现出的先扬后抑的态度:《东亚时论》在其创刊号(1898年12月10日)刊登了梁启超的《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康有为的《唇齿忧》和梁启超的《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表明对康梁的支持态度;其第二号(1898 年12月25日),卷首即为谭嗣同的半身像和梁启超的题词“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象”,正文刊有康有为“哀谭京卿复生题其象”、唐才常“挽谭君联”、梁启超“亡友浏阳谭遗象赞”、梁启超的《政变始末》、逸史氏《清国殉难志士故谭嗣同君传》、任公(梁启超)的《横滨清议报叙》等,其支持、赞助康梁的立场更加鲜明。但随后“东亚同文会”出于日本与清廷关系的利益考虑,改变对康梁的态度,转而支持将康有为等逐出日本,《东亚时论》亦改变方针,自第四号以后,不再刊登康梁的文章。而梁启超也就不得不接受“受限制的逃亡者”的生活。还应说到的是,狭间先生的讲授,在展示上述有关内藤湖南、《东亚时论》的珍贵文献的同时,又特为听众图示勾勒了日本“明治时期亚洲主义团体”的分立和演变的概况,这样的知识同样十分有益。
三

关于《清议报》时期的梁启超,狭间先生选择的是康梁关系这一视角,即由梁任公欲从康氏思想笼罩下“独立”出来的挣扎和努力,以见任公思想的变化与进步。
狭间先生认为,初到日本的康、梁,在以争取日本政界支持为目的的宣传鼓动中就表现出“策略”上的细微差别。其用以说明的事例,是早期几种《谭嗣同传》之间的关系。经过仔细的比对和考索,狭间先生指出:政变后最先出的“谭嗣同传”是《亚东时报》第四号(1898 年11月15日)刊载的逸史氏(山根虎之助)的《六士传》;之后,在东京发行的报纸《日本》,于11 月27 日刊发《清国殉难六士传》,并注明是对上海《亚东时报》刊文的“摘译”;再后是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于第75册(1898 年12月23日)上刊登的《清国殉难六士传》,该传注明“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即为《日本》所刊之译文。由此,则三传实为同一文,然比对的结果是,作为康党嫡系刊物的《知新报》,所载较其他二者多出所谓谭嗣同“绝笔”一节。“绝笔”内容为谭氏临终前对康、梁的寄语,以表明死者与生者各自应分担的责任。然而此“绝笔”却是在康有为指导下所作的伪造,时间约在11 月下旬。更加微妙的是,此“绝笔”之为伪造,很快就由梁启超予以证明,其发表于《清议报》第四册(1899 年1 月22 日)的《谭嗣同传》,并无“绝笔”的内容,因而也就实际上否认了“绝笔”的真实性。但任公之《谭嗣同传》,仍用较多笔墨渲染传主与康有为及作者本人的亲密关系,这种“渲染”符合当时由康有为主导的游说活动的主旨,说明梁任公虽对乃师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仍不能违背其意志。
狭间先生对谭嗣同“烈士”形象的初塑过程作了清晰的梳理,令人信服。可以补充的是,对谭嗣同“烈士”形象的最早宣传,或应推《国闻报》。该报于谭氏被捕后二日(农历八月十二)即以“视死如归”为题,予以报道: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即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该报道似应是著名的“变法流血自嗣同始”(或亦是谭氏为康有为弟子说)的最早出处,而梁启超本人则有可能是该说的最先传布者。据北京大学杨琥教授的判断,《国闻报》“视死如归”文的作者为夏曾佑,而其消息的来源或得自梁启超。其推断的根据是,八月十一日(农历),夏氏曾与逃亡中的梁启超相见,并接受了梁氏委托当时保护他逃亡的郑永昌转交的信件;而随后在十二日的《国闻报》上就刊发了“视死如归”一文。
如果说梁任公所撰《谭嗣同传》不收康有为指示伪造的“绝笔”,表明二人间存在着“不协调”,那么《清议报》的“改编”,则被视为梁启超试图脱离康有为思想影响的最初表现。狭间先生认为,康有为被劝离开日本(1899年3月22日),为梁启超提供了思想自由的空间,受此影响,于是有《清议报》的“改编”:1899年4月10日出版的《清议报》第11册,刊发了《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改编”后的《清议报》,最大的变化是新增了“政治学谈”栏目,并即自第11 册起连载吾妻兵治所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在狭间先生看来,“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与此相应,自《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的谭嗣同《仁学》,至第14册也停止刊登。而由《仁学》刊载的一波三折透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正是狭间先生讲授的重点。
狭间先生注意到《清议报》刊载《仁学》的可怪之处:《清议报》“支那哲学”栏连载《仁学》,自第2册始刊,至第100册刊毕,为时近三年。但具体来说,第2 册至第14册(1899年1月2日至5月10日)陆续刊发全书的二分之一,然后中断;第44 册至第46册(1900年5月9日至28日)又刊登了约为全书十分之一的部分,再次停刊;剩余的部分一次性刊于《清议报》的终刊号第100册上(1901年12月21日)。狭间先生认为,《仁学》连载于第14 册后的中断,出于梁启超的决定;第44至46册的再度连载,发生在麦孟华等人担当编辑的时候,而其再次中断,最大的可能也是应时在夏威夷的梁启超的要求,所以在考虑连载中断的原因时,不必另作讨论,可以忽略不计。而问题也就可以简化为:为什么《仁学》在连载四个多月后一度中断,时隔两年半才再次把剩余的部分一次性全部发表?
其根本原因,在狭间先生看来,正如前所述,是梁启超思想发生了由世界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使其与乃师拉开距离,也影响了以世界主义为基调的《仁学》的连载。用以说明的材料,其一是《清议报》第2册所载梁撰《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中,原有谭氏“服膺南海之学”,其《仁学》之作“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等字句,在三年后(1902)的《清议报全编》中,尽被删去,或表示康梁关系的变化;其二是1900年4月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亦即《清议报》二度连载《仁学》前十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对《仁学》的评价为:“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所谓“近今西哲之真理”,当即梁氏此时信奉的“国家主义”。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01年10月(约《清议报》刊毕《仁学》前两个月)国民报社刊行的《仁学》单行本。此单行本刊行前,曾于《清议报》第85 册(1901年7月16 日)登载广告,并称其“寄售处在横滨《清议报》馆”,而该单行本所附《谭嗣同传》,亦显然是《清议报》所载梁撰《谭嗣同传》的删减版,故狭间先生似同意汤志钧先生的意见,以为此单行本的发行实为梁启超所为。而狭间先生的进一步研究包括:
第一,推测署名“四合主人”的《仁学》发行广告(《清议报》第85册)的作者,也可能是梁启超(至少该广告反映的思想与梁氏一致)。因为该广告通过对《仁学》充分吸收泰西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成果的高度肯定,把《仁学》从此前梁撰《〈仁学〉序》和《谭嗣同传》所谓之“康学”附属物这一定位中解放了出来;而把谭嗣同从康有为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正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开始独立于康有为的结果。该广告还一改梁氏《谭嗣同传》所谓《仁学》原稿藏于梁处的说法,声称另有来源(单行本恢复了此前《清议报》连载时有意刊落的部分),似乎在故意撇清与梁启超的瓜葛。而与此相应,就有——
第二,梁启超对《谭嗣同传》的修改。单行本所附《谭嗣同传》有意删去了《清议报》载梁氏《谭嗣同传》中有关康梁与谭氏关系的所有段落,并将原传中梁氏所谓谭氏遗著“皆藏于余处”的说法,改为“君死后皆散逸”。凡此,其用意皆在与“广告”保持一致:既脱去先前加于《仁学》上的康学外衣,又将梁启超本人置之事外,这或许正是梁启超于思想上(仅限于思想)与康有为“诀别”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后来在《新民丛报》刊登的《仁学》单行本广告,标明“横滨《清议报》馆印,东京《国民报》社再印”,任公所作“内介绍”,特别突出谭浏阳的“至诚”精神,这些似乎都在交代《仁学》国民报社单行本的由来。狭间先生以为,梁启超之所以策划《仁学》单行本的印行,也是基于“诚”的心意。
最后再来说《清议报》第100册一次刊完《仁学》剩余部分的问题。在狭间先生看来,在细心完成了《仁学》单行本的出版之后,梁启超决定在《清议报》终刊号上完成《仁学》的刊载,就更多地带有总结《清议报》并保持其前后一致的用意。梁任公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列举其曾登载的重要文章,《仁学》列为第一;而就任公本人而言,刊毕《仁学》,亦算部分兑现了对故友的“程婴、杵臼”生死分任的承诺。
其实,《清议报》时期的康梁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能够揭示出“康梁关系演变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围绕谭嗣同的纠葛”,确需有洞幽烛微的功力。狭间先生通过层层剖析围绕《谭嗣同传》撰述和《仁学》刊布的种种纠葛,为我们展示了《清议报》时期康梁关系之细致、生动而又复杂的面貌,堪称力作。狭间先生曾说,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费时最长,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后,极为高兴。言谈中饱含对研究工作甘苦的深切体味。
虽然,有关《仁学》单行本的问题,我仍有未解的疑惑。当时只是一些有待核实的想法,没有当面请教,现在借机写在这里,以求教于先生。
首先,《仁学》单行本刊行前后,所谓改良与革命的阵营分野尚处于“过渡”时期,两派之间并无森严的界限,梁任公本人就依违其间,左右逢源。因此,当时一些原属康门的激进青年学生,即借助《清议报》的影响和发行渠道,从事着革命鼓吹。郑贯一等人办《开智录》如此,秦力山等人办《国民报》亦是如此。所以就有:《清议报》自第70册(1901年2月19日)迄第80册(1901年5月28日)连续刊登《国民报告白》,预告其出版宗旨及征订事;《国民报》6月10日出版第一期,《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至第85册(1901年7月16日)“本馆发售及代售各书报价目”栏中,《国民报》已赫然在列;《清议报》第85册还刊有前文所谓“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的广告。但这里想说明的是,尽管《清议报》与《国民报》有如此多的关联,也不能仅凭此即断言,《仁学》单行本是双方合作或梁任公本人借助《国民报》的结果。就当时的情况言,以秦力山为首的《国民报》中人,与康梁等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离多于即的关系,他们与《清议报》的关系,如同《开智录》,更多的是利用而非合作。
其次, 继《清议报》第85册之后,《国民报》第四期(1901年8月10日)亦刊载“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的广告。较之前者,《国民报》广告有个别字句的修改,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删去了“寄售处在横滨《清议报》馆”一句,似欲割断《仁学》单行本与《清议报》的关联。若循此思路推测,则两则广告之间或《国民报》第四期之前,或有影响两报关系的事件发生。
再次,《国民报》第三期(1901年7月10日)连载的《中国灭亡论》(秦力山)中,有“夭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作天涯沦落客”语,被认为是讥讽梁启超的“名句”,而《国民报》第四期,则于“来文”栏刊发章太炎《正仇满论》,指名批评梁启超《积弱溯源论》中为清廷辩护的言论。该文后有“本社附志”,云:
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先以驳斥一人之言,与本报成例微有不合,原拟不登。继观撰者持论至公,悉中于理,且并非驳击梁君一人,所关亦极大矣。急付梨枣,以饷国民。使大义晓然于天下,还以质之梁君可也。
上文显示的是不惜与梁氏决裂的态度。由此,再与秦力山等人为“自立军”失败找梁启超“算帐”一事相联系,则很可能在约七月间,《清议报》与《国民报》中人有过激烈冲突,并导致双方的分手。
第四,依上述推测,则《仁学》单行本(《国民报》社本)所附《谭嗣同传》,完全删去有关康梁的内容,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其他各类不同版本的梁启超著《谭嗣同传》,均同于《清议报》本,即均未对有关康梁的内容作出修改,也就可以有顺理成章的解释:《国民报》社本谭传,本非梁任公所为。《国民报》社本《仁学》所附《谭嗣同传》,在删去康梁的同时,也删去了有关袁世凯的内容,其原因尚没有合理的解释;但在其之后的《清议报全编》本《谭嗣同传》,有两处修订却耐人寻味:一是于“至初五日,袁复召见”后,加“闻亦奉有密诏云”一句;二是于列举谭氏遗著时,于“《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后,增加“《剳记》一卷”。前者意在加强对袁氏的叙述,后者则新增了藏于梁启超处的谭氏遗著的种类,这些为数不多的修改,似皆为针对《仁学》单行本《谭嗣同传》的回应。
最后,说到《仁学》在《清议报》上刊而停、停而刊的几度反复,其原因仍不离梁任公对《仁学》的评价,“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所谓“荡决甚矣”,应指下篇那些激烈批判传统纲常伦理和揭露清朝残暴统治的言辞,亦即康有为禁止《清议报》刊登的那类内容;而所谓“近今西哲之真理”,则如前述,应为“国家思想”,亦即其时梁启超新服膺和宣传的“主义”。所以,《仁学》的第一次停刊(上篇接近刊完),可以是康梁“合谋”的结果:既满足康氏的要求,又符合任公的新认识;第二次停刊,则可能更多来自康氏的干涉,因为所刊发者多为“荡决”的内容;而最终的一次性刊毕,虽然可能有《国民报》本的刺激,但主要原因还是如狭间先生所说,乃是梁启超于思想上与康有为“诀别”的一种宣示:不再在“荡决”类问题上向乃师妥协。而对于与国家思想相对立的“世界主义”的批评,则见于发表于同期《清议报》上的《南海康先生传》。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