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
“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 原创 柏琳 x 凯尔曼尼 单读
担任德国总理长达 16 年之久的默克尔即将卸任,她执政期间,经历了全世界民粹主义兴起、难民涌入国门、欧洲一体化受阻……她总是要做平衡各方需求的那个人,德国利益和欧盟利益,民族情绪和国际道义等等,新冠疫情和极端天气的冲击,无疑又带来了新挑战。面临经济衰退和各类危机的德国,在默克尔卸任后,还能不断地反思自我,继续向世界敞开怀抱吗?
今天单读重温一篇柏琳对伊朗裔德国学者凯尔曼尼的访谈。他此前来中国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德国性、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在德国的文学史中,就有关心外部世界且批判看待自己的眼光,他肯定了德国的难民政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改变,面对甚嚣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时,一再强调文化差异、交融的重要性。但转眼两年过去,世界经历了漫长的隔离期,默克尔也将告别政坛,不知道他对德国的判断、对世界的期待是否依然?

纳韦德·凯尔曼尼:
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让文化枯萎
采访、撰文:柏琳
访谈伊朗裔的德国作家纳韦德·凯尔曼尼,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难消化的工作。不仅因为这位东方学出身的教授由于同时精通东西方文化而喜欢在谈话中旁征博引,也因为他飞快的语速丝毫不影响他在阐述某个观点时灵活切换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更因为他新近写成的纪实随笔作品《沿壕沟而行》(Entlang den Gräben)是一本地理、历史和文化密度颇为紧实的书。这位信奉世界主义理想的移民作家,其言谈举止辐射出广阔的视野和多层次的文化关怀,不禁让人对他笔下的世界图景生出强烈的好奇。
必须一提的是,面对这本厚重且包含诸多冷僻名词的纪实作品,该书译者出现了几处地名的错译,此外,本书的德语原著标题是“Entlang den Gräben”,译者混淆了 Gräben 和 Gräbern ,造成了书名的偏差。这里的 Gräben 是 Graben 的复数,是“壕沟”之意,而非德语 Grab 的第三格复数 Gräbern(坟墓),所以这本书真正的中文书名为《沿壕沟而行》。面对这起翻译事故,作家选择温和地接受出版方和译者的道歉,同时坚定地要求对读者进行更正。我私下里曾简单问过凯尔曼尼关于翻译错误的看法,作家温柔地说,“错误既然已经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态度是思考如何改正它。”

不过,错过这本书会是一种遗憾。光是读完他从东欧大地行至伊朗的 54 天旅程记录,就让我重新学习了一遍区域史——今日亚欧大陆重新出现的壕沟,被重燃的战火与灾祸撕裂的危机地带。在这样一条歪歪斜斜的地理线上,国与国的边界变得模糊,人们的生活遭受着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渗透,又不得不面对曾经大屠杀、民族驱逐、核污染以及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糟心历史,生活当然还要继续,可是生活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12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凯尔曼尼讲述了各自的辛酸过往和依然一片迷茫的未来愿景。作为一个记录者,凯尔曼尼沿途经历了无数次价值观的破碎和重组,在沮丧和喜悦来回交替之间,他似乎更为坚定地捍卫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所相信的某种价值观。他相信“欧洲精神”,秉持欧洲社会应该庇护难民、提供人道空间的开放信念,他强烈反对民族主义,渴望人为的边界有一天能够敞开,因为这边界封锁的已经不单是移民和难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它们更致命地封锁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封锁了关于未来的可能性,给边界两端的民族徒留世代无法治愈的伤痕。
不单是冲突再起的叙利亚危机才让我们的视线又转向那块苦难地带,事实上和平从未真正降临过这个世界。从德国东部绵延至波兰,跨越波罗的海,穿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入克里米亚,路过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带盘旋,最后抵达伊朗古城伊斯法罕,凯尔曼尼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亚欧大陆所有躁动不安的现代壕沟。他目睹了沙皇时代的犹太人聚居区如今的萧条,二战的“血染之国”未愈的怆痛,也在乌克兰的顿巴斯前线亲眼见证了分裂分子和民族分子互相仇恨却不时流露出的对往昔和平记忆的伤感,他走到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停火线上,看见这里的封锁线冷漠如冰封地带……
在 54 天的行程中,凯尔曼尼多次身处多种族和多宗教混居之地,无论是世界主义气息浓郁的城市敖德萨,还是 50 多个民族在一起生活的面积不比德国大多少的高加索地区,或者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同时将其看作自己首都的维尔纽斯,在这个极端民族主义叫嚣的时代,一再出现和将要出现的残暴表态让人们失去了多元共存的权利,更糟糕的是,失去了共存的理想。仇恨之轮愈转愈快,甚至到了让记录者语塞的地步。作为一个笃信“欧洲魅力”的知识分子,凯尔曼尼一路上激情而又几近无力地为他的理想辩解:“欧洲”是一个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的本质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让不同的、本真的东西和平共处、互通、混合。每个人都可以归属一个精神世界,不论他是生活在大河的哪一边。
然而现实的残酷性让凯尔曼尼在论述他的理想时,带上了一丝不确定的迟疑。在对话中,当我问到因为如今欧洲的难民潮和福利危机的失控,许多真诚的自由派不得不重新思考本国利益,他们是否感到尴尬时,凯尔曼尼只能数次用“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的解释来做着某种回避。但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了,毕竟,他把自己看做一个纯粹的作家,而非政治家——媒体的宣传居然把他贴上了“总理候选人”的标签——凯尔曼尼对此显得十分无奈,他说一直以来自己都在避免对公众提出过多意见。

纳韦德·凯尔曼尼(Navid Kermani),伊朗裔德国记者、散文家、游记作家和东方学家,图片由歌德学院提供。
可是凯尔曼尼“逃避”的不只是“现实”,他还“逃避”另外一些问题。在我对他狂轰滥炸时,他很“自然”地躲闪了所有关于“自我身份”的问题。作为一个移民后代,凯尔曼尼经常因为他的伊朗背景而受到关注,他非常讨厌这种标签,认为自己被当做了某种弱势群体,而他拒绝被怜悯,也从不接受“移民作家”为由头的各种邀请。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迫要回答这些问题——这多少有些讽刺——在《沿壕沟而行》中,凯尔曼尼数次讲到,一个地方不该否定自己的历史,而一个人也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然而,访谈结束后我仔细想了想,凯尔曼尼为什么这么抗拒谈论他的身份呢?究竟是什么让他感到乏味?当我看完第二遍书时,隐约有了某种答案:在他时时生活和行走的那片多元文化带上,几乎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不纯粹的,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反复谈论这种“自我”,我们要做的,也许是把这种身份当做自然携带的精神密码,以便进入到一个可期的世界主义世界中。
我们所有人都不是桥梁,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
单读:作为一个伊朗裔的德国知识分子,你的身份本身就有东方和西方交融的特质,这是推动你促进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对话的某种动机吗?
凯尔曼尼:完全不是。促进东西方对话并非我写作的本意,而只是一个自然结果。如果我说,一件事物必须和另一件事物对话,这显然很荒谬。我的书架上摆满了东方和西方的书籍,就像一座普通的图书馆,所有书都按照作家姓氏排序,而不是按照宗教类别,它们没有东西之分。如果我只写关于西方的东西,反倒是不正常的。从小到大,我在家说波斯语,在公共场合说德语,一切都很自然,直到成人后别人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原来是一种特殊背景。但实际上我并不独特,世界上有许多作家都是如此。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以双语去思考和写作也并不困难。
曾经我是一个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大学里学的是东方学,原本可以走上学术道路,但我发现这样的话我的思维就会局限在东方学研究里,但同时我又对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学经典、摇滚乐等都感兴趣,我再一次问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想做东西方对话的桥梁吗?不,太肤浅了,这不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不会坐在那里空想“今天要研究一下基督教文学和伊斯兰文学的关系”,我可能会想,有一本书,我想起来可能与什么有关,就立刻拿来读,这样就开始了。我不会做“东西方文化的对话”这样宏大的议题。一个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或者一个信伊斯兰教的德国人,应该有怎样的立场?我不知道,因为世界文学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所有人都不是桥梁,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应该停止自满,通过自我去观照他人,保持好奇心。
单读:虽然你认为自己的双语文化环境并不特殊,但你也承认长大后别人会问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你的回答是怎样的?
凯尔曼尼:好吧,年幼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就好比热恋中的人不会反复讨论彼此的关系,而是享受这种关系。但成年后当我遭遇这样的问题,我就必须去思考了。我记得自己早年的书出版时,书店常常因为我的名字而想当然地把我的书归入波斯文学的书架,我不得不到处对书店老板说,“搞错了,搞错了!”但这些年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德国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父母都来自其他国度。人们越来越理解,德国人不意味着必须金发碧眼。对我来说,从源头上就不存在身份认同问题。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27.10.16—2015.04.13),父亲来自德意志,母亲是波兰人
其实我还不只是有双重文化身份,我更享受作为一个“外来人”的角色。在西方,当你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可能会很负面,但正是这样一个外来者身份可以带给你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比如我写关于基督教绘画的书,就能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看它,这让我的话语更强有力,但事实上我对基督教的作品并不陌生,我毕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我被“异文化”身份支撑着,说德语时,脑海里有波斯语在回响,只说德语的人不会有这优势。
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反文化的,
甚至让文化枯萎
单读:你带着“异文化”的身份在 2016 年踏上了从东欧至伊朗的旅行,《沿壕沟而行》正是你在这条当今欧洲重现的壕沟跋涉的纪实随笔。在你去过的 12 个国家和地区,遭遇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新民族主义的蔓延,从波兰到乌克兰再到伊朗,无一幸免。你对此有激烈批评,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观点:你认为民族主义导致了文化的贫瘠。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恰有一点是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无论是多么少的少数群体。当然这观点部分受到了赫尔德的民族观的影响,对此你如何理解?
凯尔曼尼:如果我们回望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之前的前现代世界,我们会看见,非常“民族”的现象就是文化的混合,当时似乎没有别的路径。当然这种文化混合图景并未带来更多和平,依然有数不清的战争和野蛮行径,那并不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但在那个时代里,各种文化都发生了交换,而这带来了惊人的影响。
举个例子,现代欧洲文学传统有两个来源:小说和诗歌。二者都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果。欧洲的诗歌来源于伊斯兰文化中的宫廷情诗,当时西班牙正处于安达卢西亚时期,阿拉伯人统治着西班牙人,伊斯兰文化对其造成了巨大影响。发端于这个时期的宫廷情诗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成为了欧洲诗歌的滥觞。同样,现代小说是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影响下才产生的,这本小说的名字和部分内容包装得好像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似的,这体现了塞万提斯的某种观念——小说这种文体,是从欧洲以外的文化中来的。
讲述民族主义之前,需要先说一说“文化”。文化如何形成?文化就是——一方面从周围邻居那儿“借走东西”,一方面又因为借了东西,就说自己与众不同。我们看但丁的《神曲》,作为欧洲文学的某种开创性巨著,结构上借用了阿拉伯文化中“九重旅行”的灵感,同时由于《神曲》是为了谴责中世纪的蒙昧和教会的腐败,因而但丁又创造了一种与阿拉伯文化相对应的、在基督教文化内部产生的“配对物”,《神曲》终结于《天堂》。这种方式,就是某种文化产生与交融的典型例证。
当一种文化繁荣时,会像流水一样流向四邦,可是当这种文化失去生命力时,它就会干涸,然后恐惧,更加迫切需要留下已有的东西,于是极端分子就会叫嚣:不要受其他因素干扰,不要不纯粹。
单读:从这个角度看,极端民族主义可能产生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恐惧心理,他们没有自己说得那么有理。
凯尔曼尼:极端民族主义者缺乏安全感,首先是因为无知。这些人恐惧失去自我,拒绝通过内省来质疑这个“自我”为何物。他们通常缺乏鲜明的个性,因此更害怕被外部文化吞噬。比如本·拉登这个人,他的意识和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受到西化和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原教旨意义上的伊斯兰世界,可他因为无知,还是要故意蓄起长胡子,穿上非常穆斯林的袍子,说起非常伊斯兰的话语,把自己打扮得就像嘉年华狂欢节上的某个角色。

“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在阿富汗山村营地
原教旨主义产生于一个已经被铺天盖地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所冲撞的世界,原教旨意义上的传统已经摇摇欲坠。现代世界让原教旨主义者丧失自信,他们害怕自己的文化被吞噬,在此意义上极端民族主义得到强化。极端分子们渴望回归“本源”意义上的传统,然而,真正的传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度,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原教旨主义者否定文化在诞生后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批判真正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已经停滞的东西,原教旨主义是反文化的。事情的真相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足够了解和自信,你根本不会惧怕和仇视外来影响,你反而愿意去包容和学习。比如,我是一个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我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弥撒仪式完全没有意见。
单读:那么从何种角度说,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导致文化变得贫瘠呢?
凯尔曼尼:现代有些民族国家,用暴力方式形成民族集体。在这些土地上,百年以前有多种语言和文化共存,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可能只讲俄语或英语,越来越封闭。十九世纪末和 1990 年代后流行的现代民族主义想法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即要保证单一种族和单一语言的纯粹,而这和社会的自然状态完全不同。比如在克里米亚半岛有这么多民族:希腊人、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还有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他们说着各种语言,不存在所谓的单一文化。可是现代民族主义理念要否定这些,消灭这些,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反文化的,甚至让文化枯萎。
现在全球政治的危险在于
大家都在纷纷响应民粹化趋势
单读:你在 2015 年德国书业和平奖的获奖演讲“Beyond the Borders – Jacques Mourad and Love in Syria”中叙述了一个故事:在叙利亚的某个基督教社区,人们热爱穆斯林,在那个社群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可以相爱的。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曾经的南斯拉夫,那个国家也有过历史上多个种族多种宗教和平共处的记忆。现代民族主义观念摧毁了这些场景。那个著名的理论——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全球未来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主要是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之间,对此你怎么看?
凯尔曼尼: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的确很多国家正在倒退,极端民族主义正在兴起。我觉得现在全球政治的危险就在于大家都在纷纷响应这种民粹化趋势。9·11 事件,是本·拉登打着伊斯兰文化极端主义的名义向西方发起的进攻,当时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出兵,也都是把战争宣传成了西方世界向伊斯兰世界的“圣战”,在这样一种民粹主义的历史倒退中,许多政客也以“文明冲突论”的名义来发动新的战争。
然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带来冲突的同时更会促进文化的繁荣。现在的问题是,某些民族文化把精力都放在差异上,却忽视了与邻居的相同之处。在今天所谓的“只有一个德国”“只有一个法国”等语境下产生了一些变异因子。有时候我必须和某些右翼德国民粹分子争论,他们发现我不是一个完全不懂德国文化的“局外人”,我研究歌德和荷尔德林,他们无法指责我不懂德国文化。他们总是在叫嚣着要崇拜歌德,我们看看歌德都干了什么?歌德为了阅读《古兰经》而去学习阿拉伯语,他还翻译波斯诗歌,歌德正是那个呼吁“世界文学”的人,歌德赋予了“德国性”以世界主义的气质,并且对于单一的“德国性”以尖锐的批评。可是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在干吗?他们说,歌德,我们的文化英雄,一生的文化成就在于肯定了“德国的民族性”!真是太讽刺了。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重要文学成果,通过描写进步青年身处一个鄙陋的德国社会的体验和感受,反映歌德自身对所生活时代的揭露与反抗
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文学,
那它就离灭亡不远了
单读:德国性,是让德国知识分子痴迷的一个概念。荷尔德林、歌德、尼采、托马斯·曼,直至当代德国著名学者沃尔夫·佩勒尼斯、克劳斯·费舍尔等等,都试图从各个角度阐述这个概念(虽然有的人是无意识的),你对“德国性”也有自己的理解,你认为卡夫卡是你心中“最德国”的作家,可否具体解释?
凯尔曼尼:如果要我选择心目中最能体现德国文学特质的作家,我会说是卡夫卡,这个非德国人的德语作家。他拥有多重身份,作为公民,他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后来属于捷克共和国。作为捷克人,他和布拉格所有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都算是德国人。作为布拉格的德国人,他又首先被认为是犹太人,甚至卡夫卡本人也无法说清自己的身份,他是自己母语的外来者。卡夫卡对德国依恋很少,这在他的日记中很明显。例如,一战爆发当天,他只写了两句话,“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德国的政治状况并未引起他的特别关注。
说远一点,德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思考德国以外的问题。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哲学家和作家,无论是歌德还是康德,都把目光投向欧洲的统一,而非德国本国。启蒙运动在德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国家计划,而是一项欧洲计划。在文学中的理想主角,往往借鉴了荷马、莎士比亚和拜伦的灵感。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在他 1825 年关于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特殊性的文章中,用的标题是“德国文学的欧洲状况概述”:“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是欧洲文化的大都会”。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年9月8日—1845年5月12日),德国诗人、翻译家及批评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成为德语经典著作。
许多伟大的德国人都是反对“德国性”的(最德国),这让他们免于任何德国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自我荣耀和拥有文化领导权的傲慢妄想。很少有人能比尼采更严厉地蔑视德国:“每当我描绘一个违背我所有直觉的人时,他总会变成德国人”。对德国性的批评和拒绝,是德国文学史上的主旨,这种民族自我批评具有无法比拟的苛刻和彻底。德国应该为这些不以德国为荣的人感到自豪。
总之,我理解的德国性,作为一种文化特征,和“最德国”并不对应,德国性是这样的价值观:沉思,自我批评,对个人的尊重,善良,慷慨,自由,开放。欧洲的思想和人文主义的主题都深藏其中。歌德的世界主义与纳粹意识形态大相径庭。我发现自己最接近德语文学的时刻,恰恰是我和德国相距最远的时刻。
单读:让我们谈谈另一个伟大的德国人,托马斯·曼,他从一个认同德国民族主义的人转变为一个拥护共和思想的人,这种转变被当代杰出的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一书中做了精微表述。事实上,托马斯·曼在转变中,依然怀疑德国秉性和民主是不相容的,他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和歌德、康德似乎相反,你怎么看?
凯尔曼尼:的确,托马斯·曼的作品《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作为早年作品,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但后来他又大幅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从一个支持德国民族主义的作家变成了世界主义者,甚至为此踏上了流亡美国的道路——恰恰是这个写出充满民族主义气息作品的人,成为批评希特勒最为猛烈的那个人。而且,《反思》这本作品一直被他看做痛苦而真诚地接受共和思想和民主信条的必要步骤。晚年的托马斯·曼在美国的种种表现正好说明,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因为批判性地理解自己的民族,是德国的文学(文化)传统。
单读:但是托马斯·曼在流亡美国后,似乎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文化的同质化趋势。从文化角度看,你如何理解全球化?
凯尔曼尼:是的,托马斯·曼在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意识到未来的问题可能不是某些文化过于强大,而是各种文化已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益趋同。从浅层上看,在资本裹挟下,全世界的人都去同样的商业中心消费,所有人都过着类似的市民生活,全世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一致。从深层看,我们发现人们的价值观也正在趋同,甚至连文学也在同质化。所有人都在写长篇小说,当然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但如果因此文学的许多其他题材就此消失,也是一种损失。
当然,也许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不想对此抱怨什么,但如果一切都整齐划一,世界上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文学,那它就离灭亡不远了。在音乐中,人们如今还尝试将不同的声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旋律,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五星级酒店的电梯里所听到的乐曲。如果所有文化趋于统一,那正暗示着文化的灭亡。我们如果有乌托邦式的愿景,并不是将所有文化合而为一,而是要让不同的文化和平共处。

根据托马斯·曼作品改编的电影《魂断威尼斯》剧照
人们创造共同的政治体制,
是为了维护差异的存在
单读:这种让不同文化和平共处的愿景,似乎就是你所信奉的“欧洲价值”,《沿壕沟而行》这本书里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在于,你一直对着这条路线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问他们是否相信“欧洲价值”,但同时也引入不同声音来质疑“欧洲精神”。你能否具体谈谈你心中的“欧洲精神”是什么?
凯尔曼尼:欧洲价值,并非要消除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而是要消除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欧洲的特点,在我看来,正是在于它并不追求文化的统一。欧洲没有统一的语言,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一切话语都要被翻译成23种语言,这是不可思议的。美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它有统一的语言,有文化熔炉的趋势,但欧洲从来就不是这样的文化熔炉。
所谓欧洲精神,是指某种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精神延续——人们努力在政治上消除分歧,从而让差异存在于文化中。也就是说,人们创造共同的政治体制,不是为了统一一切,而是为了维护差异的存在。当然,欧洲人也知道差异是危险的,会导致冲突,所以人们创造政治体制来保护这种差异。也就是说,人们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让欧洲国家一体化,使得它们彼此依存,这种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致国与国之间无法开战。但在文化上,欧洲各国并不会像美国的各个联邦州那样毫无差别,它们原本的自我身份认同依然存在于多元的文化框架中。

比利时首都、最大的城市布鲁塞尔,同时是欧盟总部所在地
单读:但这种“欧洲精神”在许多具体实例中被证明是虚弱甚至虚伪的,比如对待东欧的问题、处理南斯拉夫内战中萨拉热窝围城战的方式,欧洲的袖手旁观让波黑的穆斯林陷入绝望,最后寄希望于美国来拯救。你如何看待“欧洲精神”的虚伪和虚弱?
凯尔曼尼:是啊,我们一再发现“欧洲精神”在现实中常常行不通。你肯定也听说过“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革命,那时许多人希望得到欧洲的援助,但这一支持却迟迟不出现。恰恰相反,在突尼斯发起革命时,法国总统非但没有站在民众这边,反倒试图向突尼斯独裁者出售武器。叙利亚民众希望走上街头以和平方式得到自由,希望得到欧洲支持时,却遭到了遗弃。这些真实案例都说明欧洲的现实很残酷。
但如果将七十年前的欧洲和今天的欧洲作对比,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片战火从未停止超过十五年的土地,如今迎来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生活富足,法制稳定。我今年 51 岁,现在德法之间的学生交流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在我上学的八十年代,德国学生很难在法国找到接待家庭。因为父母和祖父母一代经常说:“德国人决不能进我们家门。”德法之间存在过深仇大恨,几乎就是世仇。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但如果我现在和一个德国或法国年轻人讲起这些,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欧洲做到了化敌为友。在我看来,这也是欧洲的一大成功。
单读:存在一个悖论——在欧洲(以及德国),当自由派经历了难民潮的冲击后,许多人对后民族主义国家的乌托邦理想产生动摇,他们不可避免要思考本国的民族利益,讨论配额、限制、遣返、德国失业率等问题,而这似乎和右翼有所关联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自由派的窘境?
凯尔曼尼:首先,成千上万的难民,因革命失败、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进攻等种种原因被迫逃离,但他们都选择了逃往欧洲,即便遭到遣返,即便每年有数千人在地中海丧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显然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欧洲,而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普京。

2016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获奖作品《海上火焰》,讲述欧洲属地兰佩杜萨岛岛民与乘船穿越地中海,来此避难的非洲、中东难民之间的故事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难民问题已经让德国乱成一锅粥,但实际上德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德国没有内战。2015 年,当时确实有一百万难民入境德国,我觉得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德国这么做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德国并不反对开放边境。
当时难民进入欧洲(德国),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联合国在难民营发放的食物只有承诺的一半,对于许多难民来说,离开难民营进入德国乃至去到欧洲,就成为必须的选择。从个人角度说,我本来就是移民的儿子,如果当年德国没有向我的父母打开边界,我活下来的机会都很渺茫。我的父母两边在伊朗大概都有四个兄弟姐妹,经过了伊朗的两次革命、两伊战争和后来政权的更迭后,他们被投入监狱或者直接死去的几率很大,和他们相比,我现在在自由安全的社会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真的非常幸运,这要归功于德国当年对我的父母打开了边境。所以,看到许多国家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方式,关闭边境不让移民进来,这些国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损失未来的生产力,同时也在损失未来的可能性。在过去的 70 年中,德国取得了很大成就。70 年前我们可能说德国是世界上最被人憎恨的国家之一,如今虽不能说是被人爱戴,但至少现在的德国在世界上是受到尊敬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虽然自由派在面对难民和移民问题时会有两难的窘境,但我觉得开放边境依然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只是从政治角度考量,我们应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不过,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意见过多的世界,我们缺失的可能不是意见,而是真正的信息。如果我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也只能从作家的角度来谈个人的观察,而所有的观察都需要建立在了解真实信息的基础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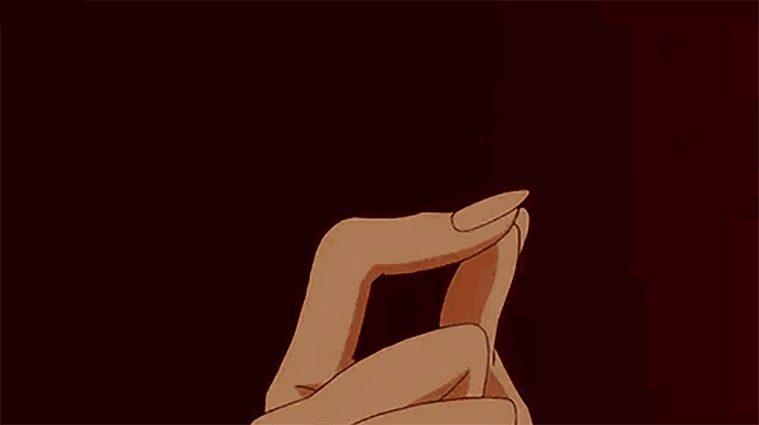
原标题:《“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