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年|铃木将久:丸尾常喜和日本的鲁迅研究

《明暗之间:鲁迅传》,[日]丸尾常喜著,陈青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9月出版,280页,69.00元
回忆丸尾常喜老师,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笔记本。丸尾老师有好几本笔记本,它们既是他研究的工具,又是他写作的源泉。笔记本里包罗万象,犹如鲁迅研究的珍宝库:鲁迅的原文、重要词汇的注释、日文的翻译、参考资料和他人研究中有价值的论述、丸尾老师自己的思考,等等。连日累岁,丸尾老师的笔记积微成著。
实际上,笔记本正是丸尾老师鲁迅研究的缩影。一笔一画地手写的笔记,自然有局限,既是抄写,便难免有错漏,但优点也鲜明,所录文字可以深入身体,身体的抄写行为让抄写者深刻领会文字的含义,而不致产生浅薄的理解,进而唤起精神深处的思考。丸尾老师非常关注鲁迅文本中的关键词,他枚举鲁迅在不同语境使用一个词的例子,归纳鲁迅赋予其的特殊意义,力求尽可能全面地把握词意。身处电脑时代的我们,只要轻敲键盘,便能即刻寻得某词在《鲁迅全集》中的所有用例。相比之下,丸尾老师的做法既费力,又未必能得其全。但由于对具体用例往往洞幽烛微,他解说鲁迅文本时总能鞭辟入里。

鲁迅(1881.9.25-1936.10.19)
丸尾老师特别重视文本细节,尤重汉语语法,比如虚字。他常看《现代汉语八百词》这样的工具书,也遍览相关论文。他之所以强调虚字的作用,当然不为研究语法,而是因为他认为虚字是连通整个文章脉络的关节,反过来说,掌握整个文章的脉络,才能准确理解虚字。我记得丸尾老师曾花一个多小时向我们解释鲁迅文本中“还”字的意义,如今我已记不清他讲的是哪一个“还”,但查阅他翻译的《阿Q正传》,就能发现他对这个字的深思熟虑。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叙述者考证了阿Q模糊的身份和名字后,说了一句:“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对这句话,丸尾老师这么翻译:“私がいささか自ら慰める点があるのは、のこる「阿」の字だけは、きわめて正確……”他把“还”译成“のこる”,意为“剩下”。按字典解释,“还”字在这里可能表示“补充说明”,即除了前面提及的几种情况以外,补充说“阿”字非常正确。但丸尾老师特意译作“剩下”,估计是为突出强调在“还”之前,已经论及各个方面,仅余下一个词缀“阿”可说。换言之,这个“还”字表示前后文之间的一种抑的语气。由此可见,丸尾老师的理解是建立在对《阿Q正传》第一章的整体结构和基调的体认之上的。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这样的虚字可能并不构成问题,但丸尾老师却会炼虚字,借此体会鲁迅小说的脉动。
在丸尾老师看来,文本细节是进入鲁迅文学整体的绝好入口,有时借助细节,我们甚至可以直抵鲁迅文学的核心。丸尾老师曾撰文讨论《狂人日记》结尾。在小说末句“救救孩子”之前有一句:“难见真的人!”以往日语翻译大都把这句话理解为“很难见到真的人”或“很难找见真的人”,但丸尾老师主张应解作“见不得真的人”,即对“真的人”感到羞愧。他引用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大量例子,说明“难见”的语义。但更重要的是,他从这句话出发考察鲁迅的文学观念,整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前后的思想活动,论述其思想里的“耻辱”感。丸尾老师主张,《狂人日记》的这句话体现了小说的主题:叙述者“我”发现自己或许在无意中也吃过人,感到莫大的耻辱,无颜面对“真的人”。概言之,由细微处思考鲁迅文学和思想的大问题,是丸尾老师研究的一大特点。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自己的思考轨迹:不仅有涉及语法的参考材料,还有关乎鲁迅文学精神的札记,这些笔记给了他构思论文的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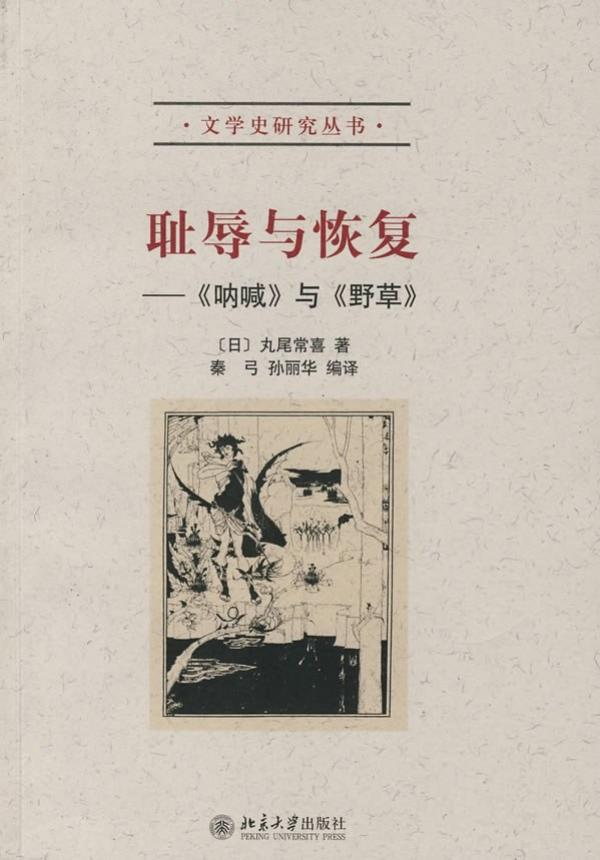
丸尾常喜著《耻辱与恢复》
丸尾老师的笔记本还展示了一项他特别重视的活动:翻译。可以说,他的研究态度集中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中。诚然,他以注重细节著称,他却不会逐字逐句、一字不差地把中文翻译为日文,他的译文反而更偏重在整体上表现鲁迅原文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否定直译,但这也不等于一味追求意译。丸尾老师依然强调鲁迅作品细节的重要性,只不过他认为只有全面厘清整个文脉,才能准确无误地理解细节。我们在丸尾老师的笔记本上可以看到他不断追求更好译文的痕迹。
从细节入手探究鲁迅文学精神的研究态度,并不是丸尾老师的独创,一定程度上,这是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家宝。丸尾老师自东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前往大阪,师从增田涉先生。增田涉先生在1930年代来到上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每天访问鲁迅先生,一字一句地请鲁迅先生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他事后回忆:“两人并坐在书桌边,我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他给予指教,关于字句、内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彻底地询问,他的答复,在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单的,在内容方面,就要加以种种说明……”(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我们不妨说,丸尾老师从增田涉先生请益鲁迅先生的方法中获得启发,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比增田涉先生年轻一代的学者,二战后在东京组织了“鲁迅研究会”,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细读文本。翻阅研究会同人出版的《鲁迅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当年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会读”。所谓“会读”,即每次指定一个文本,同人一起会面阅读。每次“会读”有一人负责,事后撰写记录文章,发表于《鲁迅研究》。文章综合“会读”结果,翻译原文,并记下重要词汇的注释,有时也记录对于一个句子的不同理解,撰写者最后用不长的篇幅提出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而当其他同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也会写短文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这批学者非常尊重同人之间的不同意见,通过公开意见分歧,深化对鲁迅的理解。可以说,正是这样见木又见林的研究活动,成就了尾上兼英、丸山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鲁迅研究大师。丸尾老师比鲁迅研究会同人年轻一些,似乎没有正式参会,但他显然深受他们研究方法的影响,并进一步综合、发扬了这些方法,他笔记本中所录便是明证。

丸尾常喜著《“人”与“鬼”的纠葛》
谈起丸尾老师的鲁迅研究,大家都会想到《“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的“阿Q=阿鬼”说。这是丸尾老师最有创意的假说,其实它也与老师一贯的研究态度有关。丸尾老师注意到“鬼”的契机是《阿Q正传》开头部分的一句话:“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可能会对这话不以为意,认为它不过表达了作者在不知不觉间对阿Q感兴趣了。但丸尾老师在翻译时,居然找到一个细微的线索。他抓住“思想”一词,查阅《阿Q正传》中该词的几种用例,发现鲁迅文本里的“思想”几乎与“想象”同义,意味着脑子里发生形象,即把“象”想出来。于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的意思,便成了叙述者脑海里产生“鬼”的形象。丸尾老师继而扩大调查范围,研究民俗学意义上的“鬼”的形象,尤其考察鲁迅从小就很熟悉的目连戏里的“鬼”。最终丸尾老师确认《阿Q正传》的文本处处渗透着目连戏等中国民俗中的“鬼”的形象,必须参照“鬼”的视角,才能清楚理解鲁迅《阿Q正传》的意义。就此而言,阿Q到底是不是阿鬼,未必是丸尾老师研究的重点,从“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个细节进入,引入“鬼”的视角,打开《阿Q正传》文本,指出《阿Q正传》与中国传统民俗之间的深刻关系,才是他的真正贡献。
近期中国翻译出版了丸尾老师的鲁迅传记——《明暗之间:鲁迅传》。这是老师在四十八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因为是面向大众的读物,老师认为它不够专业,还谦虚说,自己的鲁迅研究还不到位。但我们一读便知,这本书已清楚展示了丸尾老师的研究特点,也处处透露出他对鲁迅的深刻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日文原书的副标题:“为了鲜花甘当腐草”。照丸尾老师自己的说法,这句话改写自鲁迅1929年所写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原文是:“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这话并不特别,这篇文章也绝不是鲁迅的代表作。丸尾老师以此为副标题,或许只因为他爱养花?理由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丸尾老师在序章中提到了鲁迅描写“花”的几个例子,从早期的《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到写给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信,他在这章结尾还引用了《〈野草〉英文译本序》中的一句:“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丸尾老师告诉我们,鲁迅用“花”的形象表达心情,通过追寻“花”可以体察他不同时期的心情变化。同样是细节,带我们走进鲁迅的内心。至于这本书副标题的用意,我想可能是为了突出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即便对于一本他口中的“大众读物”,丸尾老师也下足功夫,把他一贯的研究方法用得淋漓尽致。

丸尾常喜(1937-2008)
在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他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充分解释。其实,鲁迅的文本孕大含深,犹如膏腴之地,还留下很多尚未被挖掘的细节。如果有独具只眼的朋友能够见微知著,抓住那些可以通往鲁迅深邃之处的微眇,那鲁迅的作品就依然能为当下的、未来的读者打开新的文学世界。丸尾常喜老师的教导在今天没有失去意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