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11书介丨恐怖与艺术,酷儿民族主义,情感政治
不同于以现实政治、外交政策或国际关系讨论为主、侧重于呈现事实或梳理历史的9·11书单,本书介所选取的著作从人类学、哲学、艺术史、图像学、性别研究、情感研究等视角审视9·11事件与“反恐战争”,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恐怖主义与艺术创作、酷儿运动、克隆技术的关联,挖掘看似自发的日常情感之下的政治与经济,坚守知识分子提出异议的责任,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处的方法。
1.

《来自本土的异见:9·11文集》斯坦利·哈弗罗斯,弗兰克·兰特里夏编,2002
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 : Essays after September 11. Stanley Hauerwas, Frank Lentricchia.
本书最早作为《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的特刊出版,收录了包括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内的多位知名学者的9·11反思文章。这些学者的讨论涵盖文化的政治、社会、美学、神学和伦理等多个面向,关涉爱国主义,正义,复仇,美国与以色列、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关系,美国历史和符号学,艺术与恐怖,和平主义等主题。尽管主题各异,但如标题所示,在9·11事件后美国上下对政治异议的不宽容达到顶峰之际,知识分子纷纷行使自己发出不同声音、保持冷静不受煽动的职责,在谴责恐怖主义杀戮无辜平民的同时,指出美国应承担的责任,批判政府政策,拆解灾难后的爱国主义话语,揭示用于合法化“反恐战争”的叙事,反思消费文化对袭击的挪用,追问为何中东对美国怀有深深仇恨。这些文章呼唤思考、分析与理解,敦促美国远离民族主义的自负陷阱,迈向一种积极的(警觉的、知情的、实践的)和平,而非走向被动和战争。
本书编者斯坦利·哈弗罗斯是杜克大学神学伦理学教授和法学教授,弗兰克·兰特里夏是杜克大学文学和戏剧研究教授。
2.

《恐怖时代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话》乔万娜·博拉朵莉,尤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2003。中文版由华夏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Habermas and Derrida. Giovanna Borradori, Jürgen Habermas, Jacques Derrida.
本书是9·11事件后乔万娜·博拉朵莉对当代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的访谈。在流行印象中,哈贝马斯与德里达似乎在基本(元)理论立场上观点相左:前者捍卫启蒙运动及其遗产,后者批判启蒙遗产;前者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后者则被归为“后现代主义者”;前者追随批判理论传统,以普遍的人类解放为目标,后者则质疑西方真理的普遍性,强调将其历史化、社会化、相对化的学术责任。在《恐怖时代的哲学》中,两人对9·11事件与恐怖主义的对话与讨论显然远远超出上述简单的二元框架,展现出丰富的复杂性,凸显了哲学阐释当下的力量。
例如,在对“宽容”(tolerance)概念的阐释上,德里达挖掘了这一概念背后的基督教意涵和家长姿态,破除了普世性的迷思。他有力地指出,在“宽容”框架下,他者并未被视为平等的同伴,因此这一概念不适于成为平等世俗政治的基础。德里达转而提出“好客”(hospitality)概念作为替代,这一概念能凸显个人对他人的责任。这里德里达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取向:解构虚假的客观中立、普世概念和潜在的霸权理念。这个意义上的解构非但没有减少对普遍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反而使其不断更新和焕发生机。
相较之下,哈贝马斯则试图从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捍卫“宽容”。哈贝马斯认为,宪政民主是唯一能容纳自由沟通与理性共识的政治局面,因此,尽管对“宽容”有诸多批判,但“宽容”若在有效的参与式民主制度(如议会民主制)下实施,那么其片面与不足便能得到弥补。而宗教不宽容(原教旨主义便是其表现)在哈贝马斯看来完全是一种现代现象,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信仰态度的改变,而非具体信仰内容的变化。因此,原教旨主义不是要简单回到前现代,而是对理解和实践宗教的现代方式的暴力回应。此外,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以暴力为中介,哈贝马斯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种沟通的病状:从歪曲的交流,到相互不信任,到最终的沟通崩溃和暴力滋长。对这种系统性沟通崩溃的补救措施要求重建人们之间的基本信任联系,这需要改变压迫与恐惧蔓延的生存境况。
在哈贝马斯看来,恐怖主义是现代性造成的创伤的后果,而德里达则认为恐怖主义是现代经验中固有的创伤元素所表现出的症状。两位学者的讨论无疑都是对启蒙遗产的深切反思:从自我审视开始,不懈地探索建设性的批判视角。
乔万娜·博拉朵莉是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哲学和媒体研究教授。本书中文版由华夏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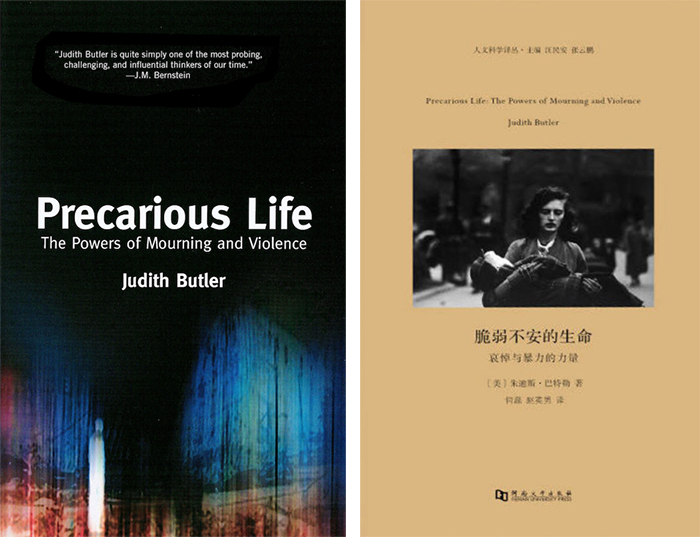
朱迪斯·巴特勒《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朱迪斯·巴特勒,2004. 中文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Judith Butler.
本书收录朱迪斯·巴特勒的五篇文章,它们写于9·11事件后,回应了美国国内不断加剧的反智倾向和压制手段与美国对外的侵略行为。巴特勒注意到,恐怖袭击后,美国一方面对内强化民族主义话语、拓展监控手段、镇压政治异见、中止宪法权利、发展审查制度,另一方面对外发动侵略,拒绝反思自身,陷入暴力循环。她指出,长期作为特权/例外国家的美国在遭遇袭击和暴力时,不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主权,而应借此机会从根本上重新构想社会关系和全球共同体。巴特勒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了失去(loss)与暴力的关联,并指出,个体注定易受伤害的脆弱性、个体生命依赖他人/陌生人的必然性,均指向将人类相互依存状态作为全球政治共同体的公认基础的理念与实践。唯有如此恐惧与伤痛才能得到充分疗愈,悲伤与哀悼才不至于点燃好战的呼号、进而限于暴力的循环。本书收录的文章不局限于9月11日发生的事件,巴特勒还探讨了主权权力与治理术、无限羁押权与“无效生命”、批判以色列与“反犹”污名等相关问题。
本书作者朱迪斯·巴特勒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教授。本书中文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4.

《论自杀式炸弹袭击》塔拉尔·阿萨德,2007
On Suicide Bombing. Talal Asad.
自杀式恐怖袭击为何尤其令人恐惧?是否存在“以宗教为动机的恐怖行动”?如果有,它与其他形式的集体暴力有何关联?自杀式炸弹袭击是否受某种“伊斯兰死亡文化”驱动?宗教人类学家塔拉尔·阿萨德试图通过《论自杀式炸弹袭击》回答上述问题。
阿萨德从根本上质疑了西方关于死亡和杀戮的假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相比恐怖活动,现代民族国家能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毁灭生命、毁坏生活,但他们的合法暴力并未受到多少谴责。因此,大家关注的似乎并非杀戮行为本身或其带来的破坏,而是杀戮采取了何种方式、出于什么动机。在现代进步主义国家行使的合法暴力中,存在着某种死亡与“爱”、残忍与同情、消灭敌人与人道主义的结合,恐怖主义暴力则不具备这一特性。阿萨德的分析揭示,在当今恐怖行动与主权国家战争的二分背后,真正重要的差异在于两者的文明地位。这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两套不相容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对生之渴望)对“野蛮”(对死之追求)的征服。善战胜恶的古老叙事在当下的“反恐战争”中找到了全新的表达方式。阿萨德认为,我们需要对塑造和推进如此话语的力量保持警惕,不断质疑和反思有关道德上善好和道德上邪恶的杀人方式的假设。
为何西方对自杀式恐怖袭击惊恐万状(与此同时对战争的合法暴力习以为常),它有何特别之处?阿萨德的回答是:首先,在公共场合的意外自杀中,人类身体破碎、日常生活被打乱,且这种暴力中的死亡逃脱了民族国家的管制;其次,在自由主义身份认同下,犯罪和惩罚、损失和归还不可分离,这对现代法律的运作至关重要,而自杀袭击使这一链条断裂,因而尤其令西方现代主体无法容忍;第三,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维系现代主体性的紧张关系(个体的自我表达与集体的法律服从、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合法毁灭、个体生命不可避免的衰败和死亡与在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不朽的愿想),但当突然的自杀式袭击发生时,这些紧张关系有可能完全崩溃;最后,对自杀式袭击的情绪反应还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有所关联,在自杀式爆炸中没有救赎,只有无意义的死亡。
《论自杀式炸弹袭击》一书绝不是在拒斥一部分暴行、而鼓吹接受另一些残忍行为。本书的目的在于揭开不言自明的假设背后的问题,充分搅动读者的不悦与不安,以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观念,对既存公共话语保持距离,因为这种话语中预先浸透了对恐怖主义、战争和自杀式爆炸等行为的规范性道德反应。
本书作者塔拉尔·阿萨德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人类学教授。
5.

《艺术与恐怖的罪行》弗兰克·兰特里夏,乔迪·麦考利夫,2007
Crimes of Art and Terror. Frank Lentricchia, Jody McAuliffe.
杀人犯、艺术家和恐怖分子有何关联?他们需要彼此吗?在《艺术与恐怖的罪行》中,弗兰克·伦特里夏和乔迪·麦考利夫挖掘了文学创造力与暴力乃至政治恐怖之间的亲和关系。本书始于对施托克豪森的著名言论——911事件后,德国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将世贸中心的毁灭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引发巨大争议——的讨论,经由对政治极端主义和前卫艺术运动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相互促进的历史的呈现,最后结束于作者虚构的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埃及恐怖分子,基地组织成员,9·11事件中19名劫机者的领袖,操纵美国航空11号班机于2001年9月11日上午8 : 46第一个撞向世贸中心北楼)与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一生落魄、不受赏识,终自杀,作品在身后得到承认)的对话。
《艺术与恐怖的罪行》揭示了众多浪漫主义文学愿景背后的欲望,即破坏西方经济和文化秩序、实现“觉醒”,而这与恐怖主义的欲望何其相似。两位作者认为,随着作家和艺术家的权威消退,继承这种浪漫主义破坏性传统的是罪犯和恐怖分子。本书通过分析高雅文化(例如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和流行文化(通俗电影和小说),揭示出浪漫主义最为核心的艺术欲望——制造越界/越轨(transgression)。艺术家希冀成为反抗一切压迫的越轨者、违抗和颠覆制度的越界者。创作越界艺术的冲动于是与实施暴力的冲动危险地靠近。
本书审视了经久不衰的浪漫主义文化中的激进精神,意在鼓励读者重新思考对于艺术遗产的流行观念,挑战了认为艺术总是“好的”、“良性的”的成见。两位作者认为,艺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犯罪性的努力注定失败,因为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保存自己的趋向,而且越界者和越界之物终会被纳入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逻辑。因此,需要想象另一种艺术欲望,这种欲望不寻求越界和改造,而是坦承世界不会因艺术彻底改变,愉快地进入边缘,放弃所有激进社会变革的野心。这种艺术只保有最低限度的希望——由于艺术家的存在,当地的文化社群可能会产生些许不同的观察方式,甚至可能会带来一点微小的改变。这是一种不会以失败和绝望告终的艺术承诺,因为它弃绝政治野心、忠于永久放逐。
本书作者弗兰克·兰特里夏是杜克大学文学和戏剧研究教授,乔迪·麦考利夫是杜克大学戏剧实践研究教授。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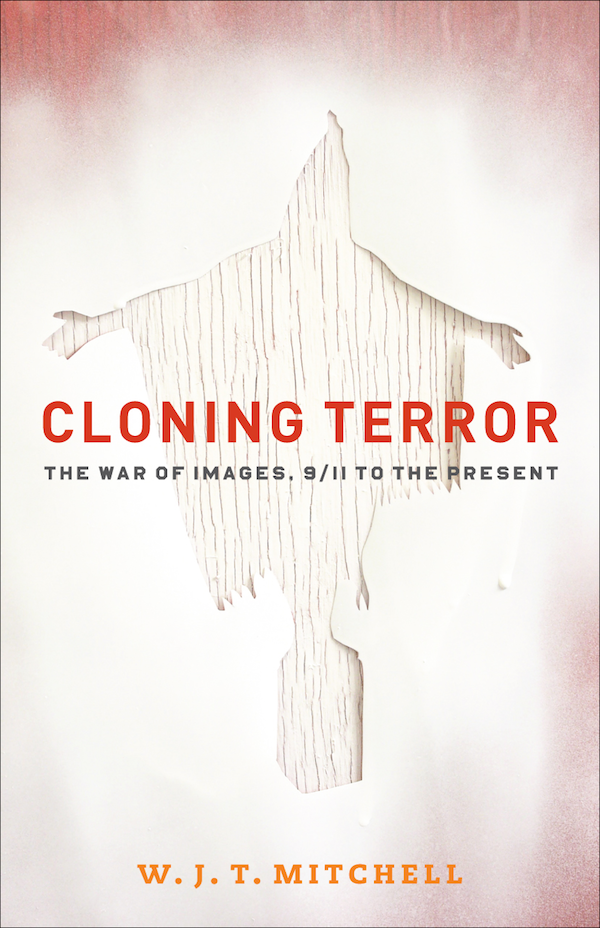
《克隆恐怖:从9·11到当下的图像战争》W. J. T. 米切尔,2011
Cloning Terror: The War of Images, 9/11 to the Present. W. J. T. Mitchell.
克隆与恐怖主义有何关联?W. J. T. 米切尔从图像学和符号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可被称为“克隆恐惧症”(clonophobia)的心理背后暗含的一系列焦虑,追溯了将克隆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深刻文化逻辑——这一逻辑在9·11事件后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克隆与恐怖主义皆为图像性(iconic)概念,充满意识形态和神话意涵。克隆的意象足以调动整个政治光谱的反感——从世俗主义对“非自然”过程的焦虑到宗教传统对“扮演上帝”、创造和毁灭生命的禁忌。它逐渐成为变种人、复制人、赛博格乃至(9·11事件后)无意识、无灵魂、丧失个体身份、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完成自杀式袭击任务的大批战士的同义词。
米切尔认为,克隆需要放置在“生物控制论”的时代背景下理解。生物控制论时代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历史继承者。如果说机械复制时代的特点在于流水线工业生产与摄影和电影技术中图像的机械复制这一双重发明,那么到了生物控制论时代,流水线生产的不再是机器,而是生物体和生物工程材料;图像生产也从传统摄影和电影技术转向视频和数码相机的电子图像。简言之,克隆乃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双重革命、“计算机和培养皿”的结合,因而成为生物控制论的代表。
部分得益于新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能力,当代恐怖主义往往在生物信息学框架内被描述为一种堪比传染病的社会现象,常常被类比为潜伏的病毒、癌细胞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恐怖主义的关键在于其背后的心理-生物假设,它是一种心理战策略,旨在催生民众的焦虑和恐惧。它通过上演相对有限的暴力行为打击民众士气,煽动民族国家做出(过度)反应。如果说战争通过图像和对图像的破坏对民众集体想象力施展攻击,那么恐怖主义则是一种主要在想象层面运作的战术。尽管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不带有军事意义,但却制造了一个奇观,给国家带来剧烈创伤。
从这一视角看,反恐战争产生的效果可以用“克隆恐怖”(cloning terror)来概括。反恐战争并未击溃或减少恐怖主义威胁,而是恰恰相反——似乎在每宣布杀死一名恐怖分子后,很快就会有更多无辜者不得不为其殉葬;无人机袭击的“附带损失”似乎与成功的精准暗杀一样多;每一次战术胜利似乎都与民主化和“赢得民心”的总体目标愈行愈远;反恐战争似乎在让敌人变得更多、更强大、更坚定;常规战争手段(轰炸、入侵、占领)究竟是对恐怖主义这一疾病的治疗,还是实际上使其恶化?
本书作者W. J. T. 米切尔是芝加哥大学英语和艺术史教授。
7.

《恐怖主义配置:酷儿时代的同性恋民族主义》贾斯比尔·普阿尔,2007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Jasbir Puar
美国的“海外”战争与美国“国内”的酷儿和性别运动有何关联?在《恐怖主义配置》一书中,贾斯比尔·普阿尔将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德勒兹哲学以及技术批评等理论框架结合起来,运用包括政府文书、司法档案、电影电视、民族志材料、酷儿媒体以及社会活动组织宣言在内的众多材料,揭示了“反恐战争”背后的文化政治,挖掘了酷儿运动被重新配置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同谋的过程。
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战争机器的开动需要“进步与正义”的伦理口号,LGBTQ+运动因而也被招募进来,参与爱国主义实践和展示。普阿尔认为,将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纳入国家项目至关重要,当代民族主义依赖于将少数群体(不平等地)纳入政治体中,用“进步”主张来支持军事扩张。(美国化的)性少数群体成为“文明”的新基准,其他社会均以此为标准被评判高下,进而成为美国的制裁/打击对象。
与此同时,北美同性恋社群的内部重组越来越沿着白人至上主义、世俗主义和亲资本主义的方向展开。自由主义政治将部分“正确”、“良好”、“符合规范”的性少数主体吸纳进民族国家,将他们从死亡的象征(艾滋病)转变为与生命力/生产力紧密相连的主体,制造某种特定的“同性恋本位”(homonormativity)。然而,普阿尔指出,这种对同性恋主体的吸纳是很脆弱的,它依赖于对恐怖分子群体的东方主义生产,“同性恋本位”的兴起乃是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普遍渗入身份政治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实际上成为“白人优越的帮凶”。白人性主体的“解放”是以其他被性别化、种族化的群体为代价的——例如,9·11事件后的锡克教徒、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往往会被无端怀疑为“恐怖分子”,遭到扣押或驱逐出境。长久以来,美国都基于白人异性恋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如今“后来居上”的同性恋意识形态实质上复制了前者狭隘的种族、阶层、性别和民族观念,而非颠覆了它们。
《恐怖主义配置》将三条轴线——美国军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美国酷儿政治的内部配置以及更广泛社会的治理化(尤其针对被种族化的少数族裔)——编织在一起,为读者呈现当下同性恋民族主义所处的网络。
本书作者贾斯比尔·普阿尔是罗格斯大学女性和性别研究教授。
8.

《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莱拉·阿布-卢赫德,2013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Lila Abu-Lughod.
本书业已成为讨论穆斯林世界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必读书目,加之其行文流畅、语句通俗,在学术界之外的读者群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力。9·11事件后,西方对穆斯林女性的呈现中“拯救叙事”无处不在,这一叙事也被用来为美国入侵阿富汗铺平道路。在西方,穆斯林女性被呈现为完全的“受害者”,而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加害者为穆斯林男性及“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女性的“拯救者”则是白人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或打着这一旗号的美国军队。此外,罩袍和头巾等穆斯林传统服饰因与“自由选择权”相悖而被直接与宗教-父权制压迫划上等号。
通过对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展开批判性分析,阿布-卢赫德彻底驳斥了上述框架。她将为入侵和干预提供合法性的“女权主义”称为“帝国/殖民女权主义”,揭示了其背后的帝国傲慢与殖民心态。她通过分析欧美社会中衣着的规范性话语破除了西方颇为流行的“自由选择”的意识形态迷思,表明遮罩身体/穿着特定服饰与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她反问道,为9·11事件寻求解释时,为什么(边界分明、内部同质、静止不变的)“文化”概念成了恐怖袭击最相关、最重要的解释因素,而不是诸如地区历史、地缘政治、政权更迭或全球化等因素?为什么穆斯林女性遭受的压迫被认为主要来自宗教(“伊斯兰”)?为什么阿富汗女性的身份、年龄、种族、阶级、具体宗教背景的复杂差异被压缩为具有同一愿望、面临同一未来(被西方解救)的同一形象?
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在为压迫寻找借口,而是更负责任地思考穆斯林女性的生存处境和权利问题的起点。通过撼动自由主义价值的道德确定性、对“权利/人权”框架的普世性(它随时可能转换为霸权[hegemony])展开质疑,阿布-卢赫德希望能回到经验现实来思考穆斯林女性的苦难和艰辛为何、其真正根源为何、如何有效改善她们的处境等一系列问题。她以自己在埃及贝都因社群数十年的田野经历为基础,描摹了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梦想、欲求、愤怒和失望,她们的幸福、虔诚、主动性与坚韧。阿布-卢赫德反思了社会科学(人类学)进行普遍化的方法以及为“文化”分门别类的倾向,为诸如“宗教”、“父权”、“结构”、“能动性”、“选择”、“自由”、“主体”、“抵抗”、“解放”等大词赋予了具体意涵。
本书作者莱拉·阿布-卢赫德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
9.

《情感的文化政治》萨拉·艾哈迈德,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Sara Ahmed
尽管《情感的文化政治》并非讨论9·11问题的专著(书中有两章直接与9·11事件相关),但本书的情感政治视角对于理解9·11事件、特别是其后果和效果而言大有助益。艾哈迈德的基本观点是,情感是社会性的文化实践,而非个体的心理状态或身体特征。身体通过情感与流行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情感的文化政治通过使部分身体边缘化来制造他者。情感具有物质性,通向集体政治和社会联盟,这种社会力量体现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甚至可以创造国家身份认同。与许多探究“情感是什么”的理论家不同,艾哈迈德着眼于“情感做了什么”,即情感的“工作”(work)或物质运作过程——它如何“制造”和“形塑”了我们的身体反应与面对他人的方式,如何在主体间“滑动”和“循环”。
在具体谈及9·11事件时,艾哈迈德详尽分析了“恐惧”(第3章)与“厌恶”(第4章)的情感政治。以“恐惧”为例,恐惧并不来自内心,继而向外转移到物体和他人身上;恐惧的存在是为了确定身体之间的关系。恐惧能作为一种情感经济发挥作用,它并不积极地驻留在特定的物体或符号中,而是在符号之间和身体之间滑动。在恐惧的空间政治中,一个常识性的假设是,最脆弱的人最恐惧,恐惧可被视为对脆弱的“合理反应”,而脆弱本身被认为是部分人的内在品质或特征。然而,艾哈迈德分析指出,对危险的焦虑与受害程度无关,“那些最没有危险的人反倒最害怕”。在9·11袭击之后的美国,由于恐惧的直接对象的丧失,恐惧变得愈发可怕。人们越是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么或是谁,整个世界就越是变得危机四伏。
此外,恐惧并非限制了所有身体的流动性,而是通过部分身体的运动来限制另一些身体的运动。尽管常识认为西方主体的身体流动性在9·11事件后受到威胁,但它其实也同时得到了维护: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西方公民得到的最直接的行动指示可以概括为“继续进行日常事务”、“去旅行”、“去消费”,这被视为拒绝成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勇敢姿态,但实际上如此做法维护了全球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部分资本和机构的流动成为自由和文明的标志。而且,恐惧还成为了再动员的根本依据——经由“爱国主义”的中介,恐惧甚至能让部分身体通过认同于集体身体而占据更多空间,参与到美国的扩张和侵略中来。
如果说恐惧引发了对资本流动性的捍卫和对部分身体的动员,那么与此同时谁的流动性遭到了遏制?什么群体的脆弱惨遭无视?9·11事件后,任何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都会被拘留,此为拘留权的扩大。但这显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以相同方式受到影响。一种种族化的识别和定性过程使得来自中东或南亚的人群、阿拉伯人、穆斯林移民、难民、所谓“亚洲人”甚至“东方人”成为高风险人群,遭遇无端猜忌、指控和羁押。
对于研究9·11事件与美国反恐政治引发的情感反应及其物质后果而言,《情感的文化政治》对情感政治与情感经济的探讨极具启发性。正如加拿大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2010)所言,袭击后的美国认为自身陷于恐怖主义威胁中,而“威胁”是一种来自未来的情动/情感现实(affective fact):如果我们感到威胁,那么威胁就已然存在,且将永远存在。从情动的角度来看,威胁是自因的(self-causing),它没有真实的指涉对象,而是通过捕获潜在对象来运作自身。“反恐战争”时代美军的“先发制人行动”会制造它声称要针对的客体,因而绝无可能出现逻辑矛盾——“虽然当下可能没有现实证据表明威胁的存在,但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威胁一定会被制造出来”。威胁于是获得了一种优先的政治在场,赋予了“先发制人行动”一种环境权力(environmental power),这种权力不求实际操控客体(也不存在实际客体供其操控),而重在调控情感、营造生命-环境——这无疑准确地勾画了“反恐战争”时代人们经历的(至少部分)现实。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