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陈侃理:中国古代灾异论能够制约皇权吗?
所谓灾异,即自然和社会的灾害和异常,古人认为其中包含着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者谴告。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直到近代科学主义兴起后,仍然隐藏在国民的“集体无意识”里。
中国传统的灾异论最早可以上溯至什么时候?汉代董仲舒确立的儒家灾异说的特点是什么?它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又如何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侃理。
陈侃理师从陈苏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汉魏晋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出土文献,他的博士论文《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入选201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近期出版的专著《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即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在他看来,“说灾异是基于普遍信仰的一种深刻的传统,曾被寄托很高的期望,也产生过声势浩大的影响,但它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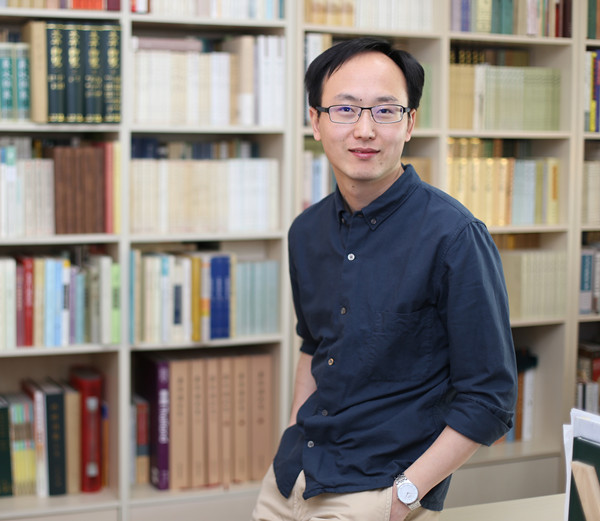
澎湃新闻:中国传统的灾异论思想最早可以上溯至什么时候?
陈侃理:在历史研究中,源头往往是最难说清的。一是因为史料不足,二是因为定义不清。我书里说的灾异论,指关注自然或者社会的灾害和异常,并且把它们与人事、政治联系起来。这种思想的产生最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比如在《左传》中记载了一段晋平公与士文伯关于日食预兆的对话,士文伯说“国无政,不用善”导致日月之灾,跟我们后来熟悉的灾异论已经很接近。《尚书·洪范》和《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在后世都被认为和灾异有关。但这些篇章最初形成时,作者的意识中不一定已经有成熟的灾异论。所以学者追溯灾异论的儒学传统,一般还是会把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看作鼻祖。

澎湃新闻:董仲舒被后世认为是儒家说灾异的鼻祖,那么经由他所确立的儒家灾异说的基本模式是什么?与此前相比有何不同?
陈侃理:董仲舒灾异论的第一个特点,是把说灾异的重心转到回溯原因上来。很多古老文明都存在把天文异常和人事联系起来的思想。天象带来预兆,这种观念非常普遍。但回溯灾异发生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灾异论的特点。这种传统不一定是从董仲舒才开始,但是经由他确立起来并且发扬光大的。
董仲舒灾异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利用《春秋》讲解当代灾异。他把《春秋》里面记载的一些灾异当作可以和眼下对照的事例。通过历史性的对比论证,来谈当下的灾异,可能由什么引起、反映了什么天意。董仲舒说灾异时,有句话常挂嘴边,叫“天戒若曰”。“天戒若曰”,就是上天告诫君主,告诉他犯了什么错误,应该怎么改正。
为什么要用回溯式的灾异解说方式呢?他想通过回溯造成灾异的原因,指出那些德行上的缺失、政治上的过错,促使君主接受他的儒家理念。他把灾异的具体表现跟儒家标准一条一条对应起来,去权衡君主是否失德失政。这样,灾异就在儒家设定的原则下反映天意,对君主的行为进行反馈、提出批评。
董仲舒的灾异论和数术占卜的传统不同,但是他的灾异论是在汉代阴阳五行学说流行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董仲舒利用了很多数术的技术和原理,他的回溯式灾异解说是不彻底的,经常把预言跟回溯结合起来。事实上,君主对灾异有所恐惧,往往不是因为想起过去犯了什么错,而主要是担心灾异预言成真。所以,董仲舒希望推行儒家理念,无法摆脱预言、占卜方面的数术理论,因为君主真正怕的是这些。
董仲舒讲灾异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主要是两个场合,一个场合是在《天人三策》里面,谈理论,没有和现实联系起来。另一个场合是所谓《灾异之记》,这是董仲舒讲当代灾异的著作。他写完以后藏在家里,不敢奏上。不巧,书稿被汉武帝的近臣主父偃发现,向武帝告发。书中的一些内容被认为是妄议政治,大逆不道。董仲舒被判死罪,幸亏武帝赦免了他。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儒学灾异论还没有普及,董仲舒自己也未能通过灾异论的实践真正地影响政治。

澎湃新闻:你认为灾异论有儒学和数术两大传统,能否具体说说这两大传统的表现,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陈侃理:灾异论的数术传统渊源更早,在儒学兴起之后变成一股潜流。它的表达比较隐晦,因为往往预言君主生死、国家存亡,这些事君主很关心,但又不能公开说。政治人物总是担心命运,对未来抱有不确定感。灾异的数术传统跟占卜联系在一块,适应了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这股潜流很有韧性,从来没有中断。
儒学灾异论借用了数术传统中的很多因素,逐渐成熟起来之后又刻意跟数术保持距离。儒家称数术为“小术”,不是正经的“大道”。儒家通过灾异提出政治理想,针砭时弊。通常是皇帝因为灾异现象出现后下诏罪己,然后大臣、儒生提出批评意见。不过,这种君臣互动,往往有表演性,仪式感很强,不一定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常常只能作为借口或者助力,推动一些已经酝酿成熟的政治变化。
儒学传统往往包装着数术。举个例子,国家为了应对日食会举行一些仪式,敲锣打鼓等等。这些仪式往往有着儒家经典上的依据,背后的原理却是数术性的。数术传统是儒学传统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事件的表层下面起作用。看到灾异,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主何吉凶?”这是我们谈灾异的心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儒学的灾异论才可能建立起来。
澎湃新闻:随着“日食”等自然规律被揭示,灾异论在发展中受到怎样的冲击?儒家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冲击的?
陈侃理:灾异论的前提是天象与人事相关,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预测吉凶,才能回溯原因。一旦人们知道日食是自然规律造成的,跟人没关系,这对于灾异论当然会造成冲击。
这种冲击首先在经学上表现出来。经学的注释会涉及经书中记载的灾异是被如何解释的。经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是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里面讲日食有规律,但又留了余地,说“日月动物”,意思是太阳月亮是能动的物体,难免一会儿跑得快,一会儿跑得慢。这样一来,算出来的那天是不是一定发生日食,就不好说了。
南北朝以前,天文学对日食规律的把握还比较模糊,预测的偶然比较大。到了隋唐之际,天文学解决了日食预测中的一些难题。经学研究者了解到天文历法的进展,认为日食的规律已经发现了。唐代官定的《左传正义》里说:“虽千岁之日食,预算而尽知,宁复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那么,日食显然就不是由人事引起的了。
不过,日食终归是耸人听闻的异常现象,白昼突然变黑夜,对人的心理是会造成冲击的。在儒学的政治设计中,君主天命所授,至高无上,除了老天爷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制约君主。所以,《左传正义》仍然认为圣人主张“神道设教”,要善于借助让人产生敬畏、恐惧心理的天象,来教化君主。君主并不一定清楚日食的规律,“中下之主”因为迷信而有所戒惧,“智达之士”就可以借此来进行教化。
经学相信日食已经可以预报,但实际上天文学家预测日食的方法在初唐就碰到麻烦,好几次日食预报都不准确。这就给天人感应、灾异说留下了余地。唐玄宗时,天文学家一行奉诏制定《大衍历》。作为天文学家,他比经学家更清楚技术的局限,因此反而相信日食与君主的行为有关。他讲历法理论,兼容了“历数”与“政教”,主张自然规律跟天人感应相互补充和配合,才产生了人们看到的天象。比如,本来要发生日食,君主表现得好可能会感动上天,让太阳月亮的运动稍改变一下,日食的食分就会变小,甚至就不发生了。

澎湃新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跟灾异关系密切的还有祥瑞吧。它们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
陈侃理:祥瑞和灾异相反而又相似,可以说是花开并蒂。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提到的一个发现:两汉多凤凰,而西汉宣帝时尤其多。凤凰就是祥瑞,汉宣帝用祥瑞做年号,有神爵(爵就是雀)、五凤,还有甘露、黄龙,都是因祥瑞而得。这不是因为当时真的祥瑞特多,而是宣帝重视祥瑞,鼓励报告,更多的“祥瑞”被记录下来。
汉宣帝为什么重视祥瑞呢?这跟他的身世和即位以后的政治形势有关。宣帝是武帝后期由于巫蛊之祸而被废的戾太子的孙子。武帝之子昭帝死后没有继嗣,辅政大臣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这个刘贺很快被废除,改封海昏侯,现在挖出了他的墓,非常轰动。宣帝就是代替他继承皇位的。宣帝长在民间,突然被霍光推上帝位,政治合法性并不稳固。还有刚刚进行过废立的强臣执政,如芒在背,权力基础相当薄弱。他即位以后,希望通过祥瑞代表天意,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来巩固权力。他做了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就是给昭帝时被杀的儒生眭弘平反。
眭弘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昭帝时发生了几件怪事,倒在地上的枯树突然站起来活了,还有虫子在树叶上咬了洞,看起来像是几个字:“公孙病已立。”眭弘用灾异论来解释,说是预示着有平民要当天子,汉朝要顺应天命。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可是等到宣帝即位,这个预言正好符合他的经历,过去的灾异变成了祥瑞,表明宣帝是天命所授。

眭弘平反以后,祥瑞就顺应时势,层出不穷。谈天人感应,成了时髦,这也为灾异论进入到政治生活中开了口子。当时有个儒生萧望之,当着宣帝的面议论灾异,认为原因是大臣专权,私门太盛危机皇权。这个说法正合宣帝的心意,萧望之火箭式升迁,做了大官,灾异政治文化也逐渐发达起来。
澎湃新闻:灾异政治文化发达以后,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有哪些体现?
陈侃理:汉代设有专门观测和记录天象的机构和官员,各县州郡发现了异常灾异现象也要呈报中央。所以地方郡县发生的一些重大灾异,也会在被史书记录下来。唐宋以后的史料对当时类似的制度就记载得更清楚了。
日食发生时会采取一些“救日”仪式,目的是消灾免祸。汉代还不能准确预报日食,只知道在每个朔日,也就是农历初一,有可能发生日食,所以朔日前后各两天,每天都要准备好一头羊,一旦日食开始了,赶紧杀羊祭祀。这时候日食没法预报,仪式不好准备,所以比较简单。后来,日食的预报越来越准确,制度上规定的救日仪式变得很复杂,规模很大。当然,具体执行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体来说,唐代以后,日食的神秘感逐渐消失,皇帝和官员对“救日”仪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明代人谢肇淛写的《五杂组》里,说当时的官员祭祀救日,磕完一个头,就在供桌旁边喝酒玩乐,嘻嘻哈哈,等着太阳复原,一点儿也不严肃。
不过,到了清代,又发生新变化。预报有日食的当天早上,京城官员们都要到礼部集合。日食一开始就齐刷刷地下跪,直到太阳复原为止。不少年纪大的官员,体力吃不消,跪得东倒西歪,还被皇帝痛骂。过去,大臣希望通过灾异来约束君主,这时候灾异反过来成了君主管束臣下的一种手段。
澎湃新闻: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灾异论从一开始就只停留在思想层面,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从未发生过实际效用?
陈侃理: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影响很深,在政治文件、政治制度、政治决策和日常行政中都有反映,不能仅仅归结到思想层面。不过,它发挥的作用,跟灾异论的最初设计,常常是相反的。即便在灾异政治文化最鼎盛的时期,灾异论还是被权力所左右,最终导致权力场中的“马太效应”。
举一个例子,西汉后期的刘向既是宗室,又是大儒,擅长说灾异。他上书皇帝,指出宠幸外戚宦官造成了当时灾异。但外戚和宦官也利用灾异作武器,说灾异是皇帝身边的士大夫闹的。结果刘向被问罪免官。这时候,决定胜负的不是灾异论的优劣,而是权势。儒生没有能力垄断灾异论,怀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人都可以利用它。
澎湃新闻:很多人认为灾异论可以起到用“天”去约束专制皇权的作用,史实上真的如此吗?
陈侃理:灾异论本身当然包含了这种意图,但从历史上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董仲舒到刘向、刘歆,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熟、严密的灾异论。在这套理论当中,特定的灾异对应着特定的不良政治行为,“天”通过灾异对君主进行警告和惩戒,而“天”判断政治行为好坏的标准是儒家的。
可是天意的执行没有现实的强制力来保障。天意之所以可以制约人君,是因为儒家设定了一个前提:君主是天命所授,只有君主能够跟天意直接沟通,天意也是专门针对君主本人。这跟西方传统大不一样。西方是政教分离的,君主是管理人间事务的行政官,另外有祭司、教会负责跟神沟通。而在儒学的设定下,只有天意能制约人君行为,天意在人间的执行者却还是皇帝。儒家没有设计出任何现实的制度或者权力,来代表天意约束皇帝、制衡皇权。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一般都知道“人君所畏唯天”。这是苏轼写富弼神道碑碑文里引用富弼说过的一句话。富弼说这句话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认为自己能够“得君行道”,皇帝可以代表他们,跟他们拥有同样的理想,这时候就不再需要天变灾异来约束皇帝了。后人把王安石的这种思想归纳为“天变不足畏”。当时,敬天、畏天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共识,只是偶尔用作实现政治意图的工具。这种态度宋人就称为“玩天”。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盛世雄主,都以圣人自居,带头批评“玩天”,主张“敬天”。不过这时候,帝王已经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太阿倒持,剑尖儿指着士大夫们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