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朱玉麒:清代新疆的史地之学如何超越传统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的重要著作,以此为开端,乾嘉学术从朴素的考据转向经世致用。其后,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主持编修、成书于宣统三年的《新疆图志》是古代中国最后一部新疆地方通志,也是清代新疆的一部“百科全书”。2015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新疆图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是前书的著者、后书的整理者,从《西域水道记》到《新疆图志》,朱教授以为,清代西北史地之学得益于一批优秀的人才,无论是徐松还是王树枏,他们不仅有扎实的传统学问,更具时代眼光,清代新疆的史地研究从一开始就不缺少科学精神。

澎湃新闻:《西域水道记》是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的重要著作。据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的记载,徐松于嘉庆十八年到伊犁,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开始考察,秋天回到伊犁,当年就写成了《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这三部号称“徐星伯三种”的书稿。《西域水道记》成书为何如此之快,是否有供其参考的文献资料?
朱玉麒:缪荃孙的《徐星伯先生事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年谱。
徐松的儿子死在他前头,徐松的去世也很突然。去世后,他的后事由弟子张穆主持料理。张穆写过《蒙古游牧记》,对于老师的后事,他料理得很好,但是徐松去世后不到两年,张穆也去世了。如此一来,徐松的大部分手稿还没来得及做好整理工作,就和张穆的藏书一起被卖到了琉璃厂。徐松本人没有留下文集,所以对于他的编年一直就不是很清楚。
至于缪荃孙,他的祖父和徐松是同年的进士,父亲是徐松的学生。于是,由他来整理徐松的事迹,而这距离徐松去世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因为资料有限,具体到某一件事情的具体时间就只能粗略地落在了某一年上,所以《徐星伯先生事辑》中记载《西域水道记》五卷的成书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
但进行具体的研究时,我们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到新疆,嘉庆二十一年有机会去了南疆,这一路行程很远。缪荃孙说徐松于嘉庆二十二年写成《西域水道记》,其实说的是草稿本,只有四卷。一直到嘉庆二十四年徐松离开新疆的时候,这个书稿依然还是草稿。徐松赐环归京后,由友人和抄手将《西域水道记》的草稿本誊写成清本。北京文献比较多,结合自己在新疆的考察,徐松开始进行文稿的修订。修订工作旷日持久,十几、二十年间,一直未得到帮助来刻书,直到道光十九年才出了刻本。这是《西域水道记》的成书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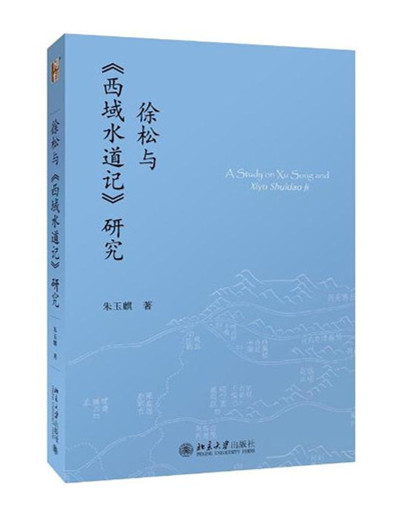
徐松在新疆完成《西域水道记》的草稿,那是不是他考察一行结束就成书了呢?显然不是这样的。《西域水道记》是一部地理学的专著,而不是简单的考察日记,所以实际的考察之外,这部著作的完成是需要诸多的历史文献来做出印证的。那么,清代新疆的平定在乾隆中期完成以后,这里的文化建设如何,有没有可供学者参考的文献来进行研究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新疆是有一定条件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个工作的。
祁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徐松的《新疆识略》中都有记载伊犁将军府所保存的书籍情况,其中,《西陲总统事略》记载的是相对重要的文献收藏,《新疆识略》则更为详备。新疆所藏的文献,一部分是图集,比如皇帝平定金川、准噶尔时的纪功碑图等;还有被贬新疆的文人官员,他们随行带了不少的书籍。据载,后来的林则徐去新疆载了一车的书;再如光绪年间的裴景福,他是个收藏家,去新疆的时候随行还带了许多名碑、名帖和名画,伯希和1907年前后与他在乌鲁木齐有交往,对其发现与研究藏经洞提供了不少帮助。除这些资料之外,新疆还存有大量本地档案,这在政书类的文献以及《西域水道记》中都有记载,后来的《新疆图志》也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都是徐松能够在新疆完成《西域水道记》初稿的条件。
澎湃新闻:提到记载水道的专书,不得不提《水经注》。您在书中也说到,《西域水道记》在体例上有模仿《水经注》的写作方式,而中原与新疆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是否能具体谈一下?
朱玉麒:《水经注》的做法非常了不起。在中原我们可能对以水引导地理学描述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刻,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叙述方式来理解。但是在新疆,有水才有人、才有生命,只有有了水,才可以把人类聚落联系起来,这种地理感觉在干旱区地理环境中就特别真切。你也因此会领悟各种的文明都是以水命名为“某某流域文明”的真谛所在。
徐松去新疆之前,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训练,他原本就是地理学专家,著有《唐两京城坊考》等著作。所以,我想他对于《水经注》是有所思考的,去之前就有考虑要写一部关于新疆的地理书。《西域水道记》原本题为《西域水经注》,应该是想把西域的水道写出一本像《水经注》这样的书,只是成书的时候,书名改成了《西域水道记》。
《西域水道记》借鉴了《水经注》的体例,以水道为纲目,自为注记,叙述自然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水经注》的记叙方式源自郦道元,当然它与当时盛行的佛经注解方式也有关系,清代学人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以水道提纲挈领呈现新疆的自然人文地理,可以说,这是徐松《西域水道记》对《水经注》的继承。

但新疆的地理环境与中原不同。《水经注》所载水道是“百川东到海”,但是干旱区地理不是这样,新疆的河流除了额尔齐斯河是流入北冰洋之外,其余所有河流都流到沙漠和湖泊中,湖泊在新疆叫“海子”。所以,如何描述干旱区的水流道路,这是徐松《西域水道记》的一个创新。他以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规律,而以湖泊为核心形成水系,将西域水道分做了11个体系。这个想法在徐松所编的《新疆识略》中就有提到,只是没有展开,而在《西域水道记》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澎湃新闻:徐松是有意识地写了《西域水道记》这样一部地理专著。
朱玉麒:对。《新疆识略》与《西域水道记》互为补充,前者是为公家编的书,徐松在编《新疆识略》的过程中就开始考察,两部书的工作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只是《新疆识略》率先完成。
《新疆识略》和《西陲总统事略》都是松筠担任伊犁将军时组织人来编写的,他想继承乾隆时期的《西域图志》(全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这是清代开发新疆以来的第一部官修志书。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伊犁将军经营管理西域的经验成熟,新疆开发有了很大的进步,松筠希望通过一部官修方志来做个总结,但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嘉庆皇帝的允许。嘉庆皇帝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在北京做,松筠作为伊犁将军为官一方,管理好边疆军备就行了,不但不支持,松筠反而还受到了皇帝的训斥。
但是,这些官员都是文人,他们没有因为皇帝不准允而放任不管,还是组织人力开始编修地方志,而且一编再编。汪廷楷做了第一稿,祁韵士编了第二稿,但是《西陲总统事略》并不是地理志,是政书类的,所以有了徐松的《伊犁总统事略》,徐松则是有意识地关注地理学,使这部书承接了《西域图志》的编纂。这部稿子得到了松筠的认可,也得到了新即位的道光皇帝的认可,亲自赐名《新疆识略》——我每次都要提到,这是“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启用。
澎湃新闻:清代对新疆的经营有几个阶段,比如统一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府,而后又有新疆建省,流放文人参与其中,在研究西域史地之学上是否也有阶段性的特征?
朱玉麒:是有不同。统一新疆前后,清廷在新疆经营管理的方式不同,大概被流放的官员在文化心理上也有不同。就史地之学来说,建省前后的变化更明显。
乾隆二十七年(1759年),清廷设置伊犁将军,而后的新疆开发是很成功的,所以,从文人的记述看,他们无论是派任还是流放,也都不是唐宋时代被贬谪、流放边地的那种沮丧心情,大家觉得这就是大清帝国的疆域,心态还算是比较开朗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对新疆的全面描述应该说是建省之后完成得更加彻底。
澎湃新闻:徐松的《新疆识略》编于嘉庆年间,而《新疆图志》则是建省之后编修的,比较一下这二者有什么不同?
朱玉麒:《新疆识略》和《新疆图志》二者差别很大。《新疆图志》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年,实际的印制出版已经是公元1912年的年初),是新疆建省之后编修的地方通志,当时新疆各地基本已经按照内地州县制的方式进行管理,所以地方官有“守土有责”的责任心,到了后期,在省级政府的要求下,每个县都编修乡土志教材,对地方事务也有很好的调查资料。

特别要说的是这每个县的乡土志,这在全国都是个特例。在编修《新疆图志》之前,清末搞新政改革,要求每个县都要编修乡土志教材作为新式学堂的课本。这是中央的命令,但是具体到每个省,执行情况各不一样。1905年清廷下达诏书后,只有新疆、山东、陕西和东北的吉林、辽宁是乡土志教材比较完整的省份,其他各省,甚至像浙江、江苏这样我们认为的文化兴盛之区都没有贯彻下去。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当时主政的地方官是否勤政。
新疆乡土志教材的编修,使每个县都上报了各类自然与人文信息,内容丰富,诸如人口、民族、物产,甚至还有中外关系的交涉,当地有多少天主教教士、多少新教教士,这些信息全部都有,所以,《新疆图志》二百多万字的编纂,与不缺基础资料以及下情上达的通畅是有很大关系的。《西域图志》是乾隆时代倾全国之力编修的地方志,《新疆图志》只是新疆建省后地方官主持编修的,但是后者内容比前者长出四倍之多。具体举例来说,《西域图志》中有“水道志”,没有“水利志”,而《新疆图志》中有完整的八卷“沟渠志”反映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成果,这就说明清廷统一新疆后对农耕的重视以及档案上呈的完备。而编修 《西域图志》时,屯垦尚没有这样的规模。而且,从《新疆图志》中也可以看到光绪年实行的新政,在新疆的确实行得很好,“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新疆图志》中表现得很出色。

澎湃新闻:西方的地图投影、经纬坐标等地理科学技术在清代就已经传入中国了,前面说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有继承传统舆地之学的一方面,那么,近代科学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中有何体现?又有哪些不足之处?
朱玉麒:要说不足和疏漏之处,当然,一定是有的。比如,书中有的说法有错漏,再比如,《西域水道记》没有明确的国界、边界的概念,说到边界就是游牧部落等等蕃地,没有明确而精细的山水分割,这是时代的局限,后来在《新疆图志》就已经有明确的国界概念了。我们今天看《西域水道记》,不能用现代地理学的标准来对待它,应该看到它的人文关怀。
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叛乱的时候,西方传教士就已经进入新疆,进行过经纬度定位。西方人发明了地图投影、大地测量法,然而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却无法实施,这个绘图方法的第一次实现就是在中国。只不过,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测量点只到哈密。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是继承其祖父的遗志,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传教士跟着进入新疆,建立了62个测量点,都有经纬坐标。《西域水道记》中的地图虽然采用的还是中国传统“计里画方”的方格地图,但是在叙述某个地方时,都首次记录了这一地点的经纬坐标,这与传统地方志不同,当然这个坐标原点是在北京。后来的《新疆图志》也是有很多很现代的地理科学理念。
近代科学技术之外,《西域水道记》值得一提的是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它不只是在写自然水道,其中有很多人文地理的内容。比如,书中讲到某一个民族,就会讲到民族的来源,当然其中有不准确的地方,至少徐松是有所考虑的。讲到伊斯兰教,会谈及伊斯兰教是如何从麦加、麦地那流传到新疆。清末伯希和、奥登堡到中国考察的时候,人人都要有一本《西域水道记》,它提供了很多经验。虽然从现代地理学来说,有些问题它并未解决,比如,当时徐松不可能到塔什库尔干上面去测量明铁盖达坂的水流方向是怎么样的(后来的《新疆图志》基本上是做到了),但这已经呈现了徐松当时所能了解到的最新的东西。《西域水道记》写到穆罕默德生年的时候有引用马六甲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说法,这是传教士用中文写的杂志,可见,徐松在一些细节方面都力求最大范围地吸收新知。跟同时代内地文人士大夫所编纂的地方志比起来,这无疑要高明许多。
我在新疆工作过许多年,整理、研究《西域水道记》、《新疆图志》,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些清代新疆的史地研究成果都是由一批优秀的人才主持编修的,这些人有很好的眼界,是传统文人中有“天下”视野的佼佼者。就拿徐松说,他当年考进士排名第四,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对中国传统学问有很好的了解,又做过湖南学政,他的见识不是一般内地省志的修纂者所能比拟的。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对徐松这个人的经历、交游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何看待徐松的“再发现”?
朱玉麒:徐松和《西域水道记》,以及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其实已经被许多学者说过很多遍了,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题目。我的这本书从研究方法上说,也没有多么高明的地方。我只是考虑,为什么《西域水道记》会在这样大一统的时代出现,跟徐松的一些个人经历有什么联系?类似这样的问题,我想只能通过细节的研究,通过纯文献的研究,从细节信息里去找答案。
至于为什么研究徐松和《西域水道记》,还是因为其重要性。研究西域历史、西域史地,《西域水道记》是绕不开的著作;研究传统的中古史,徐松也是绕不开的人物。我们今天谈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如何具有学术意义,因而多讲了他西域史地方面的成就,但事实上,徐松被贬流放应该说是他人生中的偶然事件,因为被流放新疆,使得他在西北历史地理方面有如此重要的成绩。即使不被流放,徐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贡献也很大,《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宋会要辑稿》、《宋中兴礼书》等等,研究唐宋这些也都是绕不开的。

至于我个人对他的研究兴趣,是因为过去我从事唐代文学的研究,用过徐松的《登科记考》,那时候就对他有兴趣。后来研究西北史地,那不可避免地就接触到《西域水道记》,而关于徐松的生平考证研究,除了缪荃孙的两种书之外,就没有更多更新的内容了,由此我开始关注这个人。
徐松如何从湖南学政流放到新疆,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完整的档案记载。徐松这个人是很值得研究的,从他可以看到乾嘉学派是如何转型到近代经世学术的。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者。考上进士之前,他受过桐城派的影响,又因为他考据很好,所以他的老师就鼓励他往这个方向努力。他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进士,与他同年,也出了很多人物,比如李兆洛、姚元之、周济、孙尔凖、穆彰阿等。
入翰林院以后,嘉庆年间徐松参与编《全唐文》,他是提调和总纂官,这说明他已经进入中国传统学问的很高境界。后来,他做湖南学政,也是带着书、带着问题去的。再后来,他有机会流放到新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是仕途的一个挫折,然而对他个人学术和中国学问的转型来说,这是一件幸事。

徐松继承乾嘉学派朴学的精神做历史研究,做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近代,如何应对现实,从乾嘉学术到经世致用学问的转型,徐松是首当其冲的人,《西域水道记》就贯彻了这样一种学术精神。
澎湃新闻:《新疆图志》是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地方通志,1907年开始编纂,1911年完成。跟徐松一样,主持编修《新疆图志》的王树枏也是一位极具眼光的学者型官员。简单介绍一下王树枏和《新疆图志》。
朱玉麒:王树枏是清代新疆倒数第二任布政使。早年他在河北保定莲池书院受教,李鸿章是他的引路人。在李鸿章时代,他就参编过《畿辅通志》。王树枏比徐松看得更远,他觉得崛起的西方非常重要,他在甘肃任官前后,就写了《欧洲族类源流略》《彼得兴俄记》《希腊春秋》等著作;在新疆主政期间,他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机器设备,推进西部近代化进程,多有建树。

王树枏在新疆时,与当时陆陆续续来到乌鲁木齐的西方探险家都有交往,比如伯希和、莫理循,还有俄罗斯的语言学家马洛夫等。莫理循在他的游记中就清楚地记载说,这个大学者已经编成了9卷方志。地方志是中国独一份的文献资料,西方没有,他们称其为地方百科全书。清末新政以后,新疆进行了诸多改革,但缺乏一本近代的通志,所以1907年在王树枏的主持下开始编《新疆图志》,而且王树枏亲自领了几种分志,自己编修好,再让其他人照着他的样子做。
跟以往不同的是,这部《新疆图志》非常关心当代新疆问题,交涉志、国界志、实业志、民政志等,都突出反映了当时代的现实问题。比如,警察、咨议会、近代学校,这都是清末新政提出来的内容。另外,关于国界问题可谓是浓笔重彩,而且已经不再采用以山川来粗略地说明国界。什么时候划的界、为什么这么划界、曾纪泽时代在划界问题上有什么失误、原本国界线应该在哪儿、现在国界线在哪儿,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都有谈及,近代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白地呈现在那儿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人开始往中亚、新疆探险,乌鲁木齐就成了一个都会,很多西方学者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一个中西交流的桥头堡。这些西方学者在跟北京、上海的学者对话之前,最早到达的地方就是乌鲁木齐,而像王树枏、杨增新这样守土一方,有文化、有眼界的知识人也主动接触这些西方人士,交流沟通,这对于双方的知识领域扩大,都有很大的益处。伯希和就是在乌鲁木齐通过跟当地学者的交流了解到敦煌文书并形成最初的判断,也从那里开始了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中国文化的漫漫长途。所以,关于《新疆图志》想说的就是,从中原王朝看新疆的地理位置自然是僻远,但若是以文化来考察,就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了,《新疆图志》的编纂,借助这个古老丝绸之路的近代内陆交汇点、借助清末新政下新疆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成就了晚清中国地方志的光辉灯塔。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