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唐颖:一个世纪前中国女性的生存和努力
上海的南昌路上,有条弄堂叫“环龙邨”。“环龙”是一名法国飞行员的名字,上个世纪初这位飞机员因为飞行表演摔死在上海,早前南昌路还因为纪念他而被命名为“环龙路”。环龙邨的建筑风格属新式里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楼高三层,安装了煤气灶、抽水马桶和浴缸。1949年前,整条弄堂住满了白俄人,他们在相邻的淮海路经营一些小商铺为生。后来,这些人陆陆续续搬迁回欧洲,给上海留下了一路的异国风情。

秋日的南昌路
作家唐颖就出生在这条华洋杂居的“环龙邨”,童年的她目睹过因时代变迁而被放逐的白俄家庭往事,也将从弄堂里走出去的上海女人身影印刻在心里。弄堂的热闹是表象,许多故事渐渐从那里深处浮现。唐颖沉醉于打捞被时代洪流淹没的个体生命,写完《上东城晚宴》、《家肴》,这次她将对女性的追问与质询放置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出了一个“洋泾浜现代”的上海故事——《个人主义的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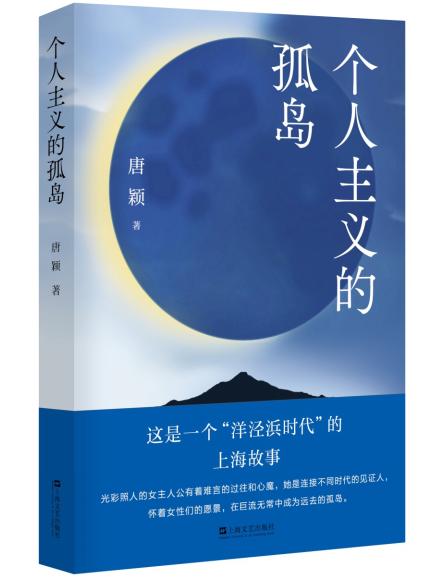
《个人主义的孤岛》书封
《个人主义的孤岛》是唐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发在《收获》长篇小说2020秋卷,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借新书出版之机,澎湃新闻专访了唐颖。
《个人主义的孤岛》以江南女子明玉的个人命运为线索,贯穿着历史维度,经纬交错,再现了上海1990年前形态各异、散发着声响和温度的立体生活图景。明玉出生于破败的江南水乡,逃出被贩卖的命运后进入上海街头戏班,出落得声色婉转立于戏台上。国民党元老赵鸿庆将明玉从戏班赎回娶回家,却一言不合拳脚相加。随丈夫东渡日本接触新文化后,明玉的自我意识开始生长,并结识了日后再见于上海的革命青年李桑农。而明玉在丈夫老家湖州邂逅的宋家祥是另一类人物,他对生活的考究超过对时政的关心,在乱世中独守,成为明玉生命里的另一抹色彩。

《收获》杂志为《个人主义的孤岛》所配的插画
1930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一座信奉“个人主义”的“岛屿”,它岂止是包容了向往现代文明的中国内地人,因缘际会中,它也庇护了世界上流离失所的各民族的难民,从来自中东、欧洲的犹太人群,到来自旧俄罗斯的白俄。“岛屿”上汇聚着叱咤风云的西欧冒险家和商人们,还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孤岛”是一座社会大熔炉,虽然危机四伏,但在现代文明的大秩序中,多民族的人群在这里融合,碰撞,互动,从而相互理解,和平共处并相互依存。唐颖从明玉的视角出发,让读者瞥见上海城市文化基因内相互缠绕的前世图谱:中国传统的江南,西欧,东欧,犹太,日本;旧封建专制和共和国,古代和现代,科学民主文明和愚昧黑暗暴力。
而在“孤岛”中努力寻求个人生存的中国女性其实是一组群像,除了明玉,还有金玉,阿小,广慈医院的女医生,美玉,属于后起之辈的心莲,朵朵。她们在世界万花筒中共时存在,各自求生;她们站在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多元的社会相处互动;也以不同的路径,和明玉的生命相互牵连。“孤岛”见证了一个世纪前中国女性个体的生存努力,摆脱封建,性别,经济压迫,实现向现代性转变的历程。
“明玉”是唐颖小说中第一个作为主角的旧时代新女性形象。“在我小时候,就见到过很多这样充满智慧的女性,她们可以在保守的年代里冲破樊篱,审时度势为自己做主,这种现代性和先锋性甚至超过当下。”唐颖回忆,2012年她在北京资料馆看到了朋友张真放映的一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默片《银幕艳史》,电影情节大致是女明星被富家公子引诱而抛弃演艺事业,又不可避免被富家公子抛弃,最终从破碎家庭挣扎出来重新回到片场走上独立之路。多年过去了,唐颖依然记得当年观片后的兴奋,难以置信那个旧时代时期的默片已经具有现代性,在封建礼教束缚严厉的社会环境下,却出现了这样一部具有现代女性自救精神的电影。
令唐颖印象深刻的是女主角的字幕台词中还有着诸如“男人都是蜡烛”的上海俚语。“这种俚语到现在上海年长一些的女性还在用,可见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这样的日常细节展示,相比那时候的民国小说更有质感更有说服力。值得警醒的是,当下种种关于‘女性美’的丑陋认知,正在毒害新一代女性。这种倒退现象,使得旧时代的新女性更值得关注。”唐颖深感写历史女性,也在映照今天的女性。沦陷或自救,无论哪个年代,都会发生在女性身上。
小说的副线呈现了一群生活在明玉周围的白俄。唐颖年幼时和白俄做过好几年邻居,公用一个卫生间,父母那代人当时称白俄为“罗宋人”,带了一些贬义。当时有少数俄国人永久生活在了上海,或娶或嫁了上海人。弄堂里,唐颖朋友中就有这样的混血儿。《个人主义的孤岛》开场就是由一个惊悚离奇的雨夜开始,中英混血小格林受伤被丢弃在海格路公寓门口,从此小格林和已故生母金玉的鬼魂再也没有离开过故事主线。
纽约大学电影学学者张真曾在与唐颖的对话中指出“白话现代的定义重要的界面是一种基于本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在上海(和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可以称之为‘洋泾浜现代’。”
唐颖很喜欢这个“洋泾浜现代”的定义,她认为这也正是民国上海这座早期移民城市的特点,“上海容纳了来淘金来谋生来亡命的各族和各地难民,呈现了晚清民国上海华洋杂居的跨文化风貌。明玉所生活的这条弄堂,便呈现了一种民间的国际化状态。”
或许正是这样的“洋泾浜现代”土壤,催生出独一无二的海派文化,给予了人们更多可能和选择,让明玉成为连接不同时代的见证人,怀着女性们的愿景,在巨流无常中成为远去的孤岛。

唐颖,以书写上海题材小说闻名,被认为是对上海都市生活“写得最准确的作家之一” 。著有长篇小说《上东城晚宴》《家肴》等,中篇小说集《丽人公寓》《随波逐流》,中篇小说《来去何匆匆》《糜烂》《红颜》《无力岁月》《不属于我的日子》《纯色的沙拉》。
访谈:
澎湃新闻:你这次把对女性的追问与质询,放在了革命频出的动荡时代背景下,这种政治身份的转移是个很吃重的议题,如何不被繁杂的历史背景束缚又不落入民国故事套子?你是如何把握这种平衡的?
唐颖:将历史背景推远,情节跟着人物命运走。无论什么时代,人物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关系、情感关系。无论时局多么动荡,民间的生活方式却是有传承的,这便给了我描述过去年代日常故事的底气。早在同治年间到清末,上海已被称为开放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风尚。在今天回看当年,我更关注历史事件中的现代性,提炼人物身上的先锋性。除了在建构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城市地理文化上下工夫,作为虚构小说,仍然需要回到严肃文学的复杂语境中,不让人物被时代大风浪遮蔽,让他们有更多的个人选择。所以,他们首先是带着自己前史、富于自己个性的城市市民,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是民国故事套子中空洞的革命者,或者是被标签化的底层民众。所以,这部小说在构思时,仍然把她当作一部城市小说书写,而不是历史小说。
澎湃新闻:小说中,“个人主义的孤岛”似乎有着两重指向,一是明玉的女性意识觉醒,二是宋家祥为代表的这类热在战乱中的自我坚守,可以这样理解吗?
唐颖:这部小说的开头,便有一段对租界西式公寓的描述“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的公寓楼,坐落在西区海格路,入口对着马路,四周无楼房,宛若孤岛,浓密的攀缘植物几乎盖住了公寓外墙。租客中有外侨、演员、金领、身份难辨的民国男女,单身,出身地不明,独门独户,自由来去……”
我虽然写的是建筑,却不无象征意义:城市人可以大隐隐于市。这类公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完全照搬西方建筑,是高级住宅,也代表了更为文明先进的城市人居住状态:没有弄堂,上下有电梯,很难形成“邻里关系”。人们在这类公寓中获得了社交独立,他或她不受原生家庭的制约也没有周围邻居的关注,保持了最大限度的隐私。今天出现的大量商品房,便是这个模式,你住了许多年都不知道邻居的名字和模样。城市人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从空间上与周围世界产生了隔绝。
我们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个人主义”曾经是个贬义词。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人们开始反省集体主义对于个人意志的裹挟,我们的语词里终于有了“个人”和“个性”。在我的小说里,“个人主义”是个中性词,我通过塑造明玉和宋家祥这两个人物,表达在时局动荡中,如何保持内心的原则和良知,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不随波逐流。然而,乱世的洁身自好注定是悲剧的,宋家祥的横死,明玉的流落他乡……“孤岛”是寂寞的,也是高贵的。
澎湃新闻:明玉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忍女性,也不是奋不顾身追求自由的自我革命女性。她的能干是毋庸置疑的,却不能简单用“精明”来描述;她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但隐忍和爆发的张力又使得她不至于堕入苦情的戏码。乱世中这种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相对少见,我可以认为,你对这个人物是十分偏爱的?
唐颖:明玉是我小说中第一个作为主角的旧时代新女性,假如说,之前的《家肴》也塑造了几个从旧时代过来的女性。她出生成长于上世纪初,那是一个相对落后、阻力更大的社会,毕竟满清推翻不久,所谓封建礼教束缚还很严厉的社会。明玉嫁给革命党人丈夫,在日本完成知识教育,她的履历便具有了先锋性。因此明玉背负了时代给予的责任,她身上的时代交替感也更加凸显。
我尤其要强调,女性们往往是通过生活方式去感受时代的先进或落后。所以明玉是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早年的苦难,往后丈夫的欺压,让她明白独立才有尊严,是女性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她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同时,她是个浑身浸透自卑的女子,没有骄傲和自恋的资本,她对生活的态度不敢懈怠,如履薄冰,却步履不停,随着时代变迁自身成熟不断刷新自我。
我深感书写历史女性,也在映照今天的女性,沦陷或自救,无论哪个年代,都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如今种种关于“女性美”的丑陋认知,正在毒害新一代女性,这种倒退现象,使得旧时代的新女性更值得关注,并让今天的女性反省。
澎湃新闻:小说中的女性关照也很动人,明玉与金玉的亦师亦友,明玉与阿小的互相帮衬,这些配角人物的写作灵感来源于哪里?
唐颖:在与戏班子结拜姐姐金玉的关系和身边女佣阿小的关系中,明玉凭本能找到了女性同盟。即使和情人宋家祥关系中,也能看出她对男性无法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我一直更偏爱女性创作的作品。在我的所有作品中,都有女性有意无意结成同盟的描述,当爱情遇到挫折时,女性是去找她的同性友人获得疗愈。在这本书里,侧面写到了绍兴戏班子,这类戏班子都是以女性为主,她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也是相当戏剧化的。小说里,通过明玉和金玉的关系,刻画她俩之间不那么甜蜜却是非常深刻的同病相怜。明玉和女佣阿小之间,更是亲如家人,相濡以沫,这段关系,是小说中最温暖的部分。
我对女性之间的友情的刻画,也表达了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感受女性互相支持的力量是多么重要和不可或缺。
澎湃新闻:故事的开头,就由梦境与金玉的魂魄,将明玉的过去牵领出来,其后也贯穿了故事,你是如何想到用这样的写作手法?
唐颖:是想给故事增添色彩和悬念。我当时并没有把握是否被读者认同,发表后得到的反馈都很正面。一旦打开这个被称为四次元的空间,我的想象力可以飞得更远,我正在写的小说中,这种奇幻色彩更加浓烈,也给我的写作带来兴奋。
澎湃新闻:在小说的后半段,明玉与宋家祥情感的“止乎礼”,叫人怅然感慨,你为何塑造这样“克制”?算是一种女性力量更完整的呈现吗?
唐颖:说到先锋性,明玉和宋家祥的关系是非常现代的。其实,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走在时代前端。他们是情人,却预知彼此没有婚姻前景。尤其是明玉,作为旧时代女性,却在两性关系上有着新女性的态度。她爱宋家祥,尊重他的不婚主义,“爱”是过程,“结局”重要也不重要,假如索取“结局”,而影响过程,是不明智的。这段关系,更能完成明玉的“独立”性――不要对他人期待,期待就会失望。
澎湃新闻:通过明玉的视角,你也圆满地完成了几位男性形象的书写以及日常与革命的关照。尤其是赵鸿庆和李桑农,革命无疑赋予了他们英雄色彩,但他们身上有着极其明显的两面性,能否谈谈你对这两位人物的塑造目的?
唐颖:满清之后的国人他们是否跟着时代更替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尤为关注的,包括早期革命党人,他们在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两面性,也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国民性。赵鸿庆身为革命党人,却仍然无法摆脱已经渗入基因的封建劣根性。他追随孙中山,参与了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回到家仍然是个清朝男人,对妻子随意打骂,没有任何平等意识。所有的口号都是装饰,唯有在个人生活里,才能知道人物最内在的本质。这类人物,在今天仍然遍地都是,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在行为方式上的南辕北辙。因此写赵鸿庆也同样是映照了今天的男性文化。
而李桑农则更复杂一些,他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多么富于感召力,“平等”这个词是他身体力行开启了明玉的心智,他的理想是富于人性的,所以感动并影响了明玉整个人生。中年的李桑农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也许更坚定,但同时,他身上温暖的光芒被更冷酷的坚强替代,他不再有“自己”,只有“事业”,当他为“事业”奋斗时,其初衷却被异化,他让明玉感到陌生甚至畏惧。
澎湃新闻:宋家祥这个人物很难写,写坏了他就是如今被鄙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在书写这个人物时是如何把握这种平衡的?
唐颖:从某种角度,宋家祥是一个更有悲剧感的人物。他是消极的,因为他明白个人无法掌控时代。人生苦短,他不想让自己的生命被乱世消耗,因此他必定会选择自保的人生。似乎,他对“咖啡是否纯正,奶油的新鲜度,超过对时政的关注”,其实只是表象。他的不婚主义,摆明他对现世的悲观态度。他对明玉从来不直接表达感情,然而从他留下的遗嘱,才能知道他对她深沉的感情。至情至性的人,一定不会被人鄙薄。
澎湃新闻:白俄难民来沪的历史并不常被人重视,你在书中多有塑造,能聊聊白俄侨居对上海经济文化的影响吗?
唐颖:据说1949年以前,南昌路这条弄堂几乎都是白俄人,之后陆续搬走,我们居住的这栋楼的白俄离开最晚,他们是一对夫妇。妻子叫丽丽,当年她的母亲带着她从哈尔滨过来。她丈夫是俄裔犹太人,在她离去后,他独自留在上海,后来因为与女性有交易关系而被驱逐出境。事实上,还是有少数俄国人永久生活在上海,他们或娶或嫁了上海人,弄堂里,以及朋友中就有这样的混血儿。
白俄当年在霞飞路(今天的淮海路)开了很多商铺,包括咖啡馆面包店,带来了欧化的生活方式,繁荣了法租界。他们中的艺术家们,为了生存,开办舞蹈教室,教授各种乐器,为上海这座城市培养了艺术人才。
我在小说里描述他们的一些细节,其实都是来自真实生活。我一直很想写写他们,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载体。也算是等了二三十年,才找到机会,在这部小说中我让明玉生活在“罗宋人”中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氛围。从心理层面,明玉被原生家庭抛弃,也充满了无根的漂泊感。同时,这也正是民国上海这座早期移民城市的特点,她容纳了来淘金来谋生来亡命的各族和各地难民。明玉所生活的这条弄堂,便呈现了一种民间的国际化状态。呈现了晚清民国上海华洋杂居的跨文化风貌。
我很喜欢张真对“洋径浜现代”的定义,是上海这座城市国际化在民间的体现,不识英文的老百性,也会说洋径浜英文,同样,不识中文的老外会说洋径浜中文。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