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年喜 | 我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镜相栏目独家首发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编者按:
陈年喜,1970年生,陕西商洛丹凤县人,1999年开始从事爆破工作长达16年。2013年底写下诗歌《炸裂志》,因而受邀拍摄纪录片《我的诗篇》。2015年8月出版诗集《炸裂志》,同年11月,《我的诗篇》播出。其后他作为“矿工诗人”被人所熟知,受邀前去哈佛耶鲁等美国高校演讲,并数次登上央视舞台。
2021年6月,陈年喜出版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文 | 桑丘
采访陈年喜老师之前,我在他朋友圈看到:“昨天到今天,我妈打来好几次电话,说家里的玉米让野猪糟蹋完了,问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野猪是保护动物,谁动了它是犯罪的,本地因为有人对动物不敬已经被抓了好几例。人啊,各自求福吧。”我不能像看到其他不幸的消息一样,留下“平安”。在面对真实生存的窘迫时,这两个字太轻了。生死之外,还有“生存”这件大事。
采访途中,他一直在咳嗽。“爆破工”“命悬一线”“贫穷”“尘肺病”,这些词汇像山一样压过来,由远及近。可终究因为隔着文字,透过屏幕,远在咫尺。只有咳嗽声是鲜活的、无处遁逃的,必须直面的他人的痛苦。

陈年喜新书《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陈年喜出生在大年三十夜里八点,算命先生没有细算,就说:“这个日子出生的人命不行。全世界的神和人都放假了,谁也顾不上你,只有自生自为。”
他从来不信命,人到中年,回想起母亲向他转述过的这番话,竟觉得一语成谶。
他从来没有单独过过生日,都是和过年一起过的。唯一一次是在2016年北京冬天,他一个人住。远近的小店、超市都关门了,屋里只有一包泡面,他一个人煮了,算是一次庆生。
过年家里会做五六个菜,配上米饭。酒足饭饱,烛光熄灭后,妻子偶尔会想起来,对他说:“又长一岁了。”对于传统恪守农历历法过日子的中国人来说,这话像是余下日子的一句双重隐喻。
一:长期不见天日,地下看惯生死
“我们这儿人烟非常稀疏。沿着河有一条公路,受河流的影响,一发大水就会吹掉。从小的时候就记得,人们把它修建起来,再发大水又吹掉了。就是河流、土路、公路不断的博弈。”
他们住在山坳的某个地方,稍稍宽一点,住着三五户人家。再走几公里,又一个地方稍稍凹进去,能宽敞一点,也就住个五六户人家,每个人家和每个人家都离得很远。“就像我们看的那个糖葫芦一样,非常稀疏的形状。”
他从小生活在陕西的丹凤县,襟带丹江。“这些人顺着河流很长很长地分布在两边,就是沿河而居,沿路而居。”不同于黄土高原的粗犷壮丽,这里的人哼山调民歌,如同远在南方的湘西。山上的通讯靠吼,谁喊一嗓子都很远很远听得到。没有电话、没有通讯设备的年代,就是靠这样用来传达彼此的消息。
“汉江流域,特别喜欢唱山调,有船的地方就是船调。其实我们那也是有的。我们就是山调孝歌这类的。长辈还有同龄的人呢,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很多都喜欢唱一唱,在山上一个人唱,很远都听得到。这边山上也会有应和,他们也会唱。”
那里的人最喜欢唱——“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来头.....说声走了就走了,万贯家财都不要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面对死亡的那一天,死亡对人的影响。悲伤时,生而无意义的虚无感在人身上都是相通的,无论贫富贵贱。当然也有欢快的调子——
“在我们老家我就记得。他们有一个歌词就特别细,特别好听,《英台闹五更》。梁山伯死了之后,祝英台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段回忆他们在学堂的生活。有一天夜里,从一更唱起,一直到五更,天就亮了。哎呀反正唱歌是常态,也有很欢快的,也挺悲苦的。”
山歌山调深深滋养了他。简简单单的曲调、质朴自然的歌词。“我有时候会想,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会沉入其中,沉淀其中。对一些历史桥段的了解就是从这认识的,而不是通过书本。这其实包含着很多的人情伦理,包括整个世界、命运的认识在里面。人群的性格、个体的性格,从这当中都可以看到。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甚至很丰满的东西。”
他写矿友王二遇难而死,竟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日子。二人初次相识,便发现彼此性格迥异。同是远在矿山,妻儿分离,交谈甚欢时,王二开始唱起《四郎探母》。两人触景生情,竟然一一哭了起来。回想着此情此景,自己也唱了起来——
三更里英台怨爹娘,
只怨爹娘无主张,
不该将奴许配马家郎。
梁兄待我恩义广,
我待梁兄空一场。
可惜他身边早已无“王兄”。

纪录片工作人员在工地取景
干爆破是个把命拴在安全帽上的工作。进工地之前,就得做好一直往里走,无法回头的准备。一天十来个小时,不吃不喝。运气好的时候,能带一瓶矿泉水,一个苹果。进入大山一路纵深,五千、一万、十万,靠人一步一步走过去,一步一步打穿。稍有不慎:垮塌、缺氧、空洞、冒顶透水、机械故障,任何一个小环节都可能出事故。
他每天早上醒来,进矿山,晚上若能平安回家,就松了一口气。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也麻木了。
“上班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还是打着一个小算盘。哎呀今天可别有什么问题。因为对于里面任何一个情况,是你没办法估计的。几十年当中,也是每时每刻想离开,但离开矿山,你到另外一个陌生世界怎么办。别的行业,完全是陌生的,你很难去回头。两三年家里没有收入怎么办。这逼着我们必须一天一天在这个行业往下走。”
做爆破工经常要换工地,每新加入一个工地,爆破资格证就要重新考。“从炸药的性能,炸药的使用一直到任何一个状况的排除,是成系统的一个东西。”他是他们当中持证最多的爆破工,前前后后考了十几个。有时候工地老板和他们说,这里有个活儿,好长时间没人干了,你们来吧。他和工友一去,发现洞顶贴着一张驱魔符:黄宣纸,红朱砂,曲曲弯弯的符号,看得人心发怵——他们心里知道,这里肯定前不久出了事故。但既然来了,就无路可退,只能提心吊胆地往下干。
“任何一个故障都可能耽误时间。八个小时本来可以拿得下来,你甚至有时候十五个小时都拿不下来。但是你不可能下去。后面跟着那十几个出渣的工人怎么办,老板怎么办呢?所以需要我们要超强的韧性。”最长的一次,他连续十五个小时没有喝过一口水,吃过一口东西。长年呆在矿山下,照不到太阳,皮肤是泛着石灰色,没有血色的白。
也许是长期不见天日,却在地下看惯了生死,写到工友的死亡,他异常冷静:“王二是死在我手上的,也是死在他自己手上,我不该不小心窜了孔,他不该把导火索弄得太短。但死,这是迟早的事,谁也没有办法。”那场事故后,他右耳失聪了。从此世间的很多声音,都要绕一圈,再模糊传到他耳朵里,随风流失了。
陈年喜手机里有一个京剧的播放器,没事他就打开听两段,在心里哼唱。他最喜欢的唱段是《野猪林》,李少春唱——
“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
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
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
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
“林冲人生的悲剧性和我自己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生活的年代,命运是不同的。人生在茫然无助的一个寒冷的冬天,那个状态其实和我在矿山很多的一些细节很相似。我们在矿山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扛着一个一个的工具。和他独自前往山神庙的那段,还真是有很像的地方。”
矿山经常出事故,每隔一两个月,这里或隔壁矿山,总能传出哪里出事了,哪里又死人的消息。老板有的也很穷,出了事就跑路,一点钱也没有,就连老板没什么可赔给矿工。整个矿山工伤死亡的赔偿全靠运气,所以工人特别凄惨。
他亲手处理过一场事故——妻子的弟弟那年在山西铁矿死了,他过了风陵渡去了山西,整整处理了十天都谈不下来,那边始终不肯松口——从2万、5万、8万,最后谈到13万,算是把这事了结。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他谈起来记忆犹新——“那个岩石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方,已经很松软,我和我弟弟在前面,工作中没有了水。我们立马判断一定是中途或是一定某一段出了事故,立马就出来。”他们出来的一瞬间,就听见身后的巷子垮塌了。回头看,垮下来的岩石把他们的水管完全压砸断了。“我们赶紧跑开,在跑开的一瞬间上面又塌下来,整个巷道几十米长全都切断。”
如果他的警觉不够,没有经验,稍稍慢一步,就会彻底被困在里面。“一整个巷道垮塌的话,里面氧气更加少。你很难支撑几个小时。垮塌的岩石需要外面的人处理掉,你在里面会才会有空间相通。”但处理一堆乱石需要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人命没有定数。
爆破工这行,他干了十六年。离开工地后,他开始写作,2011年,开通了博客。2013年,母亲因食道癌重病,当晚,他彻夜难眠,写下《炸裂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里落满灰尘。”
如同沈从文离开湘西后才开始写湘西,陈年喜离开工地后,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回溯那段生活。矿山十六年,他惊讶于人强大的韧性——孤独的环境中,不断思考每个群体的生活条件,各自对抗生活的方式。为什么会形成、延续,像香火一样代代相传。“这多年的生活切身感受就是,人在茫茫大地上颠簸流离的过程。它形成了你对生命对自然甚至对万物一种认识在里面。可能我们说它不是很科学的,但它至少是真正真实的,以现实大地为基础的,以生命为基础的架构起的,一个一个实在坐标。”
他们在矿山的机器常常会出问题,又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倘若厂家派技术人员来处理,来回十几天,时间是耽误不起的。他们当中有的工友异常机灵,很快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立马就能恢复生产。“与他们相处,我觉得人生命其实是有无限可能,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偏好,甚至有自己偏执的地方。”
对他而言,矿工十六年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座富矿,值得书写一辈子。“当我去努力去回忆那些细节,有些东西是变得很像今天发生的事,怎么去追求一种真实。这甚至就是我整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完全刻在我血肉里面。”
在他心里,虽然人与人的生活不尽相同,但根本的无助、孤独、融合世界的隔膜、与生俱来与世界的距离感——这些却是相通的。也是他书写的追求,根本所在。
后来,他在贵州一家旅游社做过文案策划,用他的话来说,主要工作是“给企业吹牛”。清闲的文职工作并未给他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没用,回到老家聊起来,大家还是在比谁挣得多。”三年后,他辞职了。这些年,他拍过工人生活纪录片《我的诗篇》,参加了真人秀栏目,录制过《朗读者》......逐渐名声大噪,写作带给了他另外一条人生路。他自认为前期的写作没有太多意义。但因为整个矿山生活对人生的压抑,使得他对整个世界、对人命运自身,对外部,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了。”
他决定居家务农,以写作谋生,与此同时,检查出了尘肺病。
二: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陈年喜朗诵自己的诗歌《炸裂志》
他从小就是爱读书的。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订一两本杂志,民间文学、古今传奇,也有报纸。小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甚至连电视都没有普及。很多家里还藏着古老的线装书,走出门,时不时听见山头放歌声。
一本书在村里不断流传,几乎村庄里每个人都看过,这本看完,马上去下一家借,再还给上一家。“那时候我在朋友家借了一本封神演义,挺厚的,但是他只给我一夜的时间。我就点着煤油灯,那时候没有电,点着煤油灯一夜把那本书看完。整个灯光也调得很大,亮度要够。哎呀,那个烟就挺大的。早晨起来的时候,两个鼻孔全是黑的。”
过年的时候,家家会做手工面条,很细、很脆,要用一层一层报纸包起来。报纸平日里攒着,攒多了,过年时留着用。他就跑到别人家里先借过来,“别糟践了”,一两百张报纸读完了,再给人还回去,“现在可以用了。”
这份习惯一直戒不掉。做爆破工的日子,有时下班后,他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贴满了报纸,读完一张,往墙上泼水,揭下来,再读另一面。
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莫言,那份依照乡村童年而非教科书建造起的独特生命观、历史观,让他倍感亲切。《生死疲劳》里写月亮:”那晚上的月亮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这晚上的月亮是从河水中冒出来的。这月亮同样是胖大丰满,刚冒出水面时颜色血红,仿佛从宇宙的阴道中分娩出来的赤子,哇哇地啼哭着,流淌着血水,使河水改变颜色。”像极了他许多篇回忆录的结尾,写道赤红的稻田、山歌和夕阳。
“有些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对人进行一个个简单的符号化。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按照先入为主的认识来刻画人物。”人是复杂的、难以一以概之的。正因如此,他对刻板化印象的书写弃之如敝屣。
读高中毕业之后,大家还是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你参加劳动,家里首先要有粮食吃。第二个盖房子。房子盖起来,家里介绍女朋友,结婚娶妻生子,这样一个一个生活步骤。人生呢,他就是这样一个流程。”一盖房子,所有家人都在干。比较大的活,就是一个两个、三五个人干不了的,村里人来帮忙。那时候,你给我帮忙,我给你帮忙,都不需要工钱。家家户户,就像亲人一样。
陈年喜的初恋其实是一位城里姑娘。那时候,心里依稀还抱着和城里姑娘结婚,改变自己乡村出身的命运幻想。他给城里杂志投稿,上他们办的函授班——把自己写的稿子寄过去,编辑修改后邮寄回来。当时他报的是四川泸州的学习班,每个人15块钱,修改半年。比较优秀的作品,选入报纸上发表。通过这种方式,他认识了一个吉林的笔友,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
九一年冬天,漫天大雪,女孩来信,让他来她们家。他带着一本地图册,翻山越岭,到河南洛阳搭火车,再到北京,最后一站是沈阳,路程大约四五天。一出车站,零下二三十度,冷得完全没办法走路。他在她们家待了三天,感觉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她们家呢是个工人家庭,住在一个棚户区,一个特别矮的房子里面。我去的时候腰伸不直。她们五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通铺,用柴把那个炕烧热,冬天就是那样取暖的方式,房子特别特别小。”除此以外,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也是一座无形大山。“我是一个没有户口没有职业的人,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去生活。我两天都没怎么说话,一直很苦闷这个事情。”
整个冬天东北非常冷的,冬天所有的厂房企业都会停掉,没有养活人的出路。陈年喜很犹豫,他问:“平常我们生活怎么办,我靠什么挣钱?”那女孩很坚决,说:“我是有工资的,我可以养活你。”
陈年喜摆摆手:“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靠你养活。”他回家了,此后他们一直留有联系,依旧是靠写信的方式。他写给她七天才到,她回信也要七天才能到。一封信如他当初一样翻山越岭,来回十五天。“那时候写的字是在稿纸上,非常的奇异,哪怕写十页的信纸,都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个字是改过的。”后来,想起这段往事,她还和他说,你年轻时候字写的真非常漂亮。
那些信他们一直保留着。直到有一年,女孩所在城市里发大水,把信都淹了。而他这里的信,也在不断搬迁、整理中遗落了,不知去向。
29岁那年,他结婚了,算是村里成亲晚的。结婚照花了一百多块钱,裱好了,挂在客厅里。
1999年,如家人所愿,他做了工人,那个年代风光的职业。最开始,他与妻子半年见一次面,后来是与儿子,半年、一个月、十个月......间隔的日子如一根风筝线,收放着远处工地的讯号,爆破的烟雾是不断归去的号角。每次回来,匆匆一别,不过两天。他在地下爆破,不闻世间事的日子里。儿子慢慢长大了,他不愿叫他爸爸。有时在家待上一两个月,渐渐混熟了,儿子才愿意改口,叫上一两声。“家庭是唯一的大本营吧,依托家庭,我们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没有家庭的话,自己所有的奋斗努力其实是无意义的,人就像飘蓬一样。”
儿子念大学要参加绘画艺考,考了两年。第一年差三分,第二年差一分。为了妻子陪读,给他报学习班,他前前后后花了八万——他两年多的收入。第三年,儿子去念了大专,工程造价专业。为了保持和儿子联系,他把每月一次的生活费,换成每周一次打过去。
他的咳嗽已经很久了。其实不是没有预兆——2016年夏天,在北京的青年公寓,同行的一位摄影师记录他的日常生活。后半夜寒气入背,他被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咳。做完颈椎手术才一年,咳起来震动得更疼。孩子正读高中,正是家里最花钱的时候。他却就此知道,再也无力去矿山挣钱。那晚,他带着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去社区诊所买咳嗽药,大夫说,当地户口才有医疗证,否则买药要贵一些。他听后无奈,只得作罢,悻悻而退。
许多工友都得过尘肺病。尘肺病有五到十年的潜伏期。从1999年上山,到2015年夏,整整十六年。
2020年3月23日,连续咳嗽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决定去检查身体,拒绝了爱人一同陪同的要求。结果令人惊愕,却又在意料之中——果然是尘肺病。
“终于轮到我了。”他心里想。
“人生的所有的理想,所谓的梦想。到这个地方戛然而止。人生到这里,走到一个断头的地方。我对写作还是有非常多的想法,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空间的无限长度。因为这个病,所有的路到此为止,当时确实是非常悲怆的。我也没打算告诉谁,告诉家人没用,她不懂,也有压力。所以也没告诉我的爱人和孩子。”
等到那天天快黑的时候,他把这个事告诉了《我的诗篇》的导演,他们是多年的朋友。
“但死,这是迟早的事,谁也没有办法。”他写矿友的死如此说道。他目睹过很多工友得这个病。尘肺病末期的状况,他是知道的。这些年他书写了很多死亡——工友干了两年,待到结账的时候,老板自己从小三楼跳了下来,账就成了死账。前几年,那位工友又买了三轮车,包了一片伐树林。有位雇工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他把三轮车卖了,也没能赔够人家。他还为当年帮忙讨债的妻弟写了一篇悼文——《表弟余海》,引言里他写:”这些年,每写下一个人物,我就死一次。”
那个表弟同样是患了尘肺病。
这是不可逆的病,只能跟死神抢时间。随着病情加重,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医院临走那天,医生在单子上叮嘱道:营养跟上,别感冒。如同字一样轻飘飘的,龙飞凤舞,无关痛痒。“尘肺病不是要命的病,要命的是并发症。我问往什么方向并发,他说不知道。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每个月需要三千元的医药费,我把四类药减去了。既然有无数种可能,有什么能堵得住呢?”
三:如果没有尘肺病,我要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

陈年喜近照(与作家袁凌等人)
2015年,《我的诗篇》播出以后,他一炮而红,很多人因此知道了陈年喜这个名字,知道了新工人文学,随后知道了《炸裂志》。他受邀前去美国,在哈佛耶鲁演讲;参加综艺为歌手填词;应澎湃镜相的邀约,着手写作非虚构文学;记者不断上门采访,到他家乡和他一起记录他的生活。
每个人都想抓紧记录他的苦难,日复一日,似乎如此可以抵御洞穴里冗长的、无人问津的时光。可是眼前人生活浓缩的血肉,却远非寥寥几笔的文字和镜头可以触及。自我消化的岁月里,它们塑造了他,一切边缘外的笔触,只能贴近勾勒他成形的、溢出的部分。
到美国的第一天,他到了帝国大厦,心里想:“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很多我挖出的钢?”
他很排斥这些奢侈的东西,觉得这是人对自己不自信的产物,是为了表现自己无限强大而理想化的东西。
“它一定是通过我这样底层的人来生产材料,才有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他:“人类强大是干什么,往哪儿强大?我们甚至为了所谓的强大而不惜所有的牺牲。”他说:“其实我自己也很茫然。这好像就是一种自证,自证我很强大,其实人类很多东西他是很盲目的。”
他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一天,走马观花一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到了很多的城市,也到了七所大学,到了旧金山工人码头,也接触了很多的人,又到了贫民窟。他并没有感觉到触动,或是和原来的生活有太大区别。反而是文学交流给了他异样的欣喜——“我原以为工人诗歌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度来说,他们绝对是不了解的。但在交流当中,他们参与度恰恰非常高,比国内都高。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呈现的生活场景既熟悉又陌生。虽然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大家还是有共识,可以探讨的。”
回国几年后,检查出尘肺病,他便辞去旅游文案策划的职务,回到了陕西商洛老家。偶尔有记者上门,和他与妻子一起吃喝同住,写下稿子再匆匆离去;有时他会去北京,成为纪录片下一部系列的主角。除此以外,生活并无不同。政府给他家在县城批了一套搬迁房,他平常住在这里,阅读、写作,买自己的书回来,签名盖章包邮发出去,每一本赚几块钱的差价,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
妻子在老家务农,前些年种小麦,这几年主要是粗粮。她心细,每一块土地都要填得平平整整的,再种下去。“哎呀确实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干什么都是。土地本身就是很贫瘠,它就不长庄稼,种什么都一样。”农忙的时候,他会回老家帮她一起种地。老家没有发快递的条件,要去二三十里的镇上,发快递也非常贵。县城有快递点,还有网络,满足他赖以为生的阅读与写作,所以他留在了县城。“其实还有很多可写的东西,哎呀主要自己懒散,身体不太好。这两年写得特别少。”
2021年6月,他出版了新书《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就是我的人生。”但其中,他最喜欢的作品,却是附赠小册子里的一首诗——《火车穿过2004》。
“K1043次5车45号
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
这穷人的绿皮交通工具
在你离开若干年后开进了历史
你下葬那天
我在另一个省份下葬
你葬于一座山岗
我葬于一场大病”
这位诗的主角,是一位叫江子的朋友。从前,遇到记者和他讲起火车上遇到的工人,听到一些细节,他都能准确分辨出他们来自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遇到他也不例外。他们相遇于2004年前往西安的火车上,因为命运相通,短时间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分道扬镳后,他继续开他的车,他回到矿山爆破。
“这个货车司机,也是在大地上颠簸流离。很多人感觉货车司机还是生活有保证的,甚至很浪漫的工作。其实在茫茫戈壁上,在非常艰难的道路上,很孤独开着车,去一个人克服种种困难,甚至很多恐惧,对于人抗压能力、生存能力、心理能力有很强的考验。一个货车司机,他也是无限丰富的,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种。”
后来他在卡拉昆仑河因为汽车的侧翻出了车祸,不治身亡。同年,他查出尘肺病。
“倘若没有尘肺病,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问他。
“去塔吉克斯坦。我去美国办了护照,所以过去比较容易。”我没料到是这个回答。
“其实我还有一个理想,我们有同伴现在还在塔吉克斯坦那边干爆破,同是三年90万。对于任何一个我们来说,真是个天文数字。我还想着最后的人生,去搏一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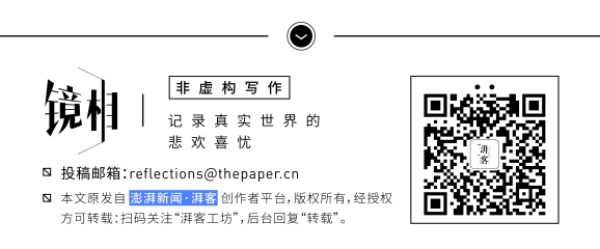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