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亨利·詹姆斯逝世百年∣礼仪斯文背后的保守唯美分子

1916年2月28日,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伦敦切尔西区的家中逝世,此时他已是英国知识界公认的文学泰斗,无论他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无法否认“詹姆斯式风格”(Jamesian)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名字衍生出的形容词,足以证明其别具一格之处的话,当年一些英国文人给詹姆斯取的雅号,虽不乏戏谑之意,仍从侧面显示出这位大作家的地位和影响力。根据詹姆斯的创作阶段、内容和手法的变化,他们分别称他为“詹姆斯一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钦定《圣经》的英译本)、“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和“老僭王”(the Old Pretender,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的一些拥簇甚至还自称Jacobeans(通常指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人物)。
文跨两洲,声名远播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7年10月18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的书评中,曾这样描述詹姆斯的创作特点:“在呈现往昔时,亨利·詹姆斯最为游刃有余。柔和的光线在过往中穿梭游动,连彼时最普通不过的渺小人物也浸润着无尽美妙。白日的强光所压抑的诸多事物的细节,在婆娑的光影中得以摇曳生姿。那份深沉, 那份浓郁,那份静谧,整出人生盛会的那份幽默自如——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他笔下自然的气韵和最恒久的意境,他那些以老迈的欧洲映衬年轻的美国的故事,洋溢着这种氛围。在明暗交错中,他以深远的目光洞察一切。”伍尔夫接着写道:“的确,要感谢美国作家,尤其亨利·詹姆斯和霍桑,给我们的文学带来对过去最美好的回味——不是说远古的浪漫传奇和骑士精神,而是在不久的往日中消逝的尊严和褪色的风尚。”
伍尔夫的评论不只捕捉到詹姆斯微妙细腻又深邃隽永的笔触,而且点明了詹姆斯特有的跨文化视角和犀利的审美眼光。她提到的詹姆斯的“美国”身份,与其说是一种国籍归属,不如说是一种宽广的文化维度。詹姆斯在1888年10月28日给兄长威廉·詹姆斯的信中曾写道:“我无法审视英国和美国的社会生活,或者对它们深有感悟,除非将两者视为注定融汇在一起的盎格鲁-撒克逊统一体,这种融合很大程度上势必发生,以至于执拗于两国的区别变得越来越乏味又迂腐;而且越是将两个国家的生活作为连续不断,或多少可相互转换,或哪怕只是同一个宏观对象的不同章节来对待,两者越是紧密交融。文学,尤其是小说,为这种必然性提供了一个了不起的手段,善加运用可有上乘佳作。”詹姆斯在这里不仅强调了英美两国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关联,也暗示了文学所承载的超越国家和地域限制的意义和价值。他坦承,“我期望我的创作方式在外人看来,已无法分清我在某一刻是个描写英国的美国人,还是个描写美国的英国人(就我对两个国家的刻画而言),这种模棱两可的特质非但不让我自惭,还让我极为自豪,因为它意味着高度的文明修养。”詹姆斯推崇的“文明修养”,显然包涵了不为自我和民族国家身份所局限的洞察世界的能力。
的确,詹姆斯常自称是“世界化的美国人”(“cosmopolitanized American”)。这位出生在美国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作家和自幼敏感的心灵,一方面深谙新英格兰的思想和道德传统,以及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很早就着迷于欧洲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貌。詹姆斯不仅熟悉当时美国社交生活中渗透的欧洲文化影响,而且早年随父亲和家人在欧洲广泛游历和旅居,在法国、意大利、瑞士、英国等地接受丰富的审美熏陶并结识文化和思想界名流,并在三十三岁时选择定居在英国(虽然他直到1915年7月因不满美国拒绝加盟英法联军才加入英国籍)。詹姆斯很快融入了伦敦的社交圈,并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多文化巨匠都有来往和思想交流,包括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罗伯特·布朗宁、马修·阿诺德、托马斯·卡莱尔、乔治·艾略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安东尼·特罗洛普等等。
此外,詹姆斯和长他十来岁的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就是伍尔夫的父亲,也交谊甚笃。詹姆斯著名的中篇故事《戴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最早即发表在斯蒂芬时任主编的文学杂志《谷山》(The Cornhill Magazine)上(詹姆斯同时也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英国旋即获得了巨大反响,也让詹姆斯在中产阶级读者中一举成名。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在自传中曾详述詹姆斯对斯蒂芬一家人的爱慕之情。1912年,两人在一次文化活动上偶遇,当詹姆斯得知伦纳德不久前刚刚娶了弗吉尼亚时,立即再次主动和伦纳德握手,还讲了一大通客套话,句句“错综盘绕,文辞华丽,还夹杂着大量插入语”,但对斯蒂芬一家“情真意切”。伦纳德还生动地描述了他从斯蒂芬的子女那里听来的关于詹姆斯的趣闻,说他们小的时候,詹姆斯常来家中做客。他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一边讲话,一边坐在椅子里往后仰。随着那些长长的句子一点点舒展开来,詹姆斯的椅子也慢慢后倾,这时所有孩子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把椅子,既担心又盼望着它失去平衡,把詹姆斯掀翻在地,可是詹姆斯几乎总能化险为夷。有一次,危机终于发生了,椅子倾倒,小说家摔在地上,但毫发无伤,不以为意,又继续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长句子讲完。
二十世纪初,詹姆斯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虽然他晚期的几部重要小说,包括《圣泉》(1901)、《鸽翼》(1902)、《大使》(1903)和《金碗》(1904)的行文越来越迂回曲折和艰涩晦暗,并包涵了大量抽象深奥的哲学思考,以致大众读者少有问津,但詹姆斯凭着这些作品已稳稳跻身于十九世纪小说名家所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他对小说作为一门艺术的深刻洞见和他的卓越艺术成就,也深深影响并启发着年轻一代精英对文学的理解判断和创作实践。小说批评史上两部早期的重要著作,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的《小说的技艺》(The Craft of Fiction,1921)和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1927),尽管论述侧重不同,观点也有所分歧,但两者都对詹姆斯的小说作出周详细致的分析,并突出了他的创作对这一艺术样式发展的重要贡献。现代学院式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奠基人之一利维斯(F.R.Leavis)在其名著《伟大的传统》(1948)中,将詹姆斯与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和约瑟夫·康拉德一道,称为英国小说传统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家。




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在致力于对文学形式的创新和突破中,其实也不断从文学传统中汲取智慧的养分。詹姆斯就是总能激发创作灵感的作家之一,比如同样出生于美国后来移居英国的现代主义诗人T.S.艾略特,还有美国著名现代主义诗人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都曾借鉴詹姆斯的名作《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创作过同名和主旨相关的诗篇。一个世纪以来,虽然詹姆斯和他的世界显得越来越古色古香,而且对每一代读者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但他从未离开过当代作家的视野,甚至被直接当作创作题材。戴维·洛奇曾将2004年称为“亨利·詹姆斯之年”,因为当年不仅有两本关于詹姆斯的传记体小说问世——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大师》、洛奇本人的作品《作者,作者》——兼之当年英国的布克奖得主、阿兰·霍林赫斯特的《美丽线条》,无论从内容(比如小说描绘的英国上层社会生活和道德危机,以及主人公正在努力完成一篇关于詹姆斯的论文等等),还是风格上,都显示出詹姆斯为文学创作提供的宝贵而持久的艺术和精神资源。

戴维·洛奇的《作者,作者》
妙尽幽微,所述纵横
当然,詹姆斯小说的诸多特性,也引发过不少争议和批评。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就曾指出,詹姆斯的小说形式虽美妙精致,但它们所呈现的世界却显得狭隘逼仄,它们关上了“生活的大门,把小说家留在上流社会的客厅中忙个不停”。福斯特尤其尖锐地批评了詹姆斯塑造的人物的种种局限:“首先,他只有一个很短的人物清单——一个试图影响情节发展的旁观者;一个二流的局外人;然后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陪衬角色,非常活泼而且通常是女性;还有出色罕见的女主角,《鸽翼》中的米莉是这一类型的完美代表;有时会有一个反面人物,有时还有一个性情慷慨的年轻艺术家,大抵也就这么多了。”福斯特认为詹姆斯的人物“不仅数量太少,而且束缚太多。他们无法享乐,或快速行动,或行鱼水之欢,英勇行为十有八九与他们无关。他们总是衣冠楚楚;折磨他们的病痛,和他们的收入来源一样,从来不明不白。他们的仆人不声不响,或者和他们别无两样。从社会的角度解释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他们全不可能做到,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蠢人,没有语言障碍,也没有穷人。连他们的感知力都很有限,他们可以登陆欧洲观赏艺术品,或者彼此相互打量,但仅此而已”。
福斯特的批评不只针对詹姆斯小说看似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也指向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阶级褊狭。“上流社会的客厅”无疑是詹姆斯小说标志性的场景,虽然他的人物有不少为了不失体面地满足某种物质财富欲求而煞费心机,但很少有人忙于为生计奔波。阶级分化和激烈紧张的社会冲突,贫穷困苦和鸡毛蒜皮的市井生活,粗野鄙俗和残酷乖张的暴戾之气等等,在他的故事中更是极为少见。福斯特的论断,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界对詹姆斯的严苛指责有相通之处。包括美国文学史名家沃农·帕灵顿(Vernon Parrington)和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内的不少学者,就曾批评詹姆斯的作品只注重形式审美,不在乎内容题材。在他们看来,詹姆斯笔下的人物充满斧凿的痕迹,他的小说也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这些负面评价当然与美国文学本土意识日渐增强有关,毕竟,詹姆斯年纪轻轻就远走他乡,并二十余年不曾返回故土,他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往往毫不相干,再加上詹姆斯本人也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文明缺乏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积淀。当然,这些评论确实指出了詹姆斯优雅华丽的艺术世界与杂乱不公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詹姆斯因此被不少学者视为保守的唯美分子。在英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以阶级、性别和族裔等身份政治批评,以及意识形态文化批评为主导的领域,审美价值和经典精英白人男作家持续地受到质疑,詹姆斯也难免成为典型批评对象之一。倒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酷儿理论兴起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詹姆斯看似不同寻常的性取向和他的艺术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这一研究方法无法避免程式化的先入之见,但还是抵消了不少身份政治批评中对詹姆斯的浓厚敌意。
但是,在詹姆斯创作的包括小说、短篇故事、游记、传记和文学评论在内的皇皇近百部作品中,只看到其中精雕细琢之美,而不谈詹姆斯对审美与思维想象、道德意识及社会风尚之间的关系,现代性条件下社会伦理生活的特征,以及文明社会的本质和理想形式等诸多重要主题的探讨,显然失之粗浅和偏颇。事实上,美国知名文化学者和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早在其重要著作《自由的想象》(1950)中,就深入分析了詹姆斯作品中一部较少被关注,但社会和政治内涵又颇丰富的长篇小说《卡萨玛茜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1886)。小说不仅生动地呈现出十九世纪欧洲社会贫富差异和阶级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欧洲政治极端主义对公共生活和个人选择的影响,而且对审美感知力所强化的道德责任心,个体尊严感和对文明雅致的索求之间可能出现的种种矛盾,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特里林敏锐地指出,“小说的核心假定是欧洲文明已经步入顶峰,正在滑向腐朽,它所发出的特别美丽的光芒,部分是辉煌往昔的反射,部分是衰颓今日的磷光,它也许难逃暴力的终结,这也不能说完全是命运的捉弄,尽管这片古老而罪孽深重的大陆从没像现在这样让我们深感其荣耀和可怜。”不能不承认,詹姆斯在十九世纪末对欧洲文明所面临的灾难的想象,颇有先见之明。
在特里林看来,詹姆斯的小说可以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来描述,这种现实主义更着重于观照现代生活的道德境况,但它反映的“不是对于道德原则本身的熟知,而是对于道德生活中的矛盾、悖论和危险的觉察”。特里林对于詹姆斯作品道德意涵的强调,为詹姆斯研究开启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随着詹姆斯研究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美国学者对詹姆斯的讨论也更加深刻透彻。越来越多的评家开始探究詹姆斯笔下精微丰富的个体意识、心理和欲念,以及它们与社会生活中的秩序、自由以及伦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比如劳伦斯·霍兰德(Laurence Holland)的《理念的代价》(The Expense of Vision,1964)和莎伦·卡梅伦(Sharon Cameron)的《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思维》(Thinking in Henry James,1989)就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代表专著。两位学者对文本的解读都极为独到精彩,在哲理层面的思考也非常严谨缜密。
对詹姆斯作品中丰富的哲学内涵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包括保罗·阿姆斯特朗(Paul Armstrong)的《亨利·詹姆斯的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Henry James,1983)和罗斯·波斯纳克(Ross Posnock)的《好奇心的折磨:亨利·詹姆斯、威廉·詹姆斯和现代性的挑战》(The Trial of Curiosity: Henry James, William James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1991)。前者力图说明詹姆斯对意识和认知的理解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萨特等哲学家的现象学理论的相通之处,后者则以詹姆斯的兄长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为切入点,将詹姆斯的思想置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智识传统中,同时融入韦伯、齐美尔、本雅明和阿多诺等人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和文化批评展开跨学科的讨论和分析,进一步拓宽了詹姆斯和美国文化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另外一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是芝加哥大学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亨利·詹姆斯和现代道德生活》(Henry James and Modern Moral Life,2001)。皮平认为,詹姆斯深知现代生活中,包括欺骗、背叛、忠诚、奉献、宽恕、善良等道德范畴既可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要求和利益,也可能只是心理层面的作用机制,反映相关主体的需要、欲求,乃至焦虑,但詹姆斯并未放弃对道德价值的寻求。在詹姆斯的作品中,这种价值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基本机制和原则共识,也有赖于主体在追求自我欲求的圆满实现中,将他人作为自由并同样独立追求自我满足的主体来对待。
近年来,学者逐步修正了詹姆斯缺乏历史意识,对社会、政治和物质现实不闻不问的成见。戴维·麦克沃特(David McWhirter)主编的文集《历史语境中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in Context,2010)全面细致地阐明了詹姆斯对他所处时代的物质、文化和思想观念变迁的深刻反思和艺术再现,詹姆斯灵慧好奇的头脑对外界发生的各种变化始终保持敏锐的反应,外界的影响也启发并催化着他的创作思路和艺术理念。此外,从文集对当前全球詹姆斯研究的详细梳理中,也可看到对詹姆斯愈益丰富多样的研究角度和有增无减的研究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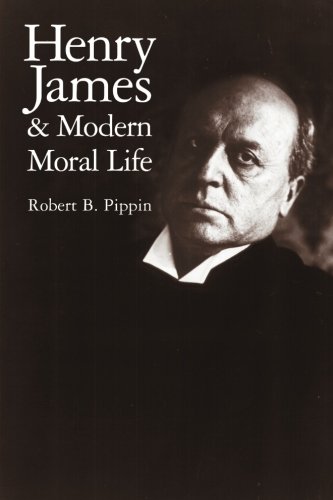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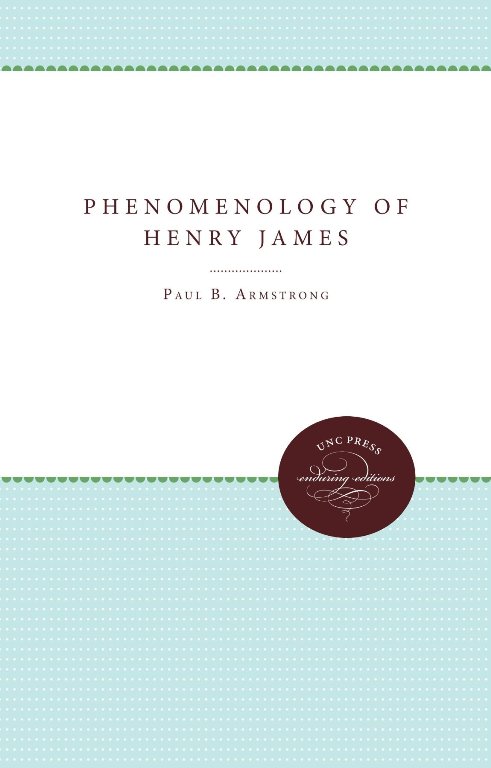

礼仪斯文,道德想象
不可否认,詹姆斯的小说从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其中的礼仪斯文所交织的审美意蕴和道德内涵形成的复杂式样。正如利维斯所指出的,詹姆斯“感兴趣的礼仪举止是精神和智识雅趣的外在符号标记,或至少可以这么来看待。本质上,他在追寻一个理想的社会,一种理想的文明”。詹姆斯最受评家称赞的小说之一《一位女士的画像》将这一特征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不久,伊莎贝尔在杜歇家遇到梅尔夫人,这位出生在美国但已久居欧洲的女士,言谈举止优雅得体,伊莎贝尔被她的教养和识见深深吸引。同时,伊莎贝尔的姨父老杜歇先生临终前,经儿子拉尔夫的劝说,在遗嘱中留下七万英镑遗产给她。伊莎贝尔虽然考虑到富足可以让她去有所“作为”,而“作为”要比消极自由更“甜美”,但她对此馈赠始终心有不安。之后,伊莎贝尔在佛罗伦萨认识了梅尔夫人的朋友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一个中年鳏夫,有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名叫潘茜。奥斯蒙德也出生在美国,在意大利已定居多年,他并不富有,也安于平淡,但却沉醉于艺术的世界。伊莎贝尔不仅被他清雅敏感的仪表和气质所吸引,也着迷于他对艺术的审美品位,其实两者在她眼中已浑然一体。伊莎贝尔接受了奥斯蒙德的求婚,并憧憬着她们可以一起同享高尚生活,对她而言,这种生活“意味着充分相知和充分自由的结合,相知给人责任感,而自由使人幸福”。
然而,伊莎贝尔婚后终于发现自己识人不深,错看了奥斯蒙德的品性。对他来说,高尚的生活,“完全是何种形式的问题,是一种蓄意谋划的态度”。奥斯蒙德的自以为是和独断专行,丝毫没有因他的艺术品位有所改变。他认为伊莎贝尔没有文化和历史传统,她的独立见解让他讨厌;他觉得伊莎贝尔应该完全遵从他的看法、追求和喜好。小说的下半部在详细展现他们婚姻破裂的同时,也引入另一条相关的叙事线索。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在潘茜的婚事上又出现了严重分歧。潘茜的两个追求者都是伊莎贝尔的旧友,一个正是沃伯顿勋爵,另一个是她儿时的朋友罗西尔,旅居巴黎,财富地位和沃伯顿勋爵都不可同日而语。奥斯蒙德很快原形毕露,他很清楚沃伯顿曾追求过伊莎贝尔,但他毫不考虑她的想法,要求伊莎贝尔利用沃伯顿对她的感情,帮助促成沃伯顿和潘茜的婚姻。奥斯蒙德的谋划(最终伊莎贝尔得知,自己和奥斯蒙德的婚姻也是他昔日的情人梅尔夫人谋划、奥斯蒙德参与的一个圈套,而潘茜是两人的私生女),提醒伊莎贝尔必须确定沃伯顿追求潘茜的动机。她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道德困境:从潘茜的婚姻考虑,她的确认为沃伯顿是更好的伴侣,可如果沃伯顿追求潘茜的动机是他对自己仍有的爱慕,那出于对潘茜的爱和责任以及出于自己对婚姻许诺的忠诚,她都无法接受。
在一次舞会上,沃伯顿不经意间提到潘茜似乎总在伊莎贝尔身边,稍作迟疑后又补充说,其实所有人都希望接近她。片刻间,伊莎贝尔似乎了解到沃伯顿的真实意图。随后,沃伯顿提起从前在英国的美好时光,有一瞬间,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伊莎贝尔觉察到他表情中闪过一丝疑虑,而沃伯顿也从她的眼神中感到些许不安。这一刻短暂的对视,将不能用言语道破的微妙心思精巧地呈现出来:伊莎贝尔明白了沃伯顿打算娶潘茜乃是为了在她身边,沃伯顿则领会到这会让伊莎贝尔无可忍受。更重要的是,伊莎贝尔对过往的缄默,无论其中包含多少无奈、痛苦和挣扎,也是斩断沃伯顿旧日情愫最坚决的方式。如此纤毫毕现于笔端,詹姆斯高超的心理描写誉不虚出。而在百感交集的对视中凝结的那份斯多葛式的冷静和克制,也可以说是詹姆斯式礼仪斯文最好的诠释。
伊莎贝尔是詹姆斯作品中最具理想主义,也是最具想象力的人物之一。她的道德意识与审美敏感密不可分,比如她继承的那笔财富,始终让她感觉是一种道义的负担,因为在她看来,“继承七万英镑不是什么非常美妙的事;美妙之处在于杜歇先生给她的馈赠本身。不过嫁给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并把这笔馈赠带给他,这也许有些属于她的美妙之处”。伊莎贝尔认为奥斯蒙德对艺术的专注,意味着“他对自己这笔财富的使用,会让她对财富的看法有所改变,也可以抹掉意外之财这样的好运所附带的某种粗俗”。伊莎贝尔在这里对“美妙”和“粗俗”的强调,以及对慷慨和公道的理解,再次混淆了美学和道德范畴。伊莎贝尔丰富的想象力,也常常糅合了凄美的画面和温暖的情感。在她对奥斯蒙德的幻念中,除了他的文雅表象,她也感到他的“无助和无能,但是这种感觉是一种柔情,它是敬意中最精华的成分”。伊莎贝尔仿佛看到奥斯蒙德是个“充满疑虑的远行者,在海滩徘徊等待起航,他朝海的那一边望去,却还没有驶向大海”。她会“为他的船放下水”去起航,爱他会是“一件美好的事”。虽然伊莎贝尔的道德想象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在詹姆斯后期的作品中,道德想象也从起初的瑰丽绚烂慢慢变得黯淡失色,但无论如何,这一想象中始终残存一份美的期许和爱的力量,这也许是进入詹姆斯美妙而博大世界的一把钥匙。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