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尘封百年,寻踪高昌故城的木构建筑遗珍
新疆吐鲁番市古称高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通中西文明的绿洲城市。译著《高昌遗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主要由16位作者撰写的17篇专题论文组成,围绕高昌故城所出的50余件木构件(多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盗运的文物)展开,研究成果涉及多学科视角,是集中呈现尘封百年高昌木构件遗珍研究的首部著作。
1902-1914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四次进入新疆考察,第一、三支探险队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率领,第二、四支探险队由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前三次的考察重点均涉足高昌(图1),探险队员考察、发掘、研究并带走了成箱的文物运往柏林。四次在新疆的探险活动,也使德国拥有了超过百年时间对新疆文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图1 百年前的高昌故城(B 1000)©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由于诸种历史因素交织的机缘,今日位于柏林西郊达勒姆的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木构件(图2)。
正如该馆馆方所言:相较于塑像、绘画以及写本文献,这些木构件自运回柏林后,常年被忽视甚至遗忘。她们如同睡美人一样静谧地躺在博物馆库房的货架上,直至2014年才重新为博物馆研究人员所关注。 由于该馆主持的《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高昌故城建筑》研究项目的实施,来自世界多国的研究者从建筑学、考古学、美术史学、语言学和文物保护科学等诸多学科对这些木构件做出研究,使得世人对西州回鹘王朝时期丝路绿洲——高昌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了崭新的认知。此次研究也是学界首次系统展开深入探讨高昌木构件的工作,为今后高昌遗存的持续研究拉开了序幕。

图2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藏来自高昌的木构件©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高昌故城西南大佛寺(β遗址)的木制柱头可以想见其原先所装饰建筑物的宏大尺寸,柱头上雕刻有希腊化艺术的茛苕叶片图案呈现出强烈的西方影响(图3)。博物馆重构了Q遗址所出的彩绘木构件,呈现为纵梁、枓栱、垫木等木件的组群,成为11世纪建筑规范《营造法式》中曾经描述的中国传统技艺的精彩例证(图4)。

图3 高昌故城β遗址出土柱头(III 5016)©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利佩(Jürgen Liepe)。

图4 高昌故城Q遗址重构后有枓栱的木梁组群正面视图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Jürgen Liepe)。
由于新疆文物的遗失,前贤一直都是面对残破不全的遗址做出不懈的探索。梳理当时的背景,若无这些独具慧眼的探险队员当年的“收集”与“保护”,高昌木构件早已被当地居民用于薪柴。而将探险队当时的绘图与老照片经过今天技术的整合,使得当下有路径继续探索较之百年前几近消失的城址且追溯其建筑风尚。一百年后,德国探险队遗留的各种材料无疑对于研究高昌故城仍极具价值。该书的研究方式提示我们,处于信息迅疾沟通交流的当下,相较于之前书斋式碎片化的研究,多学科视角的团队协作研究可以更广泛、实效的讨论并解决问题;而面对具体的实物,“微观研究”也可以提供来自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宏观与微观依然是全面解读“原物”必须掌握的研究维度。
德国探险队当年的考察与研究奠定了高昌的学术史基础,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项目的实施使我们体会到研究方式的变迁。文物流失的历史已经发生,面对当下,多学科领域的合作是今后高昌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勾连流失海外遗珍与原址的基础工作依然是推动高昌艺术史发展的必经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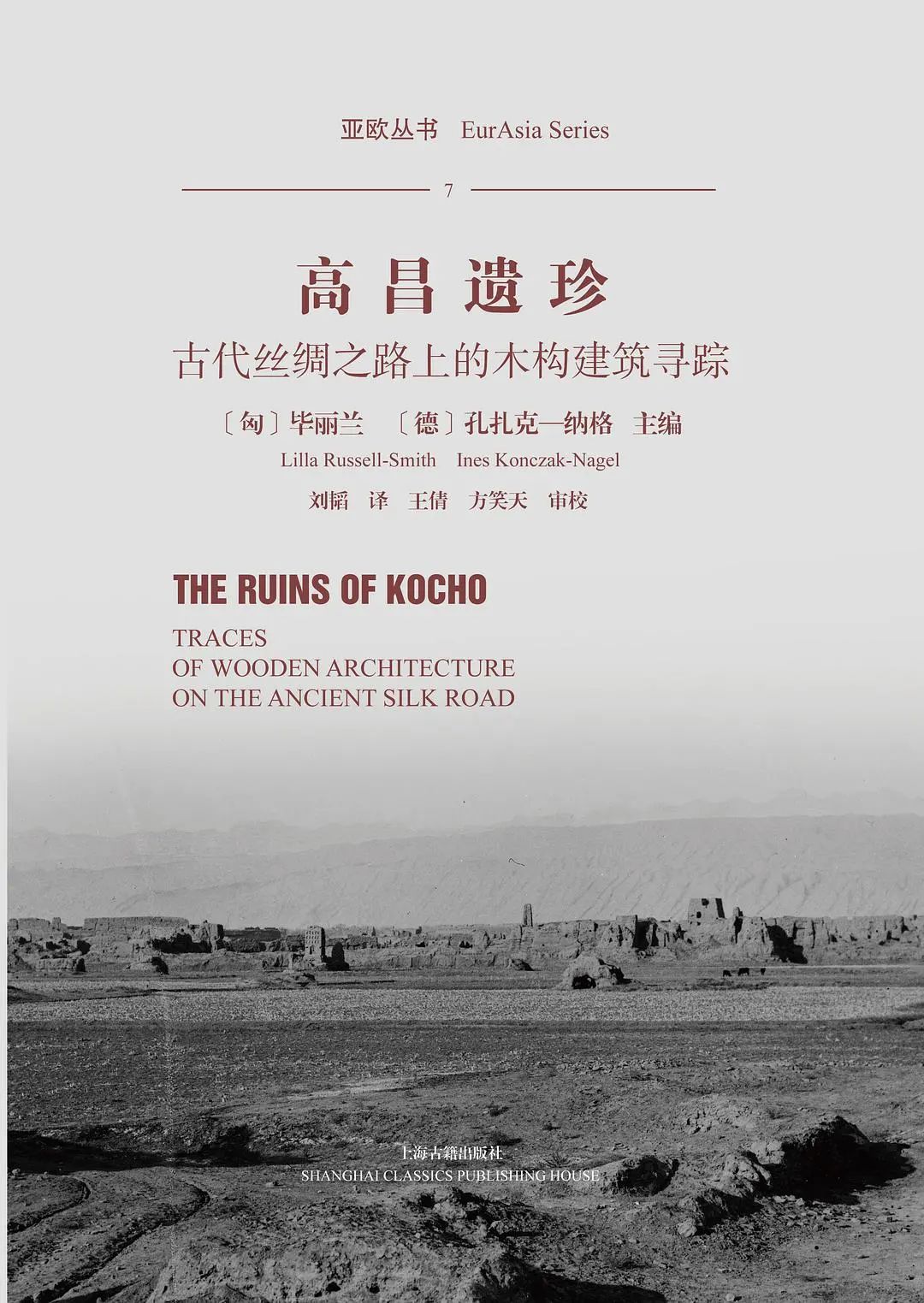
图书封面
(作者系本书译者、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宗教美术研究。)
————————————————————————————
《高昌遗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寻踪》章节节选
Q寺院遗址木构件上的彩画代表着10-11世纪典型的回鹘风格。其中最常见的图案是包括花卉与叶片在内的植物纹饰。花卉包括彩绘牡丹花开(Ⅲ 4435 a、b、c、f),胜金口的木梁上亦见有相似的图案(Ⅲ 7294)。此外,还有样式化的花卉图案,有突出的细长叶片,叶尖向侧方摆动。这些植物纹饰在回鹘艺术中颇为常见,例如在壁画中作为边饰。然而,向侧方摆动的细长叶尖是高昌故城的艺术特征,例如11世纪早期出自α寺院遗址的壁画残片(Ⅲ 776),以及9-10世纪出自胜金口的苎麻绘画(III 6618b),当然,最为精彩的是Ⅲ 4435 e短横梁上的彩画。

Q寺院遗址Ⅲ 4435e和4435c木件彩绘特写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Jürgen Liepe)。
第二种常见图案是缠枝纹(Ⅲ 4435 a、b)。这种边饰容易使人联想到9-10世纪 K寺院遗址出土绢画残片上的装饰。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木梁上的花卉与卷草图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柏孜克里克《誓愿图》壁画上亦能得见,且与自盛唐至宋代(公元7-13世纪)中国西部、北部地区建筑彩画上的图案非常相似,可参见李路珂在《〈营造法式〉彩画研究》中的再现。相似的图案亦见于《营造法式》的印刷插图中。

《誓愿图》细节,上有建筑和花卉纹饰,柏孜克里克第15窟壁画,370×227厘米,11世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y-775(鲁克斯摄影)。
木构群中唯一有棱角的几何纹饰发现于Ⅲ 4440 i木构件上,红黑相间的图案,亦见于盛唐(公元8世纪)及以后其他地区的文物中,例如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8世纪壁画、敦煌10世纪宝塔状纸本佛经的边饰、据报道出自高昌故城 β寺院遗址的麻布上绘制的观世音菩萨图(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y-777,见本书扉页和第iii页)。

有曲折纹饰图案的套斗顶构件,Ⅲ 4440i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利佩(Jürgen Liepe)
Ⅲ 4435 c木梁左侧末端呈现了并坐的佛像,源于著名的“千佛”图式,且自公元6-7世纪以来常见于吐鲁番地区,如柏孜克里克第18窟的千佛。

Ⅲ 4435c木梁上绘制的佛像 ©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 伦格(Martina Runge)
正如我们所见,Q寺院遗址木构群中的若干木构件是重复利用的,之前曾用于其他建筑。它们在此过程中被重新绘制,不总与原初彩画的质量标准一致。上述Ⅲ 4435 c木梁上的三尊佛像就是一例。基于我们将纹饰认定为10-11世纪,可以设想重绘亦发生于此时。
套斗顶(方井)的部分木构件进行过重绘。这种三角桁架构造屋顶的建筑类型源于西亚,公元前4世纪已为人所知,例如土耳其墓室中使用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套斗顶传遍亚洲,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在实体建筑与绘画中皆可见到。在中国,套斗顶以藻井为名融入了寺院与宫殿建筑,以至于达到不再被认为是外来产物的程度。最著名的例子是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宝座上方的藻井(1406年,多次重建)。北京地区套斗顶最早的例证来自于一座墓葬,年代令人惊叹,可追溯至公元105年,然而这座东汉墓中融合了纯中亚风格的元素,包括狮面柱头的凹槽石柱,这可能源于印度或波斯,然而源头应是古希腊建筑。
(注:选自原书文章《Q寺院遗址及其木制建筑构件》第146-147页,作者: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鲁克斯(Klaas Ruitenbeek),此处略去注释,引用请参见原文。)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