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沧东的小说,追求真正价值的探索
一段时间以来,对正面意义的真正价值是否存在的怀疑开始广泛扩散。近代之后的理性、科学、主体意识等核心话语中,蕴含着虚伪性与压迫性——这种合理批判急剧世俗化,且没落为一种虚无主义;对真正价值的追求索性被看作毫无意义,对绝望与自我毁灭的沉溺却在不断蔓延。在近代,追求真正价值只能以衰落的价值为媒介,如今显然情况更加恶劣。尽管如此,认为这种追求毫无意义,无疑是一种失败主义。
李沧东的第二部小说集《鹿川有许多粪》展示了一类艰辛追求真正价值的人物形象,令人感动。第一部小说集《烧纸》(1987 年)经常被评价为未体验世代分断小说的一种类型,还曾引发对接受萨满教的争论,不过那部小说集的主题其实是对真正价值的探索。秦炯俊准确把握了这一点,称其为“用成熟的认识拥抱传统生活”。李沧东试图与传统 / 现代二分法相关的理解人性的各种公式做斗争,探索如何摆脱那些公式,着眼于捕捉生活的真实。作品稀少的李沧东从未停止过这种探索,他在第二部小说集当中更加积极地摆脱了那些公式。

【韩】李沧东著,春喜译,《鹿川有许多粪》,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
积极地摆脱公式,首先表现在详细审视了那些生活的真实具有一种错综复杂性的人物。例如,《天灯》中的信惠虽然是运动圈的大学生,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混乱。她对运动缺乏坚定的信念,陷入怀疑与矛盾之中,这源于她无法与劳动者或者民众融为一体。“我竭力对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想法与愤怒感同身受。然而,不论我再怎么努力,我依旧是我,终究无法变成他们。不,我越是努力变得与他们相像,越是感觉自己不够诚实,变得不像自己,感觉自己就像是话剧中的小丑一样做着拙劣的表演。”这种怀疑与矛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韩国小说中经常出现,因此没必要赘述,不过信惠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在单亲母亲的抚养下度过了贫困的童年,至今无法摆脱那种残酷的贫穷。她只是成了大学生而已,其余的生活条件与“他们”一样,甚至更惨。她现在为了赚学费而做着矿工村茶房服务员的工作。这个世界向这样的信惠强求一种公式。母亲强迫她将来成为小学老师,运动圈的同事强迫她成为满怀信念的斗士,警察强迫她成为潜入矿工村的鼓动者。“你们此刻正在强迫我变成不是我的某种东西”,这种抗议中蕴含着她的真实。

韩国导演、作家李沧东
李沧东塑造的形象当中不乏没有谎言、没有怀疑、信念十足的人物。《天灯》里的秀任、《鹿川有许多粪》里的玟宇、《真正的男子汉》里的张丙万等,皆是如此。然而,李沧东的审视却没有对准他们。《天灯》的秀任只是在回想中短暂出现,《鹿川有许多粪》的焦点对准的也不是玟宇,而是在与玟宇的见面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混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俊植。《真正的男子汉》虽然例外地把审视的焦点对准了张丙万,却也不是直接审视,而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小说家的观察来实现的。
重申一次,这一结构特征源于摆脱公式、把握生活的真实之复杂性这种意图。李沧东在这种复杂性之中探索真正价值的方向与可能性。重新回到《天灯》,信惠在接受残酷的拷问时不断反思自己,终于意识到:
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种无可救药的罪行——无法放弃自己,从未自发地努力寻找希望,既无法向他人伸出援手,也不想抓住他人的手,而且从来不曾为了自己以外的人流泪。
请饶恕我的罪过。
这种意识让她对金光培以身相许,并拿出自己这一个月来的所有收入作为因塌方事故去世的老矿工的丧事慰问金。“她完全没有料想到自己会这样做。”这个行动的意义可以解读为利他主义和爱,重要的是,它源于生活的真实所具有的那种错综的复杂性。
《关于命运》看似普通,却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思路进行解读。这部作品通过虚假与真实的错谬构建了生活的真实的复杂性。兴南觊觎遗产,谎称是金老头的儿子光一。然而,光一只是金老头丢失的儿子户籍上的名字,儿子实际叫兴南。虽然过于巧合,但兴南其实正是金老头丢失的儿子。当兴南丢掉自己真正的名字,自称“光一”时,他是假的;当他回到自己的名字,他成了真正的儿子——这是真实。然而,金老头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突然离世,只有“光一”是金老头的儿子,金兴南成了假冒的儿子。真实与虚假在此颠倒了两次。这种错谬逼疯了兴南。
通过对真实的确认,兴南的疯癫得到治愈。这种真实表现为金老头留下的古董手表。虽然兴南当初觊觎的几十亿财产全部落入他人手中,古董手表却重回兴南手中,这才是真正贵重的真实的证据。兴南对这种回归提出了以下疑问:
如果没有所谓命运之神这回事,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重回我的手中又该如何解释呢?这块旧表失而复得,不就是命中注定吗?我反复思考着,如果这是上天的旨意,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部作品的整体情节过于虚假。不过,抛开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种虚假中强烈蕴含着的作者的意图。古董手表归来的设定,来自作家对人的根本信赖。中篇《天灯》的以下段落把这种信赖表现得十分唯美,同时也是标题的出处。
是谁在那高处点亮了一盏不灭的灯火呢?信惠仰着头,久久地看着那颗星。她从未像这样近距离地感受星光。自己在警察署遭遇那般恐怖的事情时,和金光培在一起时,还有此刻这一瞬间,地球都在一成不变地沿着自己的轨道旋转,宇宙中的那颗星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位置,闪闪发光。
下一个瞬间,信惠感觉到一种冷水浇头般的恶寒,体内有种东西突破混沌醒了过来。那颗星悬挂在空中,而我站在这里。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抢占那颗星的位置。我心里也有一颗星,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夺走。“是的,这就是我的生活。”信惠的内心充满了活下去的渴望。突然,那颗星飞到她的眼前,支离破碎。不知不觉间,眼泪已经莫名地开始流淌。
这或许是韩国小说中屈指可数的唯美而令人感动的描写。这盏“天灯”与《关于命运》的“古董手表”,是对人的根本信赖的象征。这些东西治愈了陷入混沌的信惠和得了癔症的兴南。
这种对人的根本信赖美好而感人,不过立足于冷酷的现实主义来看,却很难脱离浪漫主义的批判。李沧东小说的力量不在于这种信赖的浪漫表达本身,而是源自以那种信赖为原动力,戳穿我们的生活的——偶尔悲剧性的——错综的复杂性,同时对真正价值的方向与可能性抛出痛苦的提问。这种痛苦的提问引发了一种反思,即对人的信赖如果止步于对其自身观念的执着乃至盲目的信仰时,会不会也沦为一种公式?
《龙川白》是一个短篇,却融入了很多故事。金学圭年轻时作为南劳党员参与过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在六二五战争前后有过一段牢狱生活,一辈子成了一个废人,一个“龙川白”。他努力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甚至连儿子的名字也要模仿马克思取为“莫洙”,却一辈子不曾将这份信念付诸实践。不过,他一直顽固地拒绝融入韩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拒绝使他不愿工作赚钱以维持基本生计,整日酗酒。这样的他,突然自称犯了间谍罪。这种自称蕴含着他为了守住自身人格的辛酸挣扎。他使用了“龙川白”这个比喻,并对儿子说道:
我现在还能活多久呢?虽然对不起你……我已经决定了,不要至死做一个龙川白。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儿子尖锐地批判了这样的父亲。对儿子来说,父亲是一个卑鄙的人,一辈子只给家人带来痛苦,迫使妻子代替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儿子看来,父亲的间谍把戏只不过是另一种“龙川白”罢了。
您这么做,过去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变吗?这种做法很傻,是彻底的自我欺骗。在我看来,只是发疯罢了,又成了另一个龙川白。
通过虚假重寻真实的父亲与批判这种做法又是另一个龙川白的儿子之间的这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向我们抛出了一个痛苦的提问。这条鸿沟是一种压迫,贯穿着我们的存在与历史,最终歪曲了真正的价值追求。但李沧东却出乎意料地对逃离名为“父亲”的现实的儿子持包容态度,拒绝在结尾填补这个鸿沟。李沧东刻画的儿子“嘶哑的嗓子眼里有一种难掩的哀伤”,充满暗无天日的绝望,只是回头望向“坟墓一般的寂静中”的“高大的建筑物”(拘留所)而已。那条鸿沟前的绝望,是对我们的生活所遭受的所有压迫进行痛苦提问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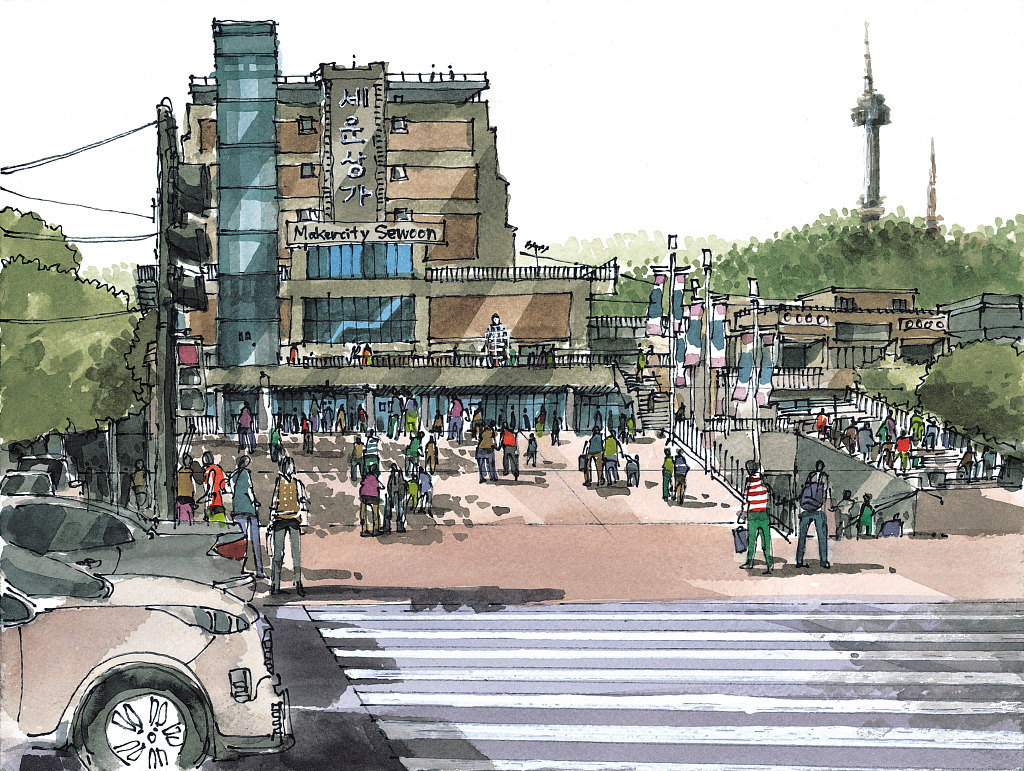
关于痛苦的提问,这本小说集中最受瞩目的作品是《鹿川有许多粪》。本篇作品中出现了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俊植与玟宇。玟宇是学生运动出身的社会运动家。根据第一段的描写(挤坐在地铁里打瞌睡并做噩梦的样子)可以推断出他有苦恼,作品却完全没有深入玟宇的内心,只通过俊植的观察对玟宇进行刻画。与玟宇不同的是,作品着重刻画了完全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俊植的内心。也就是说,与《天灯》的视角正相反。
俊植是一个奋斗型的小资产阶级式人物。他在小学打过杂,夜大毕业之后成了一名正式教师,一番艰苦奋斗之后终于凭借一己之力买下了一套狭窄的公寓。然而,他依然无法摆脱他人的蔑视。不仅在职场,在家庭中也是如此。他和同一所学校庶务科出身的妻子闪婚,他们的婚姻生活甚至不具备最基本的相互理解与连带感。同父异母的弟弟玟宇的出现,引发了变化。俊植的妻子从玟宇身上看到了俊植缺失的东西,对与俊植的婚姻生活正式开始产生怀疑。俊植的妻子毫不掩饰地蔑视俊植,却又暗自对玟宇动心。因此,俊植从小积压在心里的与玟宇有关的被害意识被激化,他终于向警察举报了玟宇的行踪。
这三个人物都有自己专属的真实。俊植无法理解玟宇所作所为的意义,同时彻底缺乏关于“活得像个人”的现实反省。然而,当无法摆脱极度贫困的过往的他扛着鱼缸回家时,途中的独白场景蕴含着彻底的真实。俊植的妻子有些虚荣,缺乏一份真挚的努力将她与俊植的婚姻生活向着有意义的方向推进。不过,在她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所产生的怀疑与对真实人生的茫然而热切的渴望中,也蕴含着真实。玟宇有点不谙世事,可这种不谙世事是他纯真的表现,他的纯真是他实践性的人生的基础。
玟宇的出现成为俊植的家庭生活显现出“这种生活是建立在肮脏发臭的垃圾堆上的谎言”的契机。在这种显现中,三个人物的真实彼此纠缠且相互矛盾。在这种矛盾中值得重视的是,李沧东选择了俊植作为视点。如果以玟宇为视点,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解读为启蒙主义;如果以俊植的妻子为视点,则很容易被解读为小资产阶级日常的幻灭的浪漫主义。
然而,以俊植为视点,这部作品可以激烈地刻画这种矛盾其内在的,或者说成为这种矛盾赖以产生的条件的社会普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鸿沟。在这种人生的条件下,“活得像个人”是什么,这是有可能的吗?李沧东更加沉重、更加痛苦地提出了这个疑问。玟宇被抓之后,瘫坐在粪堆上哭泣的俊植令人心痛。
俊植开始哭泣。他的眼中不断流泪,泪水使他更加悲伤。他不是因为后悔而哭,也不是因为自责而哭。让他哭泣的,只是那种心脏撕裂般的凄惨感觉,以及任何人也无法理解、对任何人也无法说明的,只属于自己的悲伤。他坐在粪堆上不想起身,像个孩子般大声哭了很久。他哭得不成样子,仿佛内心积攒的所有悲伤同时迸发了出来。他放任自己在体内日积月累的悲伤与不知所措的空虚中尽情地哭泣着。
俊植的哭泣向我们抛出一个无比痛苦的提问。我在这个提问中看到了李沧东追求真正价值的小说探索中最炽热的一面。这种探索摆脱了所有险恶或压迫的公式,让我们直面错杂的真实。只有在这种错杂的真实中,话语的本意中的真正价值才会奔涌而出。
(本文节选自《鹿川有许多粪》,【韩】李沧东著,春喜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