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钱新祖:一个哥大博士在芝加哥、台北、香港的际遇
【编者按】本文原题《台北、香港、芝加哥——钱新祖先生行述》(现题和文中的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最初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9期(1998年3月),作为附录收入钱新祖著《中国思想史讲义》(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1月版)。该书是依据钱新祖(1940-1996)教授生前在芝加哥、台湾、香港等地知名大学长期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
愤怒、徒劳、热狂、挫折。新祖的去世很难令人理解,为什么是在正当壮年、正是发挥天赋才华、开辟一番天地的时候?为什么比一般癌症病人遭受更多更久病痛的煎熬?我举拳问天、我咬牙问地、我激怒、我嘶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天赋才华
对我而言,新祖的死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隐喻(metaphor)。他常说一个故事——在他出生之前、甚至在他母亲怀胎初孕的时候,一位老和尚路过钱家,指着他母亲的肚子说她怀孕了,而且是个男孩,将来得避开佛门,否则必遭不测。这是新祖说故事的典型作风,一点也不忌讳他当时对佛教教义全身投入的研究,一点也不在乎类似《红楼梦》故事中的预警。但是这个故事捕捉着新祖生命中的悲剧色彩——怀才不遇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讽刺的是他可能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中唯一恨不该生为男儿身的人,因为他父亲鉴于头胎已是男孩,总希望他这一胎是女的,等到他出生之后,决定领养新祖的表姊为女儿。)
新祖的天赋才华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是他超群的思维能力——兼具哲学家运思的透析力与历史学家巨细靡遗的记忆力,另外他的语言能力,如中、英文写作文采洋溢,少有人能及。在他10岁以前,家境富裕,得天独厚,“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开始得早,和他同年的这一代当中少有人像他文史哲、书法兼修,这全是他父亲家教熏陶使然。这令人羡慕的天赋加上他独特的性格,使他所学得以致用。新祖具有吸引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人的魅力,我相信他个人的魅力,使他到处受人仰慕,在美国如此,在亚洲更是如此。从一个小小的例子更可以说明这个事实,每次他太平洋来回一周就可以听四五个人的生命故事,这些人都是他在飞机上碰到的,虽然萍水相逢,他却有本事让人打开话匣、侃侃而谈个人生命问题、困扰等等,似乎他有面授机宜、解决烦恼的能耐。
但是新祖生命过程中也时遭横逆。他的童年和 20世纪近代中国的悲剧几乎是同心圆。长江下游的钱家随着抗战,耗尽上海、南通的家产,辗转来台之后不到几年,更是一贫如洗。他的青少年时期多半是在穷苦挨饿中度过的,他养过鸡、做过家教来补贴家用。再穷,父母亲也都没有丧失送四个小孩出国念书的决心和梦想。但是这些生活阴影、时代悲剧影响他至深,他4岁大病一场、他记得在南通被日本军囚禁的可怕一晚,他也记得6岁失乳母的痛苦(新祖是四个小孩当中唯一由奶妈带大的。6岁时奶妈被遣送回乡,新祖痛如丧母,他父亲曾据此赋诗几首)。我们很难拿捏这些早年的悲剧阴影对新祖的打击有多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并不因此而倾向消极悲观;相反地,他深具自信,而且是位百折不挠的斗士。他能从逆境反扑、乐观从事,例如他与癌症拼斗最后,过程中不断强调战胜癌症的可能性。但是,他经常承受噩梦的困扰,在平静喜人的外表下,深伏着内在的激愤怒气,总在四下无人时爆发出来,这是外人无法想象关联起来的。
他童年的一些照片透露出他的某些性格:他注重服装细节,非常挑剔服饰,即使是休闲的式样,他也要坚持对味才行。有一张大约他4岁时和他哥哥、堂兄西装笔挺一起拍的照片,可以想象照片中的小男孩从照相馆回到家后仍不肯脱下西装的拗劲。他记得当时要求大人们一定要给他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后来仍是一样脾气,一样讲究美感品位,总是不假他人、精心设计自己住家的装潢、艺品的摆设。
他惊人的记忆力很早就展现出来,我记得1975年,新祖的父亲第一次来美时,父子两人畅谈往事,新祖竟然还记得阔别三十年南通老家的一角一落,一点也不含糊。同样地,我们第一次约会时,我们讨论 David Nivison所写的章学诚的书,当时我刚花好大把的劲儿把书读通读懂,而新祖几年前读过、也不专门研究章学诚,但是他如数家珍,完全掌握书中论辩的精华,说得我目瞪口呆,敬佩不已。
在 1949年以前,新祖跟着亲戚先来台湾,四个小孩当中他是最先到的,因为他是四个当中最精力充沛、对新环境不生分的一位,父母亲可以放心他一个人先到台湾,分批成行,以防万一。我记得新祖曾告诉我说他刚来台湾时最讨厌学校,因为他讨厌穿得比学校其他小孩还好。他上学第一年的表现并不怎样,之后他急起直追,从此学生生涯总与“第一名”、“第二名”形影不离,师大附中是非常奇特的,在当时的学校当中,风气最自由,学生也最调皮,脑筋也最灵活。
我对新祖的了解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我,知道自己不断在追寻一些东西,他后来常用海德格尔的“掉进瓶里的苍蝇”的隐喻来比拟自己的追寻,他追求的总与人文有关,科学和工技并不对味。他大学联考的分数可以让他进医学院,但他选择历史,为的是历史似乎最能回答他所困扰的问题,那时候他常跟殷海光的学生亲近,除了历史的兴趣之外,他也在欧洲传统的经典中找寻开启西方文化的钥匙。(这些年来,当我沉浸文学领域时,我很惊讶地发现新祖收藏着从台湾带来的盗版的文学经典,例如我在他书房里找到了司汤达、普罗斯特、汤玛斯·沃夫和其他我从不知晓的文学作品。)这些他所阅读的书籍显示他对学习外文的看法,他跳进文学、历史的真正作品当中;他与本地人沟通,使用英文不假思索,真正把英文用成学习沟通的工具。他不像许多学生用心于教科书,他记得大学时期总是倾向讲求实际而不是一味读死书。他做过家教教英文,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替美国明史专家 James B. Parsons作研究助理,这项工作经验影响新祖生命至深,不仅让他熟谙明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档案材料,而且收入颇高,在1960年代早期的台湾,一个小时一块美金。这段情谊也使他安然无恙、无风无浪地通过美国研究所生涯的过渡期,最主要的因素莫过于Jim Parsons的帮忙,他是一位大好人、来自美国南方的绅士,他看到新祖的才华,愿意栽培、让它开花结果。

Parsons是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的教授,1963年帮新祖争取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就读硕士的奖学金。河滨分校的就学经验非常难得,而且不同于新祖在美国各地的经验,他第一年和Jim Parsons住,然后和美国同学合住,他完全投入美国生活经验里——我认为这和他做事方式有关,而且河滨分校少有中国人,即使有的话,也不会在历史系,所以他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他专攻美国史、读了不少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他上欧洲思想史课程,对欧洲思想传统更加着迷,他发现了马克思和毛泽东,读了很多当时在台湾被视为禁忌话题的书籍。他后来和河边校区的朋友一直保持特别的情谊,尽管他们大多是好好人而不具有特殊才干,这种类型的人在往后的日子里已引不起他交朋友的兴趣。在河滨分校他交美国女朋友,和朋友开车到墨西哥,夏天他到内华达去探望他姊姊时发现可以到赌城打工赚钱。他之所以能被录取和他朝气蓬勃的个性,以及美国一般人认为中国人数学脑筋好、肯打拼,拉斯维加斯和雷诺赌城喜欢雇用中国人的社会现象有关。他厚着脸皮去应征,跟人说他有写 Kino票的工作经验,而他号称他工作过的赌城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烧掉,所以没人可以查证他的履历表,他被录取了而且连续做了几个暑假。
这些在河滨分校的生活点滴是他真枪实弹第一次与美国社会接触、与美国研究生竞争的经验。在河滨分校除了Jim Parsons,还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一位是Donald M. Loewe——美籍华人,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意识形态;另外一位是 Theordor von Laue——专攻德国、俄国思想史的德籍学者。von Laue对新祖思想发展激励最大的是将他的英文报告撕成碎片,身为德国移民,英文同样不是 von Laue的母语,他给新祖的教训是下功夫、再下功夫,直到英文的表达措辞恰到好处,才能号称与当地人的水准无异。受到 von Laue这么严厉的批评,对新祖打击很大,他从小学一年级以来一向成绩优异,如今落到在河滨分校与B+搏斗、甚至于B+都是老师们看他用功上进才给的分数。但是 von Laue的教训来得正是时候,使他往后受益无穷,那些碍于礼貌、总说他英文很棒的美国朋友,都比不上von Laue的当头棒喝来得有效。部分是来自 von Laue的影响,部分是他自己的学习动机,他对英文特下功夫,几年以后,他英文的功力不仅超越大部分当地人,而且比大多数华人学者出色。

在哥大追随狄百瑞(de Bary)
通过Jim Parsons,新祖建立其他关系网络,然后被引进其他领域。在河滨分校,他有机会替知名的六朝佛教研究学者Arthur Link作研究助理,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佛教材料。后来 Parsons还帮他顺利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新祖到哥大拿到的是最高荣誉校长奖的奖学金——专门给最佳社会人文科学的申请者的四年奖学金,除了展现潜力雄厚的申请书之外,Parsons的推荐信和他的人脉可能是最推波助澜的因素。他和当时哥大研究中国上古史的Hans Bielenstein是好朋友,但后来的转变相当有意思,新祖到哥大后,反而投到Bielenstein的论敌Theordor de Bary的门下。新祖常常为自己是历史系而非东亚系出身感到自豪,历史系意味着他并非只靠着语言的本钱。
当他刚到哥大的时候,他所感兴趣的领域还很游离,他考虑过德国思想史(那么他就得学德文),后来受到 de Bary的感召而进入明代思想史的领域,de Bary当时刚刚出版学界公认的巨著——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这是对于明代思想研究具有新诠释的会议论文集。他向新祖证明了中国思想史是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且有话要说,非常有意义。新祖总是对自己的思想有主张、不大听别人的指挥,对他而言,de Bary是最恰当的导师。 de Bary非常支持他的学生,当学生向他展现成品时,他是最犀利的批评者,但方式上他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这种道家无为放任的教导手法,正投新祖自我创作所好。除了找到理想导师之外,他运气好而且自我创造能力高,挑选到了对学界具有贡献的博士论文题目。他找到晚明思想家——焦竑——一位能突出左派狂禅与训诂考证之间思想渊源脉络的人物,最具“学术”气息的考证学跟最不学术、具有神秘经验的左派王学,竟有相反相生的辩证关系。这个题目使他有足够的空间发展出较大的典范架构,可以往前溯到明、往后追到清、可佛可道可新儒家、可正统可异端、可谈王阳明思想。面对这么好的题目,新祖花了不少工夫去琢磨,他学着“阅读”推敲佛学、新儒家经典——这跟他初读明史档案的经验一样,他学日文以便阅读日本学者有关佛、儒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所读的材料摆在一观念架构中,并分析其中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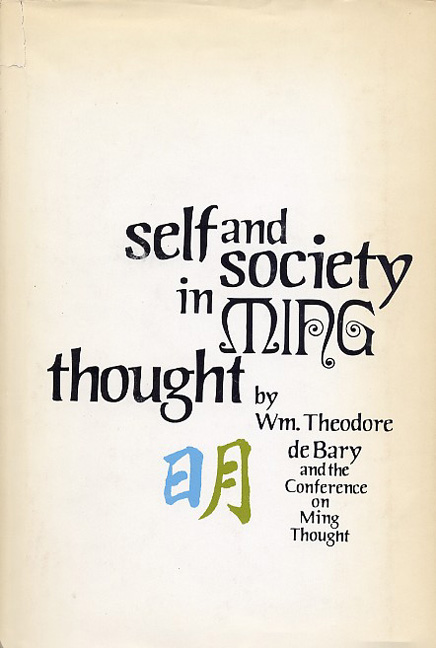
德州风味:另一个美国
1971年秋天,我们离开哥大——新祖旅居美国各地最为特殊的地方,来到休斯敦,因为他在德州的Sam Houston州立大学找到教职,在那儿他才发现、真正体会到美国乡下小城——尤其是德州——的滋味。新祖是个城市人——上海人多半喜欢纽约,但是他喜欢纽约的地方蛮特别的,他喜欢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酒吧和艺术家的世界,他喜欢纽约城市的动劲儿和拥挤着各个人种的街道,更甚于众所皆知的人文荟萃的博物馆和音乐活动。当时我们得把这些抛到脑后,来到Huntsville。它在德州的东边、休斯敦北边70英里的小城,夹在休斯敦和达拉斯的中间,常常见到有人以每小时90英里的车速来往穿梭两地,赶着看休斯敦石油队和达拉斯牛仔队的橄榄球比赛。Huntsville最有名的是拥有德州州立监狱以及德州监狱马术赶集。当地的大学曾被花花公子杂志宣传为“舞会学校”(party school)的第一名。在这儿,新祖发现并非所有美国大学都像哥大或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那样教学工作负荷很重,而是学生并非全力以赴,教授多半关心自己的房地产投资或是当地学校、自己的花园,更甚于关注学术研究工作。德州的经验扩展了新祖对美国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了解。他老是记得当初去学校面试的时候,那些教授们吹嘘着学校的音乐系有多行——他心里算计着大概是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水准,结果那些德州佬讲的是高校乐队指挥的训练。
东德州的确是个美丽的地方——松林、加上春天大片大片野花(蓝帽花和花灌木),但是到休斯敦得开蛮远的车,再者休斯敦也不像纽约那样迷人。在那儿我们交了一些同时间从纽约来的朋友,例如罗洁,他是纽约大学出身的英国史家,他和新祖特爱模仿失落的一代。罗洁每天开车到休斯敦只是为了买《纽约时报》,伙着一群学生、他和新祖学习练枪打靶——德州佬的玩意儿——457型连发手枪,像克林·伊斯威德(Clint Eastwood)的影片所使用的老黑枪(the Dirty Harry gun)。
德州的生活点滴似乎颇为黯淡,但是往回看,我认为这是因为新祖在去德州的时候比去河边校区时对自我的形象更加定型,要是他到美国的第一站是Huntsville的话,他可能会被德州佬直爽乐观的性格所吸引,而不单单计较他们知性的不足。

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我们在德州待了两年,然后到纽约州宾汉姆顿待了三年——1973年至1976年——我在那儿的历史系教书,期间新祖完成了他的论文,也教了一些书,他总是教得很成功。对宾汉姆顿的记忆总是因着它靠纽约比较近,学年期间我们每个月一次开车上纽约、回哥大参加明史的讨论课,并与老朋友聚会。在宾汉姆顿有一个为数不小的华人社区,因为那儿有一个IBM工厂雇用一大群中国工程师,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颇有兴趣,我们因着学校主办有关中国的活动而结识他们。除此之外,他们大多跟新祖和他哥哥还都是台大前后期的同学,我们在宾汉姆顿和这些中国朋友相处得很愉快。
由于新祖已完成了论文,他开始找工作,宾州大学、俄亥俄州的 Kenyon College(颇好的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等好学校都对他表示兴趣。他对找工作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我是来自中西部的一所小学校,总是被哥大的气势所震撼,不太能想象自己会在美国一流学校找到工作,但是新祖却相反,反而如鱼得水,认为在宾州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校教书是适得其所,也许其他学校真的不适合,因为他对学术水准的要求,总是把人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较,然后再往下比,当代知识分子若不够才艺超群是引不起他的兴趣的,他所比较的对象都是创立学术新典范的思想大家。在这样的脉络里,他自然看不上Kenyon College,因为它位处俄亥俄州的乡下地方,鹤立鸡群、自以为是,而且只教大学部。当时(1976年)美国的就业市场早已停滞多时,很多人在抢同一碗饭,芝加哥大学在面试新祖的时候,已经花了四五年寻找顾立雅( Herlee Creel)的继承人选。芝大重理论的面试委员教授们对那些只重语言能力、区域研究的面试者,并不太感兴趣,当他们碰到新祖时,是运气、也是新祖自己的才华受到赏识的造化。就才华而言,他比大部分研究中国思想学者理论强,这点吸引了芝大日本思想史学者;他也熟悉明清和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这点非常吸引何炳棣和邹党(何炳棣面试的时候曾权威地说:“你使我满意!”)芝大每一个派系都喜欢新祖,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芝大东亚部门内斗的情形。就运气而言,他面试的时候竟有那个胆量跟Harry Harootunian说他没有申请其他学校工作,也没有其他学校等着他去教,因为他找不到好学校教书的话,他宁愿开计程车。Harry喜欢他打破成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回答,接着他受到热烈的欢迎来到芝大。
新祖对自我形象的认识非常清楚,有时候人们会因此认为他骄傲自大,但是这点后来证明他是名不虚传的真材实料。他是美国一流大学研究所训练中国研究人才不可或缺的师资,因为他熟悉儒学、佛学、制度史等的传统典籍,同时他也能掌握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他除了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像傅柯、德希达之外,还对许多文学批评理论者了如指掌。换句话说,他是中、英文双语者,真正活在两个文化里,这个不可能的结合竟然发生在他身上,而且结合得恰到好处,他受到中、美两边学者的爱戴,一直持续于芝大的头几年的蜜月期。他对芝大的贡献很大,也充分利用芝大对年轻师资所提供的资源——校园里大师随处可见、灵感随手可掬。新祖在芝大广泛地阅读,并不局限在后现代法国的理论家的作品,慢慢地,他将他的博士论文写成一本书。书和论文非常不同,很难不强调这本书对他的重要性,完成这本书对他而言可说是一件扎扎实实的大事。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好书,里头包含了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哲学,对许多人而言这本书难度太高、不太容易懂,连一些同行也摸不清楚,但是新祖总是不愿直截了当地替读者一一指出他论辩的要点,他坚持读者要能够达到他的水准、看出他文章的要旨与环节的安排。
这本书是1984年夏天在密歇根湖畔的小木屋里完成的,新祖白天思考写作,我帮着打字,下午 5点钟左右我们就结束,燃起火炭、准备晚餐烤肉、享受密歇根湖美丽的夜晚,我想这段时光是我们相处最快乐的时候。完成这本书并达到新祖所要求的品质水准是一项具体的成就,使他能够乐观充满信心地抛开芝大对他申请终身职位的否决决定,另外展开他在台湾、香港的学术事业。

晚年的栖息与隐居
台湾和香港是新祖学术事业的最后阶段,他常安慰地说自己是游牧民族,随处为家,出入不同文化。香港的“外籍兵团”的专家群非常吸引他(虽然他不太喜欢香港),他需要接触洋人,也需要接触中国人,两者不可或缺。有时候他也需要躲起来,躲得没人找得到。每年夏天他就躲回芝加哥,躲回他喜爱的西方,他也乐得躲着不见人,他也许在芝加哥,也许不在芝加哥,芝加哥是他读、写、思考的隐居地,而且芝大的图书馆是世界有名的,他可以躲掉许多人对他的请托要求,许多人不知道他有时候累得需要休息。
现在大家也许可以了解为什么他要选择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安息,跟我父母亲一起葬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峭壁上。以前当我父母亲健在的时候,我们经常回去爱荷华州探望他们,爱荷华对新祖而言感觉像“家”——平静、安全、不变、隐秘。我和月岑将会带他回家。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