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讲座︱这本难读的小说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2022年是爱尔兰国宝级作家乔伊斯的传世巨著《尤利西斯》出版一百周年。二十八年前,译林出版社邀请萧乾和文洁若夫妇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成为第一家全本译介《尤利西斯》的出版社。近日,译林社推出了《尤利西斯》百年纪念版,成为爱尔兰驻华总领馆的指定版本,并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一本世界上最难读的小说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读书活动,邀请著名作家孙甘露先生,著名乔伊斯研究专家、翻译家戴从容老师,中世纪美学专家、爱尔兰研究专家包慧怡老师,作家、著名书评人云也退先生四人谈论乔伊斯与爱尔兰的文化魅力,探究《尤利西斯》是如何改变整个世界的。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摘发讲座整理稿部分内容。

讲座现场
云也退:《尤利西斯》是1922年初问世的一本奇书,我们正好在这样一个年代,赶上出版一百年的纪念。一百年前的1922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爆炸之年,那一年出产了很多后来架构我们文化思维的名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艾略特的《荒原》、鲁迅的《阿Q正传》都在那一年问世。还有弗雷泽《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航海者》、著名德国小说家黑塞的《悉达多》都是在1922年问世。普鲁斯特于1922年去世,那一年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了第四卷。
那一年有很多事情发生, 可以说是战争结束之后的一个喷发期,各种文化思潮已经初现端倪,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以及弗兰克·哈里斯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与爱》在同年出版,之后被禁了40年,因为里面有很多露骨内容。
今天讲的《尤利西斯》也曾经是一本禁书,它被禁的历史要更加出名一些,因为在1922年莎士比亚书店初版之前,《尤利西斯》就在美国的一本杂志《小评论》上连载。当时美国检查的人员发现这本书有点问题就要求媒体、杂志缩短连载的时间。乔伊斯十分焦急,书好不容易写得那么多,想发表一些赚点稿费都出了很多的问题。当时他坚持把书写完,但是在最后两三年里面已经是有很多的麻烦事找上门。他的出版商,包括跟他相关的一些朋友都为这本书的命运捏一把汗。
我们现在完全不用忌惮这些东西,我们是这本书的受益者,也是享受这本禁书历史红利的人。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争议开始说起。请四位老师先聊聊,当年萧乾和文洁若在翻译好这本书,它成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时候,译林出版社也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当时有没有感受到《尤利西斯》出版的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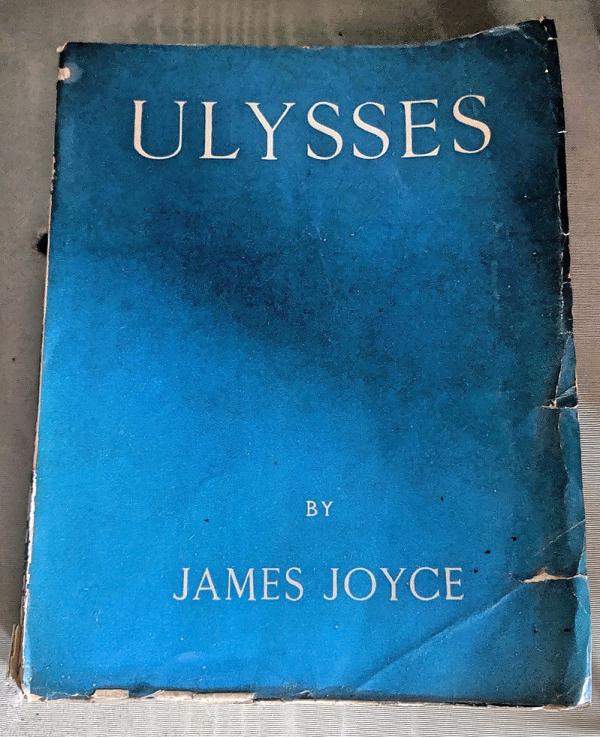
《尤利西斯》1922年初版
包慧怡:乔伊斯是爱尔兰文学的研究者,本身也是作家、诗人,也是非常合适的阐释者。因为乔伊斯这本书说是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诗集,一个小人物的史诗,也是一部戏剧。很多人觉得写作难懂或者里面的声音很多。如果把它看成戏剧,有很多声口,都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说话,有时候一个人自己也分成了好几个人,在内心说话,既是对内部世界的观察,也是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有时候聚集在一起,有的时候分开,有的时候好像很世俗,有的时候又非常诗意,是一部非常精妙编织的作品。
有人说文本是一个织体,这张毯子织得非常繁复,非常精妙。今天三位都是非常好的研究者和批评者,我其实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尤利西斯》的出版在当年实际上对读者来说是蛮震惊的,虽然史上有《追忆似水年华》《长夜漫漫的旅程》这些书。在每个语种,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一些殊异之人,做常人所不做的事情,在文化脉络里观察也是非常有意思。
云也退的开篇讲得非常好,提到1922年这个年份,我非常赞同。这本书虽然写的是1904年6月16日的事情,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小人物,一天18个小时在都柏林游历的历程。但是实际上它的内涵有很多,既可以在小说的历史脉络里看,可以在爱尔兰文学里看,也可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中来看。
云也退:《尤利西斯》是在法国出版,因为法国相对来说能够容忍这样的书出版,是乔伊斯在法国的好朋友帮他出的。过了十年,到1932年的时候,兰登书屋才在美国给他打开正规出版的市场。那个时候乔伊斯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眼睛视力很差,又有梅毒,同时被各种麻烦缠绕。直到《尤利西斯》在美国出版,他才算是可以靠这本书来过余生。这是一段非常艰难也很传奇的历史,传奇意味着当事人被深深卷入到这本书的书写,跟他的命运一起共沉浮。
爱尔兰给人的印象有点像被抛弃的小岛,但又被天主教所接管,有着跟大陆之间的疏离感,在乔伊斯书里绝对有着强烈的烙印。读《尤利西斯》有时会有种感觉,乔伊斯描述教士的荒诞和滑稽是在挖苦他们,但是乔伊斯本人又是充满着宗教的底色,所以想听听包老师聊聊关于爱尔兰、乔伊斯、《尤利西斯》和天主教的关系。
包慧怡:爱尔兰是北大西洋里的一颗眼泪,就像两千多年前希罗多德、塔西陀写作都说爱尔兰是冬境、冬天之地。他们描述说,人类文明到此为止,再西就是北大西洋的波涛,那里什么都没有。至今没有什么变化。爱尔兰作家对于自己处在孤岛上这种封闭的感受都有相当的共鸣和表现。其实乔伊斯一辈子都在跟这种岛屿性或者固步自封性做斗争。他其实是功成名就以后或者成年之前抛弃了爱尔兰再不踏回来的文学家之一,这些名字里有王尔德、贝克特等。这里的确跟刚刚提到的天主教氛围有关系。
乔伊斯是我的校友,我在爱尔兰念博士的大学叫都柏林大学,我们大学的图书馆就叫乔伊斯图书馆,好像听起来以他为荣。其实我在那儿写了四年的论文,每天推门进去看到他那张脸,好像在督促你,“再不写就有我好看”,所以我有点创伤记忆。
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实际上在《尤利西斯》出版的时候,爱尔兰没有待见过乔伊斯,甚至爱尔兰第一个出来指责乔伊斯的书伤风败俗,乔伊斯感到非常痛心。《死者》是他22岁时完成的中篇,他在22岁写完就开始积极地寻找出版,然而碰了一鼻子灰。30岁生日前没几天在都柏林,他已经在起稿《尤利西斯》了。后来出版社终于答应排版,并活字排好,最终却又谈崩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本书会触怒很多人。首先会触怒教士阶层,触到天主教敏感的神经;其次会冒犯英国国教会,因为1916年恰逢爱尔兰闹独立的敏感时期。
独立战争制造了非常敏感的民族氛围,包括叶芝等在搞凯尔特文艺复兴,乔伊斯对叶芝他们这些活动有同意的地方,也有保留的地方。最后总之不能出版,乔伊斯一怒之下,差一点要把他的手稿烧掉,活字版也被毁掉了。过了八年,作品还是不能出版,乔伊斯带着他的妻子——之前他跟诺拉已经私奔了——在当天晚上最后一次坐火车彻底离开了爱尔兰,终生都没有再回来。
这个既像他与所出生的一座岛屿做地理上的告别,同时从此以后他一直对叶芝搞的民族文学复兴颇有微词。他认为真正做文学的人是要跨越国别。他实际上在骨子里是世界主义者。当然他没有这么标榜过,也可以说他有点生不逢时。
刚刚孙老师提到,乔伊斯本身是一个诗人,第一本出版的书是一本诗集,叫《室内乐》。其实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很多地方体现出他是一个智性诗人,不是说他写分行的文字就定义为诗,而是他是用诗性的方式处理现代文明的弊病,更像波德莱尔、贝克特。
那个时候叶芝有一本书叫《凯尔特的薄暮》,后来批评者都说,包括50年代国内很多人也在反思,为什么爱尔兰放逐自己最有良心的智性诗人之一。有一位诗人著名的论调说,“抒情的爱尔兰一次又一次放逐了智性的爱尔兰”。这样他就可以把我们的问题——那些复杂的宗教、性别,所有复杂的问题放逐到欧洲的老沙漠里面,在这个绿宝石岛上我们可以不再处理它,如此爱尔兰就可以保留它那如梦似幻、凯尔特薄暮式的岛屿风情、竖笛、神话,这是一个局内人、局外人共同创造的迷思。爱尔兰岛屿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是仙子和精灵翩翩起舞的抒情岛屿,而欧洲是老到、腐败的,所有这些文明和城市的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个时候乔伊斯要处理那些普遍的人类经验,但爱尔兰人并不情愿,他们更加倾向于爱尔兰、凯尔特民族复兴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乔伊斯的孤独是注定的。当他拒绝加入叶芝那种以爱尔兰民族文学,爱尔兰抒情性作为写作名片的共同体时,这意味着他必定扎根更加普遍的世界文学,而不是岛屿的经验。虽然他在巴黎、瑞士不断地回溯爱尔兰的岛屿经验,但那是这完全不留情面的一种,拒绝去美化它。虽然他是很好的乐手,但他可能会拒绝把爱尔兰经历等同于这样一种抒情。
云也退:这很有启发。一般来说,一个大作家如果能跟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土壤特别和睦,好像他的路径就没有那么开阔。必须要跟自己的故土和滋长自己的文化环境保持紧张的关系,才能进入更广阔的文学疆域。
接下来听听戴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问题很适合问您,在您一步一个脚印翻译的时候,对乔伊斯旁征博引,每一句话都得有出处这样的风格,您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样一种写作?
戴从容:非常好的问题。乔伊斯虽然被称作小说家,但是他小说独特的风格就是百科全书式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义,这相当于在小说里开启了新的模式。
乔伊斯为什么要在他的作品中放入各种各样的知识,让人读起来非常困难?我跟我的学生会说,读乔伊斯的作品其实需要看一些注释,因为它的阅读绝对不是简单的情节阅读,相反,阅读乔伊斯的作品实际上是文化的阅读。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没有办法真正地感受到乔伊斯想表达的意思。

《尤利西斯》出版百年纪念版
乔伊斯这样做其实改变了我们对阅读小说的概念。小说是什么?它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乔伊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说法——戏剧是一面镜子,他认为小说是一面镜子,文学也是一面镜子。小说是要把我们带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逃避到一个虚构的世界里。相反,当你读小说的时候,应该能够使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发生改变。这也是我读《尤利西斯》时的第一个印象,也是最震撼我的东西。我最早读的中译本是1994年译林版,当时我读完以后,一直没有办法忘记。我躺在学校宿舍的床上,感觉整个社会、人生在我面前展开,这跟我读任何小说都不一样。
有的小说可以告诉你一个道理、一种善恶观,但乔伊斯不告诉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是你的人生目标。相反,乔伊斯的作品会让你理解各个方面的文化。乔伊斯在他作品中的态度是包容的。我一直认为乔伊斯是一个高雅的作家,即使是音乐——乔伊斯在作品当中也会引歌剧——我觉得他都应该是把一些最崇高、最深刻的东西给我们。当我去都柏林参加乔伊斯会议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说明,歌剧在乔伊斯的时代其实是属于中下层的艺术,而我们一向都认为歌剧很庄重的艺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歌剧在他们那个时代有点像我们的电影。
乔伊斯在作品里当然有表现很崇高、很深奥的东西,比如说会追溯到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圣经》等,同时他也会拉回到现在,把最日常生活的东西给读者,这是乔伊斯对生活真正的认识。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文化,不分国别,不分高低贵贱,甚至不分古代和现代,完全地呈现出来。阅读乔伊斯之后,影响我的是乔伊斯对世界各种各样文化的认可,他的这种态度能够真正改变整个人。
云也退:很不容易,您能把这本书看完,而且是做学生的时候。我记得译林的初版是上下两本、白封面,书脊上的烫金字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也是出版盛事。我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好好看过这本书,或者这本书有没有给您一些真实或者具体的启发?
孙甘露:又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乔伊斯作品的出版不管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不同作家的角度以及当时翻译出版的角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像云也退问的,我是从阅读上来讲,很多译段我是很喜欢的,有实验性,不那么循规蹈矩。这本书就像其他重要的大部头一样,一下子读下去,对任何人来说都会面临消化不良的问题。我觉得有的书需要慢慢来,不是说一次性处理掉,包括阅读的过程。当然阅读的经验是非常震撼的。
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本书出版前后,也就是1980年代或者前后那个时期,大量引进介绍的西方文学,包括拉美的文学作品,有很多重要的作家都对中国的读者和写作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刚刚云也退也提到了。但是在这个作家身上好像又看不到什么具体的影响。因为我看过他的研究性材料和他的传记,乔伊斯这个人本身非常复杂,好像有英雄气质却又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像他手底下的人物一样世俗。从他书里可以看出,他好像是通过非常微观的一天的历史在隐喻一些什么东西。同时他的喜恶又是充斥着日常里曲里拐弯的小心思,包括民谣的应用、市井的声音、意识活动、联想、反复出现的象声词。从文体上讲非常有趣,同时仔细研究,会发现实际上包含很多含义。所以我一开始讲,如果把《尤利西斯》在舞台上演出来,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因为它就像后来所谓的通感——嗅觉、知觉、味觉,描述各种各样不同,把它们汇聚在一个空间来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望那个年代,对中国读者来说,当然这本书是困难之书,如果把小说纯粹当故事来看是非常困难的。对普通者来讲,买这部书回去读,实际上帮我们开阔了视野,知道上限在什么地方,同时形成一个关照,你可以再回头来看日常阅读的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展开。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天才之书,但也是困难之书,也可能它太困难了,在当年,好像在中国的写作者中间的接受史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我讲到乔伊斯有很多耸人听闻的经历,包括云也退也在讲,有很多爱尔兰作家离开。我发现爱尔兰最重要的人好像最后都跑掉了。我记得前一年去都柏林参观了,我去了他写作开篇的圆塔,也去了乔伊斯家。好像是凯尔特民族中好的作家都是本民族语言的陌生人,在本民族语言当中寻找一种异质性的力量,好像跟这个传统有隔阂,当然这个分析起来太复杂了。这种特异性确实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如果一个读者对阅读小说非常有兴趣,我觉得像这些书实际上是来标定小说疆土的,把疆域中这样一些地标标出来,既是世界小说的地标,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地标。这是我读之后的想法。
云也退:当代的作家如果要模仿意识流,觉得很难攀登到乔伊斯的高度。可能意识流絮絮叨叨,绵延不绝,像讲梦话一样叙事的方式,在《尤利西斯》里面要比在普鲁斯特的书里面更加突出。因为这种絮叨和梦幻的感觉好像是更加局限,因为是在一天里面,使人觉得这一天怎么也过不完,如果这个人一直保持这种意识流,他就不会死一样,这一天都过不完,更别说一生了。
在这样一本小说面前,如果尝试以它为标杆写作,是非常难的,也只能写一本缩小版的《尤利西斯》或者初级阶段的《尤利西斯》,不如模仿相对来说意识流没有那么漫长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像是《喧哗与骚动》《海浪》这样的好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认识,不知道三位老师怎么看。乔伊斯使用的意识流写作,是在捍卫给小说题材的独立性,只有小说可以做到这一点,任何别的学科作品都不可能像乔伊斯这样写东西。因为每个学科都需要有创作,别的学科不能像小说这样拥有独门的技艺,让读者感受到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无限的旅程。
我们知道法国有伯格森这样的哲学家,他颂扬生命无休止的流动,但是他的书你看完以后就看完了,仅此而已。爱尔兰有萧伯纳,很多戏剧是依据伯格森的理论来的,让戏中人大量的对话密集地交错进行,使场景一直往下延续。当年这种思潮,也肯定在乔伊斯的作品里面有它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对文学和小说本身的捍卫和提升。刚刚戴老师讲到,小说是镜子,可以照出很多东西来,但是问题就是,也许19世纪的小说更多地作为一个平面镜来处理,小说反映了某个年代、某个社会里面的某个阶层的故事,读小说就解到这里有什么样的人物、阶层、矛盾,但仅此而已。在《尤利西斯》里,就像在康拉德作品中一样,一个人带着我们读者漫游、追寻,并不是要找出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走过一段旅程。这面镜子照出了什么?一定不是直接反映客观的社会,而是需要你在里面去跟着他走,跟他共振、共沉浮,一起体会的感受。包老师,你对都柏林非常熟悉,您可以不可以说一说漫游的感觉和意识的关系。
包慧怡:正好说到《尤利西斯》,它的标题大家都知道是拉丁文的“尤利西斯”,其实是“奥德修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乔伊斯这本书里面没有一个人叫尤利西斯。我觉得有三个主人翁,布卢姆是男一号。但是其实整部小说有十八章,前面三章讲的是男二号,这个人被认为是乔伊斯自己,也就是斯蒂芬·迪达勒斯。大家听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他是古希腊神话里第一大迷宫建造者,克里特岛的国王弥诺斯请他为牛头怪兽弥诺陶建造迷宫,结果迷宫建成以后自己也不被允许出来,于是他做了一对翅膀逃离。他的儿子不听他的劝告,飞得太高了,离太阳太近 ,结果翅膀融化,坠落海中。

乔伊斯
这个人很重要,因为他是乔伊斯的前两本小说的主人公。乔伊斯有一本生前没有出版的小说,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的长篇小说,叫《斯蒂芬英雄》。那本书写完了又觉得不行,自传成分太赤裸裸了,他希望有距离的自传,于是他另起炉灶写了《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但是里面主人公依然叫斯蒂芬·迪达勒斯,他太爱这个名字了。斯蒂芬其实是第一个殉道的圣人,被石头扔死的。乔伊斯那么爱他,一直到《尤利西斯》还为他写了最初的三章,有点像布卢姆的父和子,当然不是生理上的父和子。
其实最后一章是给布卢姆戴绿帽子妻子摩莉在家里的独白,没有任何标点,密集的文字倾泻而下。其实《尤利西斯》前六章挺保守的,像现实主义小说。如果想感受乔伊斯惊世骇俗在哪里,建议大家从第十八章开始读。他是一个文体大家。乔伊斯说,读这本书就知道,没有他不能拿语言做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做。《尤利西斯》里面有报刊体、史诗体、抒情诗体、论文体,论文也可以成为小说。里面有一章直接是长篇小说,180多页,小说里套的一个小说。
回到漫游的主题,大家读过《奥德赛》,觉得《奥德赛》卷数跟它并不统一,它不是一卷一卷,而是一个一个故事,因为乔伊斯虽然是一个学霸,学了很多的语言,但是他小学读的《奥德赛》故事是英国散文家、浪漫主义时期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写的《尤利西斯故事集》。所以根据他的童年记忆,像今天看美剧一样,跳出来的是一个个人物。他原来的每一章节都对应《奥德赛》的人物,第一章是尤利西斯的儿子,也就是奥德修斯的儿子。最后一章是奥德修斯的妻子,正好一一对应。包括独眼巨人、食莲者都是对应的是一个一个故事。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雄心是要进行一种史诗和仿史诗或者讽刺史诗的对照,但是等《尤利西斯》出版的时候,他最终把标题拿掉了。如果自己不把宏大的计划说出来,是很难从里面一一找到。
译林的《尤利西斯》译本,文先生在后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对照表,每一章对应的是《奥德赛》里面什么样的情节。我们读了以后,发现这个对应不是一种镜像的反射,而更像是一种回声和发挥,就像关键词一样的作用。但是它给了我们今天读者一个很好的入口,刚刚大家都提到说,读的时候会觉得,一百年过去了依然觉得它有门槛。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比如说爱尔兰人就很想得开,虽然当年说这书伤风败俗,不承认乔伊斯,但是等他被追为自己的国民作家以后,也无缝对接,毫无障碍。
布卢姆的游荡发生在18或者20小时内,等于是一张漫游地图——译林这个版本里面也有一张漫游地图。在我体力比较好的时候,我也按照这张漫游图在都柏林游览过一圈。就是从早上8点钟始于都柏林郊外的马铁罗圆塔,晚上到国家图书馆,中间到过都柏林市中心各个著名的酒吧。这既是时间维度上的一天的游历,也是空间维度的游历。爱尔兰乔伊斯中心就做了一件很吸引人的事,这也是半个世纪的传统,让大家加入布卢姆日的阅读,以每两个小时为一个单位,每两个小时换一个地方。一早在海边的圆塔上,这个时候是人最多的,因为早上八点能起来的人都去了,在那里进行cosplay,戴那个年代的圆草帽,穿那个时代的衣服朗诵、表演。刚刚孙老师说到,《尤利西斯》能够用戏剧的形式演出来是非常棒的体验。那个时候我也加入过这种接力朗读,磕磕巴巴在那读。
两个小时后到下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比如说跟着布卢姆吃他早上那一顿著名的羊腰子早餐。今天爱尔兰的旅游业已经是依据这个布卢姆日来布置,包括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吃过的羊腰子早餐。有好几家餐厅酒吧都号称自己能做出最地道的布卢姆当年吃的那个味道的早餐等等。如果对这本书心怀畏惧,大家不妨采用这种打卡式的体验。实际上乔伊斯和文字是慷慨的,是深邃无边的,并没有对我们提要求,一定要用学究的方式去读,其实普通的读者用这样的方式读挺好的,像过节一样,没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跟到下午两点,因为路盲,体力不支跟丢了,到了两点神智都不是很清楚了。在此之前,神智还大致清楚的时候,最后一站到布卢姆买柠檬香皂的那一家药剂店。这个药店在150年间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当时书里描述,布卢姆要了一块柠檬香皂,觉得味道闻起来特别好,这种香皂现在还在卖,5欧元一块。我们今天的城市是日日新的,不要说150周年,5年前的地方都不一定能找到,但是他书里出现的地标大部分还在原来的地方。有的时候读到后面的章节,比如第十八章,已经太晚了,可能很多人就去睡觉,但是这一章又很重要。所以每年都会请一些女演员,到药剂店拿一张长沙发躺在上面表演摩莉的独白。当时我神智还算清醒,当时看了非常感慨,因为摩莉独白对演员的台词功底要求非常高,几乎上气不接下气,我想象是彻底的急风暴雨一般的。
大家在读《尤利西斯》原著前,其实也有别的办法,比如说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1982年出了32盒CD,请了当时最好的广播剧演员把演播出来。这一套现在好像在亚马逊上也买不到了。这样通过听觉进入也可以。因为乔伊斯是一个非常极富感官性的作家。他给自己画了一个谱系图,他说每一章不光对应到《奥德赛》,还对应感官,从第四章开始,从布卢姆章节开始,第一章对应肾脏,因为他对应羊腰子,第二章对应生殖器,第三章对应心脏,他最后是人体感官的漫游。
其实读完,何为人体,何为身体性——刚刚孙老师说的文本性、身体性。生而为人,何为神圣?何为肮脏?里面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屎尿屁就不太能写。乔伊斯不管,到马铁罗圆塔——那个圆塔现在改为乔伊斯的博物馆——进去可能最震撼的就是那个巨幅画像,今天看来是黄色的,是当时一些画家为他画的,人物躺在那里,直白地对着这个城市。
我刚刚说有三个主人公,也有可能是第四个主人公,就是读者。他要求读者加入到多路途的漫游当中,邀请每个读者检视自己。当然身体器官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检视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拥有身体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20世纪使用语言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个意义上许多人都是许多路途和主题的奥德修斯,所以人人都是布卢姆。
刚刚戴老师提到,我很喜欢布卢姆这个人,因为早期会说,他是中下阶级平庸主义,但是我觉得布卢姆远远超越这一切。里面有每个人追求的人性的宏大或者崇高,更好的那一部分东西,也有每个人作为普通人的那一方面。乔伊斯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所有的美颜滤镜撤掉,并且邀请大家一起撤掉自己的滤镜,看看你被正视时的样子,正视一个活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的人。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我用我的文本,像乔伊斯用他的文本,向大家打开一扇门,每个人是自己的奥德修斯。 《尤利西斯》这个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普适性,我想这是为什么一百年后大家还在讨论、阅读它的原因。我们走进这位作家打开的一个迷宫——一个物理的迷宫,更多的是心灵的迷宫,这个迷宫的谜面就是认识你自己。
云也退:戴老师能不能请您说一说,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关系。为什么写了这样的书以后,还要进行那么宏大的创作?
戴从容:实际上乔伊斯是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作家。《尤利西斯》,正如刚刚包老师介绍的,是在都柏林的漫游,又不仅仅是漫游。包老师跟着专家游历都柏林,其实到了都柏林,只要花一百欧元,就会有人带着你沿着这个书的路径去走,游览都柏林主要的场景,那些地标性的建筑物都可以看到。因为实际上《尤利西斯》可以说不仅是一份地图,而且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尤利西斯》所给予的,不是简单人物的故事,而是整整一个城市的时间、空间和故事。
在写完《尤利西斯》以后,乔伊斯说过,如果都柏林城被毁掉,可以用《尤利西斯》来重建。乔伊斯是一个永远不满足的作家,而且他的每一本书,后面一本书比前面一本书更向前一步,视野更加开阔,那么乔伊斯在写完都柏林城的历史之后,应该写什么?应该写这个世界的历史,应该写整个人类宇宙的历史,这就是《芬尼根的守灵夜》。
《芬尼根的守灵夜》虽然凝聚在一个夜,但是实际上相当于是一朵鲜花与世界。这不仅仅是都柏林的一个酒吧,实际上乔伊斯通过很多文化的借用,把整个人类的文化都囊括其中,包括中国的文化,从孔子开始一直到孙中山。所以实际上《芬尼根的守灵夜》是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物历史囊括其中,从来没有作家做到过。怎么样才有可能这样做呢?只有打破原来的限制,因为实际上语言都属于某个民族的。现在乔伊斯要把所有的语言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自己重造了语言。
大家都说他的作品是天书,他在制造语言。我们中国有一个艺术家徐冰自己创造过文字,但是乔伊斯的创造法跟徐冰不一样。徐冰是自己创造,而乔伊斯其实不是创造,他实际上是借用了《爱丽丝镜中漫游记》中的那种方法,包括那面镜子。乔伊斯的镜子不是简单的镜子,乔伊斯的镜子是《爱丽丝镜中漫游记》中的镜子,是一个奇幻的万花筒般的镜子。他借助了各种词要素的组合,所以乔伊斯的造字融合了很多词语,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中文词汇,只不过是用拼音的形式,还有梵文,都是用罗马字母组合在一起的。阅读的时候,不仅仅是猜乔伊斯的语言是怎么读的,而是要读出来各种文化的语言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意义。
云也退:有时候我们的语言过于习惯既有的使用方式,我们不太会知道外面有什么样的边界,我们只满足看那些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讲的貌似很新奇的故事,感觉作者居然想出来了这么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的文学阅读就停留在这一步,很难谈得上在读文学。而外国的这些作品,对于我们的中文读者来说,可以说是大开视野,对我们语言的感受来说是一种冲击。
刚刚包老师讲到摩莉最后没有标点的长篇独白,也讲到这样的独白在戏剧舞台上的演出,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验。我记得我当年看《等待戈多》剧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长篇独白,不知道贝克特是否也从这里面吸收到灵感,他让一个一直没有台词的人,滔滔讲十分钟的话,都是上句不接下句的语言轰炸式的东西。我们看到之后非常震惊,这个剧里面有一种极端的荒诞,当两个主人公已经没有话讲的时候,之前一直没有话的人突然说出来一大堆不是话的话。这种震撼力对于我们这些沉浸在日常语言里的人来说是破坏式的体验。
可以引用书里的一句词,摩莉重复的一句话,她说我的艺术的完美象征就是仆人用的一面有裂纹的镜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作为乔伊斯自己的艺术观的提炼。因为乔伊斯认为,绝对不能从我的写作中读出一个四四方方完整的东西,它一定是扭曲、变幻的,每个人来看都有不同的体会。我想这种感受,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生事业的最终境界。他希望达到这个境界,不管他的书在他生前有什么样的遭遇,希望在今后一百多年里面仍然可以获得大量读者的喜爱,但是他可能想不到那么多了。对于乔伊斯本人这方面的抱负,在写作时候对自己的期许和理解,不知道三位老师有没有自己的心得,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孙甘露:轮着发言就像一种循规蹈矩的做法,这不是乔伊斯的做法。这是开玩笑。您刚刚讲得非常好,作为一个作家,乔伊斯是在小说创作艺术上有宏大抱负的,日常生活中他也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可能都不适合在现在的场合讲,当然不仅仅是说像《尤利西斯》当中的有些语言,当初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内容。同时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转变,有些事情在发生改变,比如说一本禁书,因为各种原因,不再是禁忌。一部伟大的小说所描写的东西,即使针对特殊的对象,在特殊时代来写,有它的普遍性,或许这个禁忌过去了,又有新的禁忌出来。另外,像刚刚包慧怡老师所讲到的,你也可以把《尤利西斯》看成是一部对传统的致敬之作,是对经典的挪用或者是形成一种对位关系。
但是小说,它是一个高度很高的智力活动,同时小说又不是论文,所以这些东西是以小说的方式处理,同时又是关于感情的百科全书,有非常崇高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处理了很多可能在某些场合不能公开谈论的东西,这也是造成禁忌,造成冲击性的原因。同时,他所处理的所有这些道德的问题,哲学的思考,人类历史的观察,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也会处理。但是通常写作关心的是乔伊斯为什么这样写?因为他可以用歌剧的方式处理这个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史诗的方式处理,作为一部小说,他为什么要写成一部小说呢?当然一个作家的成长或者发端,刚刚几位讲到的,《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等一系列作品,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包括对他所生活的城市的观察,实际上是一次内心的漫游式的旅行。
小说有两种,一种是古往今来的模式,精神的漫游或者是世界旅途的漫游,还有一种是家族式的,像《红楼梦》,大体上无非就是这两种模式。实际上他在写作上的颠覆性并不在于不好理解,如果仔细读,会发现并不是不好理解。一般传统小说的写法会有一种提示,而在乔伊斯的作品中,有的时候把这种提示都去掉,有时候是有不同的东西互相提示的。比如先写声音,然后他写了一个人的想象,这两个东西有关系。
当然,这个对普通读者来说有点费劲。有的小说是用一个人的视角写的,还有很多是让人物说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比如我是一个开车的,我有一种职业或者生活经历,一个教授有教授的说话方式。在《尤利西斯》里,人在不同的处境下,有崇高的一面,有社会规范约束的一面,也有在私下里一种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他把不同意识层面的东西汇聚在一个叙述的层面上,要理解这样一种方式,对读者是有挑战性的。
我设想,乔伊斯应该有一个阅读日,不仅仅针对乔伊斯,也是针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通过具体的读、对具体段落的讨论理解,不仅仅对乔伊斯增进理解,对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提升效果。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