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康子兴|政治现代性“系谱学”:重新发现弗格森与严复

1905年严复伦敦留影
1895年,甲午战败后,严复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开篇写道: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未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构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面对激烈的历史冲击,严复对世人的谓叹与亚当·弗格森在《论文明社会史》中的感慨颇有相似之处。严复所谓“世变之亟”大抵有两层含义。首先,甲午之战,“横决大溃,至于不可收拾”( 严复:《原强续篇》,《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黄克武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20页),战事败绩之惨烈,后果之深重,前所未有。其次,甲午战败乃“三十年频仍祸乱”最具代表性的事件,由战祸折射出的文明危机前所未有。亦即,甲午战败根源于中西文教、法制传统之差异。时至今日,国人必须承认,“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同前,12页)。中国与西洋(乃至东洋)的遭遇不只是战场上的遭遇,而是两大文明传统的遭遇。所以,战场败绩不只意味着军事与武器上的弱势,更凸显出双方在民力、民智、民德上的差距,或在孟德斯鸠所谓“普遍精神”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世变之亟”亦为超乎惯常理解之亟。所以,若固守旧说习见,对此剧烈变局,人们“莫不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认为它超越了人类理性,也非人力所能左右。面对如此重大的危机,若将国族与文明的未来托付给“运会”,自是放弃了任何积极作为的努力,也彻底放弃了对国族与文明的责任。对此态度,弗格森在《论文明社会史》的结尾处评论:“当他们将多数事务诉诸命运时,便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命运的反转。我们倾向于使这些观察形成法则,当我们不再愿意为了国家而行动时,我们便寻求一种人类事务中假定的宿命,作为自身柔弱或愚蠢的借口。”(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64)
严复当然反对将此世变简单地理解为“运会”。正如他在这段评论中所言,真正勇毅明智的做法,当如“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严复相信,当前的激烈世变实有其历史根源。关于秩序与治道,中西理解各异。在历史演化中,日积月累,观念上的差异最终塑造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形态,从而造成国力之强弱分殊。所以,若要摆脱当下之困境与危机,圣人(或立法者)必须超越所谓的“运会”,对之做一番外在、客观的审视,理解其前因后果、由来与趋势,并洞晓世变之因由与根源。亦即,“运会”绝非无头绪、不可理解的非理性力量,而是受自然大道主宰。唯有理解了这一自然之道,圣人才不会成为“运会中之一物”,才能顺应天时,积极作为,实现大治。相反,谁若放弃这一理解的努力,那他就是甘于受到蒙蔽,展现出弗格森所谓的“柔弱或愚蠢”。然而,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一大道,找到主宰治乱兴衰的根由呢?严复指明,我们应当向历史索求启发,要“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亦即,我们应当对世变做一番历史研究,考镜源流,方能追溯“流极”,找到今日困境之因由与出路。所以,严复的思考蕴含了某种“系谱学”方法:他致力于从长时段来考察世变,将一时一刻的遭遇在历史中充分展开,并在中西比较中洞晓“运会”之实质。
从马基雅维利时刻到严复时刻
十九世纪末叶,政治现代性在西方发育成熟,逐渐演化出具有全球政治视野的“文明帝国”理论。西洋的坚船利炮携带着自由贸易观念、文明演化逻辑,乃至世界帝国构想越洋而来,如海潮般冲击着东方文明。现代性遂以严复笔下的“世变”展示于中国人的心灵。
“世变”是晚清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传统秩序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一场战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严复心里明白,要化解危机,赢得战争,就要对传统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并深刻理解汹涌而来的现代性浪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文明更化,实现旧邦新命。严复的思考与探索代表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萧高彦教授仿照波考克(J. G. A. Pocock)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概念,称之为“严复时刻”。萧高彦也强调,正如“马基雅维利时刻”代表了一种西方共和主义面对特殊性政治世界所发展出的政治论述结构,“严复时刻”也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而已,而是形塑日后政治论述的关键时刻(萧高彦:《探索政治现代性:从马基雅维利到严复》,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2月,559页,以下仅标注页码)。

萧高彦著《探索政治现代性》
在导论与结论部分,萧高彦一再申述驱使他写作《探索政治现代性》的两大问题意识:“自由、民主、权利、宪政,以及国家主权这些政治现代性的价值,是如何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开出的?”以及“哪些核心的西方政治理论经典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价值的形成?而这些经典的语汇以及理解证成的方式,如何通过在地的知识以及行动,转化成中国知识分子及行动者在中国的语境中,用来论辩、说服,以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第5页、18页、719页)
萧高彦受剑桥学派“脉络主义”方法影响,致力于分析政治话语,探究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及其发展流变。这两大问题分别指向西方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系谱,也一一对应于“马基雅维利时刻”和“严复时刻”。
问题决定了方法,甚至,作者的提问方式本身就蕴含了他理解政治观念的方法。在提出问题的时候,萧高彦使用了“开出”“形成”“转化”“斗争”等一些列动词。这表明:在他看来,政治现代性价值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甚至经历了颇为复杂的辩论与斗争。在他试图回答的两大问题中,“严复时刻”问题更为根本,甚至包含了第一个问题。原因有二。首先,第二个问题呈现出萧高彦教授对中华文明命运之追问与关切,此乃他“探索政治现代性”之立足点。其次,只有充分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全方位洞悉西方政治理论经典的历史脉络(或语境),我们才能相对全面且真切地体认它们对中国的塑造,以及它们为严复们带来了怎样一种现代性视野。亦即,“马基雅维利时刻”确立了“严复时刻”试图回应的现代性脉络,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他者与自我之关系。所以,对马基雅维利时刻的重新解读与系谱学梳理就构成了理解严复时刻的部分前提。当然,“马基雅维利时刻”与“严复时刻”本身就是具有浓厚剑桥学派色彩的语境主义概念。它们特别强调政治思考、话语在历史语境中的意涵,将之视为一种历史行动。它们暗示着,由它们代表的特殊“论述结构”乃是在具体的政治论辩中形成,因此,只有理解其论辩对象,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论辩的意图与含义。因此,他才着力探究“马基雅维利时刻”与“严复时刻”之系谱,而非对政治思想结构做一番“系统论”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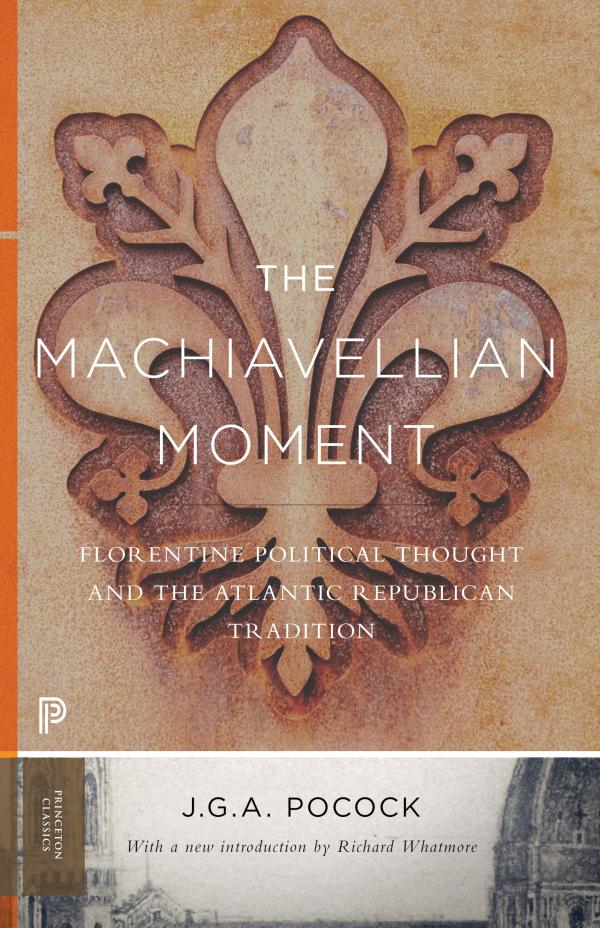
J. G. A. 波考克著《马基雅维利时刻》
萧高彦选取基尔克与施密特为代表,批评了对政治思想的系统论诠释。基尔克与施密特皆为影响甚巨的学术名家,然而,他们也都依其“偏见”来塑造政治思想的历史,令其分析与线索“相当单一化”(720页)。例如,基尔克因为过分执着于某种“正确的”社会契约论,便以奥图修斯(Althusius)之理论为准绳,批判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一切理论(720-721页)。施密特则因为“对于政治决断、主权以及霍布斯式代表的强调”,使其论述刻意压抑自由主义与宪政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政治”要素(723页)。所以,此类系统论思想史实质上是“反历史”的政治思想叙事,不能真实呈现历史与政治现代性。
萧高彦抛弃系统论,选择系谱学,力图让思想回归历史,恢复其复杂性与丰富性。如其一再强调的那样,思想即行动,思想论辩关乎国家与文明之未来。亦即,唯有历史地理解思想,我们才能培养对现实的深刻洞见。在他呈现的系谱学里,西方政治现代性的进程分为两波。第一波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终结于普芬道夫、洛克等社会契约论者。第二波始于孟德斯鸠,终于十九世纪的文明论与帝国自由主义(以托克维尔、J. S. 密尔为代表)。
两波现代性都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演变,但皆有其内在的统一主题。第一波现代性剑指政体问题,终将政体原则由追求德性与共善的目的论,转变为个人的平等。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亦随之转移,由如何构筑德治政体转变为如何确立政治权威之合法性。第一波现代性使人民主权原则落地生根,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精神。
第二波现代性则凸显“商业社会”因素。自孟德斯鸠以来,政治思想家充分注意商业对社会秩序的塑造,及其对人心的影响。在十五到十八世纪之间,商业社会逐渐兴起于欧洲,并促使欧洲摆脱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孕生出现代国家制度。亦即,商业社会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而非抽象的理论建构。所以,对商业社会的重视也意味着:在理解古今之变及政治现代性问题上,政治思想家们开始具有了现实的和历史的视野。思想家们开始扬弃静态的社会契约论模式,转而采用文明社会演化的历史视野来思考秩序的生成与规范。“基于商业活动所发展出的市民社会或文明社会论述,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商业社会不但造成了国家观念的变化,也造就各种不同的社会可能性想像,如文明阶段论、国家有机体论,以及民族作为国家形成的基础等,都成为新的理论课题。”(15页)在第二波现代性中,由“社会契约”呈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并未遭到抛弃,平等的、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仍为思索、理解社会秩序的基础。只不过,在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之间是一种静态的对立关系。但在第二波现代性中,这种对立关系演化为“人性论”与“文明社会史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然与历史的辩证)。
相比起施特劳斯与福柯对现代性系谱的勾勒(12-13页),萧高彦的划分有其独到处。萧高彦用“商业社会”来统摄第二波现代性,这无疑是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此而言,伊斯凡·洪特[Istvan Hont]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但他又大大推进了洪特的论述)。当然,这也是极具启发性的一点。正因为此,在其梳理的现代性系谱中,苏格兰启蒙哲人(尤其是亚当·弗格森)便拥有了极为突出的地位(正是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演化论中,由孟德斯鸠开启的第二波现代性才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状态)。我们完全可以说,萧高彦重新发现了弗格森。通过梳理弗格森对严复的影响,他进而重新发现了严复。
重新发现亚当·弗格森
关于第二波现代性的系谱,在讨论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时,萧高彦做了一番虽极为简略,但相对完整的勾勒(261页)。在此系谱中,孟德斯鸠是无可置疑的枢轴,对其理论的回应与辩论开出许多个面向。这些面向包括卢梭的革命政治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文明进步史观、贡斯当古今自由之分野,以及德国的历史哲学与有机体国家观。它们无不围绕着孟德斯鸠确立的视野与问题旋转。
弗格森毫无保留地吐露自己对孟德斯鸠的推崇与继承:“当我回想起孟德斯鸠庭长写下的内容时,我要不无伤感地说,我为何要探讨人类事务呢……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不仅能够发现我为了条理清晰从他那引用的原创性观点,还可能找到许多观察的源头。”(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66)当然,在孟德斯鸠学说的基础上,弗格森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萧高彦充分重视弗格森带来的创造性转化,强调其在思想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并将之与“严复时刻”密切关联起来。“洪堡特继承了弗格森的文明进步论……换言之,弗格森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共和自由主义之德行与权利观,通过洪堡特‘新希腊主义’所重构的美学式个人主义和浮士德精神,在穆勒的自由主义体系中,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政治哲学论述,其影响且及于近代中国之严复思想”(434页)。
在很大程度上,萧高彦超越了波考克的“财富与德性”框架(J. G. A. 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译林出版社,2013年,525-530页),致力于从文明社会视角解读弗格森,从而重新发现由他开创的“共和自由主义”传统。

亚当·弗格森
弗格森基于启蒙时代所积累的各民族历史及人类学志,再加上基于自然律及人性的理性分析,完成了一部叙述人类发展的整体历史,此即“文明社会史”。他将文明社会区分为四个阶段:原始民族、野蛮民族、政治国家(civil state),以及商业社会。萧高彦注意到,弗格森尝试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古典共和主义、孟德斯鸠的政府论,以及卢梭的不平等起源论等不同论述,采取了相当复杂的历史分期标准。“简言之,他以是否具有高度发展的艺术为准,区分出‘粗野’与‘开化’民族:其中前者以是否具有稳定的财产权为界,再区分为‘原始’以及‘野蛮’两个阶段;后者则区分为具有政治建制的阶段,以及社会分工高度发展后的商业社会”(307页)。
在弗格森笔下,文明社会四阶段之构想既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化历史框架,也是他对世界历史经验的归纳,为他思索欧洲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理论支点。例如,他关于政治建制史与商业社会的阐释就具有颇为现实性的一面。弗格森以罗马王政末期,贵族驱赶国王为例,表达出政治建制的新开端。在他看来,共和建制使罗马脱离了野蛮时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此以来,欧洲的政治建制史就经历了罗马共和、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中古封建制度,以及近代代议制政府四个阶段。当然,政治建制的演化并非源于立法家的伟大智慧,而是各方势力此消彼长,不断打破并重建平衡之结果。最终,欧洲近代君主通过保护人民,鼓励商业活动,形成了代议体制,成为商业社会新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建制(314页)。
这种代议制即为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混合,它正是孟德斯鸠盛赞的英国政制。只不过,在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中,它是以自由为目的、自成一格的理想政体。但弗格森将其置入历史进步的时序中,视之为西方现代性的制度结晶。因为商业的发展,欧洲各国立基于不同的境况,依循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君主、贵族与人民的平衡状态。与此同时,欧洲诸国间也维持着权力的均衡,并因此获得“幸福的政策体系”(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129)。
“作为英国学者,弗格森没有犯下孟德斯鸠的错误,用‘三权分立’来诠释英国宪政”(314页)。在弗格森笔下,英国政制之典范意义不在其“三权分立”,而在于各阶层间的对抗平衡,在于一种更现实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均势。“在适当混合的政府中,大众的利益在君主或贵族利益中找到了解毒剂,在他们当中建立起了真正的平衡,公共自由和公共秩序在此平衡中才能够持续”(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158)。在弗格森看来,唯有此等力量平衡才能塑造“法治政府”,才能制定良法,保障个人权利,实现“民族财富与权力的繁荣滋长”(315-316页)。
然而,各阶层之力量乃至利益平衡是对社会状态的外在描述,它源自社会演化,也可能因社会结构之变化而遭到破坏与瓦解。那么,自由政体如何才能对抗历史的流变不居,克服腐败,免于坠落?弗格森认为,政治自由的真实根源在于“心灵力量”,在于各阶层间的对抗平衡激发出来的公共精神与德性。倘若放任人民追逐财富、奢侈,乃至享乐,忽视对德性与公共利益之关注,民族将不可避免陷入怠惰,自由必将被专制捕获。“当商业社会中的公民只维持制定政策的角色,而将进行战争的任务交付给其他人,商业社会就会面对军政府篡夺政治权力的可能性”(319页)。在此危机中,人民因心灵腐化无视阶层对抗,贪图享乐,将保卫自身的武装拱手让人,最终遭受奴役。所以,人民只有超越个人利益,在“恻隐之心”与德性的驱使下,积极参与政治与军事行动,追求共善(不伤害、传布幸福、公共效用),才会产生捍卫法律与自由的力量。
弗格森对积极德性的强调凸显了共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弗格森的共和精神深植于商业社会这一文明阶段。对政治自由而言,商业既有积极的塑造作用,又会可能造成腐化与破坏。弗格森对此做了辩证的分析与批判,强调自由政体的德性基础。萧高彦因此主张,弗格森对共和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论综合,创造了共和自由主义,使之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开端(327-328页)。
严复与现代中国之命运
在萧高彦勾勒的第二波现代性脉络中,孟德斯鸠为枢纽,弗格森则为一副中心。孟德斯鸠的历史意识,及其关于商业社会理想政制的思考至此发展为一种更为复杂且成熟的理论形态,呈现为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学说。弗格森实现了对孟德斯鸠的批判性转化,并进一步影响了贡斯当、洪堡,乃至穆勒的政治理论。不仅如此,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学说在后世的传承与演变中,日益丧失其内在精致的平衡,丧失其普遍人性论基础,变得越发意识形态化。如果孟德斯鸠为第二波现代性之开端,那么弗格森就是其波峰,并可构成反思后世理论的参照系。
弗格森启发了十八、十九世纪德国与英国的政治学说,并因此进一步塑造了严复的政治论述。在萧高彦笔下,洪堡特代表了德国思想的“耶拿时刻”。他是一个路标式理论家,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影响深远。在第二波现代性之系谱中,洪堡特标志着:德国思想家受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影响,开始反思面对现代商业社会与分工的议题,并发展出独特论述。萧高彦重点分析了他的《论国家作用之界限》,并强调这部著作与弗格森之间的渊源。“全书的构架,受到弗格森《论文明社会史》的深刻影响,通过比较古代与现代的差异性,针砭现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并提出其关于现代个体性的理论分析,最后终结与国家权限之讨论”(429页)。

洪堡特
在《论国家作用之界限》中,洪堡特引用弗格森对吕库古斯的评述,认为其立法接近野蛮社会的习俗。在这段引文之后,下一段就出现了穆勒《论自由》扉页的题词:“根据前面的整个推论,一般而言,一切的一切,至关重要的是最多样化地培养教育人。”(429页,注释28)从洪堡特的这一段论述中,萧高彦发现了一条明晰的思想线索。这条线索通过洪堡特与穆勒,将弗格森与严复关联起来。
关于古典城邦与现代国家的特征,洪堡采用弗格森的方式,对之做了历史性的分析与对比,认为“古代国家追求德性,现代国家追求幸福”。与弗格森一致,这种古今对比也使之意识到潜藏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危机:倘若过度追求财富,人们将会忽视德性与人自身的发展。为了化解这一危机,他试图调和古今差异,在商业社会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制中植入古典教育因素。他因此强调,国家一方面应当注重人的完善和谐发展,在教育上强调“身体、理智与道德的能力”,另一方面则要打造自由政体,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涉。萧高彦在一条注释中向读者披露,洪堡特的政治教育思想对穆勒影响极深。穆勒既接受了洪堡特对国家教育功能的强调,也吸收了他对教育目标之论述,即全面培养人之“身体、理智与道德能力”。这一论述又向后影响了严复,使之发展出“民力、民智、民德”概念(430页,注释29)。
萧高彦意识到这一线索意义重大。他遂能以独到之学术眼光重点剖析穆勒之文明论,阐述其文明概念与政制构想之密切联系。他认为,穆勒虽然继承了弗格森的文明史框架,但弱化了其道德内涵,将文明标准等同于民族富强,从而使之意识形态化。亦即,穆勒的文明概念服务于其帝国构想。欧洲国家是富强的商业社会,处在文明进步的高级阶段。所以,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应当采用自由的代议制政府,并在议会中给予知识精英更高的权重,人民便能在公共辩论中受到教育,其个性能力亦能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对于野蛮落后的民族而言,它们缺乏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就需要欧洲国家派出才智超卓的总督或统治团体,采取“文明的专制”,承担对它们的文明责任。
亦因为这一线索,在解读严复的著述、翻译,乃至政治擘画时,他才能独辟蹊径,凸显严复对“新圣王之道”的演绎,及其对君主立宪的思想介入。这两者分别指向人民之德性(民力、民智、民德)与自由政体,此亦为弗格森重点关注的两大问题。

1878年严复巴黎留影,时年二十六岁。
在十九世纪西方的文明论视野中,中国已经陷入“停滞”困境,堕入某种腐败与贫弱状态。严复亦体察到,西方之文治武功皆胜于我。严复比较中西政教传统,推求其故,将西方文明优势之源头活水归纳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564页)。然而,自由与民主之前提却是社会成员的才德,即“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以及“德行仁义之强”。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在新的世变之下,传统由中国圣王之道开展出的经世之术已不足以促进民力、民智与民德。
萧高彦注意到,通过翻译赫胥黎之《天演论》,写作《辟韩》,严复演绎出应对世变的“新圣王之道”。赫胥黎的《天演论》挑战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为严复提供了一个抒发自我的空间,使之能够调和中西,在文明演化论的基础上植入圣王之道。赫胥黎在描述伦理世界的形成时,提出一个“园艺过程”的譬喻,即园丁能在天演流变的大自然中,创造出一个具体而微的精致花园。在诠释这一园艺譬喻时,严复从园夫治园之术中推衍出两大治理之术。严复强调园夫治园有两件要事:其一为“设所宜之环境,以遂物之生”,另一则为“去恶种,而存其善种”;对于社会而言,前者意味着“保民养民之事”,后者则为“善群进化之事”。这两项治理之术暗中指向了穆勒阐述的两大政府功能:“处理社群集体事务的安排”,及“作为民族教育机构的运作”(587页)。“善群进化之事”贵在“教民”,亦即取人民的“民德”与“良能”,扩而充之,成为“其群所公享之乐利”(576页)。借此,严复强调了圣人(乃至知识精英)为社会进步提供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圣人之治。

《天演论》
在沛然莫之能御的运会面前,新的圣王当“知其所由趋,逆睹其流极”,据此教育人民,培养增进“民力、民智、民德”,培育自治之民情基础。在政制维度,圣王之道的目标是要创立与民“自治”的立宪政体,因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并且,严复还在清廷预备立宪时刻,积极引介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讲授以历史与演化论为本的“政治科学”,著述《政治讲义》,介入现实政治,推动政体变革。亦即,严复注重积极的政治行动,而不满足于让其令其对文明演化之思考停留在思想层面。
结语
在萧高彦勾勒的政治现代性系谱中,严复也处在一个众流交汇的关键地位。不仅中西传统交汇于此,而且由孟德斯鸠、弗格森发源出来的众多政治理论分支也交汇于此,它们彼此激荡,启发着严复对中国文明命运的思考。“系谱学”既是历史写作,也是比较研究。通过对政治现代性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严复笔下的“运会”其实正是第二波现代性试图理解并驯服的“商业社会”。自十八世纪以来,商业社会在西方蓬勃兴起,不仅建构了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理论反思,孕育出“文明社会史”学说,令西方获得了理解、建构世界秩序的新视野。当此“新秩序与方式”随商船与军舰一起来到东方,它亦引发了传统儒家心灵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产生了中国化的文明社会理论。
萧高彦注意到,在严复时刻,“所有急切被翻译的西方经典,都是本书所称第二波现代性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英国与德国的代表性理论”。所以,发端自严复的中国政治现代性进程正是第二波现代性尚未完结的延续。因此,对商业社会与文明的反思就变得尤为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萧高彦的思想史叙述暗含了对十九世纪文明论的批判。在他呈现的思想史系谱中,第二波现代性经历了某种衰退:文明社会理论到十九世纪变得意识形态化,丧失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以至于不能发现中国具有走出“停滞”状态的内生动力。由此观之,严复的努力首先意味着对十九世纪文明论的批判。严复没有一味接受盛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学说,而是通过两种方式对之加以反思:他一面追溯文明社会理论之源头,系统翻译、解读苏格兰启蒙哲学与孟德斯鸠的经典著作;一面立基于中国自身的文治传统,对文明演化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强调严复与弗格森之间的思想渊源时,萧高彦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穆勒等人的文明论。
苏格兰启蒙哲人将“文明”视为一个历史进程,足以解释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乃至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所经历的变革。而且,由于不同文明阶段共享同一人性论与道德哲学基础,所以,弗格森的文明社会理论又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批判力量。穆勒的文明论已经变得意识形态化,既不能贯通地理解民族自身的古今之变,也不试图对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做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只用于证成既已形成、尚在扩张的帝国秩序。时至今日,文明观念进一步狭窄化、内向化与封闭化,只能反映出一种冲突的世界政治状态。抚今追昔,时人焉能不叹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