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阿富汗女性经历的,远不止战争、童婚和虐待(上)
【编者按】
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总统加尼已离开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塔利班已进入首都喀布尔。喀布尔街头目前已经开始用油漆刷掉女性露出面部的广告。
妇女在阿富汗的处境一直极为艰难,“罩袍”是她们每日固有的穿着。《罩袍之刺》里,笔者原老未数次往返阿富汗,采访六位阿富汗女性。还真实的阿富汗女性处境。“人们对于阿富汗的印象,似乎只有战争、童婚以及对女性的虐待。是的,以上皆为事实,然而事实不止于此。”
下文经授权摘编自原老未作品《罩袍之刺》第三章(有删节)

《罩袍之刺》封面
不婚主义者(上)
迪巴从一开始就知道沙伊德不想结婚,可每次他边吻着她边深情地低语“我爱你”时,迪巴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他的想法就更加地坚定。他爱她,很爱她,只爱她,他只是暂时不想结婚。
喀布尔。这里是阿富汗的首都,一座有着35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自豪的喀布里(喀布尔人)在穿着打扮上与其他地区的人极不相同,是整个国家最“时髦”的,当然,也有格外保守的人,说这儿是全阿富汗最“没有羞耻感”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女人出现在喀布尔街头,系着希贾卜(穆斯林女性头巾),年轻的女孩还会向邻国伊朗的摩登女郎一样,把发髻梳得高高的,让前额的头发从围巾中散落些出来。她们通常穿着及膝风衣,高跟鞋也不再是稀罕物,夏瑞诺(新城)区的Park Mall(公园购物中心)里,商铺的货架上陈列着各种高度的高跟鞋,不过齐膝靴子在这儿依然是新鲜货,要是有谁穿上了街,准会招来同性羡慕的目光以及异性带有各种意味的注意。与几年前相比,身穿蓝色茶达里的女人少了很多,如今喀布尔街头仍旧穿着茶达里的,大部分不是最保守的普什图族,就是乞丐,若想区别这两类人,看看她们茶达里的新旧整洁程度就可以了。
茶达里,尤其是蓝色的茶达里,似乎是阿富汗女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标签”,但足够多的历史资料表明,这种只在眼部缝有细密网格的长袍,最早却出现于南亚次大陆上。英国人在19世纪初期把茶达里从英属印度引入阿富汗,告诉作为统治阶级的普什图人:“用茶达里遮盖你的妃子,她们的美貌才不会为歹人所见。”
茶达里在阿富汗上流社会中迅速流行起来,女眷们身穿丝绸茶达里,上面有坎大哈妇人巧手绣出的整片“卡玛克”,她们养尊处优,散发着香味儿的茶达里纤尘不染,哪像现在,街上每一条茶达里的下摆全都是泥灰。
恐怕也没太多人知道,1919年,身穿茶达里的阿富汗女人,竟比大洋彼岸的美国女人更早一年获得了投票的权利。一年后,索拉亚王后在丈夫阿曼诺拉的授意下掀起茶达里,这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阿富汗君主试图对茶达里说“不”。这种允许女人不把脸遮住的举动,惹恼了阿富汗真正的当权派——那些保守的部落首领们,经过几次密谋,他们齐心合力把国王赶下了台。
转眼到了1959年,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和他的一众官员,带着他们没有穿着茶达里的女眷,一同出席了国庆典礼,当这些上流社会的女人穿着西方服饰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时,喀布尔街头刮过一阵时髦的风。两年后达乌德再次呼吁,全国的女人都应该脱下茶达里,“摘或不摘,做你们想做的事”,他的话在报纸上被放得老大。
那时的喀布尔、马扎沙伊夫等北方大城市的街头,有很多穿着巴黎最新款时装的年轻女人,而在坎大哈省、赫尔曼德省、加兹尼省以及全国大部分更为保守的地区,女人们依然用茶达里、茶杜尔(一种稍经剪裁缝制的半圆形布料)或者其他衣物完全遮盖住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因为她们的玛代尔,玛代尔的玛代尔就是这么做的,“顺从是女人最好的品性”。
迪巴不是那样的女人,她甚至一点也不像阿富汗女人。她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颧骨高耸,目光锐利而冷漠,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又大又快,似乎对自己的方向感十分自信,有时她还会戴上样式夸张的名牌墨镜,即便招来一些人异样的目光也毫不在乎。
2016年,我第二次来到阿富汗。一别三年,从飞机上俯视喀布尔,这座山谷里的城市看上去平静安详,几栋十几层的居民楼在山脚拔地而起,是上次我没看到过的和平景象,仿佛那些新闻报道中的爆炸和枪击只是一个梦,从来都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
迪巴站在机场的候机楼门口迎我,与上次相比,她看上去并无太大变化,仍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气质。我问她,沙伊德怎么没有一同来?她扶了下不带镜片的黑框眼镜,淡淡地说道:“他在忙。”
然后转移了话题:“你要待一个月,怎么就带了这么个小包?”
我们的出租车经过阿斯玛伊路,路面重铺了沥青,十分平整,上次来时碰到美军装甲车的位置附近,还新盖了一座亲子游乐场。再往南开,路两边有很多新起的高层公寓楼,底商有不少女子美容沙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迪巴从市中心搬到了喀布尔郊区一栋苏联占领时期修建的三层老式公寓,一位来自阿富汗南部的保安把守着入口。在出租车上她就对我百般叮嘱:“千万不要向保安问好,也不要看着他微笑。他从南部来,非常非常保守。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让他看出你是外国人。你知道如果他将此事告诉警察,我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美国政府在2014年5月宣布在两年内全面撤军,西方的一些投资者觉得在阿富汗的安全失去了保障,也纷纷跟着离开,部分亲西方的中产阶级紧随其后,想方设法再次离开故乡。于是喀布尔的房租和二手车价格一路狂跌,这套曾报价500美元的大三居室,现在的租金只要原来的一半。
迪巴的家闻上去很香,门厅正中的方桌上有一只放檀香的漆木盒以及几个装满了干果的木盘。方桌周围的地砖上放了四块深红色的长方形坐垫,我把背包放在上面,跟着迪巴进了起居室。房间被精心布置过,枫木色地板上叠放着两张带花纹的机织地毯,几块同色系的大方坐垫看似无意地被人随手扔在了上面,空中竟还有个铺了一整张银灰狐狸皮的吊床,毛茸茸的尾巴垂在外头,这调性一看就是迪巴的手笔。
起居室另一侧是一张L形旧沙发,迪巴将餐馆里上菜用的圆托盘做了茶几,一大一小,还分别刷了颜色。大的撒满了干玫瑰花,小的上面放着一小碗漂着各色豆皮的杂粮汤,我一下子想起和迪巴坐在厨房,一起剥豆皮的日子。“这么一小碗,怎么够你们两个人喝呢?”
“这只是做给我自己喝的。”迪巴将两杯刚泡好的藏红花茶放在了干花上,红红黄黄的很好看。
我在吊床下的大方垫子上盘腿坐下,抬眼看向沙发上的迪巴:“你在邮件里说的新生活,指的就是搬进了这间新公寓吗?”
“我被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新媒体专业录取了,等下个月考完雅思,再看看能不能申请奖学金。如果可以批下来,我就真的可以开始新生活了。”
“迪巴Jaan,真替你高兴,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谢谢Jaan,但是我也不想过于乐观,如果拿不到全额奖学金,
我根本没办法负担澳大利亚的学费和日常开销。”
“我理解。你和沙伊德还好吗?”一路上,她都对此避而不谈,我不禁有点担忧。
“......这很复杂。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关系,严格来说已经不算情侣了。”
“但在邮件中,你说你们依然生活在一起。难道,他已经搬走了?”迪巴摇头。
“这里对他而言,就像个旅馆,他付了房租,可以自由来去。我几乎见不到他。”她面无表情,好像说的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三年了,Jaan,很多事都变了。我想结婚,他不想。他依然不相信婚姻,他说他这辈子也不会结婚。”迪巴扶了扶眼镜,又说:“但他也不愿意分手。”
“那你为什么还和他住在一起?你把我搞糊涂了。”
“在一起的日子长了,不知不觉已经对他有了依赖。你也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单身女人,要想在这儿独自生活有多艰难。”她顿了顿,“就算他只拿这里当旅馆,也好过我真的一个人生活。”
我记忆中的沙伊德永远是聚会上众人目光的焦点。他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有时还有点无礼,但就是没法让人真的生他的气;他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可以逗笑周围所有人,连永远看上去淡淡的迪巴,也经常被他搞得笑个不停。
迪巴从一开始就知道沙伊德不想结婚,可每次他边吻她边深情地低语“我爱你”时,迪巴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他的想法就更加地坚定。他爱她,很爱她,只爱她,他只是暂时不想结婚。
一年......两年......迪巴逐渐被时间磨得失去了耐心,她试图和他争吵,可面对永远一脸笑模样的沙伊德,她的愤怒就如石头打入了一团棉花,没有任何回应。她灰了心,开始备战雅思,准备在后悔前,一股作气考去澳大利亚,顺其自然地离开阿富汗,离开沙伊德,离开这段她认为已经“苟延残喘”的爱情。
沙伊德过了好一段时间才知道迪巴的计划。还是迪巴故意把自己的雅思课本放在客厅的方桌上,连着放了几晚,他才注意到的。
“Jaan,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雅思的?”“一个月前。”她看着电脑上的稿子,平静地说。“怎么没听你说过想出国读书的事?”
迪巴飞快地打着字,眼睛根本没有离开屏幕:“怎么说?我每天醒来,只能看见你扔在地上的脏衣服,你那些朋友听见你打喷嚏的次数,可能都比我们说话的次数还要多。上一次我们在家一起吃晚饭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沙伊德笑嘻嘻地从身后抱住她,边吻着她的头发边道歉:“你是我的BOSS(老板),你说什么都对。我错了还不行?今晚我必须出去,明天我一定回来陪你吃晚饭。”
“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迪巴一动不动,只是打字的速度慢了下来。
“真的。你生气时特别丑。”沙伊德抱着迪巴亲个不停,“那这样吧,今晚你和我一起去,反正我那些朋友你都认识。”
“你知道有些人我并不喜欢。”
“所以我从来也没勉强过你啊,是你一直说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的。”沙伊德松开迪巴,从桌上的干果盘里抓了把核桃仁扔进嘴,“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你是那个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可以呆在外面的性别,我不是。你说你和其他阿富汗男人不一样,可你的行为又与他们有什么区别?”迪巴的声音低了下来,“你只是习惯了不管什么时候回家,我都在吧。你从来没有替我考虑过,更不在乎我到底想要什么。”
沙伊德把头靠在迪巴的背上,“Jaan,离开并不等于出路。”“我心意已定。”“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混蛋。可我舍不得你怎么办?”沙伊德埋着头。“我们在一起快4年了,现在我30岁。你要我等到多少岁呢?50岁?60岁?到了那时我又如何重新来过?”沙伊德没有说话。
迪巴像是对沙伊德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以前和你在一起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可现在,我的日子好长啊,似乎比所有人的都要长。”
“别再说了,没有意义。我累了。和你在一起看不到希望,如今的阿富汗也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就这样过一辈子。如果明天我被炸弹炸死,我一定死得很不甘心,因为在真正的死之前,我竟从来没有真正地活过。”
那次争吵后不久,迪巴飞去印度参加了三个月的雅思辅导班,同班的一位日本婶婶热情地与迪巴分享了自己永葆青春的秘诀——只吃纯天然食品。不吃白糖,天然水果和蜂蜜中有充足的糖分;不吃袋盐,印度、巴基斯坦都出产上好的岩盐;而像薯片、冰淇淋、碳酸饮料等所有经过多重加工的食物通通不吃。最重要的是,早餐一定要喝一杯加了糙米壳粉的牛奶。
日本婶婶的一番话,让有机生活成了迪巴新的信仰。从印度回来后,她扔掉家中所有的加工食品,并决心对超市中的膨化食品和碳酸饮料避而远之。迪巴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为每天早晨7点起床,晚上11点入睡。一日两餐,每周吃肉不会超过两次。
迪巴起床后吃第一餐,用水果、坚果和葡萄干摆盘,再喝一杯加了糙米壳粉的牛奶;下午吃第二餐,蔬菜种类由前一天的集市里,每个小贩的独轮车上有什么而决定。她还特地买了十二只鸡,放在朋友家的院子养着,每周让那户人家的小女儿送四五枚鸡蛋过来,“婶婶说了,肉和鸡蛋吃多了都不好,尤其鸡蛋,一个礼拜不能多过三枚。”她认真地向我解释,随即又自嘲地笑了笑:“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活得比阿富汗更有机了。”
迪巴相信用带气泡的天然蜂蜜敷脸可以缩小毛孔,也相信用泡了青孜然的橄榄油去涂抹四肢,汗毛可以变得细软,最后自然脱落。而对于年轻女性必不可少的擦脸油,迪巴倒没有决然地将有机理念坚持到底,她说自己只用××牌,这个一瓶在北京专柜售价400元左右的面霜,是迪巴心中世界上最顶级的品牌,即使与有机沾不上边,也可以无条件信赖。
三年前那个凌晨一两点才睡觉,中午12点前绝对看不见人影的迪巴,那个每隔几天都要花两个小时为沙伊德煮豆皮杂粮汤的迪巴,已经先一步从喀布尔离开了,去了哪里,迪巴自己也不知道。
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对这里简直失望透顶。”
阿富汗人自嘲贫穷使这里的农民没有钱买生产调节剂、抗生素、含有转基因技术的化学制剂,再加上战后工业水平几乎为零,所以当地农产品都是纯天然、低污染的。
“当性骚扰发生时,大多数女人不敢声张,只能忍气吞声地默默离开,否则她就是不自爱,就可以被大街上任意一个男人指责,甚至某些女人都会跳出来责备她,说她是个行为不检点的人。”

深色门帘遮住的美容院里面别有洞天
4月的清晨,城市上空飘着一层烟雾,像一只巨大的茶色玻璃锅盖压在喀布尔市区上空。我和迪巴向街口的美容院走去,一个穿着时髦的哈扎拉女孩从我对面走来,她看着我羞涩一笑,颔首低眉地走了过去。
我随口问迪巴:“我和哈扎拉女孩长得差不多,穿得也差不多,阿富汗人怎么就能认出我是个外国人呢?”
迪巴反问我:“如果刚才那个哈扎拉女孩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你觉得中国人能认出她是外国人吗?”
我想着刚才那个女孩脚上的黑色麂皮低跟凉鞋和脚踝处露出的肉色丝袜,还有风衣下的棕色窄腿裤上的银色裤缝线,摇了摇头:“我想应该不会。除了戴头巾,她的穿着打扮与中国很多小城里的女孩并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在中国不会,但在这里会。我来告诉你如何分辨阿富汗女孩。那些看上去毫无自信,永远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贴着墙根走路的,就是阿富汗女孩,因为她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开始学习如何不引人注意,还有就是顺从。”迪巴一脸不屑地说。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美容院门口,她摘掉墨镜,拉开门示意我先进去。
2002年初,喀布尔的街头逐渐出现了美容院。这儿是最好辨认的“神秘”场所,临街的深色反光玻璃,门板上贴满了伊朗女人浓妆艳抹的巨幅海报。美容院的内部装修与中国刚改革开放时小县城的美容美发厅类似,不过这里只为女性服务,阿富汗女人称之为“只对女人开放的天堂”。顾客摘下头巾,露出各色秀发,美容师干脆穿上了低胸小背心,一头染成浅金色的头发散在肩上,让人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惚。
对于月收入不超过600元人民币的阿富汗普通家庭,美容院是一个女人在参加婚礼前才能进入的世界,一个可以让人彻底放松的、没有异性的世界。阿富汗人相信星期五是个幸运的日子,很多人都偏爱在这天举行婚礼。这也是美容院最繁忙的时候,女人们会结伴前来打扮,在这里她们可以摘下头巾,让美容师为她们洁面、绞脸。新娘妆会把原本又粗又黑的眉毛画得高挑而夸张,再根据婚礼礼服颜色(通常是绿色),在眼皮抹上各种颜色的眼影。很多新娘还喜欢在脸上贴水钻,在高耸的发髻上洒亮晶晶的银色粉末也很流行。
阿富汗政府机关每星期工作五天半,星期四下午至星期五全天休息;商铺的营业时间通常为星期六至星期四,周五全天休息。美容院通常没有休息日,但星期四、星期五两天较为繁忙。
绞脸,也称开面,是中国古代女性熟悉的一种脸部脱毛法。在封建王朝时期,某些地区的女人一生只开一次面,开面后即为人妇,即使改嫁也不会再做。这种风俗可追溯到六千年前的中东及南亚次大陆。在阿富汗,绞脸曾是一种独特的成年礼风俗。不过现在喀布尔街头大大小小的女子美容院都提供绞脸服务,100—200阿富汗尼一次,与当地人的工资相比,价格并不便宜。
迪巴每个月都要去街口的美容院做一次绞脸,她通常会避开繁忙的时段,选择在星期六至星期三1的某一天前往。她说原本脸上的汗毛不重,并不需要常来。可她的一个“前”好友让她用漂白剂来灼烧汗毛,几次之后汗毛反而长得越发粗壮凶猛,她这才成了沙龙的常客。
坐在美容院的椅子上,迪巴闭着眼睛,想起有次沙伊德不知道从哪儿搞了一件茶达里,套在头上一本正经地要跟着她去“做美容”,“我舍不得和你分开,就穿着这个和你一起进去,你拉着我的手,我
保证全程闭眼什么都不看。”沙伊德歪着嘴角,看着就像个孩子。
“咝——”美容师没控制好棉线的力道,迪巴轻声吸了口气,心里默默地想:“如果早知道橄榄油泡青孜然可以软化汗毛,我根本就不会坐在这里。”
从美容院出来后,我们朝着菜市场的方向走去。她说几个月前在这个菜市场,有个小贩见她独自一人,穿着打扮又与其他阿富汗女人不同,瞬间看她的眼神变得下流,迪巴直视着他,严厉地说:“挪开你肮脏的眼睛!”
那人听完轻蔑地撇了撇嘴,眼神并没有因为迪巴的话有任何改变。迪巴原本就是不愿和陌生人多费口舌的性子,她随手抄起一个洋葱,朝着那双脏兮兮的眼睛扔了过去。这种反应与其他阿富汗女人受到性骚扰时完全不同,把小贩一下砸蒙了。他愣了好一阵,才开始嚷嚷,威胁着要教教迪巴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个戴图尔班头巾的老人,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胡须修得比大多数围观的男人整齐清爽。老人听迪巴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先是对那摊主说了句:“安拉至大。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你这样对待自己的姐妹是不对的。”
然后,他又微微侧了侧身,一脸严肃地以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吻对迪巴说:“这位姐妹,你的行为也是不对的。”
迪巴眉毛一挑:“那么照叔叔您的意思,我怎样做才是对的呢?”
老人语重心长地教导:“你是个女人,在公共场合做出这样的事对你的声誉很不好。当有男人这么对你的时候,你应该保持安静,转身离开,这才是女人最好的回应。”
迪巴冷哼一声,知道多说无益,就扭头走开了。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现状。在这儿,事事隐忍克制、委曲求全的才是好女人,才会让全家觉得体面。当性骚扰发生时,大多数女人不敢声张,只能忍气吞声默默离开,否则她就是不自爱,就可以被大街上任何一个男人指责,甚至某些女人都会跳出来责备她,说她是个行为不检点的人。”
“就是因为大多数阿富汗女人都活得那么小心翼翼,外国人才认为我们的国家只有小心翼翼的女人。”她推了推眼镜接着说,“我上次去印度时,在德里机场排队入关,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西方女人,她第一次到东方来,还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但说真的,她对这里一无所知。当她知道我是一个阿富汗人后,对着我的吊带衫和牛仔裤大呼小叫,似乎在她心中,阿富汗女人只能穿着茶达里,像个哑巴一样活着。不光如此,她还认为阿富汗人都住在山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或者骆驼,她觉得我连电视是什么都不知道,还用两只手比画了一个方块给我。”
“那你是怎么回应的?”“我说,遥控器是什么样子的,你也给我比画一下吧。”

寻找阿富汗少女剧照
裁缝、布料和新裙子
新政府上台后,很多裁缝店又重新开张,可生意大不如前,大多数女人已经不习惯接触直系亲属之外的任何男性,更别提那个男人还要拿着卷尺来量自己的身体了,真是想想都觉得可怕。
在申请学校时,迪巴把曾经发表的深度报道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寄给了招生办,对方反馈很好,她乐观地推断自己会被全奖录取。虽然离开学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但迪巴已着手准备行李,她计划做上几条极具阿富汗特色的“莎西达”长裙,在迎新会上穿,让外国人都知道,这才是真正起源于阿富汗本土的传统服饰。
“莎西达”套装由长度在膝盖与小腿肚之间的宽松连衣裙和白色宽松长裤组成,连衣裙用不同布料拼接,刺绣中还缝有亮片和珠子。“莎西达”之于阿富汗人,就像旗袍之于中国人一样,至今依然是阿
富汗游牧民族库奇人的日常着装,改良版的“莎西达”更是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迪巴去了“鸡场街”,这条街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是外国人离开阿富汗前都会来“打卡”的地方。街两旁的小店里有各式各样的纪念品,比如帕库羊毛帽子,用巴达赫尚青金石做成的工艺品,最近还流行起了政府为取代鸦片而大力推广农民种植的藏红花。迪巴熟门熟路地走进了一家店铺,老板拿出了几“莎西达”常见的样式是在胸前、裙摆还有小臂处缝上刺绣。十块从普什图部落中收上来的刺绣让她挑选,迪巴摸摸这个看看那个,有点儿拿不定主意,老板眼睛上下一扫,心里已经对这位顾客的经济实力有了更具体的判断,他又殷勤地拿出了十几块花纹更复杂、针脚也更密实的绣块,当然价格也比之前那一批贵一倍。迪巴随口问了句:“有没有‘卡玛克’?”老板听罢眼睛一亮,“卡玛克”刺绣的价格是这种普通货的数倍。
“今天没有带过来。”老板遗憾地摇了摇头,咂嘴道,“明天,明天你再来,我有五六块让你挑,都是上好的坎大哈‘卡玛克’刺绣。”
一番讨价还价后,迪巴带着4个绣块,和早先买好的布料奔往下一站——裁缝店。
步行去裁缝店的路上,迪巴经过了那个刚建成的游乐场。她听沙伊德提过,这座游乐场与赫拉特、马扎沙伊夫的都不同,竟然允许男人在没有家人同行的情况下入内。
“女人在喀布尔为数不多的乐土又少了一块儿。”她看着围墙后露出的摩天轮,一脸悲哀地想,“喀布尔早已不是原来的喀布尔了,真正的喀布里都是受过教育、彬彬有礼的,他们的眼神温和、睿智、诚恳、善良,绝不像现在大街上的这些人,只会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来骚扰女人。真正的喀布里已经逃走了,他们逃向欧洲各国,逃向美国,逃向伊朗,逃向世界各地。而这些无所事事、在大街上游荡的自称的‘喀布里’,大部分都是从偏远的村庄到这里浑水摸鱼的人,他们也许连字都不会写。”
她又想起沙伊德曾说过的话:“如果没有战争,很多人根本不会离开家乡,来到喀布尔,成为被你厌恶甚至自我厌恶的人。”
迪巴要去的裁缝店在一条脏兮兮的河沟旁,河水灰黑,上面漂满了垃圾。在内战前,这条河无比清亮,河中有时还有小鱼跳出,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中闪耀着七彩光芒,那时人们都叫它“喀布尔河”或者“我们的河”,不过现在的喀布里已经合时宜地改了口——“那臭沟”。
塔利班统治时期,当局明令禁止男性裁缝为女人量体裁衣,大批裁缝为了谋生偷偷违反禁令,被关进监狱施以鞭刑。新政府上台后,很多裁缝店又重新开张,可生意大不如前,大多数女人已经不习惯接触直系亲属之外的任何男性,更别提那个男人还要拿着卷尺来量自己的身体了,真是想想都觉得可怕。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有些偏远的省份,街头依然鲜少见到女人。喀布尔的情况比那些地方要好很多,这里不少女人在塔利班政权下台的第二天,就脱下茶达里,出现在饭馆、学校和喀布尔的大街小巷了。
裁缝店外的柴油发电机持续发出嗡嗡的噪声,与不时响起的汽车喇叭声交相呼应,吵得迪巴心情烦躁。她走进店内,这里有两台电动缝纫机,三个男人,一面墙上还贴了一张西方时装杂志的内页,上面是一个皮肤灰白的金发女人,抹胸长裙外套着长袖外衣,认真地冲着摄影师的镜头傻乐。
另一面墙上粘了排挂钩,挂着几件长袖风衣,中间还夹了件无袖碎花连衣裙,裁缝接过迪巴带来的绣块仔细端详,还就手工的精细程度和她交流了一番。迪巴很想让澳大利亚的同学看看,不是每个阿富汗女人都想把自己从头到脚包得密不透风,起码她迪巴就不是。
裁缝问清楚迪巴想要的款式后,拿着卷尺先从她的肩宽量起,从左肩松垮地量到右肩,以免接触到迪巴的长袖衣。然后是袖长,这个比较简单,从肩膀量到小臂。最后量衣长,由于迪巴想把刺绣的布块缝在胸前,裁缝只能轻轻地把卷尺的一端贴在她的围巾上面,另一只手再小心翼翼地把尺子往下拉,以确保卷尺不会压迫到她的胸脯,“Bale,103厘米。”裁缝把量得的数字一一记在本子上,迪巴又嘱咐了几句,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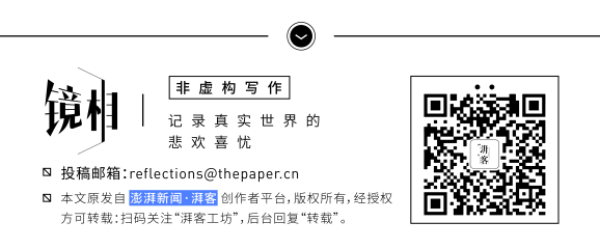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