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幅元-元图像》:福柯对委拉斯凯兹《宫娥》的阐述

© W. J. T. Mitchell
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是视觉文化研究领域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图像理论》则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更是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领域的必读书目。
今日推送米切尔的《一幅元-元图像》一文。文章从解读委拉斯凯兹的绘画《宫娥》开始:与传统作品不同,这幅画具有自我指称的功能,它添加了作品与观者之间的互动,努力地营造这个巨大而真实的空间。这种空间一方面使场景给人以“真实存在”的感觉,另一方面使观者感到自己也被包含于其中,它通过质疑观者的身份,用再现的自我认识来激发观者的自我认识。在《词与物》一书中,福柯将这部艺术史上的杰作确认为自反性的作品,自反性指向的是与其同类型的绘画,以及作者委拉斯凯兹所体现、控制的那整套绘画制度和话语。此画让我们重新思考“画家”、“人物”、“模特”、“观者”以及“形象”等概念/词。福柯借此让我们回到“模糊的、不知名的语言”,体会语言与绘画之间、词与物之间一种无限的关系。

书名:图像理论
著者:[美] W. J. T. 米切尔
译者:兰丽英
出版社: 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拜德雅
开本:16
页数:464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英美视觉理论扛鼎之作
读图时代的理论宣言
扫码直接购买
一幅元-元图像
文 | W. J. T. 米切尔
译 | 兰丽英
这样,人类就能够将世界纳入话语的主权之中,这种话语有力量去再现其表象。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
最全面地总结了元图像这一类型的所有特征的是委拉斯凯兹(Velázquez)的《宫娥》(Las Meninas)(图 11)。从形式上来看,《宫娥》在斯坦伯格《新世界》的严格自我指称和阿兰漫画类型的自我指称之间模棱两可。它再现了委拉斯凯兹作画的场面,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画的究竟是否就是这幅画,因为他只向我们展示了画的背面。《宫娥》的形式结构是图像自我指称的一座百科全书式的迷宫,再现了观者、画家和再现客体或模特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种复杂的交换和替代循环。就像《新世界》和阿兰的漫画一样,它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历史形象:福柯称其为“对古典再现的再现”,这个综合性的形象不仅关乎绘画风格,而且关乎知识型,关乎一个完整的知识 / 权力关系系统。我们可以稍作修改,说它是对古典再现的古典再现,来将其与我们在阿兰和斯坦伯格那里发现的那种启示录式的、历史性的自我指称进行对比:阿兰的《埃及写生课》呈现的是古典再现框架内的古代再现;斯坦伯格则展示的是我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新世界”框架内的现代主义再现(也就是“抽象”)。

鸭兔图,心理学家J.贾斯特罗在他的《心理学中的事实与虚构》中画出的一个模糊的图形。
然而,《宫娥》的地位可能与我们之前所考察的那些元图像完全不同,我也怀疑如果要把它和鸭兔图归为同一类型会遇到某些阻力,更别说归为同样的尝试(essay)了。两幅画之间要多不同就有多不同:《宫娥》是西方绘画的经典杰作,是大量艺术史文献的主题;鸭兔图则是幽默杂志上一幅微不足道的无名漫画,后来才成了心理学文献中的一个重要例证。《宫娥》是反映绘画、画家、模特和观者之间关系的一座无限迷人的迷宫,鸭兔图则被用来在多重稳定或含混的形象之间建立一种类零的平衡:人们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矛盾的、讽喻的或者(本身是)自反的。如果说《宫娥》以其最复杂、最清晰、最高贵的地位例证了元图像,那么鸭兔图就是元图像中最简单、最不起眼的成员,它位于人类感知和动物感知似乎相交的地方,是通俗文化进入心理学和哲学话语最基础位置的地方。如果维特根斯坦没有讨论过鸭兔图,那它几乎就不会被人记得,也不会被认定为元图像。此外,如果福柯没有讨论过《宫娥》,它仍将是一幅杰作,但也不会是元图像。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也暗示了这一点,她问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关于这幅作品最主要的研究,最严肃、影响也最持久的文章是由米歇尔·福柯完成的呢?”阿尔珀斯给出的回答是:“学科本身的阐释程序……使得像《宫娥》这样的图画在艺术史的规定下几乎是无法理解的。”我想用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述,关于《宫娥》的艺术史写作问题就像关于鸭兔图的心理学文献问题:它使图像太易于理解。在专业话语中,元图像有确定的地位和意义,和维特根斯坦一样,福柯把元图像从专业话语中解放出来,转换成另外一种言说方式。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言说方式”本身逐渐固化为一种学科建构(也就是一套陈旧或者严格的超图像),人们有时候会忘记福柯和维特根斯坦给图像带来的奇特语言游戏是为了使它们更难以被讨论,而非更容易。

图 11 委拉斯凯兹,《宫娥》,现存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图片:Alinari/Art Resource, NY
正因如此,称这种言说方式为“哲学”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福柯和维特根斯坦与其各自哲学传统之间非常成问题的关系,以及他们为元图像带来的奇特的语言等问题。这种语言的主要特征是:(1)拒绝解释和结论,偏好表面描述;(2)用极为宽泛的词汇来描述图像(福柯承认自己使用了“模糊不清、相当抽象的指称”);(3)在形象前有种奇怪的被动感,似乎要到达一种接受状态,使图像可以为自己说话。维特根斯坦希望我们不要去解释鸭兔图,而是要去聆听我们嘴巴说出的东西,思考那些说出的东西与我们的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那些有待发现的无意识不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身体语言的表达中、声音的语调中以及语法错误中。福柯认为“我们必须……装作不知道”《宫娥》中的人物是谁,我们必须放弃逸事和专有名词那种“恰当的”语言,这种“恰当的”语言告诉我们《宫娥》里的某个人物是谁,某个东西是什么,把我们局限于一种不能够充分表达“可见事实”的语言。“也许正是通过模糊的、不知名的语言媒介……这幅画才一点一点地释放出它的光芒。”(p.10)
这些“光芒”现在已经是为人们所熟悉的经典解读了,福柯将《宫娥》从一部艺术史上的杰作转变为一幅元图像,一幅关于绘画的图画,转变为“对古典再现的再现” (p.16)。我不想再复述那些由这一洞见生发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进一步解读了《宫娥》的自我指称的复杂性。只需要说的是,就像是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元图像一样,它通过质疑观者的身份,用再现的自我认识来激发观者的自我认识。在《宫娥》中,这种质疑主要与权力和再现相关——绘画和画家的权力,以及作为潜在观者的君主的权力。委拉斯凯兹把自己描画成一个宫廷仆人,只是王室的一个成员,但同时他又暗示了自己在控制再现上的主权,他的机智和谨慎使这种篡夺的暗示得以被接受。毕竟,君主也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接受教育,必须服从教师和顾问的训练。对眼睛的训练和对视觉再现的控制是主权技术的核心,包括《王子的镜子》这个视觉比喻中显示的那些自律的技巧等。《宫娥》中描绘的政治和再现权力无处不在,它们已经不需要展示自己,它们可以谨慎地,甚至无形地散布在这个宫廷内部的公众场面中,在宫廷场面的谨慎掌控者,即委拉斯凯兹自己的掌控下它们甚至出尽了风头。这一切如何联系于现代观者的自我认识?它又是如何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震动了“自主性主体” ?正是这些问题使得这幅画散发着无尽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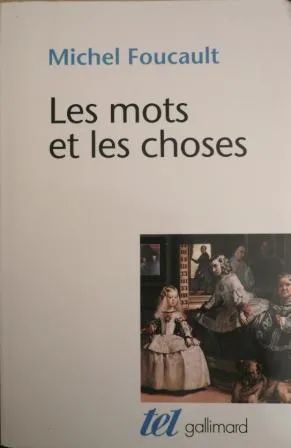
《词与物》 法文版
《宫娥》的自反性指向的是与其同类型的绘画,以及委拉斯凯兹所体现、控制的那整套绘画制度和话语。它并不是像斯坦伯格的《新世界》那样严格地自动指涉和自我构成的,除非我们想象画中背对着我们的那幅画正是《宫娥》。它也不像阿兰的漫画那样指涉另一种绘画。《宫娥》和《新世界》一样,意图向我们展示再现的全貌,但和斯坦伯格的绘画不同,它没有假装要忽视观者,而是征求甚至再现观者的位置。福柯追溯了《宫娥》中的这种总体化姿态,认为这是一种“螺旋式的贝壳”,“为我们呈现了再现的整个循环”(p.11)——画家、他的工具和材料、墙上已完成的画作、透着亮光的门框,最重要的是后墙上的镜子似乎模糊地反照出这个场景的观者,他们本身就是凝视着场景人物的隐含场面。
要进入这个循环,就像“打开了”鸭兔图的模糊面向一样。但是,《宫娥》(至少)包含了三个模糊面向,而非两面,它们存在于画面前部投射的虚构场地,此处的空间被(1)在画布上作画的画家;(2)给画家充当模特的人物(大概是在镜子里反照出来的那些人),画面中人物的凝视更突出了这一点;(3)观者,所占据。三个被投射的观者可以与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的三个画面焦点相匹配:(1)“真实的”(几何)焦点落在门口的男人之处(挂毯的保管人,名字也叫委拉斯凯兹);(2)镜子中“虚假的”焦点或者说“象征性”焦点(镜中的人可能是国王和王后,他们看着这一场景。或者如乔尔·斯奈德所说,镜中反照的形象正是委拉斯凯兹画布上所画的图像);(3)小公主,她是这幅画的传统“主体”,而作为皇室的孩子,她也是她父母 - 观者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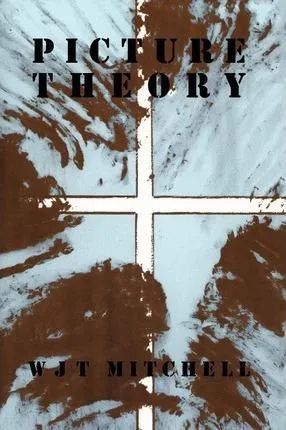
《图像理论》 英文版
《宫娥》中没有鸭兔图庸俗的错觉游戏,没有任何感官上的诡计。画中唯一最充分地位于凝视和视觉交换循环之外的正是离表面最近的那个形象,即前景中那只昏昏欲睡的狗。如果说《宫娥》的诸个“面向”在闪烁和转变,那么它们也是在一个不可见的、不可再现的空间中进行的,观者的主体性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建构起来的。正如福柯所说:“任何凝视都不是稳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穿过画布投向画面右方的凝视中时,主体和客体、观者和模特的角色无限反转了……因为我们只看到了 [ 画中的画布的 ] 反面,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在被看还是在观看?”(p.5)这幅画会破坏观者位置的稳定性,使我们幻想君主的主体性——我们将对空间、光线和设计的掌控归于画家,将对人民的掌控归于历史上的君主,将对我们自己的视觉 / 想象领域及所见和意义的掌控归于我们自己这个现代观者,这个私密的“心灵王国”的统治者。

毕加索《宫娥》之一 1957年
总而言之,我们考察的四幅理论图画组成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包含了对再现的再现中的力量的某些关键时刻,当然,它们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在画家、模特和观者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四幅图画:斯坦伯格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宛如造物主的画师,漫不经心地创造着宇宙,这个宇宙几乎是涂鸦的副产品,他抽象地创作,没有模特,也漠视那些被构图“吸进去”同时又被排斥出去的观者。委拉斯凯兹给我们描绘了一位聪明仆人形象的艺术家,给观者立起了一面诱人的镜子,这个观者同时既是君主、画家自己,也是任何过往的行人。阿兰给我们描绘的艺术家是卑躬屈膝的模仿者,模仿着同样缺乏独立性的模特;同时,观者被置于较高的视觉掌控者的地位,在一个(显然)超越历史、超越风格和惯例的立场上把整个图像生产场景看作一个历史时刻,看作一个古代的、异域的惯例。最后,鸭兔图面对的观者是实验对象,是由视觉错觉测试所构建的心理—生理状态。这幅画的“艺术家”不是画师,而是使用它的科学家,这幅画的模特也不是鸭子或兔子,而是一套关于形象化和视觉感知的假设。

毕加索《宫娥》之二 1957年
现在我想回到“模糊的、不知名的语言”这一问题,福柯借此使《宫娥》从艺术史阐释的对象转变成元图像。福柯指出这种讨论图像的方式是有风险的:
有可能使我们永远陷入这种模糊以及相当抽象的指称当中,常常容易产生误解和重复,如“画家”、“人物”、“模特”、“观者”以及“形象”等词。与其追求一种必然不足以表达可见事实的无限语言,倒不如说委拉斯凯兹创作了一幅画,在这幅画中,在他的工作室或者埃斯库里阿尔的房间里,在杜埃娜随行玛格丽塔公主下来看委拉斯凯兹描绘这两个人物时再现了他自己。
福柯指出,“专有名词”将“避免含混的指称”,从而终止解释的链条以及一连串的描述性短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这条通向确定性和封闭性的康庄大道呢?福柯的回答明确了词语和图像之间关系的性质:
语言和绘画之间是一种无限的关系。这并不是说词语是不完善的,也不是说当面对可见事物时它们是非常不足够的。二者都不能互相归结为对方的表达方式:我们言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徒劳的;我们所看到的从来都不寓于我们所说的话中。我们试图用图像、隐喻或明喻来展示我们所说的东西也是徒劳的;我们所说的话展现其光辉的空间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地方,而是那个由句法的序列因素所界定的空间。(p.9)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福柯并没有宣称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和视觉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所谓形而上学定律,我们“言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徒劳的”(反之亦然),但非空洞无意义更常见。例如,给某个形象设定专有名词,“就像给我们一个手指使我们可以指点它……使其偷偷从我们言说的空间溜到观看的空间;换句话说,把一个叠加在另一个之上,就像它们是完全对等似的”。这种对专有对应词和终极阐释的追求是艺术史的正当使命,甚至可能也是再现理论的正当使命。但这不是福柯的目标,就像他继续解释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使语言和视觉之间的关系保持开放,想要把这种不一致性当作言语的起点而非想要避开的障碍,以尽可能地接近二者,我们就必须抹去那些专有名词,保持这项使命的无限性”(pp. 9-10)。
重 磅 推 荐

书名:图像理论
著者:[美] W. J. T. 米切尔
译者:兰丽英
出版社: 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拜德雅
开本:16
页数:464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作者简介
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芝加哥大学盖罗德·多奈利杰出贡献讲座教授,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与艺术史系,兼任《批评研究》(Critical Inquiry)编辑。
译者简介
兰丽英,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毕业,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目录
插图目录
总序
致谢
引言
第1部分 图像理论
1 图像转向
2 元图像
3 超越比较:图像、文本与方法
第2部分 文本图像
4 可见语言:布莱克的书写艺术
5 艺格敷词与他者
6 叙事、记忆与奴隶制(致霍顿斯·斯皮勒思)
第3部分 图像文本
7 如图像的理论:抽象绘画与语言
8 语词、形象与物:罗伯特·莫里斯的墙上标签
9 摄影随笔:四个案例研究
第4部分 图像与权力
10 错觉:观看动物的观看
11 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纳尔逊·古德曼之后
第5部分 图像与公共领域
12 公共艺术的暴力:《为所应为》
13 从CNN报道到《刺杀肯尼迪》
结语:一些再现的图像
原标题:《一幅元-元图像:福柯对委拉斯凯兹《宫娥》的阐述》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