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四大文明古国说”错在哪里?《新世界史》又“新”在哪里?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吗? 对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顶多是拼凑过去的一鳞半爪,做“局部”的复原。我们掌握过往时代必定不如当时人,正好比一个外国人不会比本国人更了解其地一般,这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
我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个庐山中人方识此山的观点是错的。一个古埃及的村民不会知道同代有巴比伦;法国大革命在里昂进行期间,里昂人对巴黎革命的讯息会比今人少。事实上,当时人所知比我们还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们统摄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当作终极理想,即使拥抱这个理念,比起古人来,今人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统摄“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将焉附?这个“今”越往后移、离“古”越远,能花在将“古”这张意义锦缎的纹路编织得更精致的功夫就越多,因此,历史(过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在这里,亦必须纠正自然科学已进入范式阶段、史学仍局处每个时代各说各话的前范式阶段的误判。在全球化意识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这也是《新世界史》之所以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开其端,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之日趋干旱,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这个“复合带”是闪语系的原乡,它从两河古文明之曙光期即渗透美索不达米亚,从“复合带”喷发出来的最晚近一波即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有春耕秋收的农耕民方需要年历,放牧民观月之朔望即可。古代近东出现过世所罕见的太阳国埃及,但今日却是伊斯兰的新月旗插遍近东一代。
将古代近东建构为一个单位之余,本书用“卫星定位”将它定位为伊朗高原的西缘,其东缘则为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于是伊朗高原变成了范围更广的链扣;高原东西两侧是古代近东式的旱作农业,简称之为“麦与羊的文化”,它与印度河流域的关系正如环两河山侧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但古印度文明后来似乎又被多盖上了一层。如今雅利安入侵印度说已动摇,那么一个更稳妥的古印度文明二次奠基说就是长江流域的“米与猪的文化”的入侵;如此看来,印度次大陆成了远古文明的中分线,也是会师之地。
此处显示:不做跨地域的链接,只就地域论地域,那么,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即使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远古的华北不能脱离欧亚大草原的关系,华南的水稻革命可以是中国文明起源论之一环,也可以是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源头。南岛语系则是最后填满地球的族群,凭的是殖民大洋洲——一部比哥伦布更伟大的史诗。中国文明起源论不该变成画地为牢。

从地貌观之,西半球是东半球的对立命题(antithesis)。后者的文化传播乃横向传播,西半球的传播是垂直型的,需跨越不同气温带,导致文化的传播受到阻滞。这个东西两半球的对立命题后来也被作者用在非洲史上,指出:非洲的北半部是“东半球形态”而南半部是“西半球形态”,但非洲的问题是:北半部地貌虽具“东半球形态”之利,却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至于美洲,整体相对欧亚大陆来说是“西半球形态”,但在自身范围,北美洲却是内部的“东半球形态”而南美洲则是“西半球形态”的典范。今日地球的南北对立等同贫富两级化是历史与地理的合谋。
全球化的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历来写“波希战争”都站在希腊的立场,波斯变成希腊史的半影部。本书改从波斯帝国的角度透视“波希战争”,也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提供了一个亚洲的纵深度。当时中国还未递秦汉大一统,亚历山大先到达内亚,张骞于两个世纪后方抵此地,把这条欧亚横贯公路接通。到了这个转折点,世界史的全球化视野就开敞得多。
这个尖峰时刻酝酿已久。在公元前6世纪,所谓“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已进入高速挡,欧亚大陆的几个中心分别原创了后来普世化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还看不出跨地区影响的痕迹,因为它们的基础性设定大异其趣。“枢轴时代”为人类设计了新型号的文明,老一代的文明没有跟上的就被淘汰了。亚历山大开展的希腊化时代将“枢轴时代”的某些因素提炼成普世救主型的宗教。排在第2卷中的《弥勒与弥赛亚》一章分两截来说明此现象:在“希亚文明”项下,它叙述从中国边境迁徙至内亚的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它跨内亚与北印度,融合了原始佛教、伊朗祆教、希腊化时代的救主政权以及人体塑像,发展出贵霜型大乘佛教(即进入中国的北传佛教);在“希罗文明”项下,则探讨以色列子民对民族救星的期待在罗马帝国的容器内被柏拉图化,同时向个人追求永生的希腊化秘仪模式靠拢,最后被纳入罗马国教的官僚体制,形成一个簇新的基督教会。与这个精神发酵配合的则是由秦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组成的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链带,以及将它们串起来的丝绸之路。
古代帝国链带受到草原带的冲击而瓦解,乃世界古代史终结的一把统一量尺。这里暗含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historical topology)。它在匈奴、突厥、蒙古这三个草原霸权(也是三时段)的东西流向中勘测其历史走势:一般来说震央在蒙古草原,该地的草原帝国多诞生于对中华帝国的挑战,这类草原霸权较次要的右翼恒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地区”为中心,它是在蒙古草原的政权失败后退据之处,算是备胎;从七河地区,由东方败退的草原势力可建立次级帝国,亦可进一步越过楚河,图谋“河中地区”,南窥呼罗珊;如遇到伊朗文明带的阻力和来自后方其他游牧族群的压力,会直下印度,或北走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岭隘口,进入欧洲,至匈牙利而抵欧亚大草原的极西端,再往前走就是森林或农田了,故亚洲游牧民在入欧后多以匈牙利为大本营(前后三次是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后者即今日匈牙利人)。蒙古旋风将有专章处理:蒙古人并非在中国边界上碰了壁才西窜的,而是主动西征,但其波涛汹涌的河床是同一道。
“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之雄图还不只限于阐述欧亚大草原与南方文明带的互动,而是在世界史的写作中首次探讨北方寒带林木地带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纵观上下数千年,草原早期的霸主是印度欧罗巴族群,彼等乃最早驭马驾车、胡服骑射者。阿尔泰族群原本可能是“林中百姓”,他们走出草原,从印欧人处学得马政,并挟蒙古草原为草原之冠之优势,逐渐将印欧人逐出草原,使欧亚大草原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同义词。被匈奴驱至欧洲深处的阿兰人与哥特人可能不是最后的一批,在欧亚大草原中段的残余有可能苟延至6世纪。
这个草原带的换防滥觞于匈奴时代末,匈奴从汉帝国边疆遁走后,音讯渺无,后来猛然如天兵天将般空降在欧洲的地平线。这是由于世界史冷落了萨珊帝国与笈多帝国等欧亚大陆中间地段,付出的代价是使匈奴史成了谜。匈奴在2世纪下半期至3世纪的行踪仍不明,盖2世纪时贵霜帝国仍健在,堵住了草原民族南下之路。至3世纪上叶,在波斯,更强大的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并归并贵霜的西部与北部,匈奴南下更为其所阻。至5世纪末,萨珊与贵霜的后继者笈多帝国双双颓败,“白匈奴”之炽焰遂现于世界史的屏幕,此集团可能包含印欧族的残余,其攻势导致笈多帝国的覆亡,萨珊人唯有与崛起中的突厥人连手始将其解决掉。本书因此纠正了一个视差:匈奴在中国边界上碰壁后,不是一味地往西进入欧洲,他们的活动震撼了整个欧亚文明带北疆全线,“匈奴时代”的落幕不在欧洲,反而是在欧亚大陆的中段。匈奴时代落幕之处,正是突厥人时代序幕之地。
罗马帝国其实离欧亚大草原最远,但除了汉帝国之外,却垮得最早也最彻底。这是因为来自草原的巨浪与罗马的长期边患汇流。罗马在被匈奴海啸冲刷的前后,需对付的边患都是从事农耕的哥特人,匈奴在欧亚大草原西端末梢——牧草面积只及蒙古草原百分之四的匈牙利——建立牙帐,曾一度将这个传统边患组织起来,成为阿尔卑斯山北的大国,它之迅速瓦解,却造成罗马之末运。在罗马末世,是用御用的哥特人抵御北疆的哥特人,残局也是由这些忠心的哥特人支撑的,他们最后变成罗马的“中央”,罗马从历史中淡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扮演“罗马人”,并非传统教科书所谓“日尔曼人南下灭亡罗马”,如果还将日耳曼人误认为草原民族,则荒天下之大谬。
至草原史中后期,在西部始有芬匈语系(乌拉尔语系)从寒带林中闯入阿尔泰语系的天下,但未能摇撼后者的霸权,且为时较晚。过了数百年,文明地带亦开始夹“火药帝国”之威对草原甚至林木地带进军,草原带与定居带间之形势对比丕变,意味着前者最终步下世界史舞台。这些议题将穿插在第2、3卷里。
《新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概如上述。第2卷写作最艰辛的部分是“中古的印度”,比处理陌生的史料更艰辛的是构思:一方面需凸显印度史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用它来纠正传统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框架之滥用所造成的误差,另一方面仍须将它纳入“世界中古史”。古印度河流域文明没有出土铜范,它的青铜器是靠发达的国际贸易进口的,它也具同代文明间最先进的都市规划,却因没发现可破解的文字而被归入“史前”,待早期印度史迈出这个既是“史前”又是进口的“青铜时代”、进入雅利安的“铁器时代”后,因都市的没落,历史分期法反而倒退回新石器时代的以陶器类型为准则。
此后,印度史固然参与了普世性的“枢轴时代”,但印度至公元前3世纪始出现书写,故印度这个“枢轴时代”有一大半是在“史前”进行的。出现于“枢轴时代”的佛教与耆那教等因被套用了西洋史模板,常被曲解成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对婆罗门“国教”的改革。其实它们是替后起的“印度教”铺路。佛教反而首先成为印度第一帝国孔雀王朝的“国教”。古婆罗门教杀生献祭、可吃肉,在佛教与耆拿教的“戒杀生”的攻势面前,转而力主素食,却将荤食者“贱民化”,将原本倡非暴力以扬众生平等的教义用来强化种姓制度,故印度教是一件将佛教与耆那教反过来穿的衣服,而后两者在某意义上乃印度社会种姓化的共犯。耐人寻味者,从笈多帝国(320—550)开始,女神崇拜、性力崇拜、将秽物神圣化的密教渐成为印度的新浪潮,一度经不食人间烟火化的改造,对“尘世”污染极端畏惧的印度教这件衣服又朝身体化方向再度被反过来穿。相对世界各大宗教的轮廓鲜明,印度教倒类似一个各类怪鱼的养殖场,唯一演变为普世性宗教的佛教是“去印度化”的。
印度史的内在逻辑好比一个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停止适用的重力奇异点(singularity),但任何跳脱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模板之重力场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是重力奇异点。果真这样,那么我们的“新世界史”不如索性往东一、西一块互不关联的“旧世界史”书写逆退。摆在“新世界史”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尊重印度史内在逻辑的条件下将这段印度史“中古化”?本书的策略仍然是新世界史思维:伊斯兰乃公元后才出现的现象,公元一千年前后,突厥人终于突破阿拉伯征服被长期局限于西北隅的僵局,长驱直入北印度,将公元第一个千年印佛两大系对立局面转换成最近一千年印伊两大系的对立局面。也在公元一千年前后,密教化的佛教在印度本土灯灭前的最后据点孟加拉传入西藏,成为后者的文化认同;在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开始成为除越南之外的东南亚文化认同。“中古”时段也目睹印度变成一个逐渐组成的印度洋经济的一部分。
传统的世界近代史的重头戏是西方的崛起,《新世界史》将探讨在西方缔造的世界经济之形成期,中国这个先进的超巨型市场有否扮演了压舱物之角色?它能否证实“唐宋变革论”之宋代中国乃世界近代化早春的命题?还是该印象乃20至21世纪之交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地位的回溯性投射?如果这个修正主义能成立,它将大幅度改写传统西洋近代史的海洋中心论,将其往海洋与大陆互动的方向调整,不再单方面强调西方的尖兵角色,而忽视了中国和印度的诱发、后勤和压舱作用。这个改写是否成功,得视《新世界史》末卷付出的心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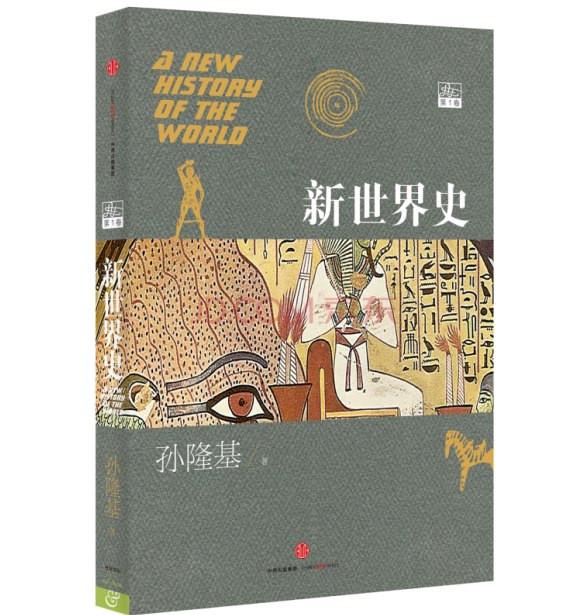
(本文为孙隆基新书《新世界史》总序,原题为“《新世界史》之‘新’”,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澎湃新闻获出版方授权转发此序言。)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