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用阳明学拯救儒学
日人冈田武彦在他的《王阳明大传》中指出,阳明学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冈田说,阳明“‘求道’的方式是整体性的”,与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时的“整体性地去理解”,即“将事物和自己的内心合为一体之后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通过思辨的态度去理解”的方式是一致的。冈田认为,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而由于幕府末期,那些具有经国之略的政治人物本身就是阳明学者,以至于“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不经世致用,不具体实践,那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显然,在冈田心目中,日本人对阳明学的理解,与日本民族的精神气质相关,也与日本民众对幕府时期阳明学者的政治实践的认知相关。
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国,阳明学所产生的作用远不如日本,并且随着明亡清兴而偃旗息鼓。而它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关于王学末流“束书不读,游谈无根”的批评和讥讽。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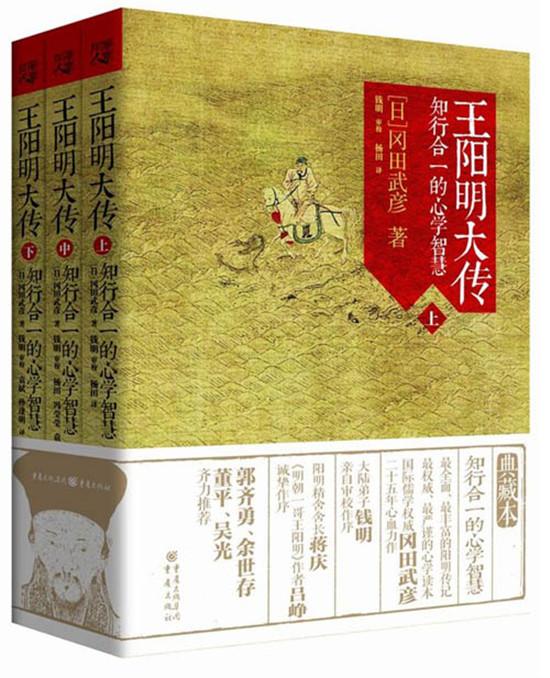
中国思想的源头,在夏、商、周之世。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过是其丰富蕴藉偶尔逸出的一些光华。随着东周策士的兴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遂成为当时的思想主流,而且越来越流于权谋。秦朝大一统之后,统治集团总结诸子百家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八个字:“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只允许人民“以吏为师”。所以,虽说那时也还有读书人,朝廷中也还设有博士官。但是,这些人,即便是在政治上,也没有思想,甚至害怕思想。以吏为师和读书人没有思想、害怕思想,是汉初无为政治的两大背景,也顺理成章地造成了日后两大政治上的恶果:一是政治上没有远虑,任由豪强违法乱纪侵凌小民,而疏于对他们的法律监督,所谓“网漏吞舟之鱼”;二是注重“君尊臣卑”的宫廷礼仪的制定,而忽视在制度上求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所谓于“几席之上、户庭之间”求治。而到了汉武帝时,为纠正长期放任(不作为)的积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集权措施;并且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旗帜,定儒学于一尊。从此,儒学虽然表面上居于统治地位,却不再真正具有思想的意义,完全变得教条化了。
汉宣帝在总结汉朝政治时说,汉朝制度的本质,就是“王霸道杂之”。揆诸西汉政治的实际,所谓“王霸道杂之”,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儒表法里”。《史记》上说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可以视之为对这种“儒表法里”的具体描述。那时,即便是酷吏断案,也都要牵强附会地从儒家经典里找出些根据。另一方面,因为朝廷的提倡,儒学作为读书人的“禄利之路”,往往“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这样的为学风气,配合着政治上所谓的儒表法里,亦足以想见当时学者在思想上所受的限制。他们在思想上,不仅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而且还要主动地将自己束缚起来。好比是旧时女子裹小脚,开始是别人强加的,之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自己给自己裹了。
儒学最根本的特点是讲道德。但是,在一个儒表法里、把儒学作为“禄利之路”的环境中,人们对实际的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缺乏诚意的,说一套做一套成为实际的政治选择。所以,在西汉政治上,就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普遍的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如汲黯当面揭露公孙弘这个人很虚伪,面对事实公孙弘不得不承认了,而汉武帝却觉得这是公孙弘的宽厚,反而是汲黯不近人情。显然,在当时的政治上,实际的道德问题是受到轻视的。辗转至东汉,由于地方宗族势力的发展,儒学所提倡的道德,在社会上普遍受到了重视。东汉在政治上是外戚、宦官交替专政,“朝政日非,而风俗颇美,天下的士流大都崇尚气节”(吕思勉)。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强烈反差,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而使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对儒家政治理想失去信心,从而对儒学经典和礼教产生怀疑,转而去谈一些玄远的东西,思想由此获得了一些自由的空间。
隋、唐以科举取士,儒学作为“禄利之路”,对天下读书人表面上甚至显得比以往更具有吸引力了。但随着地方宗族势力的衰落,儒家道德在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力,却远较东汉魏晋时期大大减弱了。只需比较一下北朝时期的坞壁与五代时期藩镇的不同性质和作用,自不难理解其中的原因。南北朝时期,遍布于中国北方的坞壁,集政治、经济和军事功能于一体,在外族政权的统治下仍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坞壁以地方宗族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为基础,社会组织的凝聚程度很高。而五代时期,中国北方在藩镇割据之下,“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皇帝、镇帅不过由一帮骄兵悍将予废予立。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能够将藩镇的军权、财权、政权一举收归朝廷,关键就在于藩镇纯粹是军事性质的,缺乏地方基础和文化上的凝聚力,一旦失去军事上的优势便无可作为。坞壁和藩镇,作为各自时代的主角,基础、性质完全不同,作用也完全不一样,一方面反映了由东汉到隋唐之间社会组织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在社会上的势力消长。

秦汉以下,儒学所崇尚的道德,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是不起作用的。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基本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当宗族势力在社会上普遍衰落之后,儒学的道德原则就只能落实于个人的道德自觉上了。隋唐五代之后,宋代理学家把文章都做在个人的道德修为上,强调个人通过自我修为达到“内圣”,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对于个人的道德修为,宋代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宋代理学家对儒家道德原则的总概括。在他们看来,存天理的工夫,就是“格物致知”,即探寻事物的原理而获得关于天理的知识。他们认为,只要用足了格物致知的工夫,越来越多地懂得天理,并由衷地信奉它(诚意),去除心中私欲(正心),进而就能修、齐、治、平了。在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上,理学家格物致知的方法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样一套方法,也导致了“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的问题。
我们知道,自汉代以来,儒者都喜欢从天道上发为高论。宋儒凡事要在天理上立论,显然是受了此等风气的影响。惟所言天理愈高,则视人心愈卑,从而否认了人的道德自觉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出于对“格物致知”能获致天理的深信不疑,宋代理学家追求博学的学问风气,无非就是“在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其结果,则是把知识与道德混为一谈。而自从实行科举选官以来,读书人大都在仕途上或向着仕途奔竞。那种“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凡饾饤琐屑无不牵强附会于“义理”的“我注六经”的方式,其中本就隐藏着很强的功利心。“所谓道徳,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结果,说是“存天理,去人欲”,实际上是“空谈心性”、“空空穷理”。这样做学问,不仅学问的局面越做越小,学者的人格也变得越来越卑微,与理学家道德修为的初衷,只能是谬以千里。
宋人自己就已看到了这样的问题。陆九渊曾以“心即理”说与朱熹就怎样认识天理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陆九渊根据儒家人性善的理论,认为人只要能“复其本心”,天理就自然呈现了。就与人伦相关的知识而言,陆九渊的这个“心即理”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他的缺点在于不否认外在天理的存在,只是反对一味向外去寻求天理。惟此,他还难以否认“格物穷理”的必要性。有人问陆九渊为什么不写书,他只是反问: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意思是说,是让儒学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呢,还是让它来束缚自己的思想?问题的立意虽高,却也无法回避儒学经典中蕴含着的许多道理确乎符合人的本能(本然之性)。而且,按照常识,只有圣人是“生而知之”的,常人只能是“学而知之”。自以为“生而知之”者,在儒者眼里都是妄人。儒家学者对此从来都是十分警惕和排斥的。

然而,到了明朝正德、嘉靖之际,又有王阳明站出来,举起了“心即理”的旗帜。阳明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蔽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这样的一番批评,针对的还只是儒学中人走错了求圣之路的问题。而阳明内心更为痛恨的,则是普遍地借着这门关于“天理”的学问,“射时罔利”,“驾浮词以诬世惑众”的“假道学”。与陆九渊所不同的是,阳明的“心即理”主张,远较陆九渊来得彻底。他不仅主张“心即理”,而且还主张“心外无理”、“心在物则为理”和“心外无物”。
阳明所谓“心外无理”,说的是只有人心才具有正确认识善恶对错的能力。即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这是要赋予人的道德追求以彻底的自由,以确立人在道德自觉上的主体性。阳明说,历史上“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无非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五经亦史”,无非是圣人在不同时代环境中的道德自觉的历史记录。而所谓“心在物则为理”,说的是具体的理总是体现在人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比如“忠”、“孝”,是体现在心之事父、心之事君的关系之中的;离开了事君、事父这层关系,又何来“忠”、“孝”的天理?同样,如果君不君、父不父,“仁”、“慈”的天理又何在呢?总之,人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就应遵循怎样的道德原则。
强调现实的关系,而不是抽象的理,是阳明的一大特色。由此,阳明又说了个“心外无物”。从政治、社会与人伦的角度出发,阳明认为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关系之物(物即事);如果各自不按照身份行事,这些关系就不存在了,各自的身份也不存在了。比如君不君、臣不臣,君臣关系就不存在了,那么君在哪里呢?臣又在哪里呢?对于“心外无物”,阳明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阳明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鬼神尚在何处?”意思是说,是人感受到了天地万物的存在;也只有当人与天地万物相遇时才能道出它们的存在;人不可能道出比已知更多的存在。总之,阳明所谓的物,都与人的实践联系在一起。
“心外无理”、“此心在物则为理”和“心外无物”,构成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基本内容,既表达了他不甘就范于宋儒所说的外在“天理”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也强调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于人认识心中所具之理的重要性,从而避免了那种把认识的可能性当作现实性的妄自尊大。由此可知,阳明所谓的“人者,天地万物之心。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的话头,实在是要求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来考察与人生、社会和政治的关系。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用主观并吞客观、用精神并吞物质的问题。
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强调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的现实性,是王阳明“心即理”说的根本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这是孟子的话。阳明接过孟子的话,说:“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这里,“吾心良知”是主体,而“事事物物”是与人发生关系的关系之物,并非纯粹的客体。“致良知”就是将人之良知贯彻于这些关系之中。固所谓“致良知”,就是要求人们积极地进入这样一个关系世界中,并将人的良知赋予这样一个关系世界。
“致良知”的思想如此,而其精髓就是“知行合一”。“吾儒养心,未常离却事物”;“须在事上磨练”;“学问思辨亦便是行”。阳明的这些话头,讲的都是“知行合一”。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知行并进”,而不是在学问思辨之外另有一个行。离开了学问思辨的行,只能是“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的“冥行妄作”。同样,离开了行的学问思辨,也只能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的“揣摸影响”。总之,人要实现其主体性, 就必须将“知”与“行”“合一”。换句话说, 真正的“知”与“行”,是在它们的“合一”中实现的。否则, 所谓“知”,只不过是“用智自私”;而所谓“行” , 也只是“造作安排”。
在“心即理”、“致良知”的基础上,阳明又提出了他自己的“万物一体”说。宋儒也讲万物一体。但宋儒的万物一体,与他们通常所谓的天人合一,都是一个意思,即“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各具天理;又在天理上统一起来。而阳明的万物一体,是万物统一于人。在阳明看来,人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而处于众多关系之中: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在这一问题上,阳明只是提到了某些表象),与社会相关联的人生,与政治相关联的人生等等。而人赋予这种关系以良知,成为这种关系的中心,所谓“天地万物,俱在我发用流行中”。所以,阳明的万物一体,是一个心的世界,而不是外在天理的世界。更具颠覆性的是,阳明讲的这个心,是“自圣人以至于愚人”的人人之心。阳明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 只自信不及, 都自埋倒了”,“圣人只是学知, 众人亦只是生知。”他的意思是说,圣人与人人,重要的是同而不是异;知识、才能不是圣贤与否的标准;不自信可以为圣,一切都无从着手。阳明因而强调《大学》所谓的“明明德”而“亲民”,是儒学立足的根本。“明明德”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则全在于“亲民”。阳明认为“亲民”的最根本道理,就是“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他这是在说,儒学的道德,绝对不应违背人之常情。所以,“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那么,圣贤与愚夫愚妇的区别又在哪里呢?阳明说:“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良知)耳!”
阳明弟子王栋曾如此评说他的“亲民”说:“自古农工商贾,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灭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冺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宗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矣。”这正是阳明的意思!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在;所以,圣人之学必定可以与人人之心沟通;圣人之学,亦即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圣人也就是人人。
儒学就孔、孟的原意来说,是用来规范统治者的。历来的统治者,却都致力于用它来要求治下的百姓。宋代的理学家,则把儒学转移为个人道德修为的学问。阳明把儒学由圣人之学,一变而为人人之学。表面上,他只是不承认有所谓外在天理。实际上,他是用心来否认天理,用人人之学来否认圣人之学。而他所强调的行(致良知),则把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的主体性,也包括进了人在道德自觉上的主体性之中。这无疑是对儒学进行的一场革命。这样的主体性,与专制的政治和思想体制是不能相容的。阳明晚年曾对他的学生说,自己在五十一二岁之前,总还有些“乡愿的意思”,做事总要顾虑会不会得罪人;后来则一切“只依良知”行事,却导致了“谤议日炽”。他不无愤激地说:“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不与俗谐”,已开罪于人了。

事功掩护了阳明的离经叛道。阳明一生,曾三次为明朝出征,立下了重要的军功。第一次(1516-1518年)是以赣南为中心,跨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在广阔险峻的山陵地带剿灭长期为害的匪患。第二次(1519年)是在江西迅速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为正德一朝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内部统治危机。第三次(1127年)是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八寨的匪患(《王阳明大传》对这三次战事叙述得非常详细)。在这三次战事中,阳明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把握能力,无疑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给人留下更为深刻印象的,是阳明在处理地方民政问题上的仁民爱物之心和讲求实际的风格。这些都足以证明阳明的忠诚。
阳明的故乡浙江余姚,地处江南。当时江南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极为活跃,而朝廷的“三尺之法”在这里“不行久矣”。黄宗羲讲,阳明去世之后,他的学问却因王畿、王艮而“风行天下”。这个“风行天下”,主要就是在江南。阳明在江南讲学,来听讲的也大多是江南士人。阳明的人人之学,在此地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了不起的事功和思想的开创汇集在一起,也使阳明在江南地方具有很大的社会号召力。而王畿、王艮等人深得师门“知行合一”之旨,把“满街都是圣人”,“良知在人, 百姓日用, 同于圣人之成能”,“百姓日用条理处, 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这样的人人之学,讲得生动活泼。这样的道德自信一旦流行起来,读书人中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的风气就淡薄了。于是,就有人跑出来指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然而,自宋至元,一直到阳明以前,用所谓“束书不读”、“束书不观”之类的语言批评读书人不读书的,本来就司空见惯,现在却独独成为“王学末流”的“罪名”。这样的攻击,其实反映了攻击者对阳明所说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不满和不懂,以及“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的积习难改。而更为深刻的是,在当时,一门学问如果不能成为“禄利之路”,慢慢地就无人理会了。本文在一开始,曾提到冈田武彦所谓“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一语,冈田似乎也有些鄙薄所谓“王学末流”,也许还认为阳明学不适合中国。他显然忽视了阳明之后,许多信从阳明的学者,大批返回到理学老路上去的政治原因。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